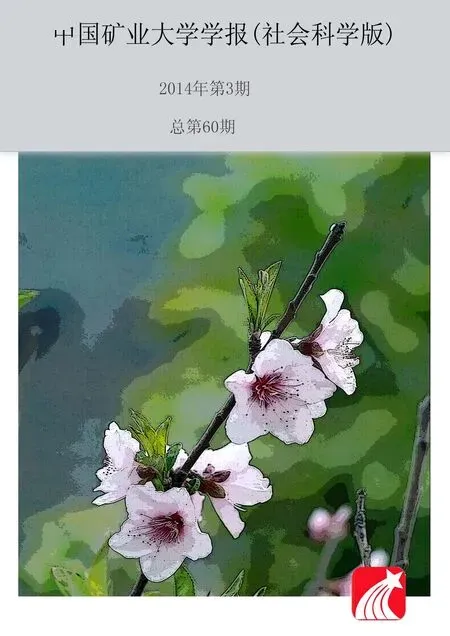“三结合”的学术视阈和学术方法
——张岂之先生史学志业述略
藏 明
(邢台学院 法政学院,河北 邢台 054001)
张岂之先生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如皋人,抗战期间,南通濒临沦陷,先生被家人辗转送至陕西城固,并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而后,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6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0年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生聆听了侯外庐、胡适、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贺麟、石峻、容肇祖等著名学者的课程。岂之先生曾感慨道:“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1]439诸先生的学识与师德对张岂之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2年张岂之先生任教于西北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涯。在这期间,他先后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四卷),并参与主编了《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思想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华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等等*有的学者对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的篇目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详见:张祖群所写的《试论张岂之先生的学术谱系》一文,载《中国轻工教育》,2012年第6期。。
在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张岂之先生以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中心,并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中国史学、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学术界对于张岂之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就著作而言,如:方光华、陈战峰主编的《人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一书,西安出版社,2008年1月版;就学术论文而言,如:范立舟所写的《张岂之先生与宋明理学史研究》一文,载《学术界》,2009年第2期。又如:陈荣庆所写的《张岂之先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宜春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又如:张越所写的《张岂之教授访问记——关于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8期。。譬如:将思想史的研究与学术史、文化史、哲学史相结合;将历史研究与文明史研究相结合;将传统文化研究与文化自觉相结合。这“三结合”的学术视域和学术方法,不仅拓展了侯外庐学派的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而且形成了侯外庐学派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鲜明特色。与此同时,侯外庐学派团队协作、教学相长之学术传统同样得以薪火相传。
一、张岂之先生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先生初涉中国思想史研究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50至70年代,张岂之先生先后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参与了第四卷即唐宋思想史的编纂工作。此外,张先生还主编了《中国思想史纲》一书。在研究期间,张岂之先生不仅逐渐成为了侯外庐学派的中坚力量,还对侯外庐学派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张岂之先生曾这样总结道:
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主要是:逻辑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因为,社会思潮往往集中反映出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的相互关系。所以,社会思想是研究的核心,是三者之中的重中之重,通过对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图将社会史中的思想史揭示出来,而社会思潮则是指一个历史时期思想领域内的主要倾向,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为诸子之学;在汉代,主要表现为经学;在魏晋时期则为玄学;隋唐时期主要是佛教的传入和佛教的中国化;宋以后是理学;清代是考据学,近代则是西学[1]404-413。
可见,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手段还是研究重点,张岂之先生对于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当然,张岂之先生并不只是继承了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张岂之先生对于思想史科学发展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其所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一书,该书共历三版,第一版于1989年出版,共计70余万字;第二版于1993年出版,共计40余万字;第三版于2012年出版,共计90余万字,三个不同版本不仅仅是字数与内容的删减和增加,字里行间还体现了张岂之先生对于思想史相关理论的思考与探究。,同时,对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诸多的理论创新。
首先,重新界定中国思想史学科,张岂之先生道:
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专门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的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2]3。
其次,重新厘定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张岂之先生道: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例如分别研究哲学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按此要求,在中国思想史的综合研究中,更多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2]3。
最后,整体性地开拓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张岂之先生总结道:
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拓展需从七个方面着手:1.学术上的“和而不同”是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准则;2.继承发扬人文学术中西融会的开拓精神;3.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文、史、哲和艺术、语言学等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要求越来越突出;4.关注新史料研究;5.加强中国思想史中宗教思想的研究;6.加强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7.现实世界与中国思想史研究[3]。
可见,张岂之先生对于中国思想学科的定义、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等都进行了理论化的归纳与总结。除了理论创新之外,张岂之先生在具体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将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或者说从学术史的视角研究中国思想史;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4]73,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融合。
(一)思想史与社会史
由于学术界对于思想史的定义以及研究对象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派别,如:以侯外庐为代表的“社会派”,即以社会思想作为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以胡适、冯友兰为代表的“哲学派”,即认为哲学史等同于思想史;以葛兆光为代表的“一般态思想史”流派,即以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作为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匡亚明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即认为中国思想史是研究观念及其存在结构演变过程的学科[5]。在众多的思想史研究派别中,尤以侯派与葛派的学术成果最为丰厚,但分歧也较大。葛兆光先生对侯外庐学派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侯外庐学派的思想史内容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分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难道只能书写精英与经典的思想吗?[6]7-12
可见,葛兆光先生并不认同侯外庐学派将精英与经典作为思想史最主要研究对象的做法,他认为:
并不是说我们不准备写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我只是说要注意思想家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背景有些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6]13。
可见,葛兆光先生想通过对“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研究来揭示人类思想的演进历程。那么,“精英思想”、“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二者谁才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呢?除了国内的学者之外,西方的汉学家也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其中,史华慈的观点极具代表性,他认为:
尽管中国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可能都有共同的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但后来与民间文化发生了决定性的分离。此外,我还主张,在随后的历史中,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并非同一种文化的两种版本,它们也不必然地呈现出平行并列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既相互影响但又相对分离的领域之间动态张力的互动关系[7]546-547。
可见,尽管史华慈认为,中国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是同根同源且相互影响的,但他还认为,二者分属于中国文化的两个不同版本,没有交集。与之相比,张岂之先生的观点更加符合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发展原貌,即认为,以精英为代表的社会思想仍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普通的民间思想与信仰同样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对二者以及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来展示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全貌。张岂之先生不仅认为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均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还将二者共同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详见:张岂之先生所写的《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一文,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张岂之先生所写的《5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文,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文,载《群言》2002年第7期;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一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1-5页。,而此种理论的提出,是张岂之先生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首先,张岂之先生将科技史纳入到社会史的研究视域,张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一文指出:
古代的理论思维虽然是朴素的,但它不是天生的先验观念,也不是普通的日常意识,而是一种巧妙地运用概念的艺术,或称之为综合各种成果的科学抽象。要掌握和精通这种艺术,认识这种“科学抽象”,并通过它们去认识人类思维的发展史,就应当把思想史研究和科技史研究辩证地统一起来[8]。
可见,张岂之先生认为,除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之外,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彰显古代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以,可以将科技史的研究纳入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张岂之先生还将思想史与科技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研究工作当中。
在1990年出版的由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一书中,先生将儒学的发展与科技的演变共同纳入到思想史的研究视域,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揭示儒学思想的变化,通过对儒学理性与独断性的论述,来揭示儒学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在第六章“汉代儒学概述”中,张岂之先生认为儒学的理性主义促进了汉朝科技的发展:1.儒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促进了医学的发展,譬如出现了著名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2.促进了宇宙理论的发展,譬如出现了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等;3.促进了炼丹业的发展[9]214。
与此同时,儒学的独断主义却阻碍了汉代科技的发展: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阻碍了数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逻辑理论的缺乏;2.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结合形成的荒诞神学,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3.谶纬迷信之学阻碍了农学、地理学的发展[9]216。张岂之先生通过对汉代科技史的研究,进而概括出了汉代儒学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两重性:理性主义与独断主义。
其次,在将科技史纳入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之后,张岂之先生又不断扩大着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张先生在1999年所写的《5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文中指出:
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作为学人的参考。当前有的学人认为,关于社会史的研究最好不要局限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应当扩大为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宗教、民风、民俗、社会信仰等。有的学人正在试着去做。……不过,在扩大社会史研究范围的时候,对于社会史的核心——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是不能忽视的[10]。
可见,张岂之先生赞成其他学者扩大社会史研究范围的做法。但是,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仍然是社会史研究的核心。随后,张岂之先生在2002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由于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史识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的思想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突破,例如:关于社会生活的研究不能只限于经济和经济活动这一范畴,应当扩大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如衣、食、住、行、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方面[3]。
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突破,张岂之先生是非常认可的。他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民间思想也是应当着重研究的课题。”[3]可见,张岂之先生已经将一般的民间文化视为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具体的思想史研究当中。在张岂之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中,每一卷基本都有社会篇、宗教篇、科技篇。以“秦汉卷”为例:“从文章结构来看,其专列‘社会篇’,用约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社会基础,这在以往的思想学说史著述中,似乎并不多见。……除了对秦汉政治、经济、制度诸多方面的解析之外,对秦汉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也作了深度发掘。特别是对时人的信仰世界和风俗习惯做了积极地探讨——具体涉及的问题,如五德终始论的实践,时人对富贵、侯王、神仙、长寿的向往,卜祀迷信、婚丧礼俗、精神风貌等。通过这些,更加凸显秦汉思想学说的‘底色’与‘基石’。”[4]69
最后,在将民间思想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视域之后,张岂之先生又系统的论述了如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进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一定社会存在对于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中,并不是经济基础直接决定,而是辩证的,特别是上层建筑中更加具有理论思维的部分,并不是经济基础直接决定,而是经过多种中间环节、曲折地加以反映的结果[11]2。
张岂之先生认为,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要在分析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诸如精英思想、宗教思想、民间思想等多种中间环节进行阐释,进而勾勒出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概貌。张岂之先生又言: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难以归之于哪一个阶级的专利品。他们的思想经过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过滤,成为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思维,他们的思想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共有的精神财富[11]3。
张岂之先生认为,对于社会史的研究是为了探究思想史演变的规律,而不是为了给思想家进行阶级属性的划分。只要是系统的理论学说,都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总之,张岂之先生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不仅将民间的思想与信仰纳入到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使得思想史的研究有了更加丰厚的社会基础,还摒弃了社会史研究中的阶级决定论,使得诸家思想的原貌得以彰显,这对于侯外庐学派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说是一个继承,更是一种发展与创新。
(二)思想史与学术史
思想史与学术史均以理论化的社会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有何种关系?张岂之先生认为:
学术史不同于政治史、法律史等,也不同于思想史。在思想史中含有一定学术史的内容,同样,在学术史中也含有一定思想史的素材,但这二者也不能等同,因为思想史更加偏重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演变和发展的研究。顾名思义,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而“学术”的载体是学术著作。著作是学术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还有其他形式。因此,要求学术史研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地位与作用)和历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以及后来社会有什么影响)[12]1。
可见,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思想”,而学术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学术著作”以及学术思想的传承,二者似乎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是以学术著作作为载体的,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脱离学术史。学术著作之间也存在着思想的传承,学术史的研究同样不能脱离思想史。所以,张岂之先生进而指出:“在历史上有些著作是学术著作,同时又是思想理论著作,这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研究加以综合,并不是人为地将它们捏合在一起,而是要寻找二者的沟通处,使之融合为一个整体。”[10]
张岂之先生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理论初创阶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岂之先生和侯外庐、邱汉生等诸先生主编了《宋明理学史》一书,该书“是一部与中国思想史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学术著作,以理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只叙述个别理学代表人物的思想,而是对理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作全面的论述。”[1]84总的来说,《宋明理学史》是一本以探讨理学思想演变为主的学术史[4]12。
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张岂之先生已经开始将学术史与思想史相结合进行研究,张岂之先生认为,二程将佛教华严宗的“事理”说概括为“万理归于一理”,并在此基础之上,用“理”解《易》,认为观卦爻象即可见“理”,理为体,象为用。二程用华严解《易》的做法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反映出儒家经学与佛学的结合,试图以经学为主,佛学为辅,将经学改造为理学。佛教传入中国,魏晋时期玄学化的佛学,隋唐时中国化的佛学都有许多宗派,至两宋时期又有汇合经学和佛学的理学,二程是真正的开山祖[1]106-114。
以上综述表明:结合学术史与思想史观照宋明理学是可取的学术取向。
其次,理论发展阶段。张岂之先生将形而上的史学作为了融合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突破口。尽管张岂之先生认为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对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但是,《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凸显的仍是史学与学术史的结合。该书提出了“历史哲学”的概念,即从学术史发展的诸阶段中提炼出学者对历史发展的不同看法,展示学术与历史之间所体现出的契合性。如该书认为,在传统的学术思维下,历史学家往往关注“历史本质”、“历史人物命运以及历史命运”、“史学经世功能”等[12]13-25。但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的大背景下,学术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陈序经、胡适、傅斯年的“个人主义”派把史学的个性和科学性放在了第一位,把理想化了的西方文化当成历史学的价值追求[12]151-152。而以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体论”派则试图将传统史学的道德人文精神转化为具有近代特征的新人文精神,把传统史学的伦理主体改造为科学与道德相统一的史学主体[12]137。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一书中,张岂之先生将史学与学术史的结合彰显得淋漓尽致,这就为作为史学重要分支的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提供了实践经验与理论范式。
最后,理论成熟阶段。张岂之先生在经由思想家、史学家融合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之后,又提出了思想史与学术史相融合的四个要点:1.对于文献资料的研究;2.对于学派区别的研究;3.对于学术本真的研究;4.对于学派之间的会通研究[13]16-17。并在此基础上用“学说史”来融会思想史与学术史,使得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理论臻于成熟。
张岂之先生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五卷六册,二百六十万字)的总序中指出:“学说史是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术史;做到了从学术史深化思想史的研究”[14]2。在《中国思想学说史》的编写过程中,张岂之先生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落到了实处,该书“力图按照中国思想史自身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不是进行孤立的理论分析,随意地剪裁、解读思想史,将思想学说削足适履地纳入某些既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预设之中,而是结合学术史的研究视野,立足于思想背后深沉浑厚的学术土壤,使理论分析更为切合思想史自身发展的实际,深化思想史的研究。”[4]63如:1.就文献资料的研究而言,该书根据郭店楚简、上博竹简重新考证了《老子》、《论语》等重要文献的源流和版本,并对《黄老帛书》等新出土文献的成书年代、主要内容、主旨思想进行了论证[14]122-158。2.就学派的区别和联系而言,该书认为,孔子“仁”、“礼”思想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儒学的分化,形成了后来思孟与荀子哲学思想的对立[14]248。3.就学术本真的研究而言,该书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虽然有神学的成分,但是,董氏的学说意在解决西汉中期的诸多社会与政治问题,进而维护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15]132-134。可见,《中国思想学说史》对董仲舒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还原本真的客观评价。4.就学派之间的会通研究而言,该书认为,宋代哲学史的整体特征是理学家吸收佛老思想以重新确立儒学的主体地位[16]139。
张岂之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学说史》全书贯穿了一个理论观点——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融合,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4]86诚如其所言,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中,张岂之先生以思想学说为主线,将思想史与学术史串联到了一起,通过思想的演变来揭示学术史的发展,通过学术的探究来深化思想史对于思想家、学术思潮的研究,真正做到了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融会与贯通。
(三)思想史与文化史
思想是文化的最高表现形态,是文化的核心,而文化则彰显了思想的时代特征,是思想发展的外在推动力,张岂之先生言:
要研究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本质,必须对思想史有精深的了解。反之,思想史研究的继续深入,也必然会扩展到文化史的领域。因为思想作为社会和人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往往在各种文化形态中表现出来,并通过这些文化形态对社会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如果能够对渗透于各种文化要素之中的思想观念作综合的研究,就能从总体上把握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展现社会的时代精神。所以从思想史研究向文化史研究方面扩展,是学术研究向纵深前进的趋向[1]87-88。
可见,将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进行研究,既可以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文化上的材料,深化其研究;又可以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使文化史的研究更加的系统。那么,能否将思想史与文化史融会贯通呢?张岂之先生认为: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带有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古希腊文明,也不同于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等。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和文化史。而“文化”含有多种层面,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还有历史文物,艺术品等。不同的文化层面用观念文化中的价值观加以联结,形成绚丽多彩的文化总体。这种“价值观”,我们称之为“思想史”。因此,“思想史”和“文化史”可以沟通并联结成一个整体[17]2。
张岂之先生认为,思想史与文化史共同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人类文明史,将二者进行融合可以丰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而张岂之先生对于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张岂之先生将儒学定位为“人学”,并认为:
孔子以“人”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次系统地论述关于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完善、人的道德、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等关于“人”的学说[1]5。
自然创造了人类的一半,人类创造自身另一半的过程就是文化演进的历程[18]5。而在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良好的自我修养与人际关系则是人类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所以,张岂之先生在《论儒学“人学”思想体系》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个人的自我修养与人际关系。他认为: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又是自我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准。就人际关系而言:要遵循“仁者爱人”的准则,而这一准则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后是“忠恕之道”。就个人修养而言:“仁”又包含着不同的标准,其中“恭”是指自重、“宽”是指宽厚、“信”是指信用、“敏”是指勤劳、“惠”是指帮助他人[1]5-9。
如果说,张岂之先生对于儒学人学体系的研究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研究的个案的话,那么,张先生主编的一系列通史性的著作则体现了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理念。如《宋明理学史》一书,以理学史为基点,进而探索宋明时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点[1]84-85。《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从哲学与文化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继承了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视野,增加了文化史视野[19]。
《中国思想文化史》一书则从整体上呈现了张岂之先生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研究理论。先生指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一书,以思想史(即文化的核心)为主体,而旁及文化的其他方面”[17]2。的确如此,该书以文化的发展为核心,以儒学的演进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思想文化在先秦、两汉、魏晋、隋唐、两宋、明清以及近代的发展概貌,将思想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如该书的第四章《两汉时期的经学思想》专设一节“经学与汉代文学艺术”来论述经学对汉赋以及东汉乐府诗的影响[17]154-155。在《唐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价值》一章中,该书论述了儒学重民思想对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影响[17]238-242。而在《近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一章,该书论及了西方文化对儒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17]544-547。真正做到了思想中有文化,文化中有思想。
概而言之,张岂之先生用思想史来贯穿不同层面的文化,用文化史来揭示不同时代的思想特质,用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来展示历代思想文化的整体面貌以及思想文化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四)思想史与哲学史
思想史与哲学史究竟为何种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史等同于思想史,如钱穆等[20]1-10;有的学者则认为思想史包含哲学史,如侯外庐等[21]。而张岂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
如果说哲学史的对象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史,主要侧重于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的话,那么思想史则包括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各方面内容,包括一般规律的认识史,也包括对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认识史。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不是从个别方面,而是从社会思想的整体方面去揭示每个个别的思想体系,探究它们的整个发展过程[8]。
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较之哲学史来说是宽泛的,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要重视哲学史的研究,借以来加强对思想家、社会思潮的逻辑思想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张岂之先生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略》一书已经开始重视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结合的研究。虽然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该书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归纳为唯心与唯物两大阵营,通过唯物思想与唯心思想之间的斗争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不过,该书仍然对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学说进行了客观的阐释,如在论述王夫之对理学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对王夫之的“认识论”、“进化论”、“本体论”等核心思想进行了论述[22]173-183。
如果《中国哲学史略》是以哲学史为基础来融会思想史的话,那么,《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学说史》等著作则是以思想史为基础来对哲学史进行了融会。无论是1989年版的《中国思想史》,还是1993年、2012年版的《中国思想史》都贯穿了这样一个编纂原则,即以哲学思想为线索来贯穿思想家的主旨学说。如以老子“道”的哲学来贯穿其“人生哲学”和“政治思想”[11]79-90;通过韩非的“认识论”来贯穿其“历史进化观”和“法治思想”[2]82-88。而《中国思想学说史》一书则对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融会进行了发展,在侯外庐先生哲学内涵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19]。如该书对先秦儒家心性论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并认为儒家心性论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14]116-185。
不仅如此,张岂之先生还通过对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融会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先生先后发表了题为《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该论文发表在《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该论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文章来关注环境保护问题。他认为:环保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将20世纪西方的环境人文成果与道家的自然哲学等中国古代优秀的“天人之学”相结合,只有如此,才能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张岂之先生对于环境哲学的研究还在继续,200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其主编的《环境哲学前沿(第一辑)》,2004年,张岂之先生开始主编“环境哲学译丛”,并陆续出版了《环境经济学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环境正义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现代环境伦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盖娅:地球生命的新视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现代环境主义导论》(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等书籍。。
总之,张岂之先生对于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结合的研究,以思想史的演变为主线,以哲学史的融会为重要手段,进而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出来。而且,张先生还将研究视角着眼于社会的发展,真正将思想史与哲学史相结合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二、张岂之先生与中国史学研究
黑格尔将研究历史的方法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而哲学的历史是对历史思想的考察,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层次。黑格尔认为,所谓历史的思想即是历史的理性,而这种理性又是指完全自由的自己决定自己的“思想”[23]1-12。张岂之先生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理性[12]26,但张先生对理性的理解却与黑格尔不同,认为所谓的理性即为文明[24]1-3。
张岂之先生文明史观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理论萌发阶段。受教育部委托,张岂之先生历时五年主编了《中国历史》(六卷本)一书,该书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各个朝代的状况、制度、民族关系与政策、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社会状况、文化与学术等七个方面进行撰写[25]。张岂之先生认为:
我们祖先最主要的创造就是制度的创造及其逐步完善。治理一个国家要有政治制度,有人才选拔制度,有财政制度,有法律制度,有农业(含土地)和手工业管理制度,有城市管理制度,有交易和商业制度等等。还有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中国文明历史没有中断过,没有出现过空白,……吸取历史经验,我们觉得首先应重视制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26]。
所以,《中国历史》一书的最大编纂特色就是:“关于历史事件、人物与制度相结合的叙述。”[25]如该书论述了商鞅变法所构建的制度被秦始皇所继承,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27]180-181。该书在撰写西汉历史时,将主父偃、卫青等历史人物和汉武帝削藩、抗击匈奴等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并与汉武帝推行的算缗、告缗、盐铁专卖等制度相联系[28]84-106。以制度文明的演进为主线,展示了西汉历史发展的宏伟蓝图。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通史,自远古至今,包括那么漫长的年代,那么多朝代、事件、人物、制度和问题,把它们融会贯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张岂之先生用中国文明的进程把历史统一起来,认为一部中国历史是一部中国文明史。”[4]37-38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这种做法很有创建性。
其次,理论实践阶段。2002年张岂之先生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中国历史十五讲》一书,该书分为文明起源、朝代更替、古代的盛世、交通与文明的传播、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古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古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古代社会生活、古代思想的演变、古代文学艺术、古代史学、古代科技等十五个专题。那么,这十五个专题的中心是什么呢?张岂之先生认为:“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看历史的演进。一部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中国文明史,具体的说,这是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演进历史。中国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29]诚如其言,张岂之先生将文明史观的理论贯穿到十五个专题的写作中,如第五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作为主线来阐释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民族关系[24]97-126。第十讲“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以古代文明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发展为主线,来揭示中国古代思想的演变历程[24]253-283。真正将文明史观的理论运用到了实践。
最后,理论成熟阶段。2004年张岂之先生领衔编撰《史学概论》。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结合历史史实,对历史学学科的性质、主要范畴、基本理论、发展历程、研究方法与工具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史学概论》一书虽然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思想,但张岂之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人学”,此处的人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所以,在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也需要以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视角来描述史学的相关理论,通过人对于文明的创造来揭示历史的发展以及相关的史学理论[30]。所以,在《史学概论》的撰写过程中,张岂之先生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质,通过人来揭示文明发展与史学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文明——人——史学。如第三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论述了近代中国文明进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又论述了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最后论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以及当代的丰硕成果[31]85-127。在《史学概论》一书中,文明既与历史发展相契合,又与史学理论相得益彰,使得张岂之先生的文明史观理论最终成熟。
三、张岂之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学习、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何裨益?近代以来,诸先生们皆有评述,观点各异*张立文先生对“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代表人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详见:张岂之主编《民国学案(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16页。。张岂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结晶[32]3-4。发掘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文化上的自觉,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33]。而要达到传统文化上的文化自觉,张岂之先生认为需要经历三个阶段*详见: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2002第4期。。
首先,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张岂之先生非常热衷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尤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人文精神》最具代表性。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其中既有儒家、道教、法家和佛教等观念文化;又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选官制度等制度文化;还有对文物*张岂之先生认为,文物含器物,如陶器、瓷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铜镜、古钱;含艺术品,如书法、绘画;还含有古建筑、陵墓、古代服饰等。详见: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以及关于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科技等古代书籍的论述。
《中华人文精神》是对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灵魂——人文精神所做的阐释。该书将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归纳为民族精神与创造精神。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包括:1.“有对”之学,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有对”之学,即辩证思维。中国的“有对”之学,反对片面性,主张全面性,老子,朱熹等思想家都对“有对”之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34]21-44。2.天人之学,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与农耕结有不解之缘。在农耕实践中需要研究天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人事范围也要探讨“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荀子的“天人相分”理论、孟子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天人和谐”理论都是古代“天人之学”的重要代表[34]45-60。3.为人之学,人兽之辨,即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先哲们认为,人有社会生活,人有人伦,人有道德规范,并由此建立了道德伦理思想体系。孔子的“仁学”、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等都探讨了人怎样才能从善去恶,以及人应当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等[34]61-76。4.会通之学,中华人文精神是一种文化会通精神,对待文化学术,有远见的思想家,学问家们都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赞成多样性的统一,反对单调呆板的一致。玄学是儒、道的会通,理学则是儒、释、道三家的会通[34]77-94。5.经世致用之学,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明清时期的诸多思想家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致用思想[34]95-114。
其次,教育工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张岂之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需要两个途径。其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就是大学通识教材。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关于教育人文观的思索》、《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理论教育》、《对立耶?—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等文章对如何进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以及大学教师如何提高人文素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张岂之先生还向大学生介绍、推荐了25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34]16-19。以此来指导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学习。
其二,对社会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张岂之先生认为,大学生毕业以后,会将个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扩展到社会群体。此外,张先生还认为,需要创办一些刊物向全社会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自1992年起张岂之先生创办并主编了意在提高公民文化素质的普及性刊物《华夏文化》,该刊刊登了大量来自社会的稿件,如刘书通所写的《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该文对涂山的地理位置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详见:刘书通所写的《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一文,载《华夏文化》2009年第3期。。如庶人所写的《简体字、繁体字与“文化”》一文对使用繁体字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详见:庶人所写的《简体字、繁体字与“文化”》一文,载《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如万昌胜所写的《内涵丰富的苗族人名文化》,该文对苗族人名与苗族文化的缘起和发展进行了阐释*详见:万昌胜所写的《内涵丰富的苗族人名文化》一文,载《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如槐山所写的《给面包涂上蜂蜜——读〈生活有哲学〉》一文对傅佩荣所写的《生活有哲学》一书进行了介绍*详见:槐山所写的《给面包涂上蜂蜜——读〈生活有哲学〉》一文,载《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上述文章的作者或是退休乡村教师,或是普通的农民,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可见,《华夏文化》杂志的确起到了传统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作用。
最后,达到文化上的自觉。张岂之先生认为,文化自觉主要表现在人文学术研究、道德自觉、理性自觉等方面,张先生进而指出:
知识分子群体的创造性劳动、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为基本理念的大学教育、对人文科学的重视,是提高文化自觉最重要的条件;同时道德自觉、理性自觉与文化自觉的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也许就是文化自觉转化为社会发展的中介环节,而社会发展又向文化自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33]。
张岂之先生认为,只有将道德自觉、理性自觉与文化自觉相融会才能彰显文化自觉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而文化自觉又是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文化自觉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岂之先生陆续撰写《试论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内容与特点》、《关于中华文化走向的思考》等文章,并编撰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详见:张岂之先生主编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一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著述深入地思考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道德伦理的支持,而中国文化只有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诸多核心理念,才能达到自身的完善与突破,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文化上的保障[35]。张岂之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进行学术研究,执着地以“人文学人”自居,其在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学术成就蔚为大观。
参考文献:
[1] 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3] 张岂之.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J].群言,2002(7).
[4] 方光华,陈战峰.人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
[5] 蒋广学.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J].江海学刊,2003(2).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 本杰明·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 张岂之.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J].哲学研究,1983(10).
[9] 张岂之.中国儒学思想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 张岂之.50年中国思想史研究[J].中国史研究,1999(4).
[11]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上卷[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12] 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3] 张岂之.张岂之自选集[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
[14]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5]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 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 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8] 王德峰.哲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9] 方光华,袁志伟.《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2010(11).
[20] 钱穆.中国思想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21]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几封信[J].史学史研究,1994(4).
[22] 张岂之.中国哲学史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
[23] 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4]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5] 张岂之.中国历史(六卷本)介绍[J].中国大学教学,2000(2).
[26] 张岂之.关于《中国历史》教材的对话[J].中国大学教育,2002(4).
[27] 张岂之.中国历史:先秦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8]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9] 张岂之.文明与历史——《中国历史十五讲》序[J].华夏文化,2002(4).
[30] 张岂之.关于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的情况与思考[N].光明日报,2006(8).
[31] 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2]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3] 张岂之.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2002(4).
[34] 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5] 张岂之.关于中华文化走向的思考[J].中国文化研究,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