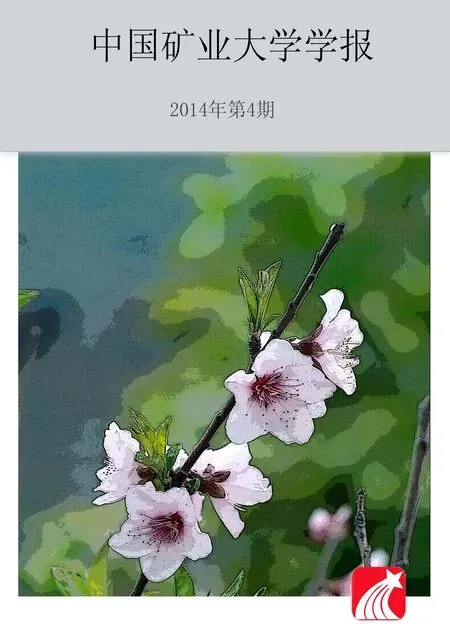孟晋超群:叶昌炽藏书研究成就与影响
周生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叶昌炽(1849—1917),字鞠裳,号颂鲁,又号缘裻,自题寂鉴遗民、缘裻庐主人等,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叶氏先祖本籍浙江绍兴,高祖时始迁苏州。他13岁时拜苏州名士刘永诗为师,由于天资聪慧,极早展露才名,与诸位地方名士接触,对其日后的读书治学影响深远。同治四年(1865),叶昌炽就读于苏州正谊书院,入著名学者冯桂芬帐下,在冯氏指导下,他“殚心古籍,不为俗学”[1]9,尤好阅读汉魏古文,诸篇习作古味十足,渐显风骨,年纪轻轻便显现出为文天赋,时与王颂蔚、袁宝璜合称“苏州三才子”。光绪十五年(1889),叶昌炽第四次参加会试始中,从此开始了仕途之路,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和甘肃学政等要职。辛亥革命后,叶氏深具前朝遗老心态,婉拒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清史稿》名誉总纂、《苏州县志》修撰等职,一心闭门治学,直至终老。
“买书难遇盲书贾,管教仍然老教官。芸香浓处多吾辈,广觅同心叙古观。”[2]1这是伦明赞美叶昌炽的一首诗,短短四句,概括叶氏辛勤忙碌于读书、治学的一生。他在藏书学、方志学、金石学、目录学、敦煌学和编辑出版学等领域,都作出了不菲的成就,在繁忙而紧张的一生中,撰著了大量的学术文集,在多个学科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天地。
一、“由旧趣新”的治学理路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3]第23卷,25,把清代学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作为第三阶段的晚清学术,最大的亮点是“新”,即随着晚清的社会巨变,学术研究与时俱进,呈现出“由旧趣新”的时代特色,“旧”的内核“伦理纲常”逐渐被“新”的主体“经世致用”所取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涌现出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人物,如魏源、严复、林则徐、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孙中山,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4]33。
叶昌炽适逢其时,读书治学不自觉地遵循“由旧趣新”学风转换理路,其治学思路的具体成因可归之如下两方面:
一是目睹国变灾难,萌生救国之策。叶昌炽一生适值晚清向民国巨变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个人身世浮沉,尤其是亲历甲午战败、庚子之乱等惨痛的民族灾难,促使他尝试探究国运衰变之因,积极探寻国家富强之路。这一思想俱载其《缘督庐日记》中。好友吴郁文说:“君观人论事,皆具卓识。记中,于戊戌,知新旧水火之争,将启阳九元黄之祸;于乙巳,断言督抚中项城不足恃,惟文忠公升允为社稷臣。其烛照若蓍龟。”[5]面对国运衰微,叶昌炽并没有漠然无视,而是静观其变,一一载入日记中,并尝试分析落败原因,寻求解决方案。如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叶氏逐日记载战争进展,其中,甲午七月初八日:
得佩鹤、粲林各函,知牙山全师尽没。吾军继进者万余人屯平壤,观望不前。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六舰巡海,踪迹杳然。合肥毫无布置。时局如此,可为痛哭![5]
此时距离开战不足半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清廷、清军的作为令人揪心,叶氏指责李鸿章“毫无布置”,可见其焦虑之情。战争进行两周后,甲午九月十一日叶氏说:
闻联英之议严严者,俱以为引狼入室,深闭固拒。见景生致胜之函,卫、叶各军皆倒戈相向。又闻为日人谋主者姚赋秋,吾苏人也。前日常熟密赴津沽议抚议侨保定侨秦侨晋。时局至此,真可痛哭![5]
两则日记中皆有“时局至此,可为(真可)痛哭”之语,及其沉痛。叶昌炽与大多数明智之士一样,对于国运之关切,了然于胸,他一直谋求破解“新”路,总结国运衰变之因,但囿于身份地位,难有大的作为。然而,但有机会,叶氏仍国运系于心间。甲午一战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叶昌炽所在会典馆修纂史书及舆图时仍将台湾列入版图,但礼部新修《学政全书》时,侍郎吴怀壬欲删去台湾,叶昌炽据理力争,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
二是深受冯桂芬影响,渐生“趣新”思想。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苏州府吴县人,晚年归隐木渎。冯桂芬自幼聪明颖异,20岁时补县学生员,后为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识拔,招入抚署学习,赏识有加,称冯为“国士”、“一时无两”。道光二十年(1840)中庚子科一甲二名进士,从此晋身仕途。咸丰六年(1856),任詹事府右春坊中允。咸丰九年(1859)辞官回乡。咸丰末年(1861),任李鸿章幕僚。期间,他完成了政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40篇,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6]的著名论点,努力寻求救国良策,成为洋务思想的先导。
同治九年(1870),22岁的叶昌炽应冯桂芬之聘,参与《苏州府志》的编纂工作,冯任总纂官。同治《苏州府志》在历代苏州府志中体现出鲜明特色,倾注了冯桂芬的变革思想。该志附录12幅地图,采用了西方十分先进的绘制方法,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各图均以正方格衬底,犹如今日之经纬线。在内容上,同治《苏州府志》紧跟时局变化,及时反映太平军在苏南一带的活动及清军的斗争,实事求是地记录了那段历史。而更为出色的是,该志十分客观详尽地记载了苏松太地区明清两代所承受的繁重赋税问题,并阐述了减赋的根据,“对研究苏州乃至周边地区的赋税史,研究苏州区域经济乃至全国的财政经济,都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的现实的意义。”[7]105
叶昌炽耳濡目染了冯桂芬修志中的“求新”思想,前后七年起居志局,尽心做好编纂工作,为蒐集史料,他经常踏勘各处村野山寺,藉此阅读了大量的碑志,获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编修过程中,他先后担任公署、学校、坛庙、寺观、释道等门的编撰任务,积极负责,潜心于此,是其未进入仕途时一项重要的著述和学术活动,为日后学术理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昌炽“治学无书不读,尤好碑版目录之学,兼通小学,善做词章。而数次为当地乡梓编撰方志,又广搜桑梓文献、历朝典故,学问为之大开”[8]。叶昌炽在近代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一)目录学
叶昌炽治学遵循旧路,多有创新,先从目录开始。他一生编撰了多部目录学著作,而最为著名的是《滂熹斋藏书记》和《邠州石室录》。
“滂熹斋”是叶昌炽座师潘祖荫的藏书楼。潘祖荫历仕咸丰、同治和光绪三朝,所到之处,精心收藏典籍,累数十年,藏书虽不及当时的“南瞿北杨”,但在苏州当地仍为佼佼者。因为叶昌炽在目录学和版本学方面深厚的功力,光绪十年(1884),致仕回乡的潘祖荫延聘其为自己的藏书编目,编成之后名曰《滂熹斋藏书记》,虽题名潘祖荫,实为叶昌炽所编。全书3卷,收书130部,其中,宋本50部,金刻本1部,元刊本29部,明刊本19部,顺治时刻本1部,旧刻本2部,日本与高丽刻本14部,影宋抄及旧钞本6部。作为解题善本书目,《滂熹斋藏书记》详记各书行款、题跋、印记和卷册数,并详细交代藏书家掌故。叶昌炽在编撰过程中,十分留意考订古书版本源流,较为详细地反映了滂熹斋藏书中最为精华的部分。该目分类科学,提要撰写翔实,辑录适宜,叙述明了,后人论此目说:“反映的是一代名流潘祖荫藏书中的部分精品,又由一代宗师叶昌炽提笔编撰,正是两美相合,使之成为珠联璧合的佳作。”[9]
金石文字历来为学者重视,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开始,直至近现代,历代学者皆以此考证史事,订正史误。叶昌炽《邠州石室录》为金石文字学佳作之一,该书为叶昌炽在甘肃学政任上,搜寻邠州庆寿寺一带的碑刻资料,并根据吴大澂初稿扩充而撰成的金石目录著作,民国四年(1915)吴兴刘承干嘉业堂承刊。全书3卷,共得唐碑刻22通、宋碑刻64通、金碑刻1通、元碑刻16通,共计103通。书中对每种题记皆有考证,并加按语,更有价值的是书中原刻文字皆叶昌炽手摹。此书所录虽为边鄙古刹刻石文字,内容多为唐宋间佛教造像和官宦游览题记,但通过其中所署纪年、姓名、职官以及铭题,可以改正不少史误,而文字变迁和避讳情况则可为历史考据提供例证。
(二)金石学
传统上,石刻研究一直是金石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叶昌炽才在理论上把它从金石学中划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0]。叶氏自幼痴迷碑版之学,“山岩屋壁,断楮残拓,珍如性命”[5]。同治十三年(1874),参与《苏州府志》纂修期间,叶昌炽便开始了金石拓片的收藏工作,此次所购汉碑数种,有《孔庙铭》、《孔君墓褐》、《礼器碑》、《孔彪碑阴》、《孔褒碑》、《百石卒史碑》、《熹平残碑》等。不久又购入《释天》手稿一卷。校《商子》、影钞《太元经》、《说文检字》、《崇政桥工记》等。此后多年,叶昌炽长期与王颂蔚、管礼耕、缪荃孙、吴大澂、陆蔚廷、沈增植、潘祖荫、王懿荣等研求碑版,互通有无,二十馀年的多方购求,得藏碑八千馀通藏在自己的“五百经幢馆”,规模仅次于缪荃孙的“云自在龛”。做甘肃学政时期,为邠州大佛寺唐、宋、金、元碑百馀通撰写题跋,详加考证,著成《邠州石室录》3卷,“书中原刻文字皆先生手摹,其精卓不可及”*陆翔云语。陆1945年购《邠州石室录》民国四年(1915)刊本上下两册,于上册封面题购书缘由,下册封面题评语。。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1896、1897),叶氏做汪鸣鸾幕僚期间,为汪编《关中金石记》、《闽中金石记》等金石学著述。
叶氏金石学研究最可道者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至次年十一月撰成之《语石》初稿,宣统元年(1909)在学生潘祖年的帮助下,他将初稿稍事增减,重新厘定为10卷,刊刻印行。共分274条目,485则。叶昌炽对于本书较为自负,曾云:“余自去年三月发愤作《语石》一书,论碑版之学,专开门径,及访求、收藏、鉴别之事,既非欧、赵之目,亦非潘、王之例,非叙跋,非考释,似于金石门中别开生面。”[11]卷九“辛丑十一月初五日”,57书中对于几乎所有带契刻文字的石制品都涉及到了,“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碑刻的发展、分类、内涵及研究对象,从而奠定了碑刻学的础石,成为中国碑刻学的一部开山之作。”[12]《语石》的撰著,开启了近现代石刻科学研究的先声。
(三)敦煌学
因缘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甘肃学政一职,叶昌炽成为晚近以来最早接触敦煌文物的清廷官员之一,也成为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一。
叶昌炽第一次接触敦煌资料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他视学来到敦煌县,县令汪宗瀚赠予书画多种,他记载这次所见:
宋画绢本《水月观音像》,下有《绘观音菩萨功德记》……其帧仅以薄纸拓,而千馀年不坏,谓非佛力所护持耶!又写经三十一叶,密行小字,每半叶八行,行三十三至三十五字不等。旁有紫色笔,如斜风细雨,字如小蝇,皆梵文。以上经像,栗庵(汪宗瀚字)皆得自千佛洞者也[11]卷十一“甲辰八月二十日”,378。
汪宗瀚而外,向叶昌炽赠送莫高窟藏品的还有敦煌本地学子王宗海。光绪三十年(1903)九月间,王两次赠送经卷及画卷,写经为《大般若经》第一百卷和《开益经》残帙,画像一帧,为唐时物。藏品中有敦煌文物后,叶昌炽便展开了学术研究,他“从文字的脱衍、书写格式及碑文断代等方面进行了考订研究,并初步推断遮羞碑文拓片对莫高窟历史研究和敦煌文物研究的重要价值”[7]182。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叶氏身处甘陇,四处视学,却从未前往莫高窟考察,因而对于敦煌文献的研究还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
离开甘省后,叶昌炽继续保持与当地学者的联系,并与有关人士成立了敦煌学研究通讯,定期交换学术信息,时刻关注敦煌文物的流向及研究的进展。然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随后不久,以斯坦因、伯希和等为代表的外国文化入侵者将侵略魔爪伸向莫高窟,敦煌文物大量流出国门。叶昌炽痛恨外国人劫掠中华文化之恶行,他亦不满清朝官吏对传统文化的漠然无视,日记中说:“张誾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象(像)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去,可惜也。俗吏边甿,安知爱古?”[11]卷十三“宣统己酉十月十六”,143他更痛惜自己做甘肃学政时未尽职责:“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象(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11]卷十三“宣统己酉十二月十三”,156已到衰颓之年的叶昌炽全无年轻时的热情,他对敦煌文物的最后研究是为私藏编目,而后一同卖给藏家刘世珩,也算是物得其主吧。
二、“搜扬潜逸”的文化根源
叶昌炽一生学术研究,创获极多,目录学、金石学、敦煌学而外,成就最大的当属近代藏书学了,他大量阅读资料,秉承史传精神,专为历史上众多私人藏书家立传。探究叶氏这一学术研究的根源,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阐释。
(一)感慨藏书家死后寂寞之境遇
在多年读书过程中,叶氏非常留意辑录藏书故实,他曾“阅《明诗综》毕,搜得藏书故实颇多”[11]卷四“丙戌二月十六日”,431,又“致寄云书,属从居停陈氏借得《有学集》一部,阙五册。其文取精用宏,洵一代钜手。谢全山从此出而诋牧翁不忠不孝,逢蒙之杀弈也。录出《述古堂记》、《千顷堂记》、《西爽轩记》、《陆勅先诗序》、《李贯之传》,可备藏书故实者甚多”[11]卷四“丙戌四月十五日”,435。叶昌炽在七卷本《藏书纪事诗》付梓时,曾撰写自序说:
昌炽弱冠即喜为流略之学,顾家贫不能得宋元椠,视藏家书目,辄有望洋之叹。因念古人爱书如命,山泽之癯,槁项黄馘。吾吴如孙道明、朱叔英、吴方山、沈与文、皆名不挂于通人之口,缥缃既散,蒿莱寂然,可为陨涕[13]30。
因为爱书,叶氏进一步有感于历代藏书家死后之寂寞无闻。藏书家们倾注终生精力,节衣缩食,朝夕访求,视书籍为生命。然而,藏书家的行为却受人嗤笑,遭人嘲讽,甚至被视为痴呆,但他们一如既往,苦心孤诣,惨淡经营,点勘不倦,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漫长历史中,有文献记载数千家之多的古代私家藏书,竟无一家能够传世长存。更为痛心的不仅是藏书遭到频繁兵燹、水浸火焚、虫蠹鼠蚀、偷盗变卖等灾害,甚而藏书家之名姓却不传于史,如史载之南都戚氏、九江陈氏、亳州祁氏、饶州吴氏、信阳王氏、遗经堂主人、东平朱氏、莆田李氏与刘氏、浦江郑氏、泰山赵氏、杭州张氏等,其姓名皆难以考证。叶昌炽对此十分感慨,故萌生为藏书家作传之念想。
(二)光大江南学者为藏书家立传之传统
明清以来,江南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术心愿,那就是为历代藏书家立传。祁承(火業)的《澹生堂藏书约》已开始专门汇集古人藏书事迹,总结藏书经验。大学者钱谦益有感于陈叔宝抄书数百卷,以备吴中故实,因此发愿为吴中“读书好古”之士网络遗逸事迹,说:“余欲取吴士读书好古,自俞石磵以后,网罗遗逸,都为一编。老生腐儒,笥经蠹书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辈流,不泯泯于没世,且使后学尚知有先辈师承在也。”[14]卷八十四《题钱叔宝手书〈续吴都文粹〉》其《初学集》、《有学集》及其他文集对于藏书好学之士记载颇多,但遗憾的是没有撰成专著。
入清,学者们更加认识到为藏书家立传之必要。顾广圻曾决心“举藏弆源流,汇所见闻,述为一编,稍传文献之信”*语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首自序,清宣统二年(1910)家刻本。。清道光间浙江海盐汉唐斋主人马玉堂曾致力于《历代编年藏书纪要》的编撰,但未见传本。之后出现了两部研究地方藏书的专著值得一提。
一是郑元庆的《吴兴藏书录》。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收录吴兴一地私家藏书目录14种,府学藏书目1种,并附录收藏事实于其后;第二部分为补辑各家传略(有4家无传),实际收录藏书家17人。《吴兴藏书录》是古代第一部区域私家藏书史专著,已经具备了藏书家传记的雏形,但是收录人数不多,遗漏较多,尚显简略。
二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申著的《武林藏书录》。该书分上、中、下、末4卷,其中卷上述文澜阁、尊经阁、南宋秘书省、太学、杭州州学、府学、杭州各书院、杭州诸公署、灵隐书藏等处藏书、藏版刻书情况;卷中及卷下叙录起自六朝范平、褚陶至清末吴煦、朱学勤等共67家藏书;卷末叙录外地居杭藏书家6人及上乘院、灵隐经藏、火德庙道藏存佚情况。“此书是中国早期地方性文献藏书资料汇编之一,亦较为详尽,很有参考价值。”[15]7
江南学者为藏书家立传的传统,深深影响到叶昌炽,是其从事《藏书纪事诗》撰著的直接诱因。他说:“顾涧蘋先生尝欲举藏弆源流,汇所见闻,述为一编,稍传文献之信。窃不自揆,肄业所及,自正史以逮稗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见有藏家故实,即裒而录之。”[13]《自序》30终至将前人事业发扬光大。
(三)丰富的藏书校书经历
叶昌炽从事藏书研究,也与自己丰富的藏书、校书经历息息相关。叶昌炽读书乡里时,最爱去的私家藏书楼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虞山赵宗建旧山楼、方功惠的碧琳琅馆等,因为多次前往铁琴铜剑楼之故,楼主瞿敬之、瞿清之兄弟给予热情接待,每次都出示多种藏书珍品。光绪二年(1876),瞿氏兄弟邀请叶昌炽校订补辑《铁琴铜剑楼书目》的史、子部分,叶昌炽欣然应允。
在广州做汪鸣鸾幕僚时,叶昌炽多次前往方功惠碧琳琅馆访书。方氏碧琳琅馆为光绪间广州城内著名私家藏书楼,藏书之富与同城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并称,亦可与同期杭州丁丙八千卷楼和常熟陆心源铁琴铜剑楼相媲美。叶昌炽在此观书,犹如探宝者走进宝藏,收获极大。为官京城期间,叶氏购书最多,薪俸所入大多交给各家书店,他利用京城购书之便,专意搜罗吴地文献,形成自己的藏书特色。叶昌炽最后的仕宦经历是任甘肃学政,在甘省他各处搜寻、摹拓,几年间,所获碑版自魏晋以迄宋、元、辽、金各代,而最可宝者为从袁伯谦处得见赵子固《落水兰亭》真本。
此外,叶氏还将目光投向海外,闻知杨守敬从日本携归不少宋元古本,即从其访购数种,充实私藏。叶氏藏书数量未见具体统计数字,但宣统二年(1910)九月间,他整理藏书时说:“位置箱架,整理题签。新旧都三十三箱:湖海投赠、坊肆雕造并丛残不全之本,另置三架;又卧室精本一架,与旧拓装册本,分上下而居之;拓片九箱。二十年塾师,二十年宦游,十束之脡,五斗之俸,尽于此矣。”[11]卷十四“庚戌九月重阳日”,169
多年的读书和藏书经历,造就了叶昌炽渊博的古籍知识,为此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图书校勘上。三十岁生日时,叶氏有诗曰:“不觉流光逝,萧疏鬓欲苍。江湖游食倦,岁月校书忙。”《缘督庐日记》中随处可见叶氏校书记载,如光绪十年(1884),叶昌炽应潘祖荫之邀馆于其家,为其校刻《功顺堂丛书》,共4函24册,校古籍凡80种;民国三年(1914),为缪荃孙校核《江苏金石目》等。叶氏好友曹元弼对于叶氏校书成就多有赞誉,云:“公校勘学冠当代,初与管明经同鉴定瞿氏《铁琴铜剑楼宋元本书目》,嗣为蒋芗荪太守校《铁华馆丛书》,精埓涧蘋。为潘文勤校《功顺堂丛书》,传习艺苑。”[16]卷十《皇清诰授通议大夫翰林院侍讲甘肃学政叶公墓志铭》正是多年的读书和校书经历,为日后从事藏书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别开生面”的研究巨著
叶昌炽从事藏书学研究,最大的成果即是编撰了一部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上,都“别开生面”的《藏书纪事诗》。他自述编撰过程:
此书自甲申属稿,迄今七载,粗可写定,犬马之齿,亦适四十有三。非敢窃附前贤,亦聊存文献于什一而已。时光绪庚寅,客都门记[13]卷六《程世铨叔平 张思孝白华》注文后按语,590。
“甲申”为光绪十年(1884),其时叶昌炽应潘祖荫之邀馆于其家,帮助潘氏校书、编目,在繁忙的工作中,他开始着手这项伟大的文化事业。“庚寅”为光绪十六年(1890),叶昌炽43岁,历时7年,编定著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叶昌炽的学生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致力于《灵鹣阁丛书》的编刻,遂将《藏书纪事诗》收录进丛书第五集,前后用时仅7个月便刻成,此为《藏书纪事诗》的第一个版本,通称“灵鹣阁本”,亦称“六卷本”。尽管江标刊刻灵鹣阁本《藏书纪事诗》依据的是叶氏亲自编定的稿本,但由于多种原因,讹误颇多,招来诸多批评。为此,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叶昌炽息政归隐,专心修订,将原来的六卷扩编为七卷,对书中时代有误、附传不明者认真校订,并在原有传主下又新增附传多人,宣统二年(1910)完稿,次年即付梓,称为“七卷本”,为通行本。
潘景郑先生说:“纪事有诗,壹皆掇拾历史、地理、风土、人物,广搜博采,以补传记之不及,可备后人之参稽,征文考献,有足称者。例如清沈嘉辙之《南宋杂事诗》、汤运泰之《金源纪事诗》,开其先河。后有述者,未能出其藩篱。乃匠心别裁,得以上下千年汇藏书家于一编者,则唯乡先辈叶鞠裳先生昌炽之《藏书纪事诗》为创举焉。”[17]叶昌炽所创作的《藏书纪事诗》,通过征引大量文献,较为全面地勾勒出了每位藏书家的生平、藏书特点、书斋名、藏书印、藏书目录及代表作,几乎相当于一部藏书家的传记辞典,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集中地记录藏书家书斋名、藏书印的工具书。
《藏书纪事诗》出,立刻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好友吴郁生直言该书与叶氏另一种《语石》“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11]卷首吴郁生《〈缘督庐日记钞〉序》。吴氏所谓此书“必永存天壤”之缘由,大概是基于该书首创为古代藏书家作传之例,但是更能够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还在于该书的编撰特色。
(一)传主选择
《藏书纪事诗》属于人物传记类史书,传主为历代藏书家,这是叶氏开创的新题材传记。叶氏在传主起迄时代和类别上,十分用心。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虽比公藏稍迟,但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其时民间已经出现了收藏兵家、法家著述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图书文献不断增多,私家藏书队伍不断壮大,历代史料对此多有记载。《藏书纪事诗》作为一部通史类人物传记,全书收集各类藏书家737人,传主起于五代,迄于清末。对于这一情况,清人刘肇隅说:“是书唐以前人概勿采取,以书有墨刻,创于唐末益州;摹刻《六经》,始于蒲津毋氏也。顾自长兴刻木以来,书出日富,书误日滋,宋、元、明迄国朝,诸储藏家于是喜言校勘,并考辨目录、板本。其学至精博者,至黄佞宋、顾思适二家为最。大率终身寝馈书窟,没后散佚,仅传书目,或并无书目,仅一二遗闻及叙跋、印记见引于各书,不为类纂,惧伤泯沫。”[18]卷尾
《藏书纪事诗》所记藏书家起于五代,迄于清末,而不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私家藏书,是叶昌炽对五代以来典籍史作深入考量之后的决断。五代以后,文化发达,历代皆大力兴建各种书院,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图书编纂事业极为繁荣……所有这一切,对私家藏书无论质还是量都是前所未有的促进。有宋三百年中,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藏书家就达七百人,是此前周至唐五代千年左右藏书家总和的近三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私家藏书发展的大起步,实从宋代起,自宋而后,万卷书楼,蜂拥南北,是中国私家藏书进入兴盛发展阶段,从而与宫廷官府、书院寺观的藏书鼎足而三,构筑成中国藏书文化活动新局面”[19]60。同时,我们也看到,从五代开始,雕本印刷得到广泛使用,宋代则印本书籍更为普及,给私人藏书以巨大的便利,大大推动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纪事诗》所记藏书家起于五代宋,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在传主的类分上叶昌炽别有旨意,在他眼中只要从事藏书活动,不分贵贱,上自贵胄,下至草民,皆可入传。全部藏书家以官员和学者为多,此外,较为特殊的藏书群体有以下几类:
宗室藏书家。宋宗室4人:赵宗晟、赵宗绰、赵令畤、赵孟頫;辽宗室1人:耶律倍;明宗室15人:朱橚、朱睦(木挈)、朱权、朱谋(土韦)、朱钟铉、朱奇原、朱知烊、朱新(土典)、朱诚泳、朱惟焯、朱宠(氵寰)、朱祐楎、朱厚煐、朱见湳、朱载埨;清宗室4人:爱新觉罗·弘晓、爱新觉罗·弘瞻、爱新觉罗·永瑆、盛昱。
方外藏书家。全书所载3人,其中释家1人:宋代释文莹;道士2人:宋陈景元及宋代无为道人。
女性藏书家。叶昌炽共为5位女性藏书家立传,分别是宋李清照、明归有光妻王氏、清陆(火亘)妾沈采、张蓉镜妻姚畹真和严元照妻张秋月。
书贾。叶氏在其中8首诗中,记载宋代书贾建安余氏、陈起、陈思、尹家书籍铺等;元代书贾陈世隆2人;金代书贾王文郁1人;明代书贾童珮1人;清代书贾老韦、陶正祥、陶珠琳、钱听默、侯念椿、陈驼子等6人。
从事活字版印刷者。叶氏记载这类传主有活字版印刷术发明者宋代人毕昇,明代活字版印刷实践者无锡华燧、华珵、华坚3人。
外籍藏书家。《藏书纪事诗》卷四所载之安岐(1683—?),字仪周,原为朝鲜人,后入旗籍,其父安图为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家仆。关于安岐之国籍问题,叶氏曾做过专门之考察:“初九日,夜赴茂如招,出示方环山《松阴待客图》,有胡天游、陈玉几、金寿门诸公题词。又文五峰《秋林晴霭卷》安仪周旧藏,有‘朝鲜人’一印,余作《藏书纪事诗》欲定仪周为朝鲜人,而无可考,得此可为确证。”[11]卷六“光绪壬辰八月初九日”,241
《藏书纪事诗》这一传主入选原则,开启私家藏书研究的新思路。关于这点,时人叶德辉甚加赞赏,云:“《藏书纪事诗》于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遗闻佚事,详注诗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即使诸藏书家目录有时散逸,而姓名不至灭如,甚盛德事也。”[20]1
(二)诗注结合
中国史书编撰繁荣,人物传记尤可称道,种类有传、表、铭、录、簿、赞、谱、牒、记等等,文字形式上有文、诗、表、图诸种。叶昌炽深谙人物传记叙写之道,《奇觚庼文集》卷下收录了32篇传记,体裁有铭、略、传、耒等;外集收录11篇寿序。在创作《藏书纪事诗》这部大型人物传记时,他别出心裁,一改传统的传记体书写模式,采用诗注结合的方式,全书7卷416篇,每篇由七言绝句、系名、注文三部分构成。
第一,绝句。《藏书纪事诗》的诗歌全是整齐划一的七言绝句,由一位或几位藏书家的史料构成,内容一般是撮录他们最具特征的藏书楼号、藏品、藏书事迹、著作、学术观点等。如第一首《毋昭裔守素》云:“蜀本九经最先出,后来孳乳到长兴。蒲津毋氏家钱造,海内通行价倍增。”首句说的是蜀本《九经》乃毋昭裔奏请蜀主所刻;次句言后唐明宗长兴年间,国子监负责雕版印书之事,所刻《五经》乃仿后蜀而来;三、四句言毋氏不但倡议后蜀官刻儒家经典,而且自家曾出资大量印制图籍通行天下,泽惠后人。
诗作不全是客观的叙写,时有对传主学术素养和治学成就等方面的评述。如卷六《陆心源刚父》说:“蓬莱道山皆荒渺,芳茮疏雨亦寥寥。守先高阁苕溪畔,乣缦卿云覆绛霄。”关于这首诗的最后定稿,叶氏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则日记写道:
补陆刚父观察藏书一绝。又校正怡府一则。存斋斥明人书帕本之谬,又诋各家刊本,动云不如不刻,而其所刻书亥豕纵横,触目皆是,本拟赠以二句云:“一语请君还入瓮,刻书容易校书难。”既思反唇相讥,非所以待逝者,特刊去之[11]卷七“丙申十二月十六日”,354。
叶氏对于绝句不断进行加工,既要能够真实反映传主的藏书及学术成就,又不愿违背史实,今人王立民说:“叶氏在陆心源的评价上是颇费过一番心思的。既指出了这位学术前辈校勘工作的失误,又不因此菲薄前人,从而显示出良好的学术道德。”[21]87
第二,系名。即在绝句下附本篇所叙述的一位或几位藏书家的姓名。由于古代藏书家情况复杂,因而叶昌炽对于传主系名问题十分审慎,根据不同情况系名。其中,最常用的系名原则是姓、名、字连录。如卷一“周密公瑾”,“公瑾”为其字,号泗水潜夫。为了配合系名的准确性,叶昌炽常在注文引用相关文献佐证,如卷三《刘凤子威》的注文第一则便引用《明诗综·小传》:“刘凤字子威,长洲人。嘉靖甲辰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佥事。有《澹思》《太霞》二集。”[13]卷三,210对于有封号的传主则封号在前,只取名,不系字。如卷二所录元代东丹王倍,明朝诸王周定王橚、宁献王权等,卷四所录清代诸王,系名时则只有封号,如怡贤亲王、国恭亲王、成亲王等,不系名的原因也许在于清代诸王为满族,姓爱新觉罗,另有名字。对于有谥号的传主则姓、谥、名连录。如宋人赵安仁(958—1018),字乐道,北宋河南道(今河南洛阳)人,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御史中丞,卒谥“文定”,叶昌炽在卷一中对其系名曰“赵文定安仁”。同一家族传主在同一首诗后的系名,正传主和副传主之间是兄弟关系,则副传主不列姓氏,只系名和字。如卷三《顾从礼汝由 从德汝修 从义汝何》,其中正传主为“顾从礼”,“顾从德”和“顾从义”都是顾从礼之弟。正传主和副传主之间是父子或祖孙关系,则副传主前要标明其与正传主之间的关系。如卷一《王莘乐道 子铚性之 孙廉清仲信 明清仲言》,“王铚”为正传主“王莘”的儿子,“王廉清”和“王明清”是正传主“王莘”的孙子。而如果正传主和副传主之间是夫妻(妾)关系,妻(妾)有名有字,则与正传主一样系名和字,如卷一《赵明诚德父 李清照易安》、卷五《陆烜子章 沈彩虹屏》、卷五《张燮子和 孙蓉镜芙川 姚畹真》、卷六《严元照久能 张秋月香修》;妻(妾)如果没有名或字留下来,则只系姓氏,如卷三《归有光熙甫 妻王氏》。传主为无名氏者,系名时以里第为主。如卷一所载“南都戚氏”、“九江陈氏”、“亳州祁氏”、“饶州吴氏”、“信阳王氏”,卷二所载“吴郡陆君”、“浦江郑氏”,卷七载“泰山赵氏”、“杭州张氏”等。
第三,注文。即从正史、方志、笔记、诗文集、墓碑、书目题跋、时贤言论、作者见闻等各种材料中辑录出藏书家事迹,或作为绝句的注脚,或仅是与本篇所叙藏书家有关,而与诗无涉。注文是《藏书纪事诗》的主体,辑录文献的内容包括藏书家的姓名籍贯、生平行止、藏书事迹、学问著述乃至掌故逸闻,从而提供了有关藏书家的基本史料和学术线索。
古代藏书史料十分丰富,蕴藏于各种史料之中,在选取史料时,叶昌炽十分关注史料的录用排比问题,而不是一股脑儿胡乱堆砌,具体而言,他在史料的排比时注意了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
所谓横向比较,就是对于某一件事多种资料均有反映,叶氏则不厌其烦,逐一收录,读者通过比较,对于资料之真伪不辨自明。如卷四《钱谦益》,关于绛云楼发生火灾的具体时间,小注所引各条资料记载不一:
《天禄琳琅》:“宋本《汉书》钱谦益跋:‘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
《人海记》:“钱蒙叟撰《明史》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毕,越后日,绛云楼火作,见朱人无数,出入烟焰中,只字不存。”
牧斋《赖古堂文选序》:“庚寅孟冬,不戒于火,为新宫三日之哭,知天之下假我以斯文也。”*(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337页。此处引文有删节。
叶氏所引《天禄琳琅(书目)》和《赖古堂文选序》中的文字,都是钱氏本人亲自记载的,两次所述绛云楼之火皆在庚寅之年(清顺治七年,1650),如此之事,刻骨铭心,当事人决不会搞错。而反观《人海记》所记,时间、情景甚详,但时间却为辛卯(清顺治八年,1651),两相比较,读者自然得出真实的时间。
所谓纵向联系,就是通过所引资料的逻辑关系,帮助读者了解事物的发展过程。如卷二《宋文宪濂 曾鲁得之》中的一则注文:
《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板,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版,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希世珍。”昌炽案:此书亦见《读书敏求记》,今藏潘文勤师“滂喜斋”[13]卷二,105。
这里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白氏长庆集》的编纂刊刻流传情况。唐穆宗长庆二年(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次年,好友元稹任浙东观察使,两地相去不远,二人又开始频繁的唱和。长庆四年(826),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之际,元稹索其全部作品编成50卷,题曰《白氏长庆集》。元稹之后,白居易又多次增订自己的作品,陆续编成《后集》、《续后集》,且多次缮写。唐会昌五年(845)白居易作《白氏集后记》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订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此处《白氏集后记》转引自韦力《黄永年跋·嘉靖本〈白氏文集〉》,《光明日报》2012年04月05日12版。按,关于钱谦益收藏该书的情况,韦力接着说:“今传世最早刻本为南宋绍兴初年刻本《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七十五卷本宋人未见著录,似仅存于传说。《述古堂书目》载有《白氏文集七十五卷》,然‘庚寅一炬,种子断绝’,故钱谦益曾藏七十五卷本之《白氏文集》,则为传说中之传说。另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言曾于钱谦益处所见《白氏文集》为庐山本,然宋人宋敏求却言庐山本止七十卷,且无续后集,故钱谦益曾藏七十五卷本之说更见可疑。黄丕烈尝以白金二十两易得绛云楼烬余残本《白氏文集》十七卷,是书既有烧痕,亦有水渍,仅知其为宋本,确否七十五卷本之残卷则未知,《荛圃藏书题记》记此事甚详。”
据顾广圻《百宋一廛赋》及黄丕烈注所言,北宋时曾以“庐山本”为底本镌刻《白氏长庆集》,宋濂藏书中就有一部,后归黄丕烈所有。嘉庆二十三年庚寅(1818),黄氏家中被火,所幸此书完好。又据叶氏按语,可知此书清初曾经钱谦益所藏,黄丕烈后,归潘祖荫所有。这样,通过《百宋一廛赋》的记述,《读书敏求记》的收录,和潘氏的入藏情况,就给读者勾画出了《长庆集》流传的一个大致线索,从而使得本来单独的资料变得较为完整实用了。
叶氏在注文中征引广泛,并对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排比,其中多有古代藏书制度、典籍聚散、版本流传、地方藏书兴衰等专题史料,因此后人有“甚至成为中国私家藏书事业的资料渊薮”[22]1022之论。
(三)缀以按语
《藏书纪事诗》注文后,还有叶昌炽的多则按语,按语前标“昌炽案”三字。一般而言,按语放在注文后面,也有穿插在注文中间的。叶氏对于按语的撰写十分留心,有引用典籍的,而更多的则为自己见闻,如卷四《张惟赤》注文在引用《涉园修禊记》、《皕宋楼藏书志》、《两浙輶轩录》、《楹书隅录》、《铁琴铜剑楼书目》诸书后,按语曰:
旧在京师,顺德龙伯鸾凤镳以所藏吕无党手钞《后村集》见示,有“古盐张氏”及“宗橚咏川”诸朱记。皕宋藏书《陆宣公集》有“张载华”、“佩蒹”诸印。张氏藏印,诸家著录数见不鲜,顾其世系未能详也。宣统纪元之岁暮,重雕此集至第四卷。张鞠生农部元济自沪上寓书来,云螺浮给谏是其先德,以涉园世系见示。始知螺浮先生名惟赤,顺治乙未进士,刑科给事中。长子(月告),号小白,别号皜亭,康熙壬子举人。有三子,长芳溶早逝,以弟子宗松为嗣。次芳湄号象贤,一字葭士。宗松即其次子,号青在,又号寒坪。著有《扪腹斋诗钞》,即农部之六世祖也。第五子曰宗柟,号吟庐,别号含厂,著有《带经堂诗话》。第六子曰宗囗(木肃),号咏川,一号思岩。第八子曰载华,号佩蒹,一号芷斋。柯字晋樵,一字东谷,葭士弟芳潢之子也。鸥舫名鹤徵,佩葭之长子。以诸家书目藏印证之,世德清芬,若合符节。螺浮先生为王文简同年进士,宜次其后。是卷缮刻至叶石君一首,而农部函适至,犹及改纂。不先不后,若有天幸,岂非先哲有灵,有以牖启之乎!附志于此,以箴前阙,亦农部君志也。岁在庚戌元日,缘督记[13]卷四,385。
这段按语为叶氏阅吕无党手钞《后村集》,以及与张元济会面并阅张氏世系后综合而来,补充了注文所引五种史料之不足,可以作为信史看待。再如卷四《席鉴玉照》注文后叶氏按语云:“玉照藏书极富,所刻古今书籍,版心均有‘扫叶山房’字。余曾见所藏《宝晋山林集》,有‘萸山珍本’印。”[13]卷四,436版心字样和藏书印,皆为叶氏亲见,这样的按语史料价值之高自不待言。
四、“永存天壤”的学术影响
胡文辉评价叶昌炽的学术成就与影响说:“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增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23]146这个评论不可谓不高,而事实上,仅就叶昌炽近代藏书学研究而言,的确可以称得上“孟晋超群”[5]。
(一)“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开创之功
金振华先生说:“叶昌炽广搜博辑,发凡起例,撰成《藏书纪事诗》一书,专门为藏书家立传。”[7]153“发凡起例”指该书体裁而言,在此之前,诗传结合为藏书家立传的书体尚未出现,因此,王锷先生说:“仅此一部体裁内容都是空前的巨著,叶昌炽足以立言不朽。”[24]体裁的独特性,正是该书受到学术界持续关注的原因之一。
《藏书纪事诗》开创的这一文体到底属于哪一类?该如何为之命名?
笔者检阅材料得知,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王余光、徐雁二先生始有论述:“该书以七言绝句,概括五代末以迄清季739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史实,开创了纪事诗体藏书家传。”[25]391第一次明确以“纪事诗体藏书家传”名之。又过十余年,傅璇琮、谢灼华二先生进一步较为详细地阐释说:
叶氏从历代正史、方志、笔记、文集、书目和藏书志中辑录出大量历史上藏书家活动的资料,集中展示了我国自印刷术普及应用以来直至清末的藏书家、书贾、印刷工匠以及有关刻、校、抄、读书人士一千一百多人的事迹及其对文化学术所作出的具体贡献,从而使得对历代藏书家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所开创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体式,素有“书林之掌故,藏家之诗史”之誉[22]1018—1019。
傅、谢二先生对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开创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评价很高,至此可以说,藏书纪事诗的诗传结合体式终于有了较为固定的文体名称。赵国璋、潘树广合编的《文献学大辞典》在收录此条时给出二义:其一指叶氏著述《藏书纪事诗》,其二即云:
纪事诗体藏书家传名。清叶昌炽首创。以私家藏书史实为题材,多作七言绝句形式并领有藏书传记一篇。其典范格式应为“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按语。”[26]1099
纪事诗体藏书家传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这一文体所咏歌对象的独特性——藏书家,形式上的新颖性——绝句、诗注和传文的结合。每一种文体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许多文体都萌生于古代礼仪文化制度,以其独特的潜质发挥着解释礼义、装饰礼仪等特殊功能,在构建群体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叶昌炽开创“纪事诗体藏书家传”这一文体后,后继之作不绝。
1935年,伦明有感于“近来银行家,多喜藏书,武进陶兰泉、庐江刘晦之,其最著者也。闻杭州叶揆初者,亦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收藏稿本、钞校本甚夥”[2]131这一藏书新现象,创作了《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倘以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为书林《史记》,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则为书林之《汉书》。叶著为书林通史,而伦著则为断代之史。”[27]27从这个角度来说,伦书实为叶书的继承与发展。
出于对广东文献的热爱,徐信符紧随其后,他撰写《广东藏书纪事诗》一书,具体撰写年代不详。徐氏去世后手稿曾经叶公绰先生校阅,刊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之《广大学报》“建校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题曰《广东藏书纪事诗稿》。该书“收广东自明代以迄民国藏书家数十人,详述广东典籍聚散之源流,阐扬藏书家之潜德,洵为不朽之作”*此语为《广大学部》编辑部为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所撰写的前言,载《广大学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第1期,第69页。,作为断代藏书纪事诗,对“纪事诗体藏书家传”作了进一步拓展。
苏州学者王謇晚年创作《续补藏书纪事诗》,此书乃“藉补缘督先生所未及,且有裨藏书家之故实焉”[28]69,收录了晚清民国以来,尤其是江南一带诸位藏书家史料,增益了许多藏书故实。1966年,安徽泾县学者吴则虞“步武清叶昌炽先生作《续藏书纪事诗》”[29],在后续诸作中,《续藏书纪事诗》最类叶书,诗后之注取自各类文献,并附有藏书室、藏书印。此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迄今,先后有周退密和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和蔡贵华《扬州近代藏书纪事诗》等续作。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尝试创作“纪事诗体藏书家传”,一方面为各类藏书家作传,另一方面则将这一文体发扬下去。
(二)杂取百家的创作思路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问世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其中,汪誾说:“(《藏书纪事诗》)网罗前闻,捃摭遗事,搜扬潜德,阐彰之功,诚不朽矣。”[30]一部著作能够得到“不朽”的评价,于著者本人亦是莫大的荣耀。
藏书活动的对象是典籍,而活动的中心是藏书家,因而研究藏书活动的中心也应放在藏书家本人身上。“过去学者们重点关注私人藏书家,事实上是把藏书史变成了一系列个人传记,绝大部分是中国士人的传记,他们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朝廷以外中国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者。”[31]5中国向来史学发达,人物传记的创作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各类史乘多以传记为主体,但传主的身份非富即贵,或忠或烈,学者传记则分在儒学门或文苑门,未见有传记设立藏书一门。直至晚清,随着《藏书纪事诗》出现,藏书家作为独立的传主开始进入传记著述之中,传记作品确立了一种新题材、新样式。
叶氏治学无书不读,尤好碑版目录,更兼小学词章,广博的读书经历有助于搜辑资料,其撰写《藏书纪事诗》所采资料除史志、文集外,更多的是杂取百家。以古代笔记为例,叶氏平日读书十分留意,从中获取大量的知识,日记中对于所读笔记记载较详。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九日:“晚至筱珊处,见旧钞本《麈史》、《庶斋老学丛谈》,皆士礼旧物,有荛圃跋。《麈史》为瓜泾徐氏本,据跋荛圃又有钦仲阳本,钦、徐皆明时吾郡故家也。”[11]卷三,387
以叶氏为宋代藏书家作传为例,笔者检索《藏书纪事诗》各传小注资料来源于宋元明清笔记资料有:王明清《挥麈馀话》、《挥麈前录》、《挥麈后录》、《玉照新志》、司马光《涑水纪闻》、陈师道《后山谈丛》、赵令畤《侯鲭录》、徐度《却扫编》、文莹《湘山野录》、黄伯思《东观馀论》、何薳《春渚纪闻》、王得臣《麈史》、叶梦得《避暑录话》、庞元英《文昌杂录》、范公偁《过庭录》、朱弁《曲洧旧闻》、沈括《梦溪笔谈》、孙升《孙公谈圃》、陆游《老学庵笔记》、黄休复《茅亭客话》、费衮《梁溪漫志》、尤玘《万柳溪边旧话》、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楼钥《攻媿集》、周煇《清波杂志》、岳珂《愧郯录》、周密《齐东野语》、《武林旧事》、龚明之《中吴纪闻》、王应麟《困学纪闻》、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楙《野客丛书》、孔齐《至正直记》、吾丘衍《闲居录》、张萱《疑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姜楠《蓉塘诗话》、张丑《清河书画舫》、陈继儒《太平清话》、李日华《紫桃轩杂缀》、焦竑《焦氏笔乘》、胡承谱《无事为福斋随笔》、王士禛《居易录》、钱泰吉《曝书杂记》、梁玉绳《瞥记》、全祖望《湖语》、蒋光煦《东湖丛记》等。
叶昌炽用了三年多时间搜辑大量资料,足迹所涉有生活多年的故乡苏州、远来做幕府的广州和科考做官的北京等地,“只有叶氏那样的经历,只有他那样的嗜书如命,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四处逛厂阅肆,与众多书商打交道;也只有他那样的刻苦钻研,以一种认真真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才有数十年如一日,将这部书做细做好。”[21]82
(三)推动藏书研究不断形成热潮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问世,标志着近代藏书学研究的成熟,是藏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藏书文化,自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开启了总结研讨之风以来,先后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22]1022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逐渐复苏的重要时期,藏书研究也一样,随之得到了长足发展。表现有三:一是藏书逐渐从私家藏书楼向公共图书馆汇集,私藏变为公藏,典籍才有了相对长久的安身立命之所,学者们可以一睹为快,藏书研究更为便利。二是各类藏书研究著述频出,有藏书史研究,如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江苏藏书家小史》、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等;有藏书家生平研究,如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略》、杨立诚和金步瀛合编《中国藏书家考略》等,有藏书家书信汇编,如潘博山《藏书家尺牍》;有古籍版本研究,如叶德辉《书林清话》;有藏书楼研究,如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还有典籍流传研究,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等等,这些著述“皆以《藏书纪事诗》为其滥觞……凡此胥由鞠裳之发阐,而诸藏书家得以不泯灭也”[32]。三是从1936年到1940年,各地举办多场近代文献展览会,主要有嘉兴文献展览会(1936)、浙江文献展览会(1936)、吴中文献展览会(1937)、上海文献展览会(1937)、漳州文献展览会(1937)、淮海文献展览会(1937)、察哈尔文献展览会(1937)、广东文物展览会(1940)等。“凡先民手泽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33]411近代文献展览会以文献收集、展览、研究为一体,多方对私家藏书事迹进行宣扬,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提升了民族士气。
日寇侵华、国共内战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文化动荡,藏书研究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藏书研究迎来了新的春天,学者们沿着叶昌炽开辟的路径,不断探索,出版了一批在藏书史上影响较大的成果。有藏书家传记,如徐雁和谭华军《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苏靖《近代藏书三十家》;有藏书辞典,如李玉安和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辞典》;有藏书目录整理,如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有藏书楼研究,如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等等。
“《藏书纪事诗》的问世,封建社会中叶以来藏书家的藏书成就及其文化学术贡献因此得以集中展示,从而使藏书史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7]155时至今日,藏书研究仍处在不断推进过程,研究不断向全面和纵深发展,这些成果的取得,均与叶昌炽悉心搜集藏书家史料、阐显藏书家事迹的开先之功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3]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M]//观堂集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吴郁生.缘裻庐日记钞·序[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6]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序[M].续修四库全书(第9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金振华.叶昌炽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8] 吴琦幸.缘裻庐日记钞·前言[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9] 陈少川.潘祖荫、叶昌炽与《滂熹斋藏书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4):65-66.
[10] 孙荣耒.如何评价叶昌炽在近代文化学术上的贡献[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4).
[11] 叶昌炽.缘裻庐日记钞[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12] 张晓旭.苏州碑刻纵览[J].东南文化,1999(3):82-89.
[13]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四部丛刊(第164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15] 范凤书.私家藏书风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16] 曹元弼.复礼堂文集[M].民国六年(1917)刊本.
[17] 潘景郑.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序[M]//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卷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8] 刘肇隅.藏书纪事诗跋[M]//藏书纪事诗.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标灵鹣阁刻本.
[19]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
[20] 叶德辉.书林清话·序[M].扬州:广陵书社,2007.
[21] 王立民.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
[22]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5.
[23] 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4] 王锷.《藏书纪事诗》跋[J].图书与情报,1999(3):76-77.
[25] 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大辞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5.
[27] 翟鹏.藏书纪事诗研究[D].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28] 潘景郑.续补藏书纪事诗后记[M]//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29] 吴受琚.悼念我的父亲——吴则虞教授[J].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4):47-48.
[30] 汪誾.明清蟫林辑传·自序[J].图书馆学会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抽印本,1932.
[31] 周绍明.书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M]//书籍的社会史·卷首(何朝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2] 蔡金重.藏书纪事诗·引得[M].哈佛燕京学社,1937.
[33] 叶恭绰.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M]//遐庵汇稿(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