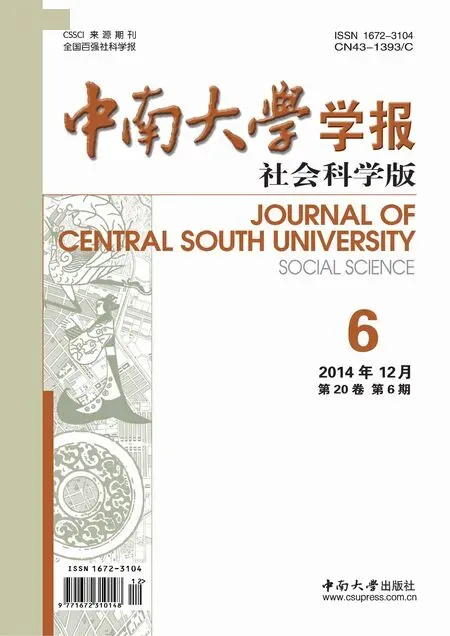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构建与历史影响
赖井洋,王泽应
(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韶关,512005;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构建与历史影响
赖井洋,王泽应
(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韶关,512005;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建构主要包括:以“心性之学”奠定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基础;以“心忧天下”确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康国济民”构筑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以清官政治彰显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以“希圣希贤”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旗帜。宋代道德理想主义对历史的影响不仅仅是学理层面的影响,更是一种精神内核的引领。直至今天,它仍然是挺起民族脊梁的精神力量,是实现民族复兴、共筑美丽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精神旗帜。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心性之学;精神支撑;人格典范;精神家园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是对先秦儒家道德理想和道德理想主义的赓续与提升,是宋代特定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凝结和凸显。其构建主要包括以至善理想人格引导人们注重身心修炼、成圣成贤;以美好的社会理想引领人们通经致用、躬身践行;以清官的政治理想人格为政治伦理生活的范导;以担当天下的责任意识确立“以天下为己任”历史使命感,内含着拯救人心、改造社会的道德实践精神,为社会道德生活指明精神方向。它的历史影响不仅仅于学理层面,更是一种精神内核的引领。它是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
一、以“心性之学”奠定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基础
先秦儒家的思想以“仁”为核心,而“为仁之方”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修身之道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的统一,展现出“仁者爱人”的精神境界追求,孟子将“仁学”扩展为心性之学,并使之成为儒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宋代道德理想主义则是对这种心性之学的肯认与赓续。
(一)以心与理、心与道的糅合挺立理想人格
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圣人人格。所谓圣人就是既要有“仁”的精神境界又要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功业,圣人人格体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但是,儒家之道,“孟子没而不得其传”,因此,以复兴儒学、承继孔孟之道自许的理学家把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提高为本体加以阐发和强调,以心与理、心与道的糅合挺立起儒家之理想人格。
《宋史·道学传》指出:“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从而提出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立人之道和“寻孔颜乐处”的精神指向。而受业周氏的二程,以“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观念为核心开创出“天理论”之思想。所以,程颐直接地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 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1](640)程颐之言不仅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也道出了思想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就是要破解“人欲肆而天理灭”之困境,并“以斯道”去“觉斯民”。很明显,程颐所言之“道”就是“仁”之道,也就是儒家的精神传统。由此,理学家在对先秦儒家“仁”之内涵的阐述上,很是做了一番工夫。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又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1](16)仁在根本上是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浑然与万物同体”的最高精神境界。二程从“天人一理”出发,指出天道“只是理,理便是天道。”[2](290)由此,仁也就是与天同在的“理”,“仁者天下之正理”[1](136),而天理内在于人,便是人之性,即“性即理”也,由此演绎出“人伦者,天理也”[1](394)。程氏之论不仅使“理”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也具有了人生论之意义。所以,他强调“学者须先识仁”。二程之“仁”,是个体内心对理、天的体验,表现出一种新的仁学方向。谢良佐所说的“心有知觉之谓仁”[2](386)的“以觉言理”则是对这种新仁学的发展。朱熹以程颐之“性即理”说为基础,从心与理的结合上对仁的理解具有总括性。朱熹主张“心与理一”,他反复强调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而“仁者,心之德,爱之理”[3](693),“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3](691),“仁是理之在心者”[3](703),也是“孝悌之本”,是“四端”的表现。朱子之言把仁的内涵界定为人秉天地生物之心的“心之德,爱之理”。所以朱熹主张学者欲得仁,须在“‘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3](694)。可见,理学家“仁天合一”和“心与理一”之“仁”说表现出心与理、心与道相糅合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的新视野,凸显出人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挺立。
(二)通过身心的修炼达到对人心的拯救和对社会的改造
理学家在对儒家道德思想进行赓续的同时,又以儒家道德思想为武器对社会道德生活进行批判与反思,以期实现对“充满私欲”之人心的拯救和对社会的改造。
1. 修炼身心,完善人格
由于五代乱世,造成了士风颓废、礼崩乐坏的局面。有宋一代始立就迫切需要重振儒家纲纪,因此,注重修炼身心,完善人格就成了理学家的人生理想追求。周敦颐由“无极而太极”之宇宙观推演出人生观,认为“诚”是人之本性,也是最高之道德境界。他说:“诚者,圣人之本。”[4](31)纯粹至善,至善之基在于“静”,无欲则静可达“中正仁义”,所以,周敦颐主“静”以修身。张载以“气”为宇宙之本,在人生道德实践方面主张“穷理尽性”的“自明诚”的道路,通过“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5](65),“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从而达到“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之境界,而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思想的确立则是个体道德意识的自觉提高,激励起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表现了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崇高性。程、朱理学对董仲舒视天为人格神的理论否定,直接以“理”为天,表现了“天理合一”的理论特性。程颢认为“天者,理也”[1](132),而朱熹则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3](900)“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性即理也。”[3](215)从而构建了一套“穷理尽性”“以至诚参天地”[1](117)的修炼心法,把“尊德性”作为人们成圣成贤之根本。为此,他们对道德理性与感情欲望即“天理人欲”的关系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以特定的时代标准作出了评判,指出道德修养之实质是“存天理,去人欲”。程颐指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312)朱熹则认为学圣之根本,要用“道心”去主宰“人心”,以“天理”节制“人欲”。因此,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明天理,从而达到 “圣人大而化之之心与理一,浑然无私欲之间而然也”的境界。可见,理学家普遍主张通过“立诚居敬”“反思求仁”及“克己复礼”“改过迁善”的涵养工夫,达到至善的人生境界,凸显了道德主体性的作用。
2. 拯救人心,改造社会
在理学家看来,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人心”问题,改造社会实质上就是要拯救人心。理学家在先秦儒家思想的熏陶与感染下,具有救世与自救的人生信念,其所救的就是人之“心”。第一,重续道统、拯救人心。因为五代之乱,不仅乱臣贼子多出,“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可胜数哉!”[6](235)以至欧阳修感叹曰:“天下为无士矣。”而且,五代之乱使君臣、父子之道乖,人鬼失其序,以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6](243)。五代之乱,不仅乱了社会,乱了人伦、也乱掉了人心。因此,重振纲纪、提振士风就是重续道统、拯救人心。第二,克己复礼、去欲救心。周敦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4](32),欲求仁之境界须克己与去欲。“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私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3](224)因为人之欲害仁,所以朱熹反复强调,“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3](3710)这个害仁者便是欲,所以要去人欲而存天理,“无欲则静”,静则心正,方能达到平天下之目的。理学家虽然主张“存理去欲”,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与道德原则相背离的不健康的人欲,摒弃的是蒙蔽“仁”“义”的私欲,反欲的目的是为了去追求比生命、生存更为宝贵的价值——道德理想,实现拯救社会之目的。
就此而言,理学家对人心、人生的内在体验和对心性之学的肯认是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并建构起的“仁理合一”“心与理一”的宇宙论和人生论,从而把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先秦儒家道德思想提升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突显出其融生命、思想为一体,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独特思想神韵。
二、以“心忧天下”确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
由“忧患意识”凝聚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集中体现了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发愤图强的精神支撑。
(一)“以天下为己任”对“以道义为己任”的超越
先秦时代,与法家、纵横家相比,儒家之士主张“以道义为己任”,实现寻求知识的“志于道”理想,因此,在孔子的眼中,士是追求知识不知疲倦的人,他们“行而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论语·子路》),具有“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的品行。孟子认为士“尚志”“志于道”。他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民不失其望焉”(《孟子·尽心上》)。荀子则说:“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贫”(《荀子·尧问》),士的天职是“正身肩道义”,荀子之士完全是道德和知识程度的代名词,是一种士君子,所以“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义之所在,不倾于劝,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可见,先儒之士“以道义为己任”,追求的是个人层面上道德修养。把道义视为人生第一要义是先儒之士的共同特质。从孔子起,“士”的传统延续了二千余年,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陈蕃“有澄清天下之志”。事实上,只有到北宋,范仲淹起而倡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终于激动了一代读书人经世致用的豪情和理想,这种豪情和理想是对个人层面上“以道义为己任”的超越。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饶、发愤图强的精神支撑
宋代理学家不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道德理想,更注重“经世致用”,在学理实践、道德实践中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与责任。
周敦颐倡“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强调以诚为修身之本。他认为“诚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4](32),主张立诚以修身,修身以成圣。他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4](41)他教程颢寻“颜子之乐”,追寻“仁义中正”的圣人之道。政治上,周敦颐则主张“以政养万民”,认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4](41)周敦颐为教重道德教育,为官倡“廉洁”之风,在道德实践中体现了“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境界。周敦颐的人生道德理想、社会道德理想不仅是理学家而且也是整个理学的发展的精神方向。
欧阳修大胆疑经,推进古文运动。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7](481)又说:“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三代两汉之学不过此也。”[7](499)欧阳修的“知古明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表现出的是一种躬身践行的实践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并开出了一条实践道德理想的道路。所以,漆侠指出:“欧阳修的道路,特别是庆历以前的四十多年中就是他的最为光辉的实践道路。”[8](215)这条道路也是士大夫所选择的共同道路。而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既重视自身的道德修炼,又积极投身道德实践。范仲淹对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践行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整顿文风,厚其风化。他说:“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9](200)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文风的作用。他认为文风关乎社会风化、关乎国家社稷盛衰,由此主张变革骈文,整顿文风。他批判四六骈体文,投身古文运动,要求朝廷“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9](200)。这种认识可谓是深刻的。第二,倡导兴学,培养人才。范仲淹对“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的深刻认识,使他对设教兴学、培养人才尤为重视。在范仲淹积极主张下,庆历四年“诏天下建郡县之学,傅岁贡群士,一由此出”[9](195)。同时,范仲淹主张以“六经”教导诸生,注重义理,从而使宋学有别于秦汉儒学,具有了自身的独特“义理”色彩。第三,整顿纲纪,提振士风。由于北宋“三冗”问题导致出官僚队伍的“百职不修、纲纪废坏”。范仲淹则每愤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为社稷计,从而使“士大夫矫厉尚风节”,并开出一代新的士风。所以,漆侠说:“范仲淹不仅能振作士风,使他们知道应当做些什么,而且还率领士大夫通过文风、学风的变革,走上政风的变革——庆历新政。而政风的变革,是实现儒生们‘内圣外王之道’理想的惟一道路!”[8](303)时隔二十六年,为了挽救北宋王朝的经济、政治危机,王安石毅然决然地高举了变法的大旗,成了“第二个要奋起改革当时政治的人物”[10](16)。而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他也是一个主张彻底的改革人物,朱熹的改革则是通过哲学、道德和文化的进步最终使社会发生彻底的转变,同样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可见,“不仅是原始儒教的复苏,而且也涵摄了佛教的积极精神”[11](10)的“心忧天下”新风范,“是中华民族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凭藉,激励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12](4)。如:司马光通达古今、鉴戒当世的“史学经世”的自觉意识;东林书院人物“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豪情;王守仁承继陆氏心学,平定江西宁王朱哀壕叛乱、平息广西少数民族暴动的事功业绩;刘宗周坚守理想和节操、以死殉节的忠贞;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13](757)的呐喊;梁启超“现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14](5425)的壮志和对“少年强则中国强”[14](411)的期盼,凡此等等,无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延伸,时时刻刻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鲁迅先生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5](118)“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价值取向成为了挺起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百压不垮的民族脊梁的精神支持。
三、以“康国济民”构筑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
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凸显了他们经世致用、康国济民理念。他们对国家社会利益的关注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意识的形成,传递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正能量。
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意识,其实质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宋代士大夫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意识的形成,原因如下:第一,士大夫的感恩心态。宋代教育的发达和科举制的完善,造就了出身寒门而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在整个士大夫阶层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以至形成了与贵族士大夫阶层相抗衡的力量,这也就使他们个人的命运、自身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并取得了基本的一致。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热情,他们以极强的感恩心态,担当起“康国济民”的大任。第二,士大夫的恐惧心理。经济上,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导致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程度加深;政治上,官场斗争的复杂性使士大夫们常常遭到被贬的情况,范仲淹、苏轼饱受其苦。今日在朝有富贵,明朝被贬伴贫寒。经济、政治地位的不稳定给士大夫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恐惧。他们明确认识到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不得不首先关心王朝的利益,并自觉地置国家和阶级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在这两种心理的交互作用下,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担当天下”的政治信念。第三,宋代学派政治化的影响。宋代社会学派的出现和形成表明,理学家一方面以极强的批判精神批判墨守成规的章句之学、异端的佛学和华而不实的骈文,并在批判中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理学家的思想分歧、对立又从属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思想分歧、斗争就是明证,但是,学术上的争论和学派的斗争并没有离开如何更好地为维护国家社稷利益这个基点。
细观历史可以看出,宋之前由科举入仕的人很快就转化为新的士族,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个人的显达,即使以陈子昂、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士大夫具有以天下“治平”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但他们的所做所为,一般只具个体性,从整体上考察,唐代士大夫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社会群体意识。”[16](31)而宋代士大夫的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群体意识则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得多。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得君行道”的人皆能躬身践行,以经世致用为旨积极进行富国强兵的社会变革,就是“未曾得君行道”的如李觏等,却也能“诵孔子、孟子群圣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17](296),为庆历新政提供理论支持。他们的行为,“绝不仅仅代表这个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广泛利益;他们试图通过变革,以维护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8](298)士大夫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首位的群体意识,突显出经世致用、康国济民的时代特色,传递了着爱国主义的正能量,从而构筑起他们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家园。
四、以清官政治彰显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
宋代士大夫由“士而仕”政治理想的实现,使他们把道德修养和个体的人格完善提高到了首位,在践行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过程中,他们不仅树立了入仕的清官意识,更为后世树立起清官这一理想政治的人格典范,并成为了政治伦理生活的范导。
清官的政治品行以清正廉明为特征,其人格力量又以“青天”而彰显,是儒家“仁者爱人”“民为邦本”和“自任以天下为重”思想在官场上的体现,凸显出儒家之道德理性。宋代士大夫入仕,如周敦颐官小职微,作风精细严毅,廉洁自律,为人称道;范仲淹“清心做官,莫营私利”[9](658);张载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其他如程颖、程颐、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皆能恪守道德自律,为官清廉、关注民生、秉公执法。而在众多的宋代清官行列中,包拯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是政治伦理生活中的楷模。
包拯为官二十余载,以“孝忠、清廉、公正”闻名于世。包拯进士及第后,曾“孝于亲”而“十年亡宦”,“已而还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洁”,委以重任,包拯则“上裨帝阙,下疗民病,中塞国蠹,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极乎是,必乎听而后已。其心亦无他,止知忠于君而为得也。”[18](329)包拯的“孝忠”由此可见。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18](270),为官端州,“岁满不持一砚归”[18](274),清正廉洁。同时,包拯主张严明纲纪、惩治贪官。他明确指出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18](230)并立《家训》告诫子孙:“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18](263)这与他的“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志向是相吻合的。包拯为官公正,不循私情。“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18](332),主张“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18](98)据此,包拯得到后世的普遍赞誉。朱熹评价说,包拯“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3](260)由此可见包拯的“凛凛然有不可夺之节”[18](279)的浩然正气。吴奎在包拯《墓志铭》中也说:“宋有劲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18](274),“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18](330)包拯为官虽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轰烈之举,但其在其职也曾提出了诸多的改革建议,并上《七事》疏中,希望仁宗能“参举众善,思而行之”。可见,包拯不仅为当世也为后世均树立起“清官”的光辉形象和理想政治的人格典范,影响深远,海瑞就是包拯精神影响的直接结果。
在历史长河里,忠君爱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兴利除弊、为民请命的清官,虽凤毛麟角但也代不乏人。清官作为理想政治的人格典范,承载了人们对一个社会的政治清明与安定的重托和希望,“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已生存希望的象征”[19](178),彰显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格典范。
五、以“希圣希贤”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旗帜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追求,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特质,凸显出它对社会道德生活的精神引领作用。
宋代理学家在吸收佛家成佛、道家成仙的终极价值理想和修炼功夫的基础上,提出了儒教成圣成贤的人生目标,以期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理学先驱周敦颐首先提出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20](95)的人格理想追求,从而为理学家乃至整个社会指出了一个精神方向。同时,周敦颐还为理学家指出了“寻孔颜乐处”的道德境界引领。周敦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20](112)在周敦颐看来,虽然富与贵是人之所爱、人之所求,但是,人更应该要有超越物质欲求的思想境界,这就是“小”与“大”的区别。颜子学道“见其大而忘其小”,说明颜子已经达到了一种超乎富贵的“泰然”的人生境界。《论语》也记,孔子对颜回不为生活贫困所扰,于学道中追求内心的快乐表示赞叹。因此,周敦颐令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把“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20](124)。周敦颐的“寻孔颜乐处”以及胡瑗的“颜子所好何学”考问,虽然不能等同,但其主旨意是相通的,都是指出了一条“学作圣人”的道路。因此,理学家以“无欲故静”可达“中正仁义”的为修养指向。周敦颐主“静”以修身,程颢主张“涵养须用敬”,朱熹也是主以敬为修养身心之根本,他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21](210)并指出孔颜之乐实际上就是一种圣人之乐,要寻得或体验到孔颜之乐的境界,“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21](796)理学家在“无欲故静”可达“中正仁义”的修养方向指引下,构建了一套“穷理尽性”“去欲存理”的修养功夫,并按照德性原则来实现道德上自我完善,以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这是“圣传之枢要,学者之途辙”[20](211)。在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以立足个人成圣成贤的道德追求和终极关怀是宋代理学家的共同价值取向。正如现代新儒家学者陈来指出的那样,周敦颐“寻孔颜乐处的思想使古代儒家以博施济众和克己复礼为内容的仁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对后来理学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36)。
总之,以道德为本位和道德高标的宋代道德理想主义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对历史的影响也是多层面而且是深远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如果说汉唐是充满英雄主义精神与自信的时代,那么有宋一代就是充满道德理想主义的时代,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后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的凝聚。直至今天,它仍然是挺起了民族脊梁的精神力量,是实现民族复兴、共筑美丽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和精神旗帜。
[1]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2]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陈金生, 梁运华点校, 全祖望补修.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 朱熹. 朱子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4] 周敦颐. 周子通书[M]. 徐洪兴导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5] 张载. 张载集[M]. 章锡琛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 欧阳修. 新五代史[M]. 徐无党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 欧阳永叔. 欧阳修全集[M]. 北京: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8] 漆侠. 宋学的发展与演变[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9]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李勇先, 王蓉贵校点.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10] 钱穆. 宋明理学概述[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1]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12] 陈来. 宋明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3] 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4]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5]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16] 郭学信. 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17] 李觏. 李觏集[M]. 王国轩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8] 包拯. 包拯集[M]. 杨国宜校注.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19] 王子今. 权力的黑光[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20] 周敦颐. 周濂溪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2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Historical influence and construction of idealism in Song Dynasty
LAI Jingyang, WANG Zey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ic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The moral idealism of Song Dynasty is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influence on history but also a kind of spiritual kernel. It’s founded on “the study of temperament”, prefabricat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by “Worrying about the world” as its value,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spiritual home, taking honest politicians as role models and fluttering the flag “seeking nobility”. Until today, it is still the national backbone of spiritual power, the spiritual support and the flag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Song Dynasty; moral idealism; the study of temperament; backbone of spiritual power; role models; spiritual home
B82
A
1672-3104(2014)06-0051-06
[编辑:颜关明]
2014-02-18;
2014-10-25
赖井洋(1964-),男,广东南雄人,韶关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思想史;王泽应(1956-),男,湖南祁东人,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伦理文化,中国伦理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