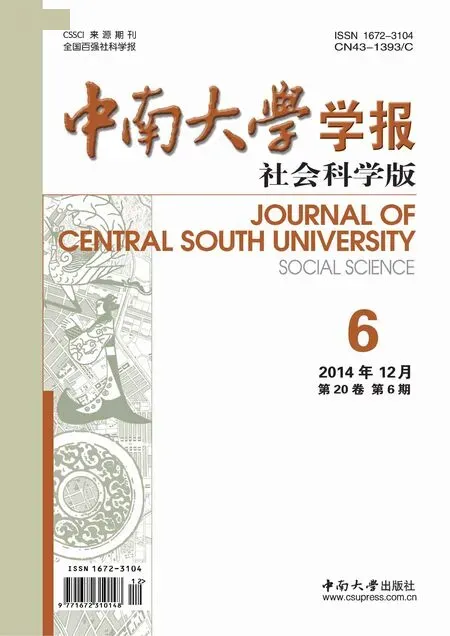巴克特里亚与希腊化的佛教
——以《那先比丘经》为中心
许潇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巴克特里亚与希腊化的佛教
——以《那先比丘经》为中心
许潇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流行,原因在于其一定程度上的希腊化,或者说是传播方式上一定程度的希腊化。《那先比丘经》的流传即反映了这一情况。作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沾弥利望群和弥兰王并不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具有多么高明的佛教智慧而心悦诚服,而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内容与古希腊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弥兰王所接受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反映出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在巴克特里亚所出现的一种多重向度、错综复杂的融合情况。
巴克特里亚;《那先比丘经》;弥兰王;佛教哲学;希腊哲学
佛教说一切有部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受希腊哲学影响较大。这也奠定了其思想特色:兼具印度哲学和希腊哲学之特点。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流行,原因就在于佛教一定程度上的希腊化,或者说是佛教传播方式上一定程度的希腊化,《那先比丘经》的流传即反映了这一情况。
《那先比丘经》在南传巴利文大藏经中叫做《弥兰王问经》或《弥兰陀王所问经》,在缅甸版巴利三藏位于《经藏·小部》中,而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版本中属于巴利藏外文献。学界普遍认为其文本大约产生在公元前后,而其所记录的事件则可以肯定要更早[1](330)。由于南传巴利文《弥兰王问经》的成书时间较晚,且从内容上看来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史实不太相符,因此本文主要以汉译《那先比丘经》为中心展开讨论。
一、巴克特里亚与弥兰王
“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葱岭以西的阿富汗东北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的称呼。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总督迪奥多图斯一世脱离了塞琉古王国宣布独立,建立起了巴克特里亚王国,中国古代称之为“大夏”。巴克特里亚的繁荣源于东西方贸易,巴克特里亚地处东西方商道的中心环节,加上巴克特里亚希腊人乐于保持他们同地中海世界的联系,这使得巴克特里亚的中介商业十分发达。
公元前二世纪初,弥兰王入侵印度西北部,而后巴克特里亚王国逐步分裂为几个部分,弥兰王所统治的版图包括巴克特里亚的西部和印度北部,以西亚尔科特(Sagala)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很多学者对弥兰王的首都是西亚尔科特持怀疑态度。《那先比丘经》称弥兰王为沙竭国国王[2](695),沙竭应为Sagala的音译。古代常以都城作为国家的代称,因此从《那先比丘经》的这一记载我们可以断定,弥兰王统治下的巴克特里亚的首都应该可以确定是西亚尔科特(Sagala)。
《那先比丘经》主要记录了巴克特里亚(沙竭国)弥兰王与那先比丘之间的对话。《那先比丘经》卷下有这样一段话:“那先比丘问王:‘王本生何国?’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2](702)这其中的阿荔散,巴利文Alisanda。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其指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也有学者认为阿荔散可能指中亚或高加索一带的亚历山大城。当时各地区的亚历山大城大都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建筑的,这反映出弥兰王的家族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有直接关系。弥兰王的祖先是希腊——马其顿军事贵族,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而后定居于东方。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瓦解,亚历山大的著名将领塞琉古在帝国的亚洲地区建立了塞琉古王国。到了公元前3世纪,随着塞琉古王国中央权力的衰落,弥兰王的祖先在东方建立起了希腊化的王国。
二、《那先比丘经》中“存在”与“存在者”关系辨析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有学者认为那先比丘和弥兰王之间的问答反应出当时佛教和希腊文化各自的思维特点。如蒲长春先生就认为,“那先比丘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方式和佛教的逻辑紧密相关;而弥兰王从逻辑角度的诘问则与希腊哲学的思辨特点遥相呼应。”[3]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是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史实:在《那先比丘经》文本产生之前,包括佛教哲学在内的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早已有了近300年的交流,即便是在《那先比丘经》中所叙述的对话发生的时代,印度文化也与希腊文化发生了近150年的交流。基于上述史实,笔者认为简单地将那先比丘的论证归结为佛教的逻辑,将弥兰王的诘问归结为希腊哲学是不科学的。事实上,《那先比丘经》中也谈到:“弥兰少小好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异道人无能胜者。”[4](695)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弥兰王的知识基础并不是完全来源于希腊哲学,他对印度哲学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
而从那先比丘与弥兰王的问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那先比丘的精神助产术似的追问以及破析与合聚的认识方法都并非基于佛教哲学或印度哲学。例如:“合聚头、面、目、耳、鼻、口、颈、项、肩、臂、骨、肉、手、足、肺、肝、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为一人。”[4](696)这种破析与合聚的方法看起来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既没有把“人”分解作“五阴”,也没提及“人”是“五阴”的假和合[5](414)。这就与佛教的观点相距甚远而与古希腊自然主义哲学十分相似。又如,那先比丘在与沾弥利望群的讨论中说到:“如人心有所念者舌为之言是为舌事,意有所疑心念之是为心事,各有所主,视之虚空,无有那先。”[4](696)“有”是佛教说一切有部哲学的基础,是其与其他部派以及大乘佛教的重要区别。“有”即是实有、存有,而“各有所主”则是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原因和根据。那么“主”的含义又是什么呢?经文中已有明言,“如人心有所念者,舌为之言,是为舌事,意有所疑,心念之,是为心事”。可以肯定“主”并不是一而是多,否则“各有所主”就无法实现。因此,不可以把“主”理解为“主宰”,因为主宰必然不能是多。从存在者得以存在这个角度出发不难发现,“各有所主”是物对其主的占有而得以存在,这就具有一种被包含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意思。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总是意味着是某个东西。因此,所有的存在物都是各别的,都有着特定的本质①。从这个角度看来,《那先比丘经》中的“主”应是存在物特定的本质。
这和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实是之所以为实是”②有异曲同工之妙。亚里士多德认为,“惟巴门尼德在好多方面颇有精义。他宣称‘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6](15)存在与存在者的问题是从巴门尼德到现在的西方哲学一直不断讨论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思想与事物存在的方式有着关联,而这突出了逻辑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思想总是关涉某些特定的个别事物的,即一个实体的。但是一个东西绝非简单地存在;它总是以某种如何以及某种为什么而存在。
《那先比丘经》中有这样一段记录:“那先便与野惒罗八十沙门共行。沾弥利望群旦欲入城时,于道中并问那先。往曰对王言,无有那先。”[4](696)这是那先比丘前往弥兰王宫殿时沾弥利望群向那先比丘发问并展开讨论的一个情况。经文在南传巴利文中题名曰《弥兰王所问经》,而此处却有沾弥利望群和那先比丘的对话,这样一个插曲并不是偶然。沾弥利望群率先发问的是那先比丘的存在问题,那先比丘必须是存在的才能成为谈论的对象。而那先比丘的回答“如人心有所念者舌为之言是为舌事,意有所疑心念之是为心事,各有所主,视之虚空,无有那先”则与早期佛教的观点有着一定的差异。那先比丘回答的内在逻辑理路是:先通过破析“那先”来排除错误的答案,逐步把握认识的对象,然后再通过综合来建构一个新的合乎逻辑的答案。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有”和“主”。作为存在者的那先比丘是通过“主”而“有那先”的,通过“主”而成为存在者。存在者之所以能够存在,关键是各有所主,如果忽视了“主”,存在者就无法存在。解决了作为存在者而存在的那先比丘,谈话才有可能继续进行。而沾弥利望群也因此心悦诚服,受五戒,作优婆塞。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希腊人的沾弥利望群并不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具有多么高明的佛教智慧而心悦诚服,恰恰相反,是因为那先比丘的回答乃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这使得沾弥利望群更易接受。
三、弥兰王对佛教的接受
事实上不仅仅是沾弥利望群,弥兰王也是如此。弥兰王的王国虽然远在东方,而他的学识、思想和事迹却是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所熟知。甚至是普鲁塔克都在其《治国箴言》中写到:“当时有一位名叫弥兰的巴克特里亚的伟大的国王于军营中死去的时候,巴克特里亚的许多城市都照例为其举行葬礼。但这些城市之间在处理其骨灰时,引起了激烈的竞争。后来,它们艰难地达成协议,决定平分弥兰王的所有骨灰,分别将之带回本地,造碑纪念。”[7]弥兰王的学识、思想和事迹能够为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所熟知,可见他对希腊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我们回到《那先比丘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弥兰王之所以能够接受那先比丘,其原因与沾弥利望群接受那先比丘的原因是一样的。同样,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能够接受弥兰王的思想其原因就在于这两者思想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源性。而另一方面,我们更可以看到普鲁塔克《治国箴言》中所描述的弥兰王死后其治下各城市平分其骨灰,并带回本地造碑纪念这一事件与佛陀灭度以后八王分舍利的故事是如此地相似。相比较而言,显然普鲁塔克《治国箴言》中的记载要比《那先比丘经》中“弥兰少小好读经学异道,悉知异道经法,异道人无能胜者”这样的说法更加公允,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英国著名学者沃尔班克就认为:由于帕提亚人的崛起,割断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与希腊化生活主流的联系,为了对付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些地方的希腊人和当地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希腊化世界的同质性值得区别对待和认真思考[8]。在其专著《希腊化世界》中,沃尔班克承认希腊化世界的同质性或希腊性是存在的,但这只存在于希腊人的主流社会中,当地人士不可能进入这一社会的,除非他被希腊化[8]。但是,如上文所述,沃尔班克又认为巴克特里亚由于其军事政治上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成为一个特例。
作为希腊人的弥兰王接受佛教接受印度绝非个案,但是他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弥兰王作为国王反过来大大推动了佛教被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接受。而在《那先比丘经》中弥兰王与那先比丘的对话内容来看,弥兰王所接受的佛教又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这反映出了希腊文化与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一种多重向度、错综复杂的融合情况。
回到经文当中,弥兰王为什么会与那先比丘发生对话?这个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这种复杂的融合情况。《那先比丘经》记载弥兰王非常喜欢坐而论道,这种爱好乃是承袭了希腊智者们的论辩传统。弥兰王雄辩无敌,无人能胜。在他即位以后,迫切希望能够寻找与其论道之人。在那先比丘之前,沾弥利望群向他推荐了野惒罗。经中记载了弥兰王与野惒罗辩论的情况:
王傍臣名沾弥利望群白王言,然有沙门字野惒罗,明经道,能与王难经道。王便勅沾弥利望群即行往请野惒罗,言大王欲见大师。野惒罗言,王欲相见者,大善!王当自来耳,我不往。沾弥利望群即还白王如是。王即乘车与五百伎共行到寺中,与野惒罗相见。前相问讯就坐,五百骑从皆坐。王问野惒罗,卿用何等故弃家捐妻子,剃头须披袈裟作沙门?卿所求何等道?野惒罗言,我曹学佛道行中正,于今世得其福,于后世亦得其福用,是故我剃头须被袈裟作沙门。王问野惒罗,若有白衣居家,有妻子行中正,于今世得其福,于后世亦得其福不?野惒罗言,白衣居家有妻子行中正,于今世得其福,于后世亦得其福。王言,卿空弃家捐妻子,剃头须被袈裟作沙门为。野惒罗默然无以报王。王傍臣白言,是沙门大明达有智者,迫促不及言耳。王傍臣皆举手言,王得胜。野惒罗默然受负[4](696)。
经文中的记载当然有衬托那先比丘智慧的意思,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信息非常丰富。这样的对话形式很容易让人想到苏格拉底,他总是发问,而不回答。从对话的内容上来看,野惒罗的回答属于典型的佛教思维方式。弥兰王和其周围的巴克特里亚希腊贵族们并不满意野惒罗的回答。
随后,沾弥利望群向弥兰王推荐了那先比丘。我们注意到,弥兰王第一次见到那先比丘时首先问到的问题就是那先比丘是谁的问题。这与后来沾弥利望群首先问起的问题是一样的,同样关注的是那先比丘的存在问题。这是因为,那先比丘必须是存在的才能成为谈论的对象。那先比丘的回答较野惒罗的回答更具苏格拉底式的风格。那先比丘并不急于回答,而是先巧妙地回避了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分析,逐一排除。然后在否定了所有的不完善的答案之后合聚而得到一个让弥兰王满意的答案。事实上,那先比丘“合聚头、面、目、耳、鼻、口、颈、项、臂、骨、肉、手、足、肺、肝、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为一人”的答案并没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性,也谈不上多么高明,但是这样的讨论方式却是弥兰王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因此,“王言,善哉善哉。”[4](696)
在弥兰王解决了谈论对象的存在问题以后,那先比丘确立了难经说道的方式:“如使王作智者问,能相答王。作王者问、愚者问,不能相答。王言,智者问、王者问、愚者问何等类?那先言,智者语对相诘相上语相下语,语有胜负则自知,是为智者语。王者语自放恣,敢有违戾不如王言者,王即强诛罚之,是为王者语。愚者语,语长不能自知,语短不能自知,悷自用得胜而已,是为愚者语。”[4](696)弥兰王对这样的论道方式是十分熟悉的,欣然接受了那先比丘确立的方式。
接下来,那先比丘与弥兰王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刻地讨论。讨论的话题涉及到生命观、善恶观、形神观、地狱观、世界观、涅槃观、净土观等等。那先比丘以深入浅出的理论和形象生动的比喻将佛教的许多核心问题以弥兰王能够接受的方式阐明。当然,在讨论中也不乏希腊因素甚至是中国因素[9]。
在讨论中,那先比丘的很多回答都与早期佛教的观点相左,反而大量吸收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比如在论及“智”这个问题时,那先比丘的回答就与柏拉图《美诺篇》中所载的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美德即善”的命题非常类似。《那先比丘经》卷上载:“王复问那先,何等为智。那先言,前已对王说,是人智断诸疑、明诸善。那先言,譬如持灯火入冥中室,便亡其冥自明,人智如是。那先言,譬若人持利刀截木,人以智截诸恶如是。那先言,人于世间智最为第一,度脱人生死之道。王言,善哉善哉,前后所说经种种智善也。”[4](698)佛教所讲的智,指的是分别世间诸法,观察一切诸法之实相。佛教讲智分为三种: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早期佛教所讲的智一般指的是一切智。《大智度论》曰:“声闻、辟支佛虽于别相有分而不能尽知,故总相受名。”[10]而那先比丘所言断诸疑、明诸善与此相比显然有一定的差异。在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当中,苏格拉底强调“德行可教”,苏格拉底在与美诺的讨论当中得出“美德需要教育”的命题。而在那先比丘与弥兰王的讨论善的过程中,“精进”成为他们所讨论的核心。那先比丘对精进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助善是为精进。”[4](697)并且,那先比丘还认为,“诚信、孝顺、精进、念善、一心、智慧是为善事。”[4](697)那先比丘特别强调诚信,信有佛、信法、信僧。从诚信出发,那先比丘提出了其佛教教育理念,而这一整套佛教教育的目的则是获得智,使人断诸疑、明诸善。可以看出,那先比丘的佛教教育理念都与苏格拉底的美德教育惊人地相似。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弥兰王与那先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占去了很大的篇幅。
四、希腊化的佛教及其影响
上文已经讲到,佛教说一切有部草创于公元前2世纪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由于军事政治上被帕提亚人的崛起割裂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与希腊化生活的主流的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希腊文化和当地文化的融合成为可能。巴克特里亚希腊贵族政治上出于统治需要,采取了与佛教联合的政策。而另一方面,佛教亦需要借助巴克特里亚希腊贵族的支持,所以自身也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希腊化运动。从浅层次上来说,那先比丘的论道方式是易于被弥兰王所接受的。而深层次上,说一切有部在许多方面吸收和借鉴了希腊哲学的成分,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思想特征。杜继文先生就将此总结为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确立唯智主义的原则;第二,确立破析与和合的思维方法;第三,确立“无我”而有“业报”的根本观念[5](413)。
在以弥兰王为代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贵族的支持之下,说一切有部得以快速发展,影响遍及包括南亚西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而到了大约公元前1世纪以后,在贵霜帝国的支持之下,说一切有部再一次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一时期论师辈出、思想活跃,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而这都是在佛教说一切有部希腊化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在思想文化以外,希腊化佛教的流行还在中亚和西域地区产生了辉煌灿烂的犍陀罗艺术。
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带有很明显的希腊哲学的印迹,其最主要的三个特征都与其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密不可分。这是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发生在中亚和南亚北部地区伟大交融的结果,它深刻地影响了佛教哲学的发展脉络。甚至大乘佛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对说一切有部哲学体系的继承与扬弃中形成与发展的。
注释: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范畴篇》[M]. 方书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第16页:“所有的实体看起来都表示‘某一个东西’。在第一性实体里,无可争辩地这乃是真的,因为所有表示的那个东西是一个单一性的东西。”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应书馆,1959,第56页。吴寿彭先生译注:这里的“实是”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动字,意谓“是”或“存在”。凡“物”各为其“是”,各“有”其所“是”。故“是”为物质“本体”。
参考文献:
[1] Warder A K.Indian Buddhism[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0.
[2] 那先比丘经卷下[C]// 大正藏·第32卷.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3] 蒲长春. 佛教和希腊文化的相遇——论《那先比丘经》的问答方式[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7(5): 65-71.
[4] 那先比丘经·卷上[C]// 大正藏·第32卷.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5] 杜继文. 汉译佛教经典哲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6]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北京: 商务应书馆, 1959.
[7] 普鲁塔克. 治国箴言[C]// 罗伊布古典丛书.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6: 821.
[8] 杨巨平. 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J]. 世界历史, 2011(6): 119-130.
[9] 张思齐. 《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和中国因素[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55-63.
[10] 大智度论[C]// 大正藏·第25卷.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3: 259.
Bactria and the Hellenistic Buddhism——centered with theMilinda-pa ha
XU Xiao
(Religious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Buddhism was popular in the Hellenistic Bactria, its reason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the Hellenistic, or its spread on the degree of the hellenistic.Milinda-pa haresponded to this situation, just as what Bactria Greek with Mili hope group and Milinda belived not because of Nagasena replied with a clever Buddhist wisdom and expressed a heartfelt admiration, on the contrary, because Nagasena replied and inherited the thought of Aristotle’s Philosophy. Milinda accepted Buddhism with a strong color of the Greek philosophy. This reflects the Greek culture and India culture, Buddhism culture in Bactria in a multiple dimension and perplexing fusion.
Bactria;Milinda-pa ha; Milinda; Buddhism philosophy; Greek philosophy
B94
A
1672-3104(2014)06-0021-05
[编辑: 颜关明]
2014-02-22;
2014-10-22
许潇(1988-),男,陕西安康人,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佛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