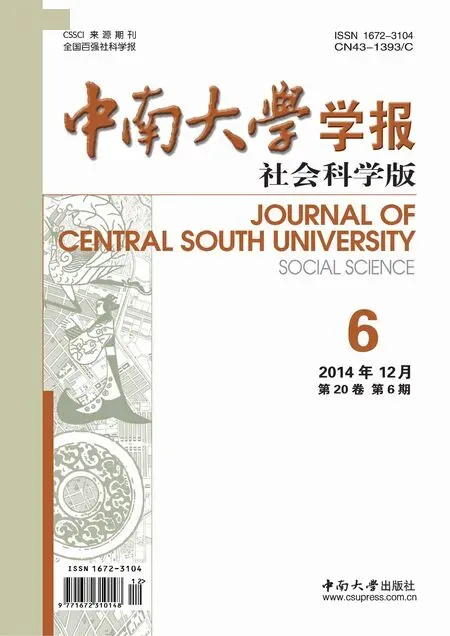“怵惕之心”何以不是“仁之端”
——孟子同情理论的内在逻辑
陆畅
(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怵惕之心”何以不是“仁之端”
——孟子同情理论的内在逻辑
陆畅
(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孟子在阐述同情理论时说“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在归纳“仁之端”时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并未将“怵惕”算上,这是有深意的。怵惕恐惧、怀生畏死,是主体以自身的主观构境设身处地想象他者痛苦并产生同情恻隐之情的前提,是刺激良知并使其呈露的必要条件。“圣人”虽然“不动心”,不为痛苦困扰,但对他者的同情依然要建立在对死亡的恐惧与担忧之上,只是这种恐惧怵惕是对全体生命之有限性的觉察与悲悯,是为他者害怕与担忧。
孟子;同情理论;内在逻辑;怵惕之心;恻隐之心;意识构境
孟子同情理论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它不仅在道德形而上学意义上被用于与康德自律伦理的比较,在伦理学意义上参与中西同情、仁慈伦理的对话,更在现象学意义上被赋予生存论意涵。然而,在不同的哲学语境下对孟子同情理论的多维度解读,是建立在直接将“恻隐之心”视作同情理论的核心涵义基础上的。对其中恻隐之心是如何由怵惕生出,怵惕何以不与恻隐并列为“仁之端”等问题,学界则有所忽视,而这些问题正是孟子同情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借“怵惕”一词对孟子同情理论的内在逻辑做一番探究,以见正于大方。
一
孟子同情理论集中表现在他的“四端”之说中,尤其是“四端”之首的“仁之端”。孟子曰: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79-80)。
人乍见孺子入井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此心不依赖于经验世界的功利主义而独立存在,是“我所固有,非由外铄”的良心、本心。孺子将入于井,在旁观者看来这种状态如果不得到有效制止的话,接续而来的将会是孺子掉入井中,导致死亡。我们通过想象置身于他人的情境中所能得到的反应,来感受对方的痛苦,从而产生同情与怜悯。但孺子匍匐将入井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是好奇与快乐,并未产生痛苦,旁观者觉察到的危险只是建立在自己经验之上的先行想象。也就是说,孺子的心理反应只是在旁观者意识结构中的应然状态,孺子只是想象中的旁观者自我。孺子作为旁观者主体构境中的对象,与旁观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不是并列对立的交互主体。因此,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主体通过情境想象所感受到的情感是自己的情感还是对象的情感?旁观者感受到的危险对没有此类经验的孺子来说是虚构的,旁观者与孺子的情感发生断裂与冲突,那么所谓的“同情”,是与谁的情感相同呢?胡塞尔认为,“怜悯并不意味着与他者遭受同样之苦,而是(意味着)怜悯他,为他在受苦而受苦,因他在受苦而受苦。”但他同时又认为,“我们的怜悯只是间接指向他者受苦的同一个对象。当我怜悯丧父的他者时,我并未直接经受他的丧父之痛,而是因为他者丧父这一事实而受苦。”[2]前者是说,主体因为对象表现出痛苦的状态这一事实而产生同情,与其所以痛苦的内容无关;后者则是通过其痛苦的事实,寻找到所以致其痛苦的原因,然后通过想象自己身处于他的情境中来感受所能感受到的情感体验。旁观者对孺子之同情则是在后者意义上讲的,因为孺子自己并未有痛苦的表现,同情并非因为孺子痛苦而产生。同样的例子亦见于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程颢云:“‘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3](135)“不堪其忧”之“其”,乃众人自设也;“不改其乐”之“其”,乃颜回自谓也。众人之忧是设身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情境中产生的情感,而颜回自己则欢乐始终,不为贫贱忧戚所动,在这个过程中,众人之情感与对象颜回本身情感并不一致。众人通过颜回的处境来想象应然的情感状态,这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讲的。而齐宣王见牛之觳觫而生不忍之心,则是在前者意义上讲的,齐宣王对牛觳觫发抖这个事实作痛苦、恐惧的理解,并未进入到牛的意识中来理解牛何以觳觫。牛之发抖,或许因疯牛病而引起的也未可知[4]。瑞士学者耿宁对这两者涵义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为他者受苦而苦、因他者受苦而苦这一事实’,包含着一种对他者感情与感觉的反思性的当下化,而为他者不幸处境而苦,在现象学上则更为自发、更为原初,在其意识结构之中也更为直接。”[5]耿宁认为,因对象的痛苦而产生的同情体现了情感反思的当下与直接,而探究其痛苦之所以然而在想象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其痛苦则更为原初与直接。想象,是联接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枢纽,它根据主体的经验、记忆来完成自我虚拟的过程。它是如此的自我,以致无法照顾到对象本身在情境中的反应。
事实上,不论哪种意义上的同情,都是主体意识构境的产物。齐宣王由牛之觳觫而得知其恐惧死亡,无非是自我意识强加于牛的产物,亦即,他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转移到牛身上。庄子与惠施辩论知鱼之乐的问题,是说明意识构境单向性的最好例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6]
也许用“同感”比用“同情”更为合适庄子的语境,因为与鱼同感不涉及道德问题。庄子通过“出游从容”断定儵鱼是快乐的,乃源于他对鱼做拟人化的处理,并将“从容者必乐”的人生经验,反用之于儵鱼。庄子所感知鱼之乐其实是自己意识构境的呈象,他将自己想象为自由自在的儵鱼,来感受其中之乐,而并非“以此合彼”式地与鱼的感情保持相同。儵鱼本身快乐与否不可得知,或许鱼在与水相融无间的状态中并不能产生快乐之情感,而只有处于“鱼脱于渊”这种情境时,才能通过痛苦反向体会到快乐。在庄子看来,我能够感知鱼的情感,乃在于我与鱼有共同的联结点——气,所谓“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一气相通,使主体注入式的理解与联想得以可能。庄子感受鱼之乐,并不属于道德同情,何也?因为对象的生生之气没有遭到破坏,激发不出主体的怵惕之感。换句话说,在孟子理论中,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主体是否真的理解孺子或牛的当下感受从而产生同情,而在于主体对死亡的恐惧是道德同情的必要条件。这种恐惧之感表现在旁观者的怵惕与齐宣王在牛之觳觫暗示下对死亡的惊恐。
怵惕,《说文》云:“怵,恐也。惕,敬也。”《广雅》云:“怵惕,恐惧也。”怵惕,是对外物尤其是死亡出乎本能的恐惧之感。戴震说:“己知怀生而畏死,故怵惕于孺子之危,恻隐于孺子之死;使无怀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恻隐之心?推之羞恶辞让是非,亦然。”[7]由于存在着怀生畏死之心,我们对孺子将入井而死总是有种恐惧之感,但问题是,本能的恐惧如何转化为道德同情呢?亦即,怵惕如何过渡到恻隐呢?恻隐,《说文》云:“恻,痛也。从心,则声。”《广雅》:“恻,悲也。”“恻”,表示悲痛之意。《说文》言其意“从心”,可知悲痛并非单指肉体上对刺激的感知,而还应包括情感上的哀伤。“隐”,意思与“恻”相同,《孟子·梁惠王上》:“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隐”,赵岐注:“痛也。”怵惕到恻隐,是由本能恐惧到情感上悲痛、哀伤,这是一个由身体气质到道德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可能,乃在于自我与他者既相同又相异的关系。一方面,自我与他者在气上相同相通,故会产生对同类死亡的恐惧,唯恐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自我与他者又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这样才能紧接着怵惕产生恻隐。一个人不会对自己产生同情,当自己遭受痛苦与毁灭时,所产生的只能是怵惕恐惧而不是同情。同情只有当痛苦发生在异质性的他者身上时才成为可能。职是之故,孟子在归纳“仁之端”时将“怵惕”排除在外,因为那是属于身体气质方面的自然反应,而不是像“恻隐之心”一样属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中产生的道德自觉。
二
道德同情之产生需要身体、气质上的刺激。身体由气构成,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存在,当这个“生意”中断或受到刺激时,才会产生同情。我们在同情地觉知他者正面的感情如欢乐、喜悦等时,会随他者一起欢乐,如庄子知鱼之乐,其中的“同情”(或同感)并无道德意涵。而只有对那些负面情感如怒、哀、惧、痛苦在他者身上发生时,才会产生道德同情,因为这些负面情感显示的是个体生命生生不息状态的中断。天地大化流行,万物生生不已,牛山之木虽被砍伐亦有萌蘖生焉,“原泉混混,不舍昼夜”。在顺从生命畅遂的生机状态中,我们是感受到的是“乐”“安”等正面积极的情感,而当这个过程突然中止,对象会在主体的“注意”下涌现出来。朱子云:“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8](1691)孺子将入于井,意味着生命即将毁灭;牛之将用于祭祀而觳觫,意味着“生意”即将被伤,因此才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程明道曰:“切脉最可体仁。”[3](59)切脉,按压住脉搏阻止血液正常不息的流动,所以能察知脉象如何。明道用切脉来“体贴”仁,意味着仁需要通过阻断其生意才能察知其存在。
怵惕,就是“生意”被破坏时主体产生的“注意”之状。身体在正常状态下,我们并不意识到它的存在,与己如此相合与上手,乃不知有身,而一旦身体某部分受到刺激或疼痛,我们便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地方,时刻警觉其存在。不独身体,心亦然。怵惕,是心被外物刺激而产生警觉的必要条件。在浑浑噩噩的日常状态的生活中,我们是感受不到自己本心的,所谓“放其心而不知求”也。“鸡犬放则知求”,是因为将鸡犬视作自己的一部分,其丢失则直接刺激到自己的生存状态(鸡犬在一般农家财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而产生寻求的行为。心,没有被刺激,则“昏然”不将心与自己视为一体,又哪来寻求之说呢?故而,气质上的刺激能够使主体意识到刺激者与自己是浑然一体的,从而产生怜悯同情。程颢曾以不识痛痒来说不仁: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3](15)。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3](33)。
手足麻痹者,对痛痒无所知觉,不论如何刺激都没效果,何谈后续的治疗?因此,首先要保证使气贯通(自己与天地万物在气上为一体),对刺激有所反应,道德自觉才有表现自身的突破口。南宋诗人杨万里对孟子同情理论中由知痛痒到觉悯爱的过程发挥道:
隐也者,若有所痛也。恻也者,若有所悯也。痛则觉,觉则悯,悯则爱。人之手足痹而木者,则谓之不仁。盖方其痹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抶之而不恤,彼其非不爱四体也,无痛痒之可觉也。至于无疾之人,误而拔一发则百骸为之震,何也? 觉其痛也,觉其一发之痛则爱心生,不觉四体之痛则爱心息。[9](卷八十六)
知觉痛痒是在身体上说的,这是道德上觉悟的前提。也就是说,怵惕产生的恐惧之感不仅仅在心灵上引起震动,在身体上也有所反应[10]。事实上,孟子在讨论道德超越性与自觉性时,从未离开过身体气质而悬空地讲道德,相反,身体气质对超越性道德呈现自身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现实条件,这从他对“践形”的高度评价、对“性”的两层涵义的划分上即可看出。孟子以掩葬其亲为例,来说明内心不安可以通过身体变化表现出来:“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1](135)头上冒汗,不敢直视都是内心触动的外在显现。身体是在世的基础,也是与他者感通的前提,而彼此感通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气的一元共通性。《周易·乾卦·文言》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气之相同者可以互相感应。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1]这是将“气”作为所有存在者中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水火、草木、禽兽、人都由“气”构成。“气”可以生出万物,亦可以毁灭万物。气而成形,形而成物,气使万物成为有限的存在。庄子云:“其成也,毁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有限的存在,其存在于世即意味着具有可死性,而正是由于这种可死性,才造就了天地生生不息的景象与人生价值意义的追求。人的有限性使人对死亡有怵惕恐惧之心,怵惕与恐惧使主体意识到自己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生生之意的破坏与我心息息相关。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张载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程颢言“仁者浑然与万物为一体”,朱子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象山言“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阳明言“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都是天人一体的表现。这种一体当然不只是在道德价值层面讲的万物为人所价值化、意义化,亦是在气上的相互关联与感通。
人与万物在气上的感通无时不在,鸢飞于天,鱼跃于渊,万物生机畅茂通遂不只是主体心境的体现,亦是我与其气息相通之故。但在日常平均生活中,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种共通的,只有当气机受到阻逆之时,这种一体关联性才在主体的注意下展现出来。孟子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1](62)朱子注:“壹,专一也。蹶,颠踬也。趋,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专一,则气固从之;然气之所在专一,则志亦反为之动。如人颠踬趋走,则气专在是而反动其心焉。”[12]“气壹”是指全身之气与意专注集中于一处,其“动志”表现在怵惕之时,将对死亡之担忧与恐惧达至最大化,从而使心志变化,萌生恻隐。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15)儒家并不禁止食肉,但“见其生”与“闻其声”使得当下怵惕之心顿时集中于一处,气壹动志,从而不忍杀生。傅伟勋先生说:“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那一点点灵犀(良知良能)真实存在,才能引发人的道德自觉。这种自觉或醒悟在日常世界也许难于发现,但在生死交关的雅斯培(Jaspers)所云‘极限情况’格外明显。”[13]这里的“极限情况”就是“气壹”的另种说法,在这种“生死交关”的情形下,人脱离日常经验之干扰,回到“独”在的状态,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 这个“几希”良知为人所独有,这样才能解释何以禽兽同样对死亡有怵惕、恐惧之感而并不能产生同情恻隐之情。
三
孟子所言的怵惕恻隐之心是针对普通人而言的,每个人都先天普遍具有同情之可能性,同情的对象也全面普遍地向所有存在者开放,但他同时又强调,恻隐之心只是“仁之端”,只是仁在现实经验中表现出的开端,远未臻至完满。普通人受到挑激虽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理变化,表现为同情的行为,但并未有自觉的道德意识。齐宣王虽见牛觳觫而生不忍,但并不明白为何会生此心:“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1](15)直到孟子向他宣示同情的道理,他才“心有戚戚焉”,有所触动。片段式的“义袭而取”产生的同情在孟子看来并不可靠,他用普通人不假思虑当下产生的同情只是为了说明良心是所有人先天固有的本质,这并不代表良心不需要工夫修养而可以随时地自我呈露。孟子描述了普通人到圣、神之间不同境界的道德范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334)有恻隐之心但没有道德自觉的普通人只能算是有所“可欲”的善人,他们与圣人、神人有明显的不同。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普通人因为有怀生畏死之心,故能够对对象的挫折、阻逆、死亡产生怵惕恐惧、心有戚戚之感,从而产生道德同情,而圣人神人则超越名利、生死的困扰,达到“不动心”的境界,那么在他们那里还会有与普通人一样的道德同情吗?圣人有没有怵惕,若没有怵惕及其带来的震恐,气还会凝聚集中,带动心志的变化吗?
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易地而处的想象来体会他者的感受,替他者忧烦、悲痛、怜悯,但对于圣人来说,因系于外物而引起的忧烦、悲喜等情感都是“动心”的表现。依孟子,富贵、贫贱、威武固然不能摇夺其志,就算拜为齐国卿相、得行仁政之道亦不足以撼动此心,用程颢的话说,“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3](61)。也就是说,圣人感受到他人遭遇困苦刺激的时候,所能体会到的同情是自己以往困苦经验的当下回忆,在这种回忆想象中并不应有“动心”之情感的出现,若是这样,那么又如何能真切地与他者情感相同,体会到他者现下的心境呢?如若不能与他者保持情感一致,而依照自己的主观构境来审视对象的情感,则也应该表现为“不动心”,又哪来的恻隐之心呢?
这种情感上的紧张与吊诡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表现更为明显,他们一方面强调无心、无意、无情,一方面又强调对万物皆有恻隐之心,甚至对石头之纹裂亦有悲悯之感,这看似互相抵牾的两面是如何统一的呢?程颢云:“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3](460-461)他认为,圣人并非弃绝人世间的情感,而是不执着、不滞固于情感之发,无心、无情只是一种“虚”的遮诠的方法,而不会影响实理的正常开显呈露。事实上,明道“顺万物而无情”的情感是喜怒哀乐之情,与恻隐等道德情感并不相同。依照这种逻辑来分析圣人的同情产生过程时,我们会有以下二点发现:其一,圣人同样具有有限性特征,身体、情感、欲望等都是不可避免与不可毁灭的。因此,圣人对痛痒的知觉,就不是仅仅在理性层面的认知,亦当包括在身体与情感上的怵惕与震动。朱子认为,人在有限性方面与动物一样,都有知觉:“犬牛与人,皆有知觉,皆能运动,其性皆无以异矣。”不仅动物如此,甚至植物也有知觉,“如一盆花,得些水浇灌,便敷荣,若摧折他,便枯悴,谓之无知觉可乎?”[8](1430)但是知觉有高低层次之分,“鸟兽的知觉不如人底,草木的知觉又不如鸟兽底。”[8](1430)人的知觉不像动植物那样纯从气质的刺激反应上讲,而应包括道德上的感知:“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8](85)也就是说,不论如何从“知痛痒”“以觉训仁”来理解同情,这里的知与觉无疑都具有气质上的意涵。其二,“怀生畏死”既是人的本能,圣人亦当如此。孔孟固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训,但这是将仁义与死亡推至极限处,必须在二者中抉择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孟子云:“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1](301)可见轻身犯险,毁伤身体的做法并不为他所认可。人终究不是神,他兼具有限与无限的两面,通过智的直觉开启无限、超越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否定有限的一面。如若没有畏死之心,那么折柳伤春是如何刺激自我而形成悲悯的呢?张载言:“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14]颠连无告之所以引发我的同情,乃在于彼我一气相通,气的有限性必然体现在对死亡的畏惧上。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圣人的畏死,并非在通常意义上对一己人生的执着,对已有之物的贪恋,而是对宇宙、生命有限性的认识与悲感。“恻隐”一词本身具有悲痛之意,正昭示了这点。圣人的畏死是替全体有限的存在者担忧,畏惧万物生生不息气机的中断,而非畏惧自己肉体生命的消亡。当然,像见孺子将入井与见牛之觳觫等生死交关状态引起的同情在日常生活中是极少出现的,更多的同情是发自于生机遭受一定程度的阻扼,而非完全毁灭。
普通人同情的产生是刺激与反应的模式,是由怵惕引起的灵明乍现,它根源于小我对死亡的畏惧。圣人则站在对全体存在者有限性之悲感的高度对孺子将入井产生同情,对牛之觳觫产生怜悯,常人则没有这种道德自觉。物来挑激,是引发同情的必要条件,在圣人则是“感与应”的关系。程颐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3](152)物来感我,我以顺应之。这里的“我”是真我、本我,物之挑激促使本心开显,形成同情恻隐,它不仅仅是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更是在对本体感知体证之上的自觉呈显。常人的“感”则是小我的感,“应”也是小我对外物的感性直观,感应是在“气”上言的,这与圣人在“理”上言并不相同。“气”上的感应若无“理”作主宰则是心为物役,“物交物则引之”,心无主宰则同于一物,这是动心的表现,是所当超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同时也强调“动心忍性”,此处的心是在“理”上说的道德本心,与前面的“不动心”之心不同。“不动心”是摆脱经验中的知识、情感、欲望等对本心的干扰,是去除本体呈现之障碍的遮诠方法;“动心”则是通过贫贱忧戚、拂逆心志等事实来刺激本心良知的开显,是道德本体生生不已的表现。圣人具有无限智心,可以超越经验;同时又具有有限性,又要内在于经验世界,良知作用于经验世界表现为同情恻隐,就是这种内在超越性的表现。
所谓的内在性,是指同情的发显具有一定的事实指向性。一件事物能否引起恻隐,是否应当引起恻隐,这是由该事物在经验世界中的情状决定的。我们不会对他人的喜悦、快乐产生怜悯,而只会对他人悲惨的命运表示同情。即便圣人视喜怒悲欣为有对无常,一律以悲怀悯之,其间对喜悦与悲惨情况的不同亦不能不有所辨别,这是人具有的有限性决定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恶臭”与“好色”的事实指向决定了喜好与厌恶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圣人意识结构中的知识背景与判断能力对同情的发挥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孟子·万章上》举例道:子产命仆人将鱼放生,是不忍其就死地也,但仆人将鱼烹杀并谎称已放生,子产不知这一事实而说“得其所哉”,仆人因此嘲笑子产不智。此例中,子产的同情为虚假的事实所引导,从动机上看固然不错,但从整个过程及结果上看则属无效。良心本体显现于经验世界要通过情感、知识、意志三个向度展开,这三个维度在具体的行为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同情并非单一的情感表现,而是知识层面的事实判断、情感层面的怵惕悲怀、意志层面的道德自觉三个方面的综合。知识判断与情感上的怵惕凡圣皆有,程度深浅不一,圣人比普通人高明之处在于多了道德自觉与对有限世界的悲感,这正是理想状态下恻隐之心所当涵括的内涵。
[1]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 Husserl.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0 und 1924 [M]. Hagu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3]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4] 童建军, 马丽. “以羊易牛”与仁慈美德[J]. 道德与文明, 2013(4): 41-47.
[5] 耿宁. 孟子, 亚当·斯密与胡塞尔论同情与良知[J]. 世界哲学, 2011(1): 35-52.
[6] 郭象注, 成玄英疏.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329-330.
[7] 戴震. 戴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96.
[8]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9] 杨万里. 诚斋集[M]. 四部丛刊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10] 陈立胜. 恻隐之心: “同情”“同感”与在世基调[J].哲学研究,2011(12): 19-27.
[11]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64.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31.
[13] 傅伟勋. 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253.
[14]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2.
Why “apprehensiveness”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benevolence”——the inner logic of Mencius’s sympathy theory
LU C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215009, China)
Mencius said in his sympathy theory, “everyone has apprehensiveness and sympathy”, but apprehensiveness doesn’t mean the beginning of benevolence, which is profound meaning. Apprehensiveness, with fear of death is the premise of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that means subject should place himself in others’ position to imagine other painful experience. It is also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stimulate and present Liangzhi. Although Saints are not tempted by other things and plagued by pain, the sympathy for others should be built on the apprehensiveness and fear of death, which is the awareness and compassion on the finiteness for all life and the fear and worry for others.
Mencius; sympathy theory; inner logic; apprehensiveness; benevolence; ideological structure.
B222.5
A
1672-3104(2014)06-0034-06
[编辑: 颜关明]
2014-02-12;
2014-10-21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教的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研究”(11BZJ038);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儒学概念、问题与价值综合研究”(2010JDXM008)
陆畅(1986-),男,江苏宿迁人,哲学博士,苏州科技学院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儒道哲学与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