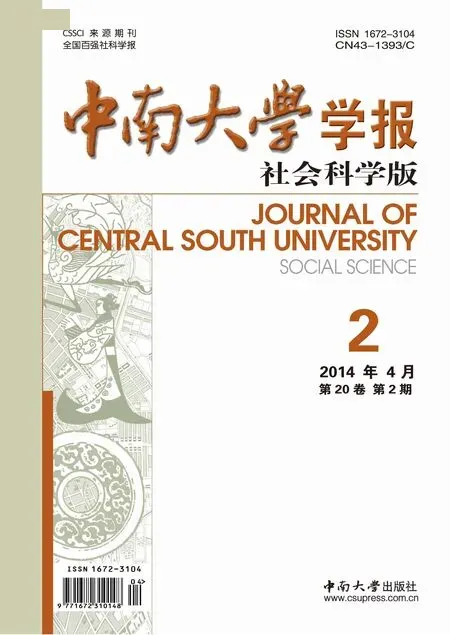从本质到共相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阴志科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从本质到共相
——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的视角演变
阴志科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一个常见的术语“共相”深入探讨了“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并由此对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在他看来,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各自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非要为文学找本质、下定义,是一种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则是一种极端唯名论的观点。
共相;文学事件;伊格尔顿;文学哲学;本质主义
特里·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全书第一章却由中世纪经院哲学入手来谈论文学话题,伊格尔顿用意何在?笔者认为,自《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发表以来,伊格尔顿始终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在《文学事件》一书中,他引入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共相”,以此作为理论出发点重新评估了文学与形而上学、神学、科学之间的关系,并用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思路为文学做出了“本质主义”式的界定,他还通过作为共相的“策略”(strategy),在辩证法意义上重新厘清了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共相”
一部谈论文学理论的著作,却在介入文学之前大谈哲学,竟然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唯名论之争作为第一章,伊格尔顿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经过反复研读,笔者发现,伊格尔顿是想用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来引入一个常见的哲学术语,即“共相”,而这个拥有古老历史的哲学术语在文学当中并不常见,但它在《文学事件》一书当中居于十分重要甚至核心的理论位置。
共相(universals)的字面意义是“普遍性”或“共性”,认识论意义上的“共相”可被通俗地理解为个别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人和马都是用肺呼吸的,“用肺呼吸”即二者之共相;但这只是共相的一层涵义,共相还是一个属概念、上位概念,比如“人和马都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也是共相。“共相”一词在佛教术语中较为常见,指“通于他者之相”,如衣之红、果之红、花之红,作为共通之处的“红”即为共相,“指事物之共同相状”,“相”是“语言思维的对象”[1](467),“共”即其特征。那么,共相的理论价值在《文学事件》一书中如何体现出来?
《文学事件》开篇提到一种常见的对于“科学”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科学话语比形而上学(metaphysics)话语具有某种“优越性”——科学同样在“研究事物的运行,却无需形而上的概念搅和其中”[2](7),科学基于经验,比如物理学,直接研究事物呈现出的现象,但形而上学却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去谈论现象之后的原因、本质、基础等抽象问题,由于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解释,因此形而上学经常会导致无穷无尽的争吵,但科学与之不同,科学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显然,伊格尔顿在此谈到的“科学”是与形而上学、神学相对立的实证主义科学,这种“崇尚科学”的思想可上溯到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他认为:人类的思辨曾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以及实证主义阶段;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推理和思辨去寻找事物的本质或者原因。但他认定这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神学,此阶段人类的理智并未进入成熟;只有进入实证主义阶段,通过可证实的经验去解释现象,尊重事实并发现规律,人类理智才真正成熟。所以孔德断言:“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3](2)“科学”正是要摆脱那些在经验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形而上学争论,从而实现其为人类自身服务的目的。
然而,伊格尔顿并不认为这种基于实证主义的“科学”比形而上学、神学更“高级”、更“优越”,相反,他认为这些思想体系之间有很多相关联、甚至相类似的地方,这些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性质或相似性、共通性,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共相”。
首先,我们目前理解的科学就是孔德设想的实证科学,但从发生学角度看,后者并非先天与神学对立,科学最初的涵义是一种知识体系①,神学“在17世纪总体上并未将科学视为上帝的威胁,在早期现代社会,科学家们会为了宗教的正统观念去辩护,自然神论是一种允许科学和宗教并存的策略”[4](76)。他在《理论之后》一书中指出[5](80-81):曾几何时,知识分子们在神学当中安营扎寨,后来哲学又给了知识分子们栖身之所,到了19世纪,秉承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才逐渐成为此后人类知识的范式。那么,既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神学之间并非如我们想当然理解的那样尖锐对立,所以伊格尔顿说,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自我理解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对此前的简单否定,它有自己的本体论学说和符号体系(symbolic framework)”[4](77),在他看来,神学和科学都是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或者思考方式。
其次,实证科学的出现,并没有表明“信仰时代被理性时代所取代”[4](76),“科学也和其他的知识形式一样,都要面对一些有关信仰(Faith)的问题”[4](131),比如,伊格尔顿用自己曾工作过的牛津Wadham学院的历史说明,科学有自己的信仰,即科学的本性应当是思想和探索的自由,而不是对于教士和君主的忠诚。“科学也拥有自己的主教、牲祭、圣经、意识形态排斥、以及压制异议的仪式程序”[4](133);和宗教一样,“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组程序或者假设”[4](132)。伊格尔顿还进一步指出,科学所谓的超然根本无法脱离道德或信仰而存在,比如说:没有某种东西的吸引,我们怎么会献身于科学这种劳作当中?为了真实地理解对象,我们还必须具备某些美德去躲避陷阱、控制欲望;再比如,在科学工作中必然存在下列现象:对错误的豁达态度,忘我、谦卑、慷慨、努力工作,坚韧、合作意愿,谨慎判断……等等,难道不都是“信仰”的具体形式吗?
综上可知,一方面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的自然科学最初是补充和服务于神学的,站在所谓“科学”的立场去认定神学缺少知识论价值既缺少合理性,也不尊重历史;另一方面,不论在各自的具体形式上,还是在二者与“信仰”的关系上,科学和神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甚至共同性。
然而,伊格尔顿对于神学和科学关系的讨论并不是为了论证神学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是为了说明科学与神学至少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或者一个共相,即:“二者都把万物归置到一个抽象的一般法则集合当中”[2](13),他认为,科学和神学不过是从左手倒腾到右手的关系,科学和神学都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去解释世界,科学关注经验世界,神学关注理念世界,任何对科学和神学的质疑都会遭到这两种话语体系的强力压制,而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让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某种抽象之物,科学作为一个范畴已经成为“实在”,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但解释世界,更得到了无穷无尽的解释和论证。因此,神学也好,形而上学也罢,皆属于思想体系,这样,神学、形而上学、科学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共相”。至此我们会问:伊格尔顿在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当中,只是为了说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共同特点吗?
当然不是,伊格尔顿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共相”并非事物的本质,同理,作为具体存在的文学作品,其“共相”——比如内容上的道德性、虚构性、语词上的修辞性等等——并不是文学的本质。伊格尔顿是为了借神学、形而上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共相”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质”这个宏大问题。
二、文学的共相并非文学的本质
根据上文所述,神学(包括形而上学)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具有相似性,这些可视为二者的共相,在孔德看来,神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共相”,在伊格尔顿看来,神学和科学亦有“共相”。那么,在西方哲学中“共相”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共相问题上有两大分歧②,实在论(Realism)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于精神之外的实在,共相产生于事物之前,主要以柏拉图学说为依据;唯名论(Nominalism)则主张共相不过是名称,在心灵中和心灵外都没有实在性,共相产生于事物之后,以亚里士多德学说为依据。当然这只是大概区分,各派观点内部分歧很大,实在论、唯名论内部也有极端派和温和派的差别。在当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共相(the universal)存在于人的心灵和理智当中,作为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属性”,它既可以理解为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性、一般性、相似性,也可以理解为事物间的“类概念”或者“属概念”。我们关注的是:哲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共相呢?
对于柏拉图而言,共相是一种实体,共相即“理念”,是个别事物存在的本源,万物是理念的复制品③;对于经院哲学家们而言,尤其是持实在论观点的神学家而言,共相具有实在性是为了论证作为共相的上帝存在,柏拉图和中世纪实在论者都认为共相是不依赖于主观意识的独立实体。但唯名论观点与这二者明显相反,他们认为共相只是基于事物存在而归纳总结出来的思维产物,是一些概念、名称。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认为,“实在论与唯名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正是“共相”问题,实在论一方坚持共相是实在的,而唯名论一方则坚持共相是人的观念甚至语词。
神学认为上帝是万物的本原;形而上学认为认识事物必须把握其“本质”④,本质是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原因。在神学和形而上学阶段,也就是孔德所假定的人类思想不成熟阶段,本质、共相、原因几乎是同义语,柏拉图认为理念就是本质,理念决定了万物;而经院哲学中的实在论者则认为共相就是本质,共相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万物。到了20世纪,维特根斯坦依然提出:“命题中本质的东西是一切能表达相同意义的命题共同具有的东西。同样地,符号中本质的东西一般地说就是一切可用于同一目的的符号共同具有的东西”[6](202)。可见,在实证科学大行其道的20世纪,本质和共相依然难舍难分。虽然柏拉图和实在论者所坚持的实在论共相早已经被当代哲学所抛弃,但是,唯名论提出的共相,即从不同事物当中抽象、归纳出来的共同的东西,能够代替“本质”吗?
答案在伊格尔顿这里当然是否定的,他并不同意唯名论的观点:共相并不等于事物的本质,而找到共相,并不等于找到了事物成其自身的原因,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即便能够通过推理得出,也不能用这种推理的结果去理解甚至定义具体事物,共相决不是事物的原因。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去回答文学中的类似问题,也是最常见、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即:“是什么特征让具体的文学作品被统称为‘文学’?”“让作品成为文学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是什么?”“文学有没有本质,有的话它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从所有文学作品当中归纳出来的普遍特征(共相)吗?”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年代里,伊格尔顿承认那时自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当时他认定文学并无本质可言,因为确定文学的本质“就像试图确定一切游戏所共有的唯一区别性特征一样地不可能”[7](8)。本质如果是同一类事物所具有的、与其他类事物相区别的共同特征,那么,确定这个本质,就是在这一类事物当中归纳出一种“共相”。而在所有文学作品中寻找本质或者共同特征,就像给所有游戏下定义一样不可能,因此在那个时候,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可以认为,伊格尔顿所反对的文学本质主义观正是错把所有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共相当成了文学的本质。
而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的《文学事件》中他改口道:“尽管我仍然可以捍卫那个观点(注:指文学无本质的观点),但现在我却比当时更清楚地认识到,唯名论并不是实在论的唯一替代品。”[2](19)为了理解这句话我们还是得返回到中世纪。彼时实在论认为作为本质的“共相”是实在的,唯名论则认为“共相”只是语词、概念,并非具体的实在,如果从日常经验上理解,后者似乎更符合人类的理性判断。可众所周知的是,唯名论并没有把实在论完全击败,相反,它具有的某些唯物主义倾向反而让自己屡屡被视为宗教异端而遭受打压,最终,两种哲学观点并未决出胜负。伊格尔顿对于文学的本质问题也持类似的观点:一方面,他站在实在论立场上认为,文学具有本质属性,这样才可以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唯名论立场上认为,文学只是一个个具体的“殊相”(the particulars,与共相相对,即个别事物,佛教称其为“自相”),要在经验上予以直接把握,文学只能被描述,而不能用下定义的方式去把握,尤其不能利用文学的“共相”来为文学下定义、规定本质。
比如,许多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征,如修辞性、道德性或者虚构性等等,并非文学所独有,广告、布道词、政府公告、笑话也具备这些特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所谓的文学特征在伊格尔顿看来只是文学的“共相”,并不是文学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当然也不是文学的本质。所以,伊格尔顿还是借鉴了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类似”和“语言游戏”的哲学观点,为文学进行了一种“反本质主义”式的“本质主义”界定:一方面,之所以是“反本质主义”的,是因为伊格尔顿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并不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些)共同的本质,这个(些)本质不能用来为文学下一个定义,这个(些)本质也不是文学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之所以是“本质主义界定”,是因为像维特根斯坦一样,伊格尔顿认为作为理论研究对象的文学是有本质的,只是它们只可以描述,不可以下定义,一旦下了定义,就是在用“共相”代替“本质”,用“词”代替“物”。我们知道,命名方式和事物之间的困境不仅仅是文学特有的现象,比如说,“圆”“红色”都不是实体,绝对的、丝毫不差的圆形和红色并不存在,它们只是理智的产物,当我们指认某些作品属于文学时,就像指定某些图形属于圆一样,既是在发现它们身上所具有的共相,又是在用一个抽象概念去命名它,所以我们不能为文学下一个四海皆准且一成不变的定义,因为“什么是文学”或者“什么不是文学”的命题总归可以在现实当中找到反例,和“圆”“红色”类似,绝对的、丝毫不差的文学,与定义严丝合缝的文学永远处于思维中的理想状态。
至此,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为“游戏”所做的界定:“我对游戏的概念,难道不是已完全地表达在我所能够给出的说明中?也就是说,表达在我对不同种类游戏的例子的描述中,表达在我对如何模拟这些例子而构造出各种各样别的游戏的说明中,表达在我声称不会把这个那个包括到游戏中去的这个说法中,如此等等。”[8](53)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游戏只能被举例、描述、说明,无法被定义,更重要的是,游戏者会在进行的过程,也就是遵守游戏规则的过程当中尝试对部分规则进行微调,游戏是在游戏中被定义的,各种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类似的特点。同样的道理,文学也只能被描述,而不能下定义,对它的“界定”(而不是定义)只能在文学作品当中去描述;同时,文学作品又在历史和现实当中不断尝试打破原有的边界与规则,文学在其形成自身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着既定的文学定义,文学是动态的,因而无法定义,对它的“界定”只能是对其共相的描述,而不是对其本质的概括,因为显然,共相不等于本质。所以,伊格尔顿承认,在《文学事件》找到的五个本质要素,即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以及规范性,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上的范畴”,“来自于日常经验,而不是来自于逻辑概念自身的考察”[2](25)。
唯名论没有替代实在论,反本质主义也没能替代本质主义,正如后期维特根斯坦不能否定他的前期⑤,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一书中充分运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正题-反题-合题”逻辑,对实在论与唯名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看似对立的关系进行了彻底反思。正像伊格尔顿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英国批评界吸收法国结构主义思想时所打的比方:英国批评家们的工作“是在来自巴黎的各种新奇观念卸货时守在多佛尔港口,从中检验出似乎多少能与传统批评方法调和起来的星星点点,并态度和蔼地放这些货物过关”[7](120),我们现在同样可以断定,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到《文学事件》出版的数十年里,伊格尔顿不仅一直关注着文学的本质问题,他依然和传统中的英国批评家们一样,对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一贯秉承着“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学术态度,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与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大陆哲学在伊格尔顿这里,不但没有什么冲突,反而关系十分融洽。
文学既是历史性的,也是规范性的,从若干文学作品当中归纳出某些“共相”来很容易,但伊格尔顿提醒我们注意,切不可把这些“共相”当作文学的“本质”,甚至把它们当作文学的定义。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界说和反本质主义界说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人们同时站在实在论和唯名论各自的立场上去理解文学:对于实在论而言,“文学”作为共相是存在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学正是实在论意义上的文学共相;对于唯名论而言,“文学”只存在于具体的作品当中,“文学”作为共相只是一个语词,作为作品的文学是殊相而不是共相。由此可知,伊格尔顿既同意实在论的观点,也不反对唯名论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实在”的文学共相,文学理论就无法进行,而如果没有那些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文学殊相,文学根本就烟消云散了。如果非要为文学下一个定义,那么就是在坚持极端实在论的观点;而如果非要认为文学没有本质,那么就是在坚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当中所做的正是要调和这种论争,他既认为文学不能下定义,同时又认为,文学是有本质的,至此,我们便回答了对于“唯名论并不是实在论的唯一替代品”的疑问。
总之,“共相”不等于“本质”,我们为了认知的方便去寻找共相,甚至可以说,共相是我们认知世界和自身的一个视角。在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当中,“共相”帮助我们认识了文学,共相并不是文学成为文学的原因,作为共相的文学与具体文学之间、具体的文学和文学本质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共相对伊格尔顿来说不过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方法论。
此外,唯名论者还认为,通过理智和直觉,尤其是通过经验,人类才能认识到个别的实体,事物成其自身的“此性”(thisness)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共相”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共相”只是名称,它们的存在会遮蔽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每个事物是与众不同的,“共相”不可能说明事物的特殊性。同样,在文学领域里,也有很多人坚信,文学作品都是个别的“殊相”,对任何作品进行理论化的抽象概括,都会导致文学“意味”在不同程度上的损失,文学必须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去感受,对文学的理论化、抽象化经常会遮蔽我们对文学的直观感知。可问题在于,缺少了理论的文学,和缺少了作品的文学,同样不可思议。这正是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最后一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既然文学的共相不是文学的本质,那么,文学理论有没有本质?文学理论之间有没有共相呢?
三、文学理论的“共相”
粗略地说,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文学的过度“理论化”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感知,这一类可归入文学的内部批评,强调回归文学本身;另一类则认为感受文学之前必须通过思辨去澄清一些预设的前提概念,这一类被泛称为“文论”,这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被伊格尔顿用来举例的文论包括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政治批评等等。
伊格尔顿认为,这二者其实没有根本区别,所有理论都有预设,不论什么理论都有一些概念需要解释,他说:“所有理论都是理论。”“不要以为理论运用复杂抽象的概念,而经验主义或者印象主义式批评就不用。”“所谓的非理论式的批评一贯都在追求那些象征、比喻、性格、韵律、隐喻、净化等类似的概念。”似乎“性格、情节或者抑扬格应该是不证自明的,而无意识、阶级斗争和漂浮的能指却需要解释一番”[2](167)。既然所有理论都有预设,那么所有理论都具有的“共相”是什么?
在论述所有理论的某个“共相”之前,他做了一些铺垫,他先是发现以“无意识”为例,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会在不同程度与层面上理解和运用这个精神分析概念;再比如,政治批评和精神分析也有共相,对前者来说压迫性的统治力量被称为“霸权”,而对后者来说就称之为“法则(Law)”;对于现象学批评和精神分析来说,文本的意义和身体的意义都是“半遮半掩”的(half reveal and half conceal),文本和身体都是语义和肉体的结合,对文本和躯体的关注就是这二种理论的共相。
接下来,借助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思路,伊格尔顿敏锐地发现,所有文学理论果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相”,那就是,它们都会采用一种把作品视为某种“策略(strategy)”的视角去认知作品[2](169),“作品自身不能被看作是对于外在的历史的反映,而应该当作一种‘策略化的劳动’(strategic labour),这种劳动为了进入现实,必须对现实有影响,必须以某种方式置入现实之中”[2](170),在这个地方,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起着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作用,这种建构类似于“劳动生产”,在此生产过程中,有的原料被抛弃了,有的原料则化身为成品的一部分,而这个成品(即文学)将构成影响现实世界的某个组件。因此,伊格尔顿认为,任何把文学内部和外部予以截然两分的想法都是愚笨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压根儿没有什么内外之分。文学面对并处理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然外在的外部世界。在随后的分析当中,问题/解决、内容/形式、事件/对象、意识形态/审美……这一系列在文学理论当中常见的二分法“成见”,在伊格尔顿看来都是过分简化的,也是缺少辩证法思维的,所以,“策略”其实就体现了文学和世界之间的种种辩证关系。
例如,针对“文学反映现实世界”的成见,伊格尔顿提出一种辩证的看法:“通过对现实的故意损耗或者故意疏远来实现自身存在。”“所有文学都被迫通过损坏世界的方式来重建世界”[2](172);针对“文学为现实提供想象式解决”的成见,他又提出:“文学不会在一般教科书的意义上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2](173)“文本不会像医生诊断那样提供答案”,“它可能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响应”[2](174);而针对形式和内容二元对立的成见,他提出:“文本策略需要在形式和内容的边界之间不停穿梭。”“就像启明星和长庚星,形式和内容在分析时有区别,但其存在却是等同的”[2](184);“文学作品的结构所生成的事件会反作用于结构,并转换其关系,在此意义上,文学作品拥有一种属于人类自由活动的形式”[2](200);针对“文学审美与意识形态矛盾”的成见,伊格尔顿提出:“文学文本会在寻找解决的同时抛出问题。”“文本包含着一系列的策略性妥协与谈判,包括‘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停的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矛盾可能会以一种形式上的进步来实现其临时性解决,但是这种进步又会在意识形态水平上再产生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又会产生一个全新的形式困境,如此往复。”[2](181)可见,伊格尔顿既不同意文学是对现实的机械式反映的观点,也不同意文学是对现实问题的想像性解决的阿尔都塞式观点,更不同意文学形式比文学内容更值得研究的形式主义观点,在他这里,文学和科学、神学都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文学就是文学,它不但不依附于什么外部世界,反而从伦理学的意义上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影响,文学所提供的方案既是想像式的,又是临时性的,既是对问题的解答尝试,又在解答的同时在新的层面上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
可见,通过运用“策略”(strategy)这个共相,伊格尔顿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重新条分缕析了各种文学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运用“共相”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贯穿《文学事件》一书的“底层逻辑”。
从历史的观点看,文学理论是用来研究“文学”的,当文学的道德、审美甚至其他功利价值在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当中“值得”研究时,文学理论就成了对文学的一种认识方式,这和阅读纸质文学或者通过电影电视改编文学,在认识论意义上是等价的:文学研究者通过理论来认识文学,普通大众通过印刷品或者电影来认识文学,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对大众来说,感受作品意味着价值,但对理论研究者来说,文学有着更广泛甚至更深入的价值,他们既要用理论来研究作品,还要研究理论本身,所以,作为“共相”的文学既是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对象,尽管各种各样的理论一开始如同螺丝刀、斧头、剪刀那样是以种种“工具”或者“手段”的身份出现,但逐渐地,“手段”会演变成某种“目的”,研究文学不得不事先熟知文学理论,这或许是“理论”一词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广受诟病的哲学根源。
文学不仅是一些具体作品,也是一个抽象的“共相”。在普通读者那里,文学作品具有“殊相”存在的价值,而在专业读者(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那里,作为理论关注对象的文学则具有“共相”存在的价值,文学既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殊相”,也是一个具有共同性质的“共相”——区别在于,普通读者从认识论层面上把握文学,而专业读者从本体论层面上把握文学。而对伊格尔顿来说,只有将文学当成一种本体存在,后者才能起到干预世界甚至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强调现实与政治的伊格尔顿,他对政治、人生、实践、伦理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值得我们去深入认识和不断反思的“存在”,所以文学研究者研究的“文学”既是共相,也是殊相,故而,《文学事件》一书反复提醒我们,从共相这个视角出发去把握文学、去重新认识理论,其意义是巨大的。
综上,从“共相”出发,整部《文学事件》既对文学及其所谓的“本质”做了哲学思辨,也重新考察了文学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伊格尔顿在21世纪为文学理论、美学甚至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与论证方式经常体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但他“站在文学之外来研究文学”的思路是未曾改变的[9](197-203):之所以断定其论证属于后现代风格,是因为他能把哲学、神学、文学问题巧妙地嫁接在一起;而之所以说他站在文学之外,则是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仅就文学而谈文学的所谓“文学理论家”,他有自己横跨哲学、美学、文学甚至伦理学的庞大理论体系,而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密切的关注。
注释:
① 英语中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知识”(Knowledge),最初与艺术通用。后来科学有了“理论性”的含义,而艺术(Art)侧重指实用性的知识。到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Science)把神学和形而上学排除在外,专指实验性质的自然科学,尽管其他学科也有理论和方法,但“科学”专门用来指那些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具有所谓客观性的的学科。参考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
② 在西方哲学史上,古罗马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曾提出的三个关于共相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分为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这三个问题是:(1)共相是实体还是思想中的观念?(2)如果共相是实体,它们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3)共相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存在于可感事物之中?
③ 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柏拉图是最早坚持“实在论”的哲学家,他认为共相既包括种属(kinds)概念,也包括性质概念(properties)与关系概念(relations),参考斯坦福哲学大百科在线(SEP)的“Nominalism in Metaphysics”词条。本文主要将其理解为性质概念。
④ 有学者指出:西方哲学思维的特质即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后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深藏在其外在形态之中的本质,从而把揭示事物的本质视为哲学认识的目的。参见王晓朝、李树琴:《西方古典哲学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演进》,《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可以简单地理解,所谓的本质主义一定要先设定一个“本质”,比如,柏拉图设定“理念”作为本质,亚里士多德把本质归于事物本身,后来的神家家又把本质归于上帝或者真主。
⑤ 有学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本质主义持反对又坚持的态度,参见顾乃忠:《四论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观》,《学海》2012年第4期。毛崇杰指出:维维特根斯坦前后期的思想矛盾并非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而在于他早期思想的核心是语言表达意义的清晰,后期专注于其模糊性与非确定。参见《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 任继愈. 佛教大辞典[M].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 Eagleton, Terry.The Event of Literatur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 孔德. 论实证精神[M]. 黄建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4] Eagleton, Terry.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Eagleton, Terry.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6]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M]. 陈启伟,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 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8]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 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9] 阴志科. 寻找阿基米德支点——反思《理论之后》争鸣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问题[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 2013(1): 197-203.
From essence to universals: the perspective evolution of Terry Eagleton i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YIN Zhike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erry Eagleton has kept a watchful eye on the essential issue these years. InThe Event of Literaturepublished 2012, Eagleton discussed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issue by virtue of a term Universals of scholasticism in the Middle Ages., and gave literature an essential definition with an anti-essential thought. Eagleton holds that literature has its essential attribution on the realism position and meanwhile, he holds that literature is an specific nominalism. He insists that the reason of essential and anti-essential minds of literature both exist, due to the double position that different people adhere to realism and nominalism. If we agree that literature has its very definition, we stand on the radical realism point; and if literature hasn’t its essence, we stand on the radical nominalism.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Eagleton; Literature philosophy; Essentialism
I01
A
1672-3104(2014)02-0183-07
[编辑: 胡兴华]
2013-10-19;
2014-02-18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基本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与论争研究”(10BZW011)
阴志科(1979- ),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论,西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