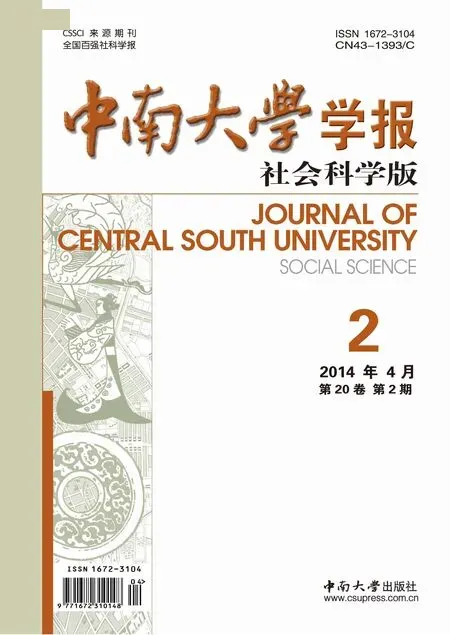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杨万里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历来研究《沧浪诗话》者,多围绕“兴趣”“妙悟”“入神”等问题进行探讨,而关于这几个关键批评术语在严羽诗学中的内涵至今未形成定论。周裕锴先生指出严羽复古诗学的实质在于“试图重新恢复诗歌的音乐性”,进而对严羽诗学研究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错误理解进行了澄清。不过,重视诗歌的音乐性仅是严羽复古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实质应是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的浑然美学传统。他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1](252−253)严羽将苏黄之诗与盛唐之诗作比较,指出盛唐诗胜出宋诗之处正在于一个“浑”字,而“浑”字不仅是他论诗的脚跟点地之处,也是他推尊盛唐的“使人知所趋向处”。以“浑”易“健”正体现了他扭转宋人“以文为诗”的错误倾向,试图恢复汉魏盛唐以兴起情、妙悟天成、气象浑厚的诗歌传统的愿望。
一
严羽主张浑然之美的回归,首先表现为对诗歌浑厚气象的提倡。《沧浪诗话》论气象,尚朴拙之格而黜尖巧之风,这是其推崇高、古二品的内在要求。严羽推尊汉魏之诗,实是推崇其浑然一气、整一无间的混沌美。
对汉魏盛唐诗浑朴古拙之格的提倡是《沧浪诗话》论气象之浑的首要表现。从字源上看,“浑”为天地未分之前元气的混沌状态。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淮南子》亦云:“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可见“朴”是万物未蒙,淳朴自然的元初状态。因此诗歌浑然之美必然表现一种朴拙之格。罗大经《鹤林玉露》云:“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2](288)明人侯方域亦云:“浑朴之气,惟拙者全之,巧则或凿之矣。”[3](515)严羽既想恢复古诗的浑然之美,推崇朴拙之格,反对尖巧之风就在情理之中了。他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1](144)又说:“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陶明浚《诗说杂记》释:“粗之反面曰精,拙之反面曰工。……拙则近于古朴,粗则合于自然。”[1](140)汉魏古诗气象混沌,以质为美;而盛唐诗虽已有人为精工的因素在里面,但这种粗拙与工巧完美结合的人工浑成直追汉魏之天然,虽工而不失拙的一面,这也是严羽区分“不假悟”与“透彻之悟”的关键所在。对此,王运熙先生指出:“盛唐诗歌的浑成,不是对汉魏古诗浑成的简单回归。……比起汉魏古诗来,大抵语句比较工致,音韵更为和谐流畅,在浑成中往往包含着精工的因素。”[4](402)可见严羽这“似”与“非”下得极好,将盛唐诗特有的工拙相参的浑然之美十分准确地展现出来。
严羽提倡诗歌气象的浑朴古拙,意在批判宋人“以文为诗”和过于追求精工的诗学倾向,确立诗歌的高古本色。“以文为诗”自杜甫开其端,由韩愈壮其大,到宋代则由苏黄继其衣钵,形成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主要特征。而江西末流更是因聱牙的音节、迫切的意象,加上过多的论议,丧失了诗歌吟咏性情之功能,因而遭到南宋诗坛的批判,较为激烈者如张戒《岁寒堂诗话》等。严羽也是批判潮流中的一员,他针对宋诗不讲兴趣而“作奇特解会”、专务文字、议论与学问的错误倾向,指出“不必太着题、不必多使事”[1](114−116)。“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1](116)可谓直击宋诗要害。严羽对扭转宋诗错误倾向的贡献在于为宋诗建立一种新的诗学标准。他在《诗辨》中提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26)关于“别材”与“别趣”之意历来见仁见智,结合当时的诗学话语主流来看,问题即迎刃而解。时人刘克庄将诗分为两类:“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5](415)他认为以比兴手法描绘自然生活中的鸟兽草木、讲究幽微意趣的风人之诗才是诗歌本色,这与严羽的观点十分相似。联系观之,“别材”当指作诗的材料,是针对宋人“以书为本,以事为料”而发;“别趣”当指作诗时诗人所依本的兴趣或曰情趣,是对宋诗出于学问竞技之趣而发,均是对风人之诗的提倡。在之前,陈师道论及韩愈诗歌时也认为虽工而非诗之本色。可见江西诗派早期已经在有意规避这种误区,奈何他们还是陷入其中而受到后人诟病。文人诗或雕琢尚巧刻意精工,或逞才使学以笔墨为戏,均背离了古诗浑朴平拙的自然本色,与工拙相济的盛唐诗相比,在严羽诗评中就难免处于下风。虽说风人诗与文人诗的根本区别在于材与趣的不同,但最终表现为诗歌气象的差异。因此为恢复诗的浑厚古拙之美,严羽极力提倡高古之格。《诗辩》推尊高、古为诗九品中的前两品,足见他对高古诗风的重视。他虽认为韩愈之诗妙悟不及孟浩然诗,然又极为推崇韩诗的高古本色。《诗评》曰:“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1](187)而高古正是汉魏诗之气象:“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1](155)又说苏武《黄鹄一远别》一诗:“今人观之,必以为一篇重复之甚,岂特如《兰亭》‘丝竹管弦’之语耶!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1](199)汉诗语言难当精工,但高古浑朴、一唱三叹正是其本色气象。周裕锴先生指出,这类极高古的作品,以严羽的评价标准来看正是极本色之诗。严羽还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次拟作乐府古题,戴复古《祝二严》称严羽“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此时诗坛盛行晚唐体,严羽独标汉魏盛唐可谓独辟蹊径,张毅先生指出:“他对当时江湖诗人效法贾岛、姚合的晚唐体并不以为然,对刻意‘苦吟’以求工巧的创作倾向是不满意的。”[6](225)何以如此?正因晚唐体“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清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7](32)。
《沧浪诗话》论气象之浑还表现在对汉魏盛唐诗浑沦一气、整一无间的混沌美的推崇。《诗评》曰:“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1](151)混沌到底是一种什么气象呢?《庄子》中有“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其中的“混沌”用来比喻事物元初状态的和谐完整,而倏与忽破坏了这种完整以致其死。庄子思想是承继老子而来,老子言“大音无声,大象无形”,即指一种浑的状态。曹顺庆先生指出:“老子所说的大,不但是永恒的,无限的,而且还是浑成的。它是全的,而不是零碎的;是整一的,而不是杂乱的;是一般的,而不是个别的,这是中国‘雄浑’这一范畴中‘浑’字的重要内涵。所谓‘大音’、‘大象’正是这浑成整一的境界。”[8](18)混沌”又类于《周易》中的太极,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王夫之云:“阴阳异撰,而其氤氲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9](15)诗学批评中的“浑”范畴也具有整一无间的涵义,清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云:“大力无敌为雄,元气未分为浑。”郭绍虞《诗品集解》也指出:“浑,全也,浑成自然也。”严羽认为汉魏诗具有混沌之气象,其结构浑然整一、血脉贯穿一体。正如《诗薮》所言:“汉人诗不可句摘者,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无一芜蔓,不着浮靡故耳。”[10](32)严羽把诗歌分为词、理、意兴三个要素,并指出:“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1](148)他认为这三个因素在汉魏古诗中完全融合为一,浑沦无间而不相悖害;唐诗有所偏尚但并不极端,亦属可贵;而南朝与宋则词理意兴互相剥离,破坏了意脉的完整性。因此他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1](158)又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1](151)谢灵运作为南朝的代表诗人,被严羽视为“无一篇不佳”,然而仅指其词胜,有佳句无佳篇,着意精工即驱散了浑然一体之元气,故而不及渊明。正可谓:“浑然不露者,元气也。而有句可摘,则元气渐泄矣。”[11](750)
以气象论诗是对诗歌风格的把握,本身即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严羽自称“辨家数如辨苍白”,并自诩为“参诗精子”,其评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气象是否完整。《考证》言:“《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数句类太白,其他皆浅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误入也。”[1](226)又说陶诗《问来使》一篇“体制气象,与渊明不类,得非太白逸诗,后人谩取以入陶集尔”[1](222)。均是用宏观的眼光,从整体气象入手去辨别真伪。篇中部分语句破坏了整篇气象的浑成整一是值得怀疑的。依照此种批评标准,为使诗的整体气象浑然一体,严羽仿效东坡删柳宗元《渔翁诗》之做法,对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一诗进行了删改:“‘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一联删去,只用八句,方为浑然,不知识者以为何如。”[1](249)严羽删去后一联其用意何在?正是“从诗的含蓄浑成的艺术效果立论,这与他追求气象雄浑的诗歌境界有关”[4](376)。
二
严羽谈诗之五法曰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这五法应是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气象的浑然之美在其它几个方面亦有体现,接下来就以兴趣与音节为例参之妙悟来综合考察严羽对汉魏盛唐诗浑之美的追求。
“兴趣”说是严羽诗学理论的核心,他认为诗出于兴趣无意而发方能自得天成浑然无迹。《沧浪诗话》中论“兴趣”集中体现在下面一段话: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1](26)。
“不涉理路”与“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相映射;“不落言筌”与宋人“以文为诗”“多务使事”相照应。最终诗的根源均着到“兴”这一点上,或曰“兴趣”“兴致”“意兴”。用王士祯的话说则是“兴会”:“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12](78)这段话正可作严羽“兴趣”说之注脚。严羽所谓“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正是对作诗根柢的重视,“吟咏情性”“惟在兴趣”则与“兴会发于性情”同意。可见严羽的“兴趣”就是触景所兴发之情趣,是一种直寻式的自然兴感。由兴起情,因情满于诗而形成一唱三叹之余味,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意。诗须即兴而作,妙手偶得,唯此才能不为文字句法所累,达到浑然天成之境。汉魏古诗由兴会发之,天籁自鸣,故“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胡应麟说:“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10](24)严羽在论及《十九首》时云:“‘青青河畔草,……’一连六句,皆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1](200)汉人叠字或出自口语,或乘兴而出,总之非有意为之,而今人以句法格律相缚,自难能欣赏其浑然天成之美。
无意发之的汉魏古诗,浑然天成自不待言。而盛唐诗已有用力处,杜甫则是全面用力的分水岭。从严羽对李杜二公诗歌风格的评价中亦可看出端倪:“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1](170)有节制已然是用力为诗的表现。而在严羽的诗学体系中,李杜之诗是唯一可“入神”的,是被奉为至尊,须朝夕讽咏枕藉观之的。那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浑然美在杜诗中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此时,“妙悟”便出场了。《诗辩》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1](12)他认为孟浩然诗能超越韩愈依靠的正是“妙悟”,历代诗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创作主体悟之深浅。“不假悟”和“透彻之悟”才是“第一义之悟”,即“指对诗歌原初本质的理解,‘透彻之悟’指这种理解的程度,是对同一等级诗歌的不同表达”。而“第一义之悟”等级内其实又包括“不假悟”和“透彻之悟”两种诗歌类型,严羽之所以由推崇汉魏古诗转而提倡以盛唐为法,其原因正如周裕锴先生所言:“对于严羽所处时代的诗人来说,经历了千百年的诗歌演进之后,再想‘不假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从方法论上讲,汉魏古诗虽是第一义,却不具备实际仿效的可行性。这样,若要获得诗歌的正法眼藏,便只有晋盛唐提供的透彻之悟的路子值得遵循。”因此,可以说从汉魏的“不假悟”到盛唐的“透彻之悟”实则是一种诗歌由无意发之到着力为之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也是严羽诗史意识的体现。有人力即有悟加入进来,悟的等级决定着词理意兴的浑然程度。“不假悟”的汉魏诗可谓天成浑然;通过熟参妙悟诗法,从而达到创作技法的出神入化无斧凿痕的盛唐诗,可谓之人工浑然。许学夷谓:“汉魏古诗,盛唐律诗,其妙处皆无迹可求。但汉魏无迹,本乎天成;而盛唐无迹,乃造诣而入也。”[13](48)正是此意。李白诗虽飘逸无迹,也并非完全无法可寻,朱熹曾言:“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14](3326)有法而不为法所缚,达到浑然无法的地步正是“透彻之悟”的体现,所谓“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1](131)。宋人亦有一二透彻之悟者,如严羽盛赞王安石:“集句唯荆公最长,《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1](189)叶梦得也曾指出:“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15](406)可见虽用力精工,只要妙悟浑成,亦是第一等级之作。
诗法的浑成无迹也包括音节的自然和谐。提倡诗歌音节的浑脱浏亮、雄浑铿锵是严羽恢复古诗浑然之美的重要一环。以庄子“三籁”比喻的话,严羽更欣赏浑然无迹的天籁,而非有律无韵的人籁。陶明浚曰:“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1](7)严羽极为欣赏孟浩然诗,认为其“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1](195)。王孟诗歌均无意音韵与格律的锻炼,却能保持浑成的音乐美,这是严羽推崇王孟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他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灏《黄鹤楼》为第一”[1](197),其中当然有李白为之搁笔的影响,然而严羽推其为至尊而超越他的偶像杜甫,更多的是因为其起法是盛唐歌行语而非如杜诗的格律精严。《黄鹤楼》音节浑成天然,无依律强为的人工痕迹,自然合乎严羽的审美标准。随着律诗的成熟,古诗音节的浑然之美被扼杀了,因此严羽对囿于诗律的创作行为嗤之以鼻:“有四声,有八病(作诗正不必拘此,弊法不足据也)。”又说:“有律诗上下句双用韵者。(唐章碣有此体,不足为法。……又有四句平入之体,四句仄入之体,无关诗道今皆不取。)”[1](72−73)和韵诗在宋代成为一种创作时尚,而只依固有格律,丧失了音节之浑然美,对此严羽批评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1](193)可以看出严羽对于玩弄音韵的游戏之作是不以为然的。他所欣赏的是韵律自然浑朴,无人工做作之痕的作品:“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1](73)文辞浑脱响亮之作,虽不成对,却音韵铿锵。音节的响亮铿锵亦是盛唐诗雄浑气象的重要表现,严羽说:“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1](177)郊岛以苦吟著称,恐怕草间虫吟与铿锵高歌是相去甚远的。
三
妙悟是使诗法自然浑成的重要环节,“入神”则是妙悟的最高审美追求。《诗辨》云:“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8)严羽 “入神”论唯此一处,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是他恢复古诗浑然之美的诗学建构中对诗境提出的要求。《诗说杂记》卷七云:“一技之妙皆可入神。……魁群冠伦,出类拔萃,皆所谓入神者也。”又说:“巧者其极为入神。……其能诗者,不假雕琢,俯拾即是,取之于心,注之于手,滔滔汩汩,落笔纵横,从此导达性灵,歌咏情志,涵畅乎理致,斧藻于群言,又何滞碍之有乎?此之谓入神。”[1](9−10)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点:一是陶明浚从技术层面将“入神”看作诗艺出神入化的至高境界;二是技艺的由巧、妙入神,一定程度上受到书画论中以“神”、“妙”论品的影响,联系观之可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三是“入神”需要“导达性灵,歌咏情志”。下面分而论之。
“入神”首先指技法层面的超形入神。严羽认为能当“入神”之称的唯有李杜,且论述方式与杨万里如出一辙,诚斋曰:“唐人未有不能诗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5](289)杨万里是从李杜诗技法之工的角度论述的,严羽受其影响,对李杜精妙的诗艺也是极为称赏。他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1](168)在学诗的过程中应“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那么技术层面的入神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津人操舟若神”等故事均指技艺的出神入化。文艺创作中形似与神似为两种不同的创作道路,六朝时尚形似,唐时贵神似。宋人也主神似,尤其在画论方面,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的崛起正是靠着遗貌取神的技法向追求刻画逼真的画工画发起挑战的。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载:“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2](343)此论与严羽“入神”说虽不可等而视之,然其物我浑融一体的境界却颇为相似。严羽的“入神”说也应是一种略形貌而取神似的更高级别的技法,唯此方能在因物起兴基础上形成物我浑融一体的境界。这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表达则是“意与境浑”,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在物我浑一的境界中写出来的诗歌不觉神来气来情来,自然臻于混沌无迹的至美境界。
严羽的“入神”说一定程度上受到以“神”“妙”论书画之品的影响。张怀瓘《书断》首次提出“神、妙、能”三品,随后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在“神、妙、能”的基础上另加一“格外有不拘常法”的“逸品”。此后“四品”说成为品评书画的基本标准。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论“神品”曰:“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妙品”:“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16](405)能得物之形似的可谓能品;超形得神又能秒和自然的可谓神品;妙品为两者之折中,刻物精湛绝真而神之将入。这为严羽妙悟诗法以达神化之境做了一定理论铺垫。《诗说杂记》的“一技之妙皆可入神”和“巧者其极为入神”均将“神”置于“巧”“妙”之上,加之严羽的“妙悟”与“入神”说,不得不让人作此联想。那么“逸品”又作何处理呢?这里需要引入严羽的另外一段话:“其大概有二,曰悠游不迫,曰沉着痛快。”[1](8)严羽更为称赏沉着痛快一派,郭绍虞先生指出:“悠游不迫的诗其入神较易,而沉着痛快的诗其入神较难。逸品之神易得,神品之神难求。”他进一步指出:“《答吴景仙书》中争辩‘雄浑’与‘雄健’的分别,即在一是沉着痛快,而一是痛快而不沉着的关系。”[17](283)唐擅雄浑,宋落雄健,苏黄之外发式的健笔,将意象和盘托出,如八万四千宝塔堆砌起来,缺少了物我浑融的意境,不免给人“够”的感觉。朱熹批评苏轼之文“指摘说尽”,而欣赏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14](3325),也是赏其痛快而能沉着。内敛式的浑笔,给人印象发端,留下无尽联想之空白,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样看来沉着痛快容易偏行,更难“入神”。可见,在“入神”上严羽推尊李杜的神品而暂为遮蔽王孟的逸品,也是出于矫正宋诗之病的考虑。
严羽的“入神”说又是以入情为前提的,因此他十分注重诗歌“吟咏性情”的功能。他极为欣赏那些含蓄蕴藉地表情达意的诗歌:“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198)“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1](184)因此他要求诗歌:“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音韵忌散缓,亦忌迫促。”[1](122)意脉深入含蓄,诗味深远醇美,音韵优游不迫,此即“入神”之境也。这与苏轼“美在咸酸之外”,杨万里“以味论诗”有诸多相似之处。古诗之一唱三叹,非仅叹其韵也,亦叹其情也。入神的作品其主客观世界在情感的包蕴中浑融一体,正所谓“诗之道,出于情性则浑为一”[18]。如果将一首诗看作一个由情充溢着的实体,那么物与我畅游其中,不分彼此的浑然状态即为入神。唯有读这种诗才可使人感慨,一唱三叹,不能自己。因此,意境浑融是指诗人的情思浑然无迹地融入诗歌的物境之中所达到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艺术境界。
四
严羽推尊汉魏盛唐诗因其具有浑厚古朴、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以及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严羽作《沧浪诗话》的动机是“说宋诗之病”,而在他眼里,苏黄为代表的宋诗是不乏劲健之笔力的,所输于唐诗的正在于一个“浑”字。全面恢复古诗浑然之美的诗歌传统才是严羽复古诗学的美学旨趣所在。
自严羽始,雄浑之美的重心由以雄为主的壮健大美逐渐转向了以浑为主的完整冥和之美。自此之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如方回说:“简斋诗气势浑雄,规模广大。”[19](109)二字顺序已悄然发生变化。杨载继承严羽之处颇多,在指点诗的立意时说:“要高古浑厚,有气概,要沉着。忌卑弱浅陋。”[20](727)王若虚论诗词主张浑然一体,不露痕迹,如他说:“‘市朝冰炭里,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21](527)王世贞受严羽浑然诗学的影响,竭力推崇汉魏盛唐诗:“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22](960)又在《徐汝思诗集序》说:“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23](217)在明代承袭严羽以浑论诗首当其冲者为谢榛,据统计,他在《四溟诗话》中共提及“浑”字40余次,其中包括“浑然”“浑成”“浑厚”“浑化”“浑沦”等,以“浑然”为例,谢榛曰:“《离骚》语虽重复,高古浑然。”有学者指出,此处的“浑然”即“融合一体,圆美和合,完整纯一,不露圭角,无饾饤之迹”的意思[24](248),可谓全面继承严羽以浑为美的诗学旨趣而又有所发展。清人开始大量使用“浑脱”论诗,亦未脱离严羽以浑为美诗学旨趣的藩篱。此时承袭严羽浑然诗学的主要人物当推王夫之,他也主张诗歌应该整体浑然无间,语句浑成自然、句法不露痕迹。他在评历代诗过程中经常提到“浑成”“圆润”“无痕”“平浑无痕”“不留痕迹”“天衣无缝”“浑浑成成”“一色和浃”“一片合成”“妙无圭角”“用事用景,以浃洽得平”“全不以针线为缝”“意象浑然”等语,可谓将浑然之美推到了新的高峰。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2]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王树林.侯方域集校笺[M].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4]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6]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俞文豹撰, 张宗祥校订.吹剑录全编[M].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8]曹顺庆, 王南.雄浑与沉郁[M].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9]王夫之.张子正蒙注[A].船山全书12册[C].长沙: 岳麓书社,1996.
[10]胡应麟.诗薮[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1]田同之.西圃诗说[A].郭绍虞.清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2]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13]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14]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5]叶梦得.石林诗话[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6]黄休复.益州名画录[A].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C].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1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8]陈旸.乐书[M].广州菊坡精舍本, 光緒二年丙子.
[19]方回撰, 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0]杨载.诗法家数[A].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 中华书局,1981.
[21]王若虚.滹南诗话[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2]王世贞.艺苑卮言[A].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C].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23]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24]李庆立.谢榛研究[M].济南: 齐鲁书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