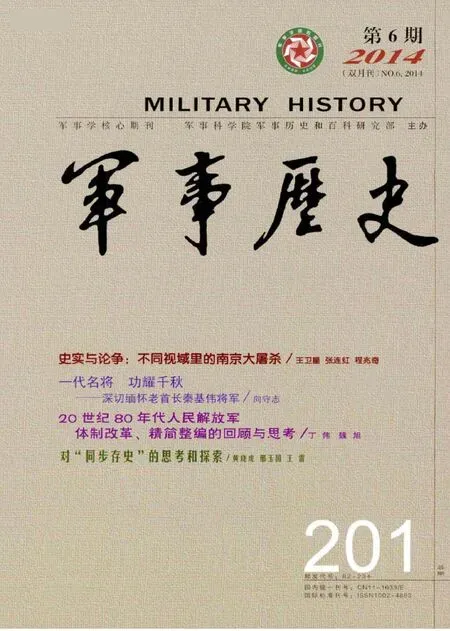史实与论争:不同视域里的南京大屠杀
□ 王卫星 张连红 程兆奇
一、日军在南京的集体、零散屠杀:无可辩驳的历史证明
【王卫星】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和零散屠杀持续了约6个星期,直到1938年1月末才有所缓解。然而,日本总有一些人找出种种“理由”和所谓证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中方、日方及第三方的史料陆续被发现,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日本“虚构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不攻自破。
(一)攻城战中的俘虏“处置”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击。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日军俘获了大批中国军人。对于中国战俘,日军并没有按照相关国际法人道地对待,而是“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以实现其围歼中国军队于南京城下的军事目的。
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一千三百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12月13日,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占领了南京太平门。该联队士兵池端正巳回忆:“俘虏很多,缴获的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处置这些败残兵就成了问题。我们部队人数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虏那么多,有一千几百人,无法供他们饭吃。……我们部队自己吃饭也成问题,就去请示作为上司的师团,师团命令说‘处置掉’。”
日军第10军第114师团步兵第127旅团第66联队第1大队,于12月12日在南京中华门外“扫荡”时俘获了1500余名俘虏。据该大队《战斗详报》记载,12月13日下午,第1大队接到联队命令:“根据旅团命令,俘虏应全部杀死。”第1大队“最后决定各中队(第一、第三、第四中队)平均分担处理,即每次从监禁室带出50人,第一中队将俘虏带至露营地南方谷地,第三中队带至露营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队带至露营地东南谷地附近,全部用刀刺死。”
日军对中国战俘最大规模的屠杀发生在南京北郊幕府山附近的长江边。12月13日,由日军第13师团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率领的山田支队,攻占了南京乌龙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等地,捕获了大批俘虏。15日,山田栴二派人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说全部杀掉。12月16日至18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附近的长江边屠杀了约2万名俘虏。
山田支队步兵第65联队第4中队的宫本省吾少尉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傍晚攻打乌龙山。阵地上并没有敌军,俘虏了许多敌残兵并杀掉了一部分。”在14日的日记中他又记述:“凌晨5时出发,扫荡敌人残兵。……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立刻实施了警备。”16日,日军开始实施大屠杀,将约3000名俘虏押到扬子江边枪杀。17日,宫本省吾在日记中记述:“傍晚回来,立刻出发加入了对俘虏兵的处决。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损失。”该联队第8中队的远藤高明少尉在日记中也详细记录了屠杀俘虏的经过:12月16日,“俘虏总数有17025人。傍晚,按照军部命令,把俘虏的三分之一拉到江边,由第一大队实施枪杀。正如下达的命令中所说的,即便是一日两餐的粮食供应,也要一百袋(粮食)。而如今我们士兵都得靠征缴提供给养。因此提供粮食是不可能的。军部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17日,“晚上,为了处决剩下的一万多名俘虏,派出了五名士兵。”
尽管上述记载对俘虏的人数表述不一,但山田支队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俘虏并加以屠杀是不争的事实。从上述日军屠杀战俘的史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即这些屠杀是根据军、师团或旅团的命令实施,而不是个别部队的个别行动。
(二)南京陷落后的搜捕与屠杀
南京陷落时,许多守城中国官兵未及撤离,不得不丢弃武器,换上便衣,进入由留在南京的西方人设立的安全区等地避难。为此,日军在包括安全区在内的城内各处反复进行搜捕,并采取体貌辨别、亲人相认、“良民”登记等多种方式,“甄别”和捕杀中国军人及疑似军人的普通平民。凡是手上有老茧、肩上有磨痕的青壮年男子,日军均认定是“败残兵”而遭到捕杀。
日军搜捕到中国军人和疑似军人的青壮年平民后,除就近屠杀外,更多的是押往下关江边、汉中门、水西门、江东门、玄武湖、古林寺等地进行集体屠杀。其中,下关江边是日军集体屠杀最为集中的地区。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士兵高岛市良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记述:“第一小队抓到了两百多名残兵。他们是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而逃来的吧。我去问大岛副官如何处置这些俘虏。大岛副官说:‘不管是200还是500,随便拖到什么地方都杀了!’于是将他们装入了车站的空置车厢。决定由小队协助重机枪队在扬子江边处理俘虏,……俘虏排成四队,两手举起。我们拉着50人来到江边。……把人从货车和仓库拉出来,共1200人,让他们面朝江水坐在没膝盖的泥土中。命令一下,躲在后面战壕里的重机枪就一齐开火。他们便像骨牌一样倒下去,血肉横飞。跳进河里的数十人被等在栈桥上的轻机枪全部打死,鲜血染红了泥水。”
南京陷落之初,日军第9师团步兵第7联队是“扫荡”安全区的部队之一,该联队上等兵井家又一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述:“上午10时出去扫荡残敌,缴获了一门高射炮。下午又出去抓来335名年轻的家伙。抓走了难民中像是败兵的人。这些人中间也可能确实有军属……335名败兵被带到扬子江边,让其他士兵把他们全枪毙了。”根据该联队《战斗详报》记载,搜捕期间,该联队共“(刺)杀残敌6670名”。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和《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是仅有的两位目睹日军在长江边屠杀的西方人士。12月15日,经过交涉,斯蒂尔等少数西方记者在日军当局的允许下离开南京,在下关登上了美国炮舰“瓦胡”号。斯蒂尔通过“瓦胡”号上的报务员,向芝加哥每日新闻社拍发了亲眼所见日军在江边屠杀的新闻稿。当天,《芝加哥每日新闻》就在头版以“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地狱般的四天’,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为题,刊登了斯蒂尔的电讯报道:“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第3机关枪中队士兵北山与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汉中门屠杀的情形:“出了汉中门,去征缴菜叶、水牛。我们到的地方死人堆积如山,总数有500多,被堆在一起杀害了。其中主要是军人,也有穿着如一般百姓的死尸。”日军步兵第20联队上等兵增田六助在其手记中记述:“第二天(14日),要去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区扫荡。数万残兵一直誓死抵抗到昨日,但被四面八方包围后,他们一个也没跑掉,结果全部逃进了这个难民区。今天我们即使拨开草丛,也非要把他们搜出来不可,为阵亡战友报仇。我们分成小队,各自挨家挨户搜索。每家的男人都受到我们的盘问。”
1938年任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战时写下的阵中感想录中记述说:“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从冈村宁次的“感想”中不难看出,屠杀俘虏并不是日军部队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线部队普遍存在的“恶习”。
(三)随意的零散屠杀
除了大规模集体屠杀外,日军还放任士兵三五成群在城内外四处游荡,滥杀无辜,零散屠杀时有发生。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记述:“今天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日军步兵第33联队士兵松田五郎也回忆说:12月11日,“一个士兵抓住了一个俘虏,说:‘谁来杀他?’说着就在我边上举起长刀朝脖子砍去,结果因为砍在了骨头上,所以没有砍下来,于是他就把人往死里打,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人给杀了。”
南京陷落时,许多市民进入国际安全区避难,但在安全区外,仍有一些市民因各种原因在家中居住。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城区进行反复“扫荡”,并随意屠杀平民。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民纷纷呈文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痛陈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张施氏1945年9月26日在致南京市长马超俊的呈文中称:“窃民人张施氏,江苏人,年四十岁,居住马台坊拾贰号门牌,于民国二十六年,因民夫张万义,年四十四岁,彼时日军进城事变紧急之时,随同妻女连家五口往山西路美国保护难民区避难,走至半途忽有日兵拖夫,民夫那时即被他拖去至中央门,因慢行一步被日兵一枪打死。”
夏淑琴一家的遭遇是日军零散屠杀的典型案例。夏淑琴证实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母亲吓得抱起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母拼命护着她们,也惨遭枪杀。”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面对日军的屠杀暴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西方人士不断致信日本大使馆官员,抗议日军的暴行,要求日军停止屠杀。但是,这些西方人士的抗议,并未能制止日军的暴行。
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军“慰安妇”制度: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与批判
【张连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不仅肆无忌惮地强奸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而且为了防止性病蔓延开始在军中大规模推行“慰安妇”制度。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有20余人,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信日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真相。
(一)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方式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传教士人身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尽管他们无法了解日军占领南京所发生暴行特别是推行“慰安妇”制度的全貌,但仅就他们所留传下来的书信日记,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几种方式:
一是日军通过大肆抢掠强迫中国妇女充当临时慰安所中的“慰安妇”。收容妇女难民的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女士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第二天,魏特琳的难民所也不幸遭到日军对年轻妇女的掠夺。当晚,日军以搜查便衣兵为借口,将魏特琳等外国人控制在前门口,让数名士兵入校园里挑选妇女,然后从后门偷偷带走。这一次日本人共抢走12名年轻姑娘。
当时南京安全区所报告的日军暴行几乎天天都有大量的案例。例如:“12月15日,日本兵闯入汉口路某宅,强奸一个少妇,并绑去三个女人。”“12月16日,日本兵架去陆军大学内的七个姑娘,从十六岁到二十一岁,五个释放回家。据十八日所接报告,她们每人每天被奸污六七次之多。”“12月17日,日本兵从陆军大学架去南京青年会总干事某君家内的三个姑娘,她们本来是住在阴阳营七号的,为安全起见,才迁往陆军大学,日本兵把她们绑到国府路,加以奸污,于半夜间释回。”“12月23日下午8时15分,七个日本兵绑去四个姑娘。”
实际上,到了南京大屠杀后期,日军到处搜捕妇女的暴行一直没有停止。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30日致夫人的信中说:“就在今天(也许是昨天),那位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而被抓走杀害的学生的年轻妻子以为现在安全了,到安全区外的明德中学买些东西,这时一辆卡车在她身旁停下,把她抓上去,车上还有其他20多名妇女,她们被带到城南的一所房子里,那儿有日本军官,她们将供他们‘使用’。”
为了能够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充当“慰安妇”,日军还借妇女难民登记之机进行强行搜捕。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登记,登记必须在今后的10天内完成。……有一大批年轻姑娘也被挑选了出来,为的是建一个大规模的士兵妓院。”
二是有组织地到各大难民所强行征召。1937年12月24日上午,日军专程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向魏特琳提出要挑选100名妓女到慰安所去。魏特琳详细记录了当天的经过:“10点,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同时,日军还强迫“南京自治委员会”设立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到各难民所招募“妓女”,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史迈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治政府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在日本人12月22日召集之时,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24日,史迈士记载道:“红卍字会正着手和日本人一起建慰安所,以满足日本士兵和军官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上周六贝德士就暗示过此事,当时林查理吃惊不浅。许先生(按:指许传音)说他们准备建两个分部:一个在鼓楼火车站以北供普通士兵使用,一个在新街口以南供军官使用,全是营业性的。”
三是日军通过招募洗衣工等谎言,欺骗中国妇女而被迫沦为“慰安妇”。如鼓楼医院外科的威尔逊医生记载,在1937年12月31日,有6名中国妇女“被从难民营里带出去,诡称让她们为几名军官洗衣服。……在白天她们洗衣服,到了晚上她们就被强奸了。她们中的五个每晚要接受10到20次的凌辱,而那第六个因为年轻漂亮要接受40次左右的蹂躏。”
(二)“慰安妇”的悲惨生活
在日军占领南京初期,“慰安妇”遭受非人待遇,为了不让她们逃跑,不给她们衣服穿,每人每天要遭到十数次乃至数十次的轮奸。威尔逊医生在1938年1月8日的日记中说:“两天前我接待了一名病人,她22岁,结婚4年了。她和其丈夫在日本人进城那天进了安全区。她的丈夫当晚就被抓走了,再也没看见。她那天晚上也被抓走,带到了城南的某个营房,在那儿她每天要被强奸十几次,一共呆了38天。到此时,她已经身患两边化脓性腹股沟腺炎、列性淋病和大面积阴道肿大性溃疡,因此她就被送出来了,因为没用了。”
约翰·马吉曾拍摄到一名15岁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女孩子的悲惨遭遇,该影片是马吉所拍影片中的7号片,其内容如下:“一名15岁的姑娘站在教会医院的汽车旁边,她乘这辆车刚到医院。她的父亲Yu Wen-hua在芜湖有一家店铺。一些日本兵闯入他家翻找值钱的物品。他们把住宅和店铺都抢劫了。姑娘的哥哥在一边帮助他的父亲,他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受过军训并有一套军装。日本兵发现了这些就说他是个士兵。据姑娘讲,日本兵想砍掉他的脑袋,要他跪下,但他拒绝了,因此被杀害。她父母跪在日本兵跟前,乞求他们饶了孩子们的性命。然后这群日本兵试图强奸姑娘的嫂子,她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护士,她坚决不从,他们就把她杀了。他们又要强奸她大姐,她也不从。然后,在她父母跪下乞求时,日本兵把他们也杀了。全都是用刺刀刺死。父母临死之前告诉她女儿,日本兵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位姑娘已昏了过去,日本兵把她捆起来带走。到了另一个地方,她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已被强奸。她发现她是在一栋楼房的二楼,这座房子现在是座兵营,有200~300名士兵。楼里有许多妓女,她们很自由,待遇也不错。也有许多像她这样的良家妇女,有的来自南京,有的来自芜湖或其他地方;她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因为她们都像她一样被锁在房间里,而且她们的衣服也都被拿走。她认识的一个和她同时从芜湖抓来的女孩子自杀了,她还听说其他人也有自杀的。日本兵想强奸她,她拒绝了,因此挨了耳光。她每天要被强奸两到三次,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半月。当她病得很厉害时,日本兵就不靠近她了。她病了一个月,这期间她经常哭泣。一天,一位会讲中文的军官进了她房间问她为什么哭。她把她的遭遇告诉这位军官后,军官用汽车把她送到南京,在南门释放了她,并在一张纸上给她写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个字,这是一所著名的美国教会办的女子学院,在最危险时期曾保护了1万名妇女。这个女孩子病得太厉害,第一天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都去不了,途中在一家中国人的房子歇脚。第二天,她终于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然后被带到了教会医院。”
上述马吉所拍摄到的这位姑娘最后得了十分严重的性病,事实上,在日军慰安所中慰安妇的性病比例很高。“自从日本人进城后,性病的比例从15%上升到80%。军队要大量妓女,不断有人从周边农村抢走妇女,把她们送进城以满足需要。而且因为她们对性病毫无防御力,很快就会染上重病。在这种行当里不再有使用价值,所以就不断地要求新的妇女来补充。”
除了性病,日军慰安所也是交易和吸食毒品的场所。据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调查研究,到了1938年11月,“在过去几天,一家日本和韩国的慰安妇机构,就买进80箱鸦片。”“有时日本士兵用鸦片来支付妓女和在军需物资供应站干活的劳工。”
(三)西方传教士对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批判
西方传教士对日军在南京违背人类良知、公然四处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恶劣行径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日军担心性病传染,影响士兵战斗力,成立了统一管理的“慰安所”,但他们却声称设立专门的“慰安所”是为了保护良家妇女。日军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令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深感吃惊与愤慨。马吉对此从日本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日本人似乎是一个没有性道德的民族,在这个国家,一个女子为了经济方面帮助父母而当几年妓女被认为是孝顺的行为,然后再结婚。当然在这方面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与之打交道,这些日本人根本不认为强奸是什么罪行。”
贝德士针对在南京大街上出现的“慰安所”广告,讽刺说这是“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成为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政治工具”。
他写道:“南京居民常常回想,在国民政府治理下这里是不允许有有伤风化的淫秽展示的,市政当局严禁各种恶行。现在他们正在了解日本首相宣言的意义,他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把中国提升到日本的文化水准’。
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淫秽的混合物,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友好关系’,最好别印出来。
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以及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针对日军所推行的“慰安妇”制度,尽管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根本不可能深入调查,但仅从他们所留下的所见所闻,我们从中可以大致得出如下判断: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慰安妇”来源完全是强制掠夺的,根本不是所谓自愿的商业行为。二是在慰安所的妇女过着非人般的生活,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日军在南京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极大地伤害了南京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道德文明。
三、谁在编造谎言:日本国内论争的此消彼长
【程兆奇】1971年6~7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获中国政府特许,访问了还处在“文革”中的中国广州、长沙、北京、沈阳、抚顺、鞍山、唐山、济南、南京、上海等地,寻访日军暴行的旧迹和幸存的受害人,这些记录成了自当年8月起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中国之旅》的主要内容。由于本多胜一的严厉批判,加上《朝日新闻》的特别影响力,“南京大屠杀”成了日本大众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引起的是反省还是反感,非一言可以轻断。但它的影响本身使持反对所谓“东京审判史观”者不能自安,由此为推动力形成了一波强于一波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汹涌浪潮。另一方面,在左右两方的争持中也推动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展开。
其实,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早在本多胜一报道发表之前。日本学者洞富雄在“文革”之前就曾赴南京,调查有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68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文,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文。1972年洞富雄出版了第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南京事件》;次年,两卷本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出版。洞富雄对南京大屠杀问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探讨,从他的代表作《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看,他提出的问题和对日本“虚构派”的辩驳基本构建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框架,确立了回应“虚构派”挑战的方向。虽然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进,洞富雄的一些具体结论已被超越或修正,但从总体上说,洞富雄奠立的基本格局并未动摇。
在《中国之旅》发表的次年,第一个站出来“批驳”本多胜一的是铃木明。1972年,他在日本右翼刊物的重镇《诸君!》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谜》(“谜”的原字为假名“まぼろし”,以往多译为“虚构”,作者后来澄清说应为“谜”)。次年铃木明的论集也以此为题名。此文发表后,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派即被称为“まぼろし派”,或“虚构派”。《“南京大屠杀”之谜》涉及第16师团诸如尸体桥等等的疑问,但主要是对“百人斩”的质疑。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之前,此案是最主要的争论点。双方的代表性人物一方是洞富雄、本多胜一,一方是铃木明和《我心中的日本兵》的作者山本七平。
进入80年代,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全面展开。当时教科书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成了激化争论的外部触机。1984年“屠杀派”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除了洞富雄和本多胜一,成员还有前辈学者藤原彰,中生代学者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等20人。这一时期是“屠杀派”取得最大成绩、也是在和“虚构派”争论中最占上风的时期。当时“屠杀派”的重要著作还有藤原彰的《南京大屠杀》、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本多胜一的《通往南京之路》《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以及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编辑的《思考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等。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推进和“虚构派”的挑战密不可分,同样“虚构派”的愈演愈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屠杀派”的刺激所致。80年代“屠杀派”的最主要论敌是战时在大东亚协会跟随过松井石根的田中正明。他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南京屠杀”的虚构》和《南京事件的总括》两部书中。两书从所谓南京人口、战后难民的急速增加、进入南京的日本人未见尸体、国际委员会报告的虚与实、难民区的安泰和感谢信、大量屠杀俘虏的虚构、崇善堂埋尸的不实、斯迈思调查可证没有大规模暴行、事发时中国军事会议未提及、中共没有记录、国联没有成为议题、美英法等国没有抗议、美英媒体几乎没有报道、没有钳口令、没有目击者以及史料都是所谓“传闻材料”、照片出自伪造等等广泛方面,否定日军有过大屠杀和其他暴行。如果问田中正明与之前的虚构论者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一点就是从对南京大屠杀的某一点的质疑到对整体的彻底否定。田中正明不仅和“屠杀派”辩难不已,和“中间派”也势同水火,有激烈交锋。虽然从“虚构派”那里看到的永远是胜利宣言,但在这一轮的攻防中至少在声势上“虚构派”是被压了下去。除了上引著作,这一时期“屠杀派”的更重要贡献是通过广泛搜求,全面建立了支撑以屠杀为代表的日军暴行为实有的史料基础。90年代初出版的《南京事件资料集》最重要的上卷“美国关系资料编”也成之于这一时期。
日本“中间派”是认为屠杀人数在数万到1万的宽泛表述,近年又有人将其中主张被杀1万左右的称为“小屠杀派”,被杀4万的称为“中屠杀派”。“中间派”只是对屠杀数的认定介于两者之间,其“政治”立场则远为复杂多样,不像“虚构”、“屠杀”两派那样单一明了。如在日本有大名的樱井よしこ在被杀人数的认定上属于“小屠杀派”,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面反中的旗帜,和“虚构派”没有分别;而“中屠杀派”的秦郁彦的基本看法则接近于“屠杀派”。“中间派”长期以来与“虚构派”、“屠杀派”两线作战,总的来说,在80年代“中间派”对“虚构派”的批驳力度还是更大一些。比如田中正明编辑的《松井石根大将阵中日志》出版后,“小屠杀派”的板仓由明经过逐一核对指出田中“改篡”松井原文达900处。80年代“中间派”在资料上也有建树,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旧军人团体偕行社编辑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和90年代初出版的《南京战史资料集Ⅱ》。尽管战时文献多已被焚,但残存的日本军方文献仍可证明日军曾大规模屠杀俘虏。《南京战史资料集》所收日军官兵日记的特点是包括最高长官以下的各个层级,与“屠杀派”所编资料集悉为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同。进入90年代后,“中间派”中虽然仍有偏重“技术”的倾向,如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原刚通过重新研究幕府山屠杀俘虏等个案,将屠杀数从1万提高到2~3万。但大体上说90年代后“中间派”整体是在右转。如“小屠杀派”的畝本正己自称他著作的目的就是“洗刷”日军的“冤罪”,80年代曾批驳田中正明“改篡”史料的板仓由明的遗著《真相是这样的南京事件》所附追思篇题名即称板仓为“屠杀派”的“天敌”,即使秦郁彦也多次说“正确的数字只有上帝才知道”。在“虚构派”甚嚣尘上的今天,“中间派”的“中间”意义已十分弱化。
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年“虚构派”声势日益煊赫和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势力卷土重来的大背景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虚构派”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一是右翼“学者”成为主流。90年代中期前,除了曾从事媒体、出版工作的铃木明、阿罗健一(畠中秀夫),“虚构派”主要是战时的一辈人,而90年代中期以后的代表性人物无论是“意识形态”味浓厚的东中野修道、藤冈信胜,还是基本算是专业型学者的北村稔,都是长期在大学执教的大学教授。二是“组织”化。和“屠杀派”80年代即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不同,“虚构派”90年代前完全是散兵游勇,近年则频有聚合,2000年还成立了“南京学会”。三是和政界互通声息。90年代中期以前政界人物偶有对历史问题的“失言”,但并未直接介入“虚构派”的活动,近年自民党“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会”的“南京问题小委员会”及参众两院超党派“检证南京事件的真实之会”都与“虚构派”时相过从,互动密切。四是主流电视台的推波助澜。长期以来日本主流电视台间或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议论,如渡部昇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主持的东京电视台(十二频道)的谈话节目,但从未以南京大屠杀作为专题,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门节目近年始见。这些节目因“屠杀派”从不参与(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揭日本伤疤的压力可以想见),而“虚构派”总是有备而来,这样的不对等造成了看似有正反两方的相争总是“虚构派”以“证据”获胜。因此,对“虚构派”来说,这种节目其实比单方面宣传更有效果。五是虚构观点的全面深化。“虚构派”在铃木明时期还只是提出几点疑问的初型,到了田中正明的全盘否定始具規模,这一时期“虚构派”上穷下索,对以往的主张全面强化。如田中正明在《南京事件的总括》的结尾说到照片“伪造”,东中野修道等人接过衣钵号称检查了全部照片:“对‘证据照片’143张首次进行总括的检证”,证明“作为证据的照片一张也没有”。铃木明“发现”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误书为“情报部”)“顾问”,北村稔以此为线索写了一本在“虚构派”中备受推崇、号称从源头上抓到了所谓“南京事件”与“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和对外战略”有“密切关系”的“把柄”的专著。六是新著连篇累牍的问世。七是第一次拍摄电影《南京的真实》(三部曲,第一部已完成)。八是开始向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输出。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虚构观点的影响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面对“虚构派”的全面进攻,“屠杀派”仍在顽强抗争。与80年代“屠杀派”给人的“众志成城”的印象不同,9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13个谎言》,“屠杀派”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在不同方向上各自为战。这一时期在实证研究上成绩最为突出的是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中石田勇治编译的《德国外交官所看到的南京事件》是德文官方文献资料的第一次结集。小野贤二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战时报道的“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俘虏的1.4万名中国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枪杀。“调查会”之外,松冈环编辑的《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采访第16师团为主的老兵达102名,为迄今抢救当事者记忆的人数之最。这一时期在笠原十九司著述以外的寥寥“屠杀派”著作中,我觉得有一本书应该一提,即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津田此书的中译本在两岸三地都已出版,不算僻书,之所以说“应该一提”,是因为此书在日本连“屠杀派”也“视而不见”。被无视的原因当是由于此书以南京大屠杀“实有”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诸派所争本在史实,但我觉得之所以被无视多少也和此书尖锐批判的对象是日本民众的责任有关。日本各派“党同伐异”由来已久,80年代“屠杀派”占据上风和90年代“虚构派”甚嚣尘上可以说都是拜同派之间声应气求“一致对外”之赐,“屠杀派”在这一时期的影响力下降不能说没有整个风气右转的大环境原因,但和“屠杀派”“各自为政”过于孤高也不能说全然无关。
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争论的历史,可以说诸派论争是推动研究的最主要原动力。目前“虚构派”虽然气盛一时,但没有也不可能笼罩一切。由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史料已接近穷尽,所以各派影响力虽会有消长起伏,在看得到的将来,不可能由哪一派定于一尊取得压倒性胜利则当无可疑。
——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