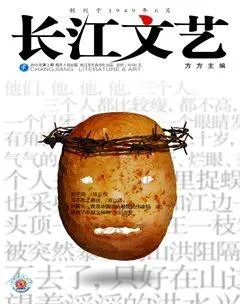纯净的力量(7首)
九宫山无量寿寺闻僧闲话
两位青布僧衣的僧人
一老一少 走在我的前面
山间黑色的碎石路上溅满了暗绿的鸟粪
老的说 有个人一次送了他四双芒鞋
像他是垃圾收购站的
少的说 夏天就要来了 穿这种布鞋
可能抵不住 不如草鞋透气
老的又说 他们总是十点三刻来送菜
真是准时啊 少的说 这次是不是
不用走到山门去接
老的说 还是到山门吧
他们边走边说 满口的武汉话
在拐弯的地方
一棵树拦了一下我的视线
树枝上结满了红色的樱桃
纯净的力量
当所有的事物都在那一瞬回到了自身
每一个命名就像被雨水洗过 这样的时刻
事物因为拥有自身而显得不可战胜
这样的时刻 没有什么是多余的
这就是我渴望已久的 纯净的力量
自由在这一时刻变得可能 我可以怎样热爱
像回到生命的原点并可以清晰地观照自身
一个人要在一生中找到几个瞬间
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而从不把自己屈从于未来
一个具体和另一个具体一样具体 这就是奇迹
美原来是这么简单 并且因此而拥有了重量
如果这时我看到黑鸟那只漆黑的眼珠
它看着我却一无所视 并且空无一物地看着我 转动
我会毫无理由地对它心存感激
它看到的事物在我眼中充满了诗意和力量
在大幕山看到苍鹰
楠竹与古木就着山势
弯曲着性感波峰
山体在初夏晴朗的触抚中
沉默 盲目 不知疲倦
看 虚无的天空中
出现唯一盘旋的黑点
这是谁的一滴墨 甚至
一块铁
我故乡的凶猛苍鹰
和它盘旋于天空中同样漆黑的饥饿
神游当阳神秀墓
失败者也能拥有完美的一生
神秀大师 一个著名的失败者
至死也坚持自己失败的法门
——渐悟
叶落归根 但神秀
没有把遗骸寄往故乡
他把自己埋葬在信仰的大法确立的地方
北宗初地——当阳度门寺
那里 有他参禅的洞窟
身体的记忆 精神的泉水和核燃料
百年人生 八十年追求
他输给了年轻人 但没输掉自己
神秀墓上 供养的铁塔被雷击垮了
但长出了一株高大的雪松
这株雪松 肯定也不是最好的
但是真实 完整 长得很好
苞茅
江夏的苞茅 总有让我放弃
修辞的冲动 为什么这里的水稻土是黄的
而田埂却是红的 它们如此贴近
却截然不同 这是土地的考古学么
在江夏的天空下 田埂
张开着季节的牙龈
苞茅就生长在它们边上
或别的没有开垦过的 有土的地方
不需要任何看护
南楚最适合生长的植物 看来非苞茅莫属
哪怕已经是深冬了 有的苞茅
虽然茎叶已枯 但在茎叶交界处
总有一块拒绝枯萎的绿
像腰间佩玉的破落贵族
在江夏 它们是稻草人 守着身下的稻田
是水师 驻扎在长江边
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 有的坐在树下
有的靠在江夏丘陵的青石边
陆水河上的老粤汉铁路桥
陆水河上的老粤汉铁路桥
和我在战争片上看到的铁路桥一模一样
远远看去 像我三年级练毛笔字时用的一排米字格
但颜色是灰色的
那是我最早看到的大铁
摸上去硬邦邦的 有寒气
大铁上布满了蛋杏元大小的铁钉
手感很好 可以用指甲刮下红糖似的铁锈
在梦中它像传说中的巨兽
但颜色还是灰色的
那时是1983年左右
火车头像一个巨大的京剧脸谱
呼啸着来了又走
它喷出的黑烟被甩在铁桥上空
慢慢变灰 变白
变成铁桥上空的云朵
回忆老家墙壁上的李铁梅剧照
老家堂屋后面的正房拐角处
李铁梅的剧照就贴在上面
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从她右肩斜穿上身
她双手握着它 像握着一把步枪
姿势非常英武
当年我觉得她穿的红布衣和大辫子是多么美啊
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觉得她人美
才这样印象深刻
红灯记 在历史上叫样板戏
但只是我童年中的一张画
我经常在起床后的第一眼看到它
和它下面的粪桶
那是夜里我尿尿的地方
李铁梅的眼睛很大很黑
在画上喷射出仇恨的光芒
她的身姿是抵抗的和有力的
想起这样的事让人心生厌倦
当美的身体和事物都成为反抗的武器
所有的生存都不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