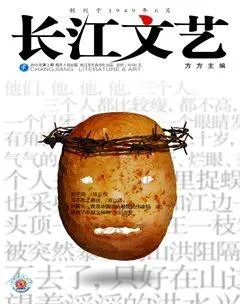现代语境下的归隐之窘
徯晗的小说,大俗大雅,体现的是她对小说创作多个领域的拓展和努力,以及对社会人生的多方位观照和思考。《花叶繁盛》(发本刊2012年第9期)可以视作“大俗”的代表,题材时髦,情节抓人,通过讲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借腹生子结果男主人却对代孕者产生爱情的故事来对抗物欲,呼唤真情;而本期刊发的《隐者考》可以视作“大雅”的代表,形式考究,文字从容,立意深刻,通过叙述一名科学家发明了食品添加剂却对它的泛滥应用和可能造成的恶果无能为力从而遁入山林的故事,来彰显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担当、困惑、忧虑和对现代性的拷问。
文体结构新颖。在《隐者考》中,徯晗有着鲜明的文体意识,或者说,对小说文本有一种自觉的实验。小说结构由微博、笔记、小说、访谈四种形式构成,每个部分独立成文而又具有内在的逻辑性,相互补充而又互相消解,从而让小说的形式感大大增强。这种形式的丰富和内容的现代性内外呼应,从而把二者打通,使小说更具张力和包容度。也就是说,这种叙述手法是作者的一种有意为之,它不但是对传统小说结构的一种突破和颠覆,更是用这种现代性结构来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省和解构,因此这种颠覆和解构更有力度。
对现代性的反思。科学是把双刃剑,现代性亦然。小说通过生物学教授高阳研究出食品添加剂却无法控制它的推广泛滥,批判了食品的工业化给当下带来的食品危机。而造成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现代性。现代社会犹如一架高速运转的庞大机器,创造着一切也吞噬着一切。它对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追求,对线性时间的拼命追赶,对便捷、一体化、规则等诸多元素的自我设定和要求,膨胀、腐蚀了人心,也压迫、违背了人性。所以高阳才逃逸出来,归隐山林:“这种被遗忘的生活,是我努力选择的。它把我的生命拉长了,让我在这种拉长中体会着自己的存在:生命是这么真实,自然,如同万物生长,鲜花绽放。”
然而,高阳的归隐,却有别于中国自古而来的隐士生活:虽然淡泊恬静,但一直关注世事。他在隐居的东山岭做生物试验,建现代化农场,繁育和保存几乎所有农作物的天然种子——这可以视作一名科学家的忏悔和将功补过;同时,他与淳朴娴静的当地女人玲结婚,生了孩子之后还不让他们出去上学,而是自己亲自教授,让孩子们在山川河流青草树木中自然成长——这也是对人类种子的一种保存。这两种有意味的“保存”都是把现代性视为扼杀自然和灵性的大敌,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抗和补救,并把这种方式当作拯救人类现代社会的诺亚方舟:“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那些贪得无厌的人正在侵害我们的种子——局势比我当初料想的还要不可控。我真担心,有一天,谁来为我们人类保存种子?”
对自由精神的呼唤。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东山岭的原始密林:藤蔓缠绕,大树参天,生灵活泼,幽远浪漫,充满灵性与力量,犹如世外桃源。这里的密林,是与现代生活相对应的理想存在,是人类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是反抗现代性的一种存在形式或文化符号,也是对远古文化之光的呼唤和传统人文精神的回归。它影射的是现代机器对人的生命力和原始本性的压榨和压迫,以及对人的蛮性和灵性的异化和毁灭。而只有回到没有污染的密林,在与大自然的亲近中涤荡心灵,从最古老的知识与文化中汲取营养,才能找回人之初的自由、激情、力量与灵性,找回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也只有置身这样的氛围中,人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极致快乐(如康娅和园丁那般)。
对现代人无处隐居的忧患。隐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老庄思想,到魏晋风度,隐居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情结。然而现代社会的隐居与此已经截然不同,无论是高阳的主动退隐,还是园丁的被迫归隐。高阳的退隐,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消极反抗,即使身处山野也心在人间,与外界有着各种联系,而他的科研成果和保存工作,更是直接为现代社会和人类自身所用;园丁的归隐,是一种犯罪之后的逃避(杀了强奸自己女朋友的导师),然而却忍受不了被遗忘的寂寞和没有身份的痛苦,他宁可承担“罪”,也不能失去存在感,所以园丁最终主动自首,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回归,也是妥协。两个人的隐居,都是不彻底的,都是因为中现代性的“毒”太深,身心皆不能真正隐而安。对于现代人而言,隐居只是一个永远的梦。
徯晗在此探讨了现代隐居的不可能性,用回归山林、重拾原始本性的方式来解救现代性弊病的不可能性,以及时代环境对人的强大制约性。所谓“现代,正是现代人的枷锁,诅咒,痛恨,却不得不赖以生存”,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无法突破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所以人对此的一切挣扎都是无效的。高阳隐居而被毒蛇咬伤成为植物人,即便醒来,也是弱智,这一悲怆而反讽的结局是具有深重的象征意味的。
性与情的分裂及隐喻性。高阳和妻子玲以及情人康娅三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奇特而和谐的关系。而高阳、康娅和园丁三个现代人的性与情都是分裂的:康娅是性与情二者的双重无处安放,高阳是性与情二者的永远不能合一,园丁是情的失却与性的昙花一现。
高阳、玲、康娅三人间的默契和谐,在于原始密林的强大感染。玲就是大自然的隐喻,她与密林是一体的,她让高阳和康娅有“还乡”之感,她甚至有点圣洁之光,所以才会那么大度、包容而自信地看待三人的关系,她知道高阳的精神所需,他离不开她;康娅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凝聚着现代文明的一切利与弊,所以高阳才会对她在精神上依恋,在肉体上抗拒——喻示着文明的力与反力;高阳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游离恰恰说明了他对自然精神和现代文明的矛盾纠结,他的分裂感正是现代人的精神存在。而康娅和园丁两个现代人可以尽情享受性爱却是建立在陌生化的基础上的(陌生化,这同样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喻指):互不相识的他们只有卸下现代面具、置身原始自然才能享受生理上的极致快乐和隐秘快感,而一旦这种陌生感消失,他们的交集和快乐也到此为止。
徯晗的《隐者考》,让我想起杨遥的《在圆明园做渔夫》(发本刊2013年第1期),前者是知识分子在山野的隐居,后者是底层人在闹市的避世。这种错位,都是现代生活的一出荒诞剧或一记警钟,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之窘:无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底层,是身处庙堂还是山野,都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因为,环境和人心这两大现代锁链的羁绊,让现代人已然无法迈开归隐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