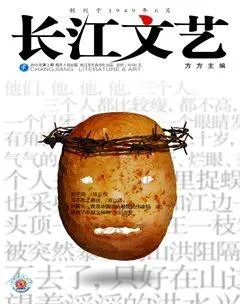莫言获诺奖和洋人的政治标准唯一
莫言获得诺奖以后,西方世界一片喧哗,讨伐之声,震耳欲聋,中国网络上跟风炒作,风生水起,虽然众说纷纭,然而异口同声,出发点却似乎雷同,那就是莫言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美国号称中国通的洋大人林倍瑞,宣称莫言没有对中共政权发出全面抗议,就不配得诺奖。这是什么逻辑?诺贝尔文学奖的准则中不但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以往的颁奖也没有这样的惯例。六七十年代倒是有人总结过,这个文学奖照例是发给“西方的浪子和东方的叛徒的”。所谓“叛徒”的意思,只是指思想上的,并不一定上是行动意义上的。例如,苏联的肖洛霍夫就没有对苏联政权发出过正面挑战,相反,他还是在得到苏联当局的允许之后,才接受这个奖项的。林倍瑞混迹文学评论界多年,但是,其评论的标准却并不是文学的。在极左时期,在中国文坛流行的政治标准第一已经片面了,但是,毕竟还有艺术标准第二可以稍作弥补,可这位洋大人竟达到政治标准唯一的程度,而且这个政治标准还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如果林倍瑞大人的理想,是要把这种标准推广到中国,从而推广到全世界,其文化专制的惨烈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诺贝尔文学奖,顾名思义,就是奖励那些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士。文学成就是唯一的标准。至于其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可以五花八门。肖洛霍夫并没有向苏联当局发出抗议,没有遭受镇压,相反享受到官方的殊荣可以获奖,而遭到打击乃至流亡异国的索尔仁尼琴也可以获奖。这是诺贝尔奖的历史明明白白昭示的,可是林倍瑞却视而不见。在这位洋大人的潜意识中,作家的思想行为只能从一个政治模子里脱出来:莫言,一定要变成刘晓波,才有资格获得诺奖。西方的中国通,实际上是吃中国饭的,可是他对中国人的获奖却暴露出民族岐视。肖洛霍夫获得诺奖,并没有谁责备他对斯大林的暴政沉默,也没有人责问他为什么不跟萨哈罗夫一样公开与前苏联政府对抗。偏偏中国人得了诺奖,一些洋大人就义愤填膺起来: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模式思考,你为什么不按我的逻辑行事?西方谚语云,一个傻瓜的问题要比聪明人多许多倍。事实上,这样愚蠢的问题,从根本上违背了西方起码的价值准则。伏尔泰有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以生命捍卫你发出此言的权利。可是,洋大人却只允许你讲和他一样的话,一旦有所不同,就冠之以“狡猾”、“妥协”。再说,如果莫言如他们所向往的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那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林倍瑞一张脸的克隆了,哪里还可能有莫言那种永远眯着眼睛、憨态可掬、大智若愚的神态?
这些洋人口口声声要反对文化专制,但是,他们武断的逻辑却是彻头彻尾的文化专制。
我为莫言获奖而高兴,并不因他抄了毛语录就责难他。相反我尊重他的选择,我欣赏的是他的作品,他的才华,并不求他的行为和我遵循同一准则。人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自由。政治准则并不是文学的准则,美国意象派伟大诗人庞德,曾经为法西斯摇旗呐喊,他的诗不仍然是美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吗?王维在安禄山进入长安以后,接受了伪官,虽然有错误,但是,他的艺术不是仍然不朽吗?
狭隘的政治功利和文学审美价值的超越性是矛盾的。
如果洋大人仅仅是于此不明,不过是过度自恋而已,但是,他们的国际话语霸权,他们道德优越感,却掩盖了他们在知识结构和理论上的缺陷。
这一点在德国人顾彬身上显得特别严重。
此人一方面以汉学家自居,但近二十年来,他怀着文化优越感,一贯居高临下,多次发出狂言,说中国当代文学完全是“一堆垃圾”。我第一次听到他这种高论是在1994年。那时苏州大学开一“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他以为中国的学者都不懂英文,乃以英文发表“垃圾论”。还说,并不是每一个穿上球衣的都是足球运动员,一些中国作家哪怕是到了西方两三年仍然没有自己的语言。意思是许多中国作家都算不上是作家,等等。殊不知被在场的黄维梁、余光中和本人听清楚了。黄先生和余先生在肯定他的“学术勇气和道德勇气”之后从根本上提出质疑。接着本人则发出更直接的挑战。我指出,首先,他的理论前提乃是西方主流的话语学说,但是,这样的理论,并未经过反思。文学的感染力纯粹由于语言,至少与贵国康德的审美情感价值论不符,至今我仍然未见西方在这方面有过系统的学术的分析和论证;其次,从中国文学史来看,贵论则更难以通过全面的实证。我说,不知你是否读过《三国演义》,就其话语来说,完全是王朝正统话语,但是,它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长篇小说,早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拉伯雷二百年,其中曹操、关公、周瑜、诸葛亮的形象至今活在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的心目中。他无言以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继续贩卖他的“垃圾论”。
莫言得了诺奖,这无疑是给他的“垃圾论”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他并没有以实践来检验、修正他的理论,而是用诡辩来堵塞他理论的漏洞。近日他大言不惭地宣称,莫言的作品,他根本就读不下去,其之所以能够获得诺奖,主要原因乃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葛浩文教授翻译得好。看到这样的说法,憋不住想起中国的一句歇后语:放屁拉椅子——没有地方遮羞了。中国人得了诺奖,是因为美国佬翻译得好。葛浩文翻译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书,按顾彬的逻辑,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的中国作家得诺奖了。其实,用五四时期作家们论战的话来说 ,翻译充其量不过是媒婆,原作才是新娘。而现在这位洋大人居然把媒婆当成新娘出嫁,实在不能仅仅以诡辩来解释,最根本的奥秘乃在洋人的潜意识中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
在顾彬想象力之外的,可能是如果莫言出身在德国,没有中学毕业文凭,没有考过德国中学的“阿比妥”,就不可能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那样的大学,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在这方面起了决定作用的乃是当时慧眼识珠的中文系主任徐怀中。当莫言在河北保定得知这个招收作家的文学系的时候,招生已经结束了。按照德国的严苛的文牍主义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通融余地的。但是,就凭莫言发表在保定文联《莲池》上的两个短篇,徐怀中先生毅然对之破格录取,让他成为当时以《高山下的花环》红得发紫的李存葆的同班同学。一年以后,他和李存葆一起交上了学年作业。李存葆的是后来也甚有名声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他交上的是《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的评价是,两个都是好作品,但是,李存葆的是没有(艺术)追求的,而莫言的则是“有(艺术)追求”的。在徐怀中的推崇下,莫言一举成名。
葛浩文当然有贡献,但是很难和徐怀中相比。莫言是在文学尚未充分显露才华、有可能夭折时被徐怀中发现、培养的,而葛浩文不过是在莫言成名之后,做了比较公平的选择而已。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
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有准则的。虽然西方前卫文论这一阵咋咋呼呼地说,作者已死,由读者决定一切,但是,历史是最严峻的裁判官。从八十年代以来,莫言以他文学上的探索和多产,在中国文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的影响和成就使他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列,诺贝尔奖的获得也足以说明他同时也进入世界文学的前列。这是林倍瑞那样的洋人,所不愿意看到,但也绝对不能无视的。他能够聊以自慰的只能是,莫言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当然可备一说。问题在于,他认为最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就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中国作家,较之于莫言在艺术上的探索,对人的理解,尤其是对英雄和荒谬的理解,在语言上的突破,都是望尘莫及的。
对付这种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胡言乱语,我忍住了孔夫子所说的那样“鸣鼓而攻之”的冲动,但却忍不住用阮籍的白眼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