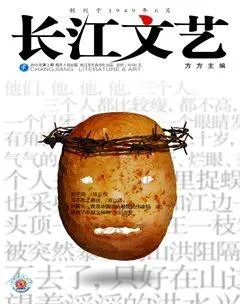昙华世纪(三题)
几十年前,
我住进这条街时,
也曾隐隐感到它稍稍不太寻常,
不单是那里有赫赫有名的三厅政治部旧址,
街两旁依山而建的几幢西式建筑,
也显出身份不凡。
比起周边的几条街,
它没有那么喧嚣,
没有那么浓浊的市井气,
尤其是通向云架桥的后半段,
少有人行,僻冷、落寞中,带着孤傲。
昙华世纪
平生似乎未曾见过昙花,虽然早知道“昙花一现”的成语,知道它极其美艳却吝于展示,转瞬即逝,却难辞自己的缘浅与寡识。然而,我确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武昌的昙华林。古汉语中花与华可相通,则昙华或即昙花,昙花繁茂而成林,这景象实非同小可,另有一说,昙华系从佛经来,何以此地命名如此深奥,似乎也都不甚了然。
几十年前,我住进这条街时,也曾隐隐感到它稍稍不太寻常,不单是那里有赫赫有名的三厅政治部旧址,街两旁依山而建的几幢西式建筑,也显出身份不凡。比起周边的几条街,它没有那么喧嚣,没有那么浓浊的市井气,尤其是通向云架桥的后半段,少有人行,僻冷、落寞中,带着孤傲。
说到对这条街最初的印象,就一定要谈起我们那位房东,他姓桂,我们都叫他桂老头。这是一所大宅子,前后三进,住了六、七家租户,桂老头自己一人占了第二进东侧的三间房,这在当时委实是一件相当豪奢的事,以我们这些房客而言,一家子五、六口人,大都拥于一室,已经殊为不易矣。何以桂老头能如此阔绰,当然因为他是房东之故。但何以他能占有如此多的房子,对于我们这些孩子,就颇为■了,仿佛是他与先前这里的教会有着什么关系。比较可怕的一种说法,是他曾经被公安叫去谈过话,有人甚至怀疑他在房里藏有发报机,以便与美蒋敌特联系。因之,在我们的眼中,他的面目遂不仅秘诡,而且更有些狰狞。
桂老头年岁也不很老,印象中是一张瘦长脸,眼小,鹰钩鼻,胡茬粗硬。他不大出门,见人也基本不搭理,除了到期向各家收房租,有的房客一时交不上,会听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一堆生气指责的话,然后又一头钻进屋里不再出来。他究竟在屋里做些什么呢?这件事很令我们好奇,有个小伙伴说他曾经跟随妈妈去交房租,敲开桂老头的房门,似乎除了床、桌、衣柜之类也别无所见,也有人说曾看见他在读一本很厚的精装英文书,联想他在教会做事,以及屋里还挂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很可能是《新约》、《旧约》一类。如此说来,他是一个很信教的人,然而,哪有信教的人会这么凶巴巴的呢?
这院落往里,有一段砖砌的阶梯,上面推出一块平面,盖了两间瓦房,我家就住在那里,我母亲也因此获得一个名称,被人叫做“山上妈妈”。说是山上,果然是山,因为再往上就通向山顶了。路也是有的,但早已为荒蛮的灌木荆棘所覆盖,很不容易找到,加之又颇陡峭难登,一般无人上去。这对我们这帮孩子一直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单是上面有两棵硕大的梧桐树,其豆粒状的果实可以摘来炒食,而且,站在山顶上,还能一眼望见各家层层叠叠的屋宇,仿佛可以得见许多见所未见的“西洋景”,更何况此山即是著名的花园山,据说当年教会害死许多中国孤儿的尸骨,都埋在那里。桂老头最恨我们爬上山,每每会突然现身,大声呵斥,不准我们上去,这愈加证明那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许就藏有与帝国主义联系的发报机呢。我和小伙伴们便常趁不被他发觉的时候偷偷上山,一点一点地拨开荒草藤蔓,辨寻残缺不全的石阶,但这时出来阻止的往往是我的“山上妈妈”了:“还不快给我下来,山上有马蜂,蜇死你们。”妈妈说得没错,那里果然有蜂窝,不知怎么碰上了,嘭的一下,散飞开来,吓得我们几乎是翻滚下来,也有人着实被叮了两口,疼痛不已。后来我们很少上去,倒真不是因为桂老头阻止的原因。
然而就我曾经上到山上的很少几次而言,委实所获也无几,左右两侧不但都有依山而建的院墙,而且杂树蔽空,往一侧望去,倒是可见邻家的西式洋楼,灰墙红瓦,拱形阳台,唯不见人影,不知住着何许人家,另一侧,是我所知道的一家医院,也是灰色的西式建筑,正前方,越过街道,又是依山而建的一幢幢房屋,听说对面的山上有驻军,甚至是炮兵阵地,当然看不见,这也更加深了此地的复杂感和神秘感。 我模模糊糊有一种感觉,这里的历史故事是我所看不懂的。
有一次,我下午放学回来,妈妈一把把我拉进屋里,做手势指着山上,低声对我说:“桂老头在上面。”我头一偏道:“我又不上去,怕他什么。”妈妈摇摇手,叫我听。我把头伸出去,好不容易听出来了:“他在哭——”妈妈说:“已经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上年纪的男人,独自跑到这荒山上去恸哭,究竟有什么样的伤心事呢,这是我们谁也无法打听和知道的。等他哭声止住,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见他踉跄着下来,眼眶红肿了一圈,照例是谁也不理,径直走回他的屋里去。
这事在邻里间引起了议论,有人就说可怜可怜,一定是一个人过日子太孤单了,要是有个女人陪伴他也许就不会如此啦。住在院子第一进有个年约三四十岁的女人,离了婚,带个孩子过活,孩子一头黄头发,我们叫他“黄毛”,她就叫黄毛妈。黄毛妈先前是个小学教师,后来不知就怎么没工作了,她有点文化,也有点姿色,于是好事者就极力想促成一件好事,问过黄毛妈,她似乎不成问题,为了生计,其它皆可忽略不计。哪知进屋对桂老头一说,差点被呛出来。为人如此不通情理,亦可见真个不值得同情,有关桂老头奇异的恸哭的兴奋点乃渐渐消失。
提亲的事过了不到半年,桂老头竟一觉不醒,也或是病重多日,并无人得知,总之,待发现时人是早没救了,斯时他的儿子、儿媳一干人等方陆续出现,原来他并非孑然一身,显然,他活着时是刻意不让他们上门的。不久,桂老头的住屋要另租他人,腾房的时候,院子里一时摆放着从屋里搬出来的各种各样西式家具和物件,小山一般,据说他有一间屋是专门用来堆杂物的,里面也确有一些发旧的精装西文书。
桂老头和他的谜团一般的传奇,就此湮没在昙华林的历史烟云里,永远永远无人可以索解。我在“文革”后搬离那里,直到最近又故地重访,看到仿佛海水退潮一般,那里有许多当初以为奇特的东西,诸如各种教会、教堂,都重现真实面目,不禁又想起这个人来。如今,当年我们的院落早已无存,一条开向粮道街的新路从那里穿过,或许路旁那绿草葱郁的行人休憩之地,便是桂老头曾紧紧封扃的住屋所在吧。在这以世纪为刻度的历史生活中,凭谁说,有多少东西都只是偶尔一现的昙花呢?
南化的忧郁
“民以食为天”。上个世纪很长时间里,吃饭的事一直困扰着中国人,非但好山、好水、好地不管用,费尽心思兼之出大力、流大汗也不管用,在当时,这真是不得其解的难题。
那时地、县机关干部还是这样的:都要下农村,领导干部叫“蹲点”,普通干部叫“驻队”,目标是确定的——要把粮食生产抓上去。我到郧阳的当年,就被派到南化去。那里是司令员“蹲点”的地方。此事说来便有点怪哉,何以出来一位军事首长,莫非有什“军情”、“戍机”?其实非也,盖当时通行由军分区一号人物兼任地区一把手,所以司令员就要挂帅地委的“点”。我手头至今还保留当时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司令员讲的“农业经”:
“司令员:(1)改田要抓紧;(2)坑带,深耕,可多用拖拉机;(3)双季稻,坚持试验,不插夏至秧;(4)肥料,有的已经出圈造肥,有的还没垫圈,草肥加土肥掺沙,是好肥,氮磷钾都有了。还要喂羊。……”
以年龄论,司令员应属“扛过枪,渡过江”一辈,或者早年也在家务农,念起这套“农业经”并不太难,但今人看起来,多少有点“不伦”,此皆乡野老农盘算的活计,何劳一位堂堂司令员郑重部署呢?
而实际上村里的农务就是如此被工作队“托管”了,工作队队员分住各生产队,跟队长一起喊上工,有时就直接取代队长派活儿,收工时还要忙着检查,开会评工分,记工分。有的社员(村民)干脆就将工作队员叫“某队长”。除此之外,地委的“点”上,当然也会“开小灶”、“吃偏饭”,多弄来一些化肥和农机之类,目的是让它“一枝独秀”起来,好带动“万紫千红”。
南化处鄂豫陕三省交界之地,原即在层山叠岭之间,有滔、洮二河交汇,赖造化鬼斧神工,竟辟出一片恢廓区域,渠水丰沛,可以浇灌大片水田,亦颇有“小江南”之概。
我所在的生产队,与南化街隔河,约莫一、二里路。我与另一位工作队员老包住队部,外面是场院,这里派工、打场、分粮、开会,可谓是全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一棵硕大的老槐树,很具戏剧舞台上的那种标志性,也挂有一口破钟,用以召集村人。月明之夜,我们常常顶着一片清光,坐在那里,直到很晚。
记得有一次是开全队社员会,约莫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原就收工的人们回到家烧饭、吃饭,这才疲累不堪地走出来,稀稀落落地散坐开,等人的时间,有的人闷头抽烟袋锅,有的打趣说笑两句,也是极力打破闷葫芦的意思。老包传达工作队紧急会议精神,道是:今年口粮分配原则基本不变,每人每月三百二十斤,按月取粮,不许借粮,各队要把夏粮、秋粮、种子粮再盘存一遍,防止在秤杆子上做文章,要抓粮食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有人说“我们就是吃稀的命,这回该吃顿干的了,碗端到手里又给夺走了。”还有人说“今年望到明年富,明年还是叉叉裤。”这是谁说的,要查出来,狠狠批;有人到坡上挖“金刚刺疙瘩”(一种可制酒的野生植物),一斤卖五分钱,明天各队派人到合作社查账,干部搞的,要检讨;社员卖的,钱交出来记工分,花了的记下年终扣钱……传达既毕,问大家有没有意见,照例是“闷”,再问,便爆发似的有三两人喊出:“没有意见。”而后便是问问今天的各路人马活计进行如何,明天又如何派工。
人渐散去,还留下几个队干部,妇女队长熊瑛说:“今天岳凤妮没出工,也没见人影儿。”
“嗳,是的,刚才开会也没看见她,我还想问呢,上哪儿啦?”老包道。
“她家里人也正在到处找她。”
岳凤妮的身份颇特殊,她十八九岁,属于所谓“子女”,“子女”者,“地富子女”之简称也,在当时中国农村甚为通用,然而,又是大队的团支部委员,在大讲阶级路线的时代,这多半表明是有意树立的样板,即所谓不唯成分,重在表现。凤妮的表现确实很好,她个子不高,微胖,圆圆脸,齐耳短发,干起活儿来,是属于“铁姑娘”那一型的,不怕苦,不喊累,天天出勤,叫干啥就干啥,你叫她歇一歇,她总是浅浅一笑:“没事,不累。”她的口中,从无是非臧否,不是装老好人,实在是她安时守分,自知没有指东道西的资格。大家因之对她口碑也一致的好。
她的突然失踪引起众人的牵念,有人说,就看见她前几天精神有点恍惚,默默地像有心事,熊瑛也回忆,好像听她说起,家里要叫她去相亲,对方是几十里外河南的一家,成分好,就是男的腿脚有点跛。她不愿意,说:“成分好有什么用,我不还是个‘子女’。”
这样议论一阵,大家心下都有点黯然。其实,凤妮的家里也算不得什么,她祖母从河南嫁过来,土改时,查出她名下分有若干田产,划了个地主成分,从此这一家就成了“五类分子”家庭,她父母辈属“子女”,到她这一辈该不是了吧,却也还算成“子女”,又无人认真甄别,稀里糊涂就如此“子女”下去。
几天过去了,凤妮还是音信杳然,大家便有些慌了。究竟出了什么事呢,这样一个好闺女?队长老陈犯嘀咕:“她离家的前一天,生产队的水轮机坏了,从河南请她四舅来帮我们修,他四舅是‘分子’(地主分子),可就他会修,不找他找谁呢?中午吃饭,队干部要陪一下,工作队不让,说有阶级路线问题,末了我只好安排凤妮陪,我看她也是不大情愿的……”
终究,这些也不像是她出走的直接原因,大家不由得感叹,女孩子家心思深呢。
她家的人把几十里范围七姑八姨家都访个遍,仍无结果,大约半个多月,从陕西商洛一个表姐那里传来一个坏消息,说凤妮先是辗转来到她家住,前两天留下一封信,便不见了。后来有人在河边,拾到了她的鞋袜和外衣。家里人顿时哭成一团,忙着赶紧赶过去料理,工作队领导听了汇报,也想着凤妮平时种种好的表现,并不以成分划线,指派老包和一名生产队干部一起前往。
他们带回来凤妮的衣物,以及那封信。信上写的是:
表姐转父母亲、小弟:
我要走了,我没有什么事,就是心里有点想不开,不想让你们牵挂我,我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心里好沉好沉……弟弟长大要好好孝顺父母,他们日子过得太难。……
读到这封信,我才知道我们平素是怎样的粗疏,忽略了这个见人笑嘻嘻的女孩子,一定在人所不注意处流露出异常忧郁的目光。她或许是过于敏感和脆弱了吧,然而,以她的年纪,于众人眼前,要时时有那样完好的表现,又该是曾动用了多大的心理能量,她的崩溃一定是最终能量不支的结果。
遥望着远山顶上连日不开的积云,我也不免想到,据如此之地,举如此之众,倾如此之力,却不能让人生活得舒心,甚至连一个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不好,难道还不该从这难以释解的忧郁里,反省出一些正确的答案吗?
渔 念
近来“南水北调”,将源头在丹江口水库的清水,千里迢迢送到北国,我“饮水思源”,因而想起当年在丹江口库区生活的一段时光。
郧阳地区的五七干校设在当时均县六里坪往北,一块临江的坡地上。照毛主席的指示,干部都要上“五七干校”,受一番劳动锻炼,用那时的一句流行语说,“战天斗地炼红心”是也。轮到我去的时候,已是“文革”后期了。
每期为时半年,人不多,按部队的班建制。我所在的班,大多数人来自宣教口,也有个别人是别的系统的,班长选电影公司经理老孟担任,他说话有点结巴,大家没大没小,不呼名姓,喊他“结巴子”。他热情,风趣,能干,是很受欢迎的人。另有一位特别的人物老靳,官居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这十几个人的一个团队,就特设一个指导员,请他当了。
宿舍当然分男女,同一性别者,则无论官职、级别高低,来自何方,一概住同一房间,睡高低床,吃同一样饭,干一样活儿,这就很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味道。老靳虽然在机关有点“架子”,到这里却端不起来,到出工时,和大家一起拿起工具去干活,吃饭时,拿着碗筷排队去打饭。只是既担任指导员,开会学习时候,一边谈自己的“体会”,一边也存着“谆谆教导”的意思,然而,这并不太引起反感,毕竟人家年长,阅历多,又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
干校种了一面坡地的柑橘,需要锄草、追肥、剪枝,又种了几十亩麦子,到了麦收季节,自然也少不了收割、打场一类的活儿。而我所在的班,还有一项最引人羡慕的活儿,是到库区去打鱼。
这个活儿,不是人人都可以去干的,主力是“结巴子”班长,还有一位姓闻的姑娘。小闻姑娘工作单位是地区百货批发站,却是在库区农村长大的,对这一带很熟悉,水性好,又会打鱼,自然是不二人选。其他便是我们轮换当配角了。
记得我初次跟随着去打鱼,幸福得几乎发晕。一条小船,撑离开岸边,驶入寥廓浩茫、万象澄澈的水面,纵然说是负有任务的劳动,却也免除不了游玩的兴致。偌大的水面,一时看不到别的船只,只有摇桨的咿呀声,和水鸟的啾啾鸣声,穿透水天之间的寂静。这时候,就有一种舒怀长啸的冲动,忍不住“啊——啊——”,向空中大喊几声,也不因杳无回声而扫兴。库区的水碧清至极,又有温润如玉之感,令人真想抱个满怀,加上阳光闪耀不定,就像来到了一个珍宝堆里,目眩神迷。远处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重重叠叠,展现着未知世界的神奇魅力,吸引我们向前。直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大海,而这浮光跃金、浩瀚汪洋的库区,给我的印象是,大海也无过于此。
不仅眼前有如此美景令我们心旷神怡,更富有青春的“小资”情调的是,还有一位美女与我们同船,尽管谁也不会在口头上承认,其实,这一点足以令船上所有男性“渔民”肾上腺素隐隐上升。小闻姑娘确实是一位美女,与一般美女不同的是,她的身上透出特别健康乃至健壮的气息,她的皮肤被晒得红黑,却依然有一种红玛瑙般的莹润,映衬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真有点艳光照人。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七分裤”,在船上干活,她通常会卷起裤腿,那光滑的、圆滚滚的小腿,肯定会让人暗中多瞄一两眼。又何况她的嗓音略含磁性,笑起来却赛过银铃,她一次摇桨时竟然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歌声优美而清新,令我们大为赞叹,看她端的真有“韩英”的秀姿神采,包括指导员老靳的在场者,并无一人煞风景去提醒这在当时是一首“禁歌”。
最令人开心的事,还是出行的任务:捕鱼。我们一般都会把船划到十多里外崖边水阔而深处,撒下网,紧盯着浮子,等鱼儿挂网。如何选定鱼儿出没最多的地方下网,以及掌握起网的最佳时机,“结巴子”和小闻姑娘,无疑都有丰富的经验,甚至是很高的天赋,所以,我们常常斩获甚丰,忙不迭地从网眼摘下一尾尾白条子、胡子鲇,特别是我们最爱吃的“季花子”。这“季花子”,就是我们经常吟诵的“桃花流水鳜鱼肥”中的鳜鱼,俗名“季花鱼”,我们则昵称之为“季花子”(现在则已被誉称为“淡水石斑”了)。将捕捞来的“季花子”,送到食堂,经大师傅稍加盐腌,一油炸,焦脆之下,丰腴细嫩之极,真堪称是一道人间至味。自从离开那里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美味的鳜鱼!比起干校其它班来,我们还享有另一种尝鲜的“特权”,便是在船上煮鱼汤喝。既然午餐赶不回来吃,我们就在船上自备锅灶,像渔民一样,就地取材,烹出一锅浓白鲜美的鱼汤来,大快朵颐。在我的印象中,虽然胡须长长的黄腊丁的味道也很不错,但也绝对比不上齿尖体壮的“季花子”。
绝大多数日子,都是云淡风轻,凯旋而归,唯有一次,“结巴子”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的错误,使我们几陷险境。那一天,先是运气不佳,鱼儿像事先经过会议约定一般,纷纷离场,兀自投网的傻瓜竟然少而又少。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结巴子”决定挥师东征,说是另一处近岸有水草,下网必有大获。岂料还未到达,只见西边的天空蹿上一团团乌云,不一会儿,就将天空占满了,紧跟着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铜钱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我们的小船自然也在风雨浪涛里急剧颠簸,当务之急是将小船泊在一个较为安全之处。幸而,离岸边不太远,我们不顾淋着大雨,七手八脚,总算把船弄靠上岸,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收工的时间,雨虽小了一些,天色却更暗了。我们并不认为库区的四边,会有无人栖居的荒岛,怪兽丛集,让我们面对种种不测,但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如何回得去,或与校部取得联系,免致担心,这很重要。一番紧张的聚议之后,决定四个人,两个留守,两人外出侦查、报信。“结巴子”争着由他出马,但最后还是拗不过小闻姑娘,毕竟她是这里的原住民,对周围更熟悉。报社记者小苑陪同——这两位后来发展出一段姻缘,不知是不是与此经历有关。他们上岸后要去找路,雨天的路又十分泥泞,其艰难备尝可想而知,而我与“结巴子”留守舱中,坐立不安,度时如年。左等右盼,约莫过了两个多时辰,总算看见远处有一、两星灯火亮起,且越来越近,援兵终于请来了。
来的人中,不但有附近村子的干部和村民,竟还有我们指导员老靳和干校的程校长,这么一段时间,他们居然能赶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真令我们不敢相信。原来,我们虽然在水面划行了很久,其实离校部并不太远,翻过一道山梁即可到,而且还有一条近路可抄。小闻他们找到村干部,却不知道干校的电话号码,无法与校部联系,于是又摇电话(当时村里的电话都是手摇的)到公社,公社转县委,县委转地委,才传到干校。干校一干人正为我们着急,一听到消息,立即就赶过来了。见到他们,我们居然有一种大难之后久别重逢的感觉,真真切切感觉到,不是亲人,也可以非常相亲,这种情谊,不是这种“同舟共济”的经历,决缔结不了。
那个时代,从大环境来说,是很压抑的,“五七干校”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物,并因它与极左思潮相伴生,而饱受诟病,我所经历的干校,或许是已到“文革”后期,从改造知识分子转向机关干部锻炼的缘故,倒真没有什么风刀霜剑严相逼。之所以如今我还如此怀念这段生活,实在因为它确实曾经提供过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不但在那个年代极为难得,即在现今,也或者是一种奢望,就像我们驾着一条小船,似乎靠近了某个向往已久的地方,然后又驶离了,从此再也没有靠近过。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