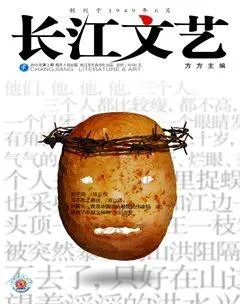淫荡的文本与阶层神话
《人再囧途之泰囧》的成功又一次提醒人们,出国旅游已经成为全民爱好,如果这个目标是泰国的话,那么SPA性爱泼水节泰拳人妖拜佛等等一定是必备节目。《泰囧》令人印象深刻地把商务竞争/观光旅游、老总/卖葱油饼的、美女/人妖、SPA/性、泰拳/功夫、偷窃/偷窥、按摩/做饼、讽刺义/字面义等等进行了嫁接杂糅重组,尽可能后现代地把性爱、偷窃、黑道、绑架、追杀、节日、偷窥、功夫、打斗等等都糅合在旅游/赛跑里,在各种摹仿致敬(比如《虎口脱险》的偏三轮摩托追逐戏)中表达毫无新意的生活箴言——不要过度功利,生活不仅仅是赚钱。各类老旧套路的躁动重复如此淫荡地组织起来,在表现层面上牢牢呼应着人的欲望的无限延伸,《泰囧》因而也是对欲望的摹拟和矫情表演,它最大的特点是毫无特点地投射出大众的欲望需求,所以它同时成为2012年最平庸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泰囧》刷新中国电影票房历史最高纪录的奥秘在于,当中国的导演人人都渴望着不平庸,平庸就成了最不平庸的稀缺资源。
当然,《泰囧》最不平凡的组合还在于徐总和宝宝的组合,“泰国传奇”,其实这个传奇应该叫做中国传奇,或者说是阶层传奇。电影里,徐总被王宝的忠诚天真与对母亲的爱所感动,在盲目逐利的人生道路上翻然醒悟,回到妻子和孩子身边,以一种最为简单老套的方式解决了人生价值问题,更以一种想象性快捷方式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裂与冷漠。事实是,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间的交流只是想象,冷漠与敌意才是现实。草根们不仅从来不曾试图感动有钱阶层,而且仇富情绪严重。因为和电影里的故事相反,宝宝们在现实生活中只会一千次一万次地被富人们所抛弃,毫无怜惜和反省。富人们利用底层为自己谋利服务,一旦需要兑现诺言,却常常中途背信弃义、绝尘而去。“泰国传奇”因此乃是阶层传奇或者说神话。
《泰囧》是以牺牲底层智力、压平底层形象作为代价来成就这个传奇和神话的。宝宝的近乎二傻的忠诚憨直一一成为笑料,但竟然最终产生了价值——赢得了有钱阶层的信任和友谊。这是影片最令人作呕的说教。
在现实社会中,宝宝实在是毫无生存能力之人,影片中宝宝的好运则是以自尊尊严为代价换取的。这个死心塌地一根筋式的人物,完全是个不完全人,他只有对母亲的爱是被许可的,除此之外,他就是一个毫无生气的被阉割的人物——只知道V字手势憨笑没有头脑没有思想无辨别好坏之能力没有知识不懂礼貌不会外语毫无美感的一个被压扁的底层形象。相反,富人拥有家庭子女爱情金钱知识智力品位地位等等,虽处于危机,但后又一一化解,转危为安。影片最后,徐总赠给宝宝的礼物,是一套海滩背景的名人粉丝照,让宝宝彻底成为照片中的那个定格的笑容,旁边是如假包换的范冰冰。问题在于,宝宝就是最大的虚假,空壳的底层人,没有灵魂的仿制品。如此,影片告诉我们,穷人最大的幸福在于定格为明星旁边的那个笑容。这个位置是一个穷人跨入梦想或者说幻象的机会,也是一次富人对穷人的赠予,作为后者使他人性复苏的报答。这应该就是穷人的后现代式的剩余价值了。
《泰囧》是对富人的想象性拯救,一如是对穷人的阉割羞辱与安慰。正如宝宝这个名字所暗示的,一个宠物或者一个未成年的无助婴儿,这才是富人所能接受和照料的草根。
从这个角度看,《一九四二》无疑展开了一幅对立的中国社会图景: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分裂冷漠,刺痛人心。那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无一不陷于濒死的极度自私的逐利/生存之中,各种丑恶源源不绝,除了堕入深渊,整个社会和国家已毫无他路。如果说《泰囧》是对穷人的想象性安慰,《一九四二》则无异于穷人的揽镜自观,谁会不在镜子里的那些丑陋愚昧自私可怜可悲的形象前感到陌生呢?陌生源于拒绝和否认,《一九四二》犯了主体的忌讳。没有人会选择真实的自我形象,或者说几乎所有的认同都是误认。《泰囧》的观众乐于与犯了人生认识小错误的富人认同,一路嘲笑那个傻子,就是不知道他所嘲笑的就是自己的角色。宝宝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人妖化的穷人,源于倒错,只供娱乐。
相反,《一九四二》是一部意欲让穷人进入历史并成为主角的叙事作品。需要注意的是,穷人上一次进入历史叙事后来被证明是个谎言和笑话,它的后遗症就是一脸憨笑的宝宝。穷人的生活与某种社会理想一起是现代文明社会丢弃的不具再生性的废物,它具有废物同等的隐秘性,正确的消费态度是一次性使用和丢弃,因为它的高污染性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威胁。按照穷人使用手册,《泰囧》正确地配置了惟一的属人的生活,就是徐总的生活,再通过宝宝及其情感的过滤功能,成功将徐总的生活毒素清理分离出来,徐总的生活因此变为正常健康的。
《一九四二》以一种悲壮的方式试图正面描述穷人真正的历史遭遇,却意外地偏离了其主旨,甚至被嘲弄为远离穷人的影像:演员都白胖。这是一个借口,其实是因为作品啃得太深,反而漏掉了正题。《一九四二》在努力平衡历史语境和咎由自取这两个灾难根源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争辩和拆解,越到后面甚至越倾斜于后者,灾民之灾是自然之灾、政权之灾、战争之灾,更是人性之灾之恶。但《一九四二》恰恰在人性方面表现无能,无法解答苦难以及人性之罪与恶,这是《一九四二》最后留下的一个核。虽然电影一开始甚至还不失时机地嘲笑了宗教的无能,它自己的无能难道不是在两个小时后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吗?观众的创伤性体验本身没有得到足够安慰和解答,不反过来质疑电影,难道承认自己也吃了两片人肉?
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一九四二》如此真诚地展示了与当今中国社会高度同构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见死不救,《人于囧途之泰囧》怎么可能赢得了来自观众的最强最多的欢呼声?说真话的从来没有好下场,这是常识;匮乏强化需求,这也是常识。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