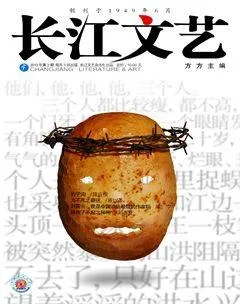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
文学曾经扮演过许多角色,它是屈原涉江时候吟哦的天问,是司马相如呈献帝王的华章,是陶渊明隐庐外的秋菊、大雁和南山,是李白盏中酒香、杜甫眼角清泪,是文人扇底徐风,折起来的小诗,画角墨漾的花鸟,是一场大观园里的太虚幻境,是匕首投枪,是埋葬王朝的朗笑,是旗帜,是解放的思想,奔涌的灵魂,是日光流年里一个无聊的饱嗝,是附庸、边缘、冷影,同样也是许多人的心灵归宿,以及精神家园。
文学可以是很多种形象,不过有点遗憾,幽默并非中国文学所擅长。
这与刘震云有什么关系?因为几乎从《一地鸡毛》开始,刘震云就在用一种不经意的幽默,逗弄着读者的神经。他没有消解文学的沉重,因为他笔下的荒谬、诡异和变形里,同样浸满人性和民族的严肃;但他也没有给文字带上枷锁镣铐,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从《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戏谑与反讽,洞见与智慧,让生活变得轻盈。
是幽默而不是滑稽,刘震云延续着《手机》以来的一针见血,去年不仅推出新书《我不是潘金莲》,甚至在《一九四二》这样的沉重题材中,他也融入了对幽默独特的理解:对待灾难,中国人往往选择用幽默来消解。
刘震云让人笑,笑中有泪,有反思。
一
如果要问刘震云最关注什么,答案一定是“说话”。从2002年的《一腔废话》开始,刘震云就没有停止“发声”。《手机》是在讲话,《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在讲话,到了新书《我不是潘金莲》,为的还是要找回一句话的理儿:“我不是潘金莲!”
原来,刘震云从这中国话里,发现了一个值得不断书写的天机。
范宁(以下简称“范”):您近年来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题材,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再到《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也延续了这一角度,写了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因为一件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而上访的故事,您怎么定位这部小说呢?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这部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四处解释说这不是政治小说,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一辈子也没解释清楚,大家还觉得是政治小说,所以他跟李雪莲是一样的。
李雪莲告了20年状,就是为了一句话——“我不是潘金莲”。当她开始告状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离婚案变成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出现了其他64件事。这个逻辑本来很荒谬,但李雪莲却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结果是无法说清楚。
但是到了最后一章,史为民把这个话说清楚了。本来如果不跟李雪莲遭遇,他20年之后可能是省长,但就是因为两人见了一面,说了一句话,他就成了个卖肉的。他突然明白过来,然后用荒谬的态度对付荒谬,从而达到了自己一个特别伟大的目的,他利用“上访”回到了老家,跟患了脑瘤的朋友打上最后一场麻将。
《我不是潘金莲》是什么小说呢?我觉得是底线小说。写这本小说是为了探讨生活的底线,看它到底能够多荒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喜剧时代,在喜剧时代里荒诞的底线、幽默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比道德底线还要深,在深远里边,还得下去很多。
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64件事说明白。前两章占了63,后面占了1。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离婚和各级政府全无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
生活就像一个深渊,荒诞没有底线。如新闻联播里台上的人在读一个文件,台下的人也有这个文件,但台下的人还是在认真地记。如果我们到这个位置,也会这样参加表演。在面对离婚案的时候,李雪莲就直接去找村长、县长,她没有法律意识,她更相信人治。
真正的生活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事实上,幽默的底线、喜剧的底线,以及生活中所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如果很幽默的话,反而就达到了悲剧的底线。
范:写一部小说大概要多长时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呢?这些灵感或者说是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刘:写的话很快,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但是我要准备思考酝酿的时间要准备三到五年。写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细节、一种景象,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简单,但它背后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
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和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和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和果发生了变化。
范:最近几年,您每部作品的书名都会成为流行语,比如“一句顶一万句”、“我叫……”等等,现在又来“我不是……”。“我是”和“我不是”,是一种对应关系吗?您之前说想把书名叫做“严肃”,是不是因为“严肃”这个词很难流行起来,所以就没用呢?
刘:原本的书名想叫做《严肃》和《太严肃》,有些朋友不太同意,主要是出版社的朋友。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它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
这两部小说有相同之处,书里面的主角都是在路上。也有不同之处,《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非常困难,不是说不出这句话,而是埋藏了很久,找不到听这句话的人。为了找到这个人,不惜跋涉千山万水,一定要找到他;《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这个比在人群中说一句话更困难。
范:这次您讲李雪莲的故事,是因为觉得自己必须写一个女性了呢,还是一种偶然?
刘: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为主,但在生活的逻辑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别的差异已经微不足道了。但李雪莲并不是《我不是潘金莲》真正的主人公,前17万字都是序言,后3千字是正文,真正的主角是男性,史为民。
以前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现实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
范:如您所说,这部小说的结构的确很有意思,一共三章,前两部分都是序言,只有最后寥寥十几页才是正文。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刘:《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公路小说,杨百顺、牛爱国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有停止。《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李雪莲也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利用了前面200多页积累的生活逻辑,成功地打上了一桌麻将。
小说最后把一切逻辑都摒弃了,所有能遵守的规律、法律、规则都摒弃了。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但史为民比我想的还要深:不用纠正,你相信它才会想去纠正它,不用相信,不用纠正,要摒弃。李雪莲还信,史为民是被李雪莲告倒的人,他不信。李雪莲用一辈子没想清的道理,到史为民这里想清了。小说的正文部分,是最见功力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范:“潘金莲”这个意象在故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对李雪莲,对整个故事的发展,有何影响?
刘:李雪莲和潘金莲相同的地方是,都是中国妇女,都反叛。潘金莲反叛的是性,李雪莲的反叛是想纠正一句话,她们的共同点是都没有反叛成功。
如果我们把潘金莲放到历史上,或者放到今天这个历史长河里来看,她一定是一个坏女人吗?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塑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反叛形象。中国从先秦开始,男女在性上是非常不平等的。因为男人可以妻妾成群,但是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潘金莲的形象颠覆了男女在性上的传统。起码从艺术形象来讲,她是第一个反叛的、冲破性束缚的。就是这种颠覆男女传统、冲破性束缚的反叛,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民族英雄。在性这个方面,她起码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
二
几年前刘震云来武汉签售新书并讲座,问到创作情况,他先从身上穿的一件妈妈做的棉袄说起,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说到作品。2012年,他推出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告诉读者“一件事背后其实有10件事,而且第10件事和第1件事不是一码事”。去年底,根据其作品《温故一九四二》改编的电影上映,人们又必须费脑筋去理解,什么叫做“用幽默消解苦难”。
这位《一句顶一万句》的“茅奖”得主,由此获得“中国讲话最绕的作家”的称号。
范:您被称为“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您也曾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思路使然。那您会不会哪天改变这种思维惯性,说话直截了当?
刘:我也经常听到评论说我绕,读我的作品绕,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有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但是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事不绕,但事背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为什么是绕的?因为别的民族就产生过绕的人,国外有人来钻这六十四个管道,但中国没有人来钻。
中国没有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都只是人生的感慨,没有上升到社会、政治体系,没有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胡塞尔、康德、维特根斯坦、尼采……他们负责了这个钻的责任,把人上升到社会层面,中国没有,我就来钻吧,我就来绕吧。
范:知识分子和作家同样是介入生活和社会,二者都是绕,区别是什么?
刘:二者的方式不同,康德的思想和哲学是直面社会和政治,我是直面人背后的情感。哲学家关注的是生活和现实对不对,要进行比较,比较后提出新的概念,而作家是写生活和现实背后,桌面之下的情感,我们的管道不同,但殊途同归。
其实,我否定假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其实是“知道分子”,他们重复、解释别人的观点,没有独立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不会尊重那些以知识分子之名欺骗世界的人。
范:老是这么绕的话,对于您自己而言,生活会不会很纠结?
刘:在生活中,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个是我们村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事到底是弄还是不弄,要不就弄,要不就不弄。
但是你看,越往上走,一个弄和不弄就变得特别的复杂,一层一层地加码。 其实,我们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复杂吗?需要这么复杂地叠床架屋吗?需要这么多管理我们的人吗?需要设计出这么多的东西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和不绕的一个道理。
范: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觉得在这种思维方式里,自己其实是比较适应和舒服的?
刘:我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一点是,我现在能够做到,去听不同的意见。我的生活突然变得更加的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当我们对一件事很糊涂的时候, 我们是郁闷的,当我们把一个事想明白的时候,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是愉快的。所以还是孔子说过的那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早上弄明白,我晚上死都可以。但他没有说,朝闻道,朝死可矣,你让我明明白白活一天,我就非常愉快。所以对身边的每一件事,都要想明白。
范:你的写作风格一直有丰富变化,这种愉快,是否就是您变化的动力?
刘: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写作和艺术的认识心态在改变,这些改变的合力促成了一种“化学反应”,产生了新的观念,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如果说创作道路有100里,那我才走了51里,剩下的路还很长。
三
电影是刘震云的一个关键词。他不仅是多部电影的编剧,还在一些电影中客串演出。如果按照电影的知名度和票房看,刘震云绝对在金牌编剧的行列。但他最想做的还是个好作家,编剧对他而言,“有点难”。
范:您在创作《温故一九四二》的过程中,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历史和真实的关系?
刘:在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但是,就连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过我的外祖母,她是1942年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她竟然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到底说的是哪一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这些亲历者也无法清晰地回忆起来,这就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灾难太多,太频繁,太多了就不容易记清。
除了遗忘本身,温故灾民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让人震惊的。河南人在临死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这个民族一种特别的悲凉。
事实上,历史是永远无法还原的,当你去回忆历史时,真相的百分之八九十已经流失了,所回忆起来的往事是人自己所想回忆的,如果说对过去还有一点可以真实地还原出来,那就是当时的心态。
范:对于灾难,您面对的方式是幽默。幽默不等于轻浮或盲目的乐观,那您是否也会从“沉重”这个角度去审视您笔下的灾难?
刘:我们这个民族,用幽默的态度来消解繁重苦难的话题,我之前也对媒体说过。不管是在首映七千人的体育馆,或者是在我们走过的城市里,我在和观众一块儿看电影《一九四二》时,笑声不下十次。我觉得观众看懂了,唤起了过去人性中,没被唤醒的神经。原来我们还有这样的笑声,这笑声出来的声道、强弱,包括它喷发出来的情感,跟看小品和相声时发出的笑声是不一样的。
哭是一种宣泄的方式,但悲痛至极的时候则会笑,这也是常识,大悲不泣,大恩不谢,大变不惊。这使我想起老舍先生说的一句话,大师说过:“特别想写一出悲剧,但是里面充满了笑声。”
还有一个,小说最后有一个附录的部分,有两条有趣的离婚故事,其中一则离婚声明说两人“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所以经双方同意离异,“从此男婚女嫁各听自便”。大灾荒是当年的主旋律,但主旋律之下,仍有正常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日常生活。“1942”这么沉重的事,里边透着一种幽默的东西,这都是另外一个东西。用幽默的态度对待这种苦难,以往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范: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再到《一九四二》,每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都会引起关注,您也成为备受关注的与电影紧密结合的作家。这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以后在创作中会不会不自觉地考虑到改编、镜头表现这样的电影问题?
刘:我是一个作家,我考虑的是将我的文字变成书。我没有做过职业编剧,只有我把自己的小说变成电影剧本时才做,就相当于把自己家的树做成了板凳,与专门做板凳的木匠还是不一样的。
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作家写作一个人说了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了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说拉大车的话。我在编剧的道路上得分非常少,只走了0.1分。
作为作家,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电影对白和小说语言的区别:电影对白需要很简练,而且要涵盖很丰富的信息,而小说的对话就是顺着说。与导演、演员甚至是工作人员的接触都让我长了很多见识——认识不同的人,学习他们的观点,对于创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创作的素材在生活中并不缺乏,我们缺乏的正是对事物的见识。
范:那您还会在冯小刚今后的作品中继续客串吗?
刘:不会,他们和我都认为我没有任何表演天赋,所以我这条路已经像姚明打篮球一样退役了。
范:除了小说和电影,您还想尝试哪些领域?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经商的刘震云,或者搞文化公司?
刘:我舅舅不是告诉我了吗?“你不聪明,那你就只干一件事,要干得慢一点,退得远一点。”这样就有可能写得更好一点。
有媒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作家,你现在名气不比一个明星差,你怎么想?我过去没想过这个问题,想了想之后,我觉得,一个作家比一个明星的名气大,这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名气,它首先不起源于我,别的作者也比别的明星名气大,比如像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李白写的,不是梁朝伟写的,曹雪芹的名气也比梁朝伟大,他创造的人物,名气也比梁朝伟大,像贾宝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它的传播的范围比梁朝伟和刘嘉玲要广泛得多。
我还是想做个好作家,一个民族需要好的作家,它有时候会是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中国这个民族,是拥有过司马迁、李白、白居易的,这些名字有如灿灿星河。如果说一个民族没有好的作家,流于平庸,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
四
如果因为电影《手机》金句四溢,因为《我叫刘跃进》腾挪跌宕,就认为刘震云是搞笑派的作家,那显然是一种误解。无论是“手机即手雷”的妙语,还是“狼爱上羊”的荒诞,甚至《一九四二》中那些引人发笑的地方,其实底层下包裹着坚硬的内核,残酷、冰冷、感伤。
范:有人说,今年的文学界,莫言在左,刘震云在右。您有这种感觉吗?对于莫言获奖您怎么看?您和莫言都获得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肯定,您觉得这是否是作家的标杆?
刘:莫言获奖之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好多人问我的感受。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烛夜,别人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祝他愉快。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莫言获奖,很正常,如果是阎连科获奖,也很正常。
范:那您肯定也不介意,您登上作家富豪榜这事了?
刘:不介意。如果我的书确实值一千万,那是好事啊,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范:也不介意您所面对的争议和追捧?
刘:(笑)我心里早就磨起了茧。
范:获得茅奖的时候,您说可以下决心买西红柿下面吃。您又说买菜这件事情应该纠结。那您在生活中还纠结哪些事情?
刘:如果在北京没事,我就爱回河南老家,每次都从北京西站坐火车。我发现北京西站的过街天桥自动滚梯是封闭的,我们的同胞每天大包小裹,满头大汗地爬楼梯,我感到很痛心也很纠结。滚梯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的,为什么我们做不了主?
做了主的人一定不会坐滚梯,都是车直接开到站台上。正因为纳税人一直沉默,我们才受到这样的对待,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说话,监督这些管理滚梯的人,把工作做得更好。
范:创作与现实贴合得太紧,您会不会担心失去了观察的深度和余地?会不会担心读者只看到了一个故事,而失去了思考的空间?
刘: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就是读者。我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写《一句顶一万句》,过去写作品的时候,觉着自己是个作者,因为我的见识比你好,我的见识更深一步,其实,作者的见识是永远无止境的。无形的见识一定更接近根本,小说为什么要逼近真实和根本呢?根本是个大道理。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一定是一条“大道”,能延伸几百年、几千年的“大道”。它一定是特别根本的,是人类人性、情感、生活等各个方面综合出来的“大道”。
作者永远是有偏颇的,永远是主观的,而主观的东西是最站不住的。所以,得把主观还原成客观。你不是诉说者,你是一个倾听人。你的写作不是要变得复杂和绕,而是要变得特别简单,写作就是聊天,就是跟小说中的人物聊天。
比如说这段时间我想跟李雪莲聊聊,想跟史为民聊聊,想跟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储清廉这些人聊一聊。在聊的过程中,人物自己一定能说出你不曾认识到的东西。而且这个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认识化解了,化解成对整个生活的认识。
这是一种无形的、没有具体化的认识,而这种无形的认识是从人物关系的缝隙里透露出来的。首先,它跟所有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混合的产物,这种混合出来的真实,与生活里的任何真实都是不一样的。但这种不一样,却也更接近真实,同时也更感人。
老史在正文里边为什么必须要赶回去,他是要赶回去打圈麻将,朋友得了脑瘤,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可能是最后一场麻将了,那好,既然是世界上最后一场麻将,那就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刻。我们看来,其实没什么大事,但对老史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大事,他必须回去。于是他用了李雪莲的办法,李雪莲是要一直走向大会堂,他是反方向走,走回到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身边。这个麻将,此时就不是生活中的麻将了,这种无形的情感和关系,也就变得特别感人。
范:您写了很多河南人,有没有考虑写别的地方的人?比如湖北人?对于湖北人怎么看?
刘:河南,特别是延津,对我的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塔铺》就是延津一个具体的地名,传说这个塔没顶,是神仙经过时袖子把顶拂掉了。“故乡系列”三本书也与延津有关,《一句顶一万句》有两章是《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
这种呈现有直接性,也有间接性。河南文化对我这个作者的影响,不只是地名,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河南人特别勤奋,我每天睡觉时,外婆都在纺棉花,纺车一转,麻杆就会亮一下,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只睡几个小时的觉。河南人特别能吃亏,特别幽默。很多人问我幽默从哪来,我说就是从河南,从河南人来,这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是生活态度。
直到现在,有人说20公里,我就马上想到我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是用这个距离来丈量世界上的距离,它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考习惯。羊肉在河南一定会做成羊肉烩面,在西安就要做成羊肉泡馍。开封是六朝古都,洛阳就是九朝古都。
我对甘肃也很有感情,我在嘉裕关东风附近当过四年半兵,对当地的气温和风速有切身的体会,风很硬,气温低。甘肃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但其实,无论是河南人还是湖北人、农村人和城市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人。我乐意写家乡的人,河南给了我很多,河南是我创作的根。我书里的人物可以是河南人,也可以是湖北人,湖南人,是本质的人。
范:您会在微博上发掘题材或灵感吗?
刘:我平时也会看微博,包括我小说的结尾,也是汲取了微博段子的灵感,倾听很重要。不仅要倾听网络上别人说的话,更应该倾听作品中人物说的话。
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微博对中国民主的推进作用非常巨大,尤其是我的好朋友陈彤所在的新浪微博。一方面是开新浪微博的人,包括每个使用微博的人没有想到的,微博最大的好处是,让过去少数人知道的事,很快多数人都知道了。云南监狱里,一人躲猫猫死了,通过微博,马上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重庆选美,美不美本来都是重庆的事,最后变成全国的事,由角落变成整体,这个是我们之前不曾想到的,我们总以为,是由社会的改变,推动社会的改变,没想到科技推动了社会的改变。
另外一个,你的发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别人的手里,微博上牢骚巨多,反对的巨多,我觉得这是民主的开始。
范:新生代的作家中,您有没有比较看好的?
刘:很多作家都很好,郭敬明写的东西和我们这一代作家非常不一样,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世界,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他用郭敬明的角度写。韩寒的博客我爱读,笔锋非常犀利,笛安则是从大家熟悉的地方,挖出了大家没有料到的东西。
范:您平常的生活也崇尚化繁为简吗?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
刘:我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跑步,然后写作,从来不熬夜写作。在书桌前是写作,更重要的写作是我在外面行走时、和朋友聊天时,这时我是在思考,思考是比写作本身更重要的写作。接下来我想写一本书,《一地鸡毛》的续篇,写小林变成老林后的故事,书名我想可以叫作《鸡毛飞过三十年》。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