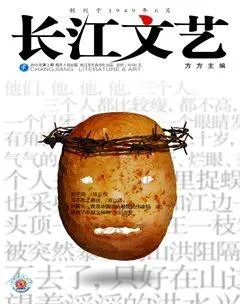消失的领袖
1
秋去冬来,我在这个不大不小的邮政部门也混了一段时日。单位一年一度的贺卡营销攻坚战打响的时候,我恨不得变成一只小龟,把头缩进硬壳壳里,不管外面的纷纷扰扰和风吹雨打。这不是欺负咱外地人没关系没门路嘛!牢骚归牢骚,发完牢骚,媳妇说,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去摆摊!媳妇就是媳妇,总能在你绞尽脑汁也无计可施的时候帮你把出路找到。而我竟然也同意了。在社会上混不容易,有人靠天资聪慧成功,自然也有人靠勤勤恳恳起家,从外地投奔于此的我,只能是后者。于是乎,周末的学校门口成了我和媳妇的战场。我俩逮了个空位,把色彩斑斓的贺卡铺了一地,生活也随之色彩斑斓了些。
临近中午时,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广东湛江的电话。对于陌生来电我一向敬而远之,可是那天中午,当手机显示来电位置是湛江时,我的心突然一紧,总觉这个地名有些许的熟悉,难道是我投稿的刊物打来的吗?湛江能有什么文学刊物呢?
我犹疑地按下接听键后,对方没问我是谁,也没自我介绍,上来就是一连串疾风暴雨般的疑问:K哥哪去了?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你们有多久没聊过了?
电话是益智打来的。他的声音还挺好听。经他一问,我才猛然间意识到,我有半年没在互联网上遇到K哥了,自打他上次说要去北漂之后。而我和益智,我们俩更是有近一年没像苍蝇扎堆一样聚在一起讨论K哥了。没有K哥的日子里,我们竟也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竟然过了这么久。
风从我头顶呼啸而过,把垃圾吹得到处乱窜。每当这时,我就会想,上天一定长了一双眼睛,在那双眼睛里,我们,其实和地上的垃圾并无差别。唯有K哥,他不是垃圾。我同时也相信,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的K哥的。
下面,我来讲讲K哥。
我从没见过K哥,但我却自信地认为我是了解他的,从我阅读他一篇又一篇精彩的小说开始。2008年大学毕业之前的那段岁月,我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随着大学毕业的临近,我的文艺范儿不断升级。在完成了撰写论文和签约工作这两件大事后,我们这些别人眼中的师哥师姐们都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臭狗屎。这其中,有成天晚出早归、让自己的荷尔蒙尽情释放,然后再在镜子前顾影自怜的L;有把扑克牌摔得啪啪响,试图让人注意到他的存在的J;也有拿着相机晃悠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叶子上的露珠他都想与之合影的Q。当然也有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生活过得没有日夜之分的懒猪。我懒得梳头,即便头发已经长到我肩膀以下;我也懒得刮胡子,好像留个胡子挺有艺术气息;我甚至懒得正经八百地洗脸,反正早已没课可上了,谁还会在意我毛孔是否粗大、青春痘又多了几颗呢?我只会叼着小烟,然后在一个个烟圈中告诫自己要面对现实。而现实就是:我的梦想濒临破灭了。
大学四年里,我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像韩寒、郭敬明那样的作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开着跑车,每天清晨被大把大把的钞票砸醒;不用关心粮食,不用关心人类,也不用想那个“你”,因为那个“你”正坐拥在我怀,娇嗔地冲我撒娇。然而,悲催的是梦醒过后,我通常发现自己坐在乌烟瘴气的网吧里,可能还有只硕大的蟑螂正从我脚边逃窜。我写了四年,仍旧连学校门也没写出去。我垂死挣扎着,决定把别人用于午睡的那段时间交给图书馆。
K哥就是在图书馆期刊室的某本国家级期刊上蹦出来的。那是一篇讲述“三角恋”这一原本庸常的话题的中篇小说,作家K通过讲述一名大龄转业军官的几次情感遭遇,把不同的几个人物性格描摹得恰到好处,把城市的浮华和躁动讲述得淋漓尽致。最难能可贵的是,作家的叙述一下子就让你想到海明威、契诃夫、卡夫卡这样的外国大师,你能感觉到他深谙小说之道,成就远在当下多数青年作家之上。这种诱惑使我自然而然地翻到了标题页的作者简介,一张透露着纯真气息的脸出现在我眼前。半身相里的K留着小平头,穿着一件军绿色短袖T恤,背对大海。他目光炯炯,神情干净如秋天的天空,他颧骨略凸,一身干练,精气神足以震慑任何与之初次相遇的对象。
作者简介:K,本名王K,1970年生,江苏籍。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西北某部队服役17年,现驻守西北某边防连。代表作品有××、×××等。近日,长篇小说××、×××出版。
38岁的军人,帅得堪比任何港台或日韩明星,你很难把“作家”这一职业与之产生联系。我需要强调的是,他可不是随便写什么畅销文学的伪作家,从他发表作品的刊物便能知道,这是在纯文学写作领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照片上的K那纤瘦而精干的身材,以及古铜色的皮肤,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以前我心目中作家的形象,比如大肚腩的M,抑或萎靡的Y和高傲的B。
我被他“迷”住了。
这话听起来很暧昧,可我不得不承认事实即是如此。我赶紧跑到阅览室那一个个抽屉中去找其他的一线大刊,一本一本翻,果然又在别的刊物上见到了K的作品。那个下午,我捧着发表K作品的一摞刊物,看得精神抖擞。
走出图书馆时,早已月上柳梢。校园里有人拿着酒瓶,有人搂着美女。在糜烂的路灯光下,一个念想从我脑子里跳了出来:我要找到K。于是,我又改变了行进路线,奔着网吧去了。我打开一台电脑,点开BAIDU页面,键入关键词:作家,K。点击确定。万万没想到,第一条,竟然就是K的博客。沙漠寻金,我刚一进去,竟真被我挖到了宝藏。
K博客的第一篇日志,是一篇征稿启事。写得很简单:
征稿启事
各位朋友,我是K,我已调任C军区任×刊物编辑,欢迎军内外的朋友踊跃投稿,我刊以发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为主,兼发优秀的社会题材。投稿发至如下信箱:……。
看看落款时间,三天前。这么说来,K已经从边防连队获得了升迁,由边防官兵作家K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作家K,这让我心底里对他产生的兴趣打了折扣,可随之而来的一个想法又似乎立刻拉近了我与K之间的距离:何不把我四年来写的一些小说选几篇自己最满意的投过去试试呢?
2
我在QQ上问益智,你和你女朋友咋样了?
益智说,唉,一言难尽,估计快黄了。
在之前的一次聊天中,益智向我讲述了他的“情史”:他被昔日的好哥们拉出去喝酒,喝醉了酒的益智又被强行拉去“按摩”,可在小姐脱去他裤子的时候,他猛地清醒过来,赶紧提起裤子走人了。没醒酒的益智犯了浑,回到家就一五一十地把跟哥们出去“按摩”的经历如实讲给自己的女友听了,他本以为他的坦诚会让女友对他刮目相看,甚至对他不为女色所动的精神赞赏有加。不成想女友根本不信。任他跟在屁股后头反复强调“我们真的什么事也没发生”,换来的仍旧是两记响亮的耳光。女友哭喊着夺门而出,他方才彻底清醒过来。
这次八成是要分了。益智无奈地说。
不至于的!我劝他。既然事实真的是“只脱了裤子”没发生别的,那就好好和嫂子解释解释。
我一个北方人,只身一人混在湛江,容易吗我!这两年我相亲无数,好不容易这个是谈得最顺、时间最长的,已经谈半年多了,我们打算年底就谈婚论嫁了。……他跟我滔滔不绝,差点快哭出来了。难得他如此信任我。
才谈半年,你还敢那么实诚啥话都和她说啊?看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我说。
唉!什么好不好的,只能说相处得挺顺的吧。益智补充道。跟你说句实在话,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K哥。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明白。我想他之所以想到K哥,决不是因为年近不惑的K哥尚保持单身,而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些没意义的放纵之事的时候,K哥似乎总在哪里提醒着我们。那种感觉,虽有束缚,更多的却是温暖和亲切。
我沉默了。
我俩都沉默了。
沉默过后,益智说,好久没见到K哥了,但有些东西一直都在,他在提醒着我,我好像变了。
他有些语无伦次。但是我理解。即便他什么都不说,我也一样理解。K哥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在我第一次向K哥的信箱投稿的一周后,接到了K哥的回信:
“弟弟,你给我发的作品我都看了。其实我蛮感动的。从发表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你这几篇作品都显平淡了些。平淡不是问题,问题是平淡中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锐光,所以我暂不送报你这几篇作品了。但我觉得你是细腻的,也有敏锐的自觉性,所以我希望你不断写下去。既然你喜欢我的作品,你就应该相信我,你能行。”
看到这样一封信,我激动得直颤抖。我关上电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沉思了约莫一刻钟,然后就掏出了剃须刀,对着镜子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然后直奔理发店:老板,来个小平头。
理发师手起刀落的同时,我的脑子里的写作素材有了井喷的趋势,仅仅半个小时,我基本想好了三篇小说的框架。理完发,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日记本奔自习室跑去。
2008年,是我最百无聊赖的一年,同时也是让我把人的丑恶嘴脸看得最真切的一年。从那一年开始,我一向敬佩有加的辅导员竟然变成了一个对签工作签得又好又快和迟迟签不出去大有砸手里之势的同学区别对待的势利眼。她对考进省里即将成为公务员的同学那副摇尾乞怜的嘴脸和对我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骄傲姿态形成鲜明对比。我曾在网吧里、在厕所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千千万万次地诅咒她。
委屈中带着批判和愤恨,使得《到处是天堂》写得极快。几天后,我便把那篇名为《到处是天堂》的短篇传到了K哥的信箱。K哥第一时间回复了我:
“弟弟:抽空把这个小说用心修改一下再投给我。这个小说的感觉很不错。就作品本身而言,也基本没有问题。但我还是想给你提点修改意见。小说写年轻人初涉社会时开始目睹社会的黑暗,由此愤怒和迷惘。但是要知道社会本来就是两面的,既有阴面,又有阳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如果没有阴暗面,就显示不出它的丰富性。问题在于,一个写作者如果过分针对社会的阴暗面,对它指责不止,这种写作心态本身就是不成熟的。因为不是还有阳面吗?它自始至终也横亘在那里,我们不也是在感同身受吗?为什么不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和激赏呢?……”
K哥加了我的QQ。他对我说了很多由小说牵扯出来的题外话,他说,当你对生活给予的东西不满时,应该想想自己是否有资格得到更多;当你抱怨生活时,你应该想想自己是否做到最好、能否对得起自己。人,不该过分抱怨生活。面对生活,我们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强大。
很多年前,当这样的说教从父母口中说出时,我心里会有一百个不服,我甚至敢回屋就摔东西或者夺门而去。然而,当它从一个陌生人的口中说出,我却一点气愤也没有。这究竟是时间带来的成长改变,还是和远近亲疏息息相关,我说不清。像一句台词说的,“成熟的人往往晚熟,骄傲的人又很急性。”我那时有些意识到,辅导员口中的话未必全无道理,就比如她说我们这些大学生、这些天之骄子太眼高手低。而给予我这样提醒的,是K。我隐隐发觉,无论我们成长到多么成熟,总得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克制”着你。起到这个作用的,正是偶像的力量。
茫然中,我有些崇拜起K来。
在K哥的鼓励下,我反复对《到处是天堂》进行不断修改和完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隐约在朝着某条未知的道路前进着,而这种感觉,是K哥给我的。
3
益智自然是笔名,我不知道益智的真名。我与益智的相识也源于K哥。那时的K哥像一盏炽热的白炽灯泡,和其他几位同样名气响当当的70后作家一道照亮了一个有名的文学论坛Z。而我和益智恰好是Z论坛的会员。我俩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益智是论坛的活跃分子,常常有事没事去跟个帖,也时不时贴篇自己创作的作品上去,而我则相对走马观花,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潜着水浏览帖子,很少发言。
恰巧有一次,K哥贴了一篇自己的小说上去,那是一篇K哥的标签式题材——沙漠士兵,写他们因常年驻守边防站岗放哨的孤独和危险而导致的另类精神世界,从而在那种歌颂军人的主旋律军事题材作品中独辟蹊径。显然,官兵的精神世界中的细枝末节是被放大了的,不仅如此,小说还带有很强的意识流色彩。
不成想,这样一篇小说竟使论坛燃起一片战火。舆论两边倒。喜欢的跟帖大赞溢美之词,不喜欢的则提出诸多质疑。看着益智针对某些评论发的大段大段的跟帖,我也按捺不住了。双方由一开始针对作品的交火渐渐上升到道德层面,竟有人说作为刊物编辑的K哥不看重新人,专爱发关系稿,还说他高傲,没写出什么好作品却靠跟编辑套近乎把自己搞出名。这些人越说越离谱,渐渐升级为人身攻击。天呐!他们在攻击K哥,我简直不敢想象,针对这些不着边际捕风捉影的评论,K哥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忍无可忍。在我心中写作功力堪比世界级大作家、假以时日绝对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K哥竟然会在人品问题上遭人质疑?一位光明磊落、正直坚定的解放军军官竟然会被人身攻击?我立即和益智结成了统一战线。益智也从我的跟帖中读出了很多我俩对K哥作品一致的见解,像找到知音一样在论坛里给我留言。继而,我们给对方留下了各自的QQ号,没多久,我们又在QQ里向对方公布了各自的手机号。我们并肩而战,对攻击K哥的人展开了一轮又一轮还击。
从此,K哥成为我和益智在QQ上每次相遇必聊的话题。我们一般是从某篇作品开始,即便有一方在电脑前忙着工作隐着身,只要另一方一提起K哥,马上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K哥的早期成名作都是沙漠官兵系列,都是写边防士兵的精神生活的,那篇《旱死的鱼》,当年被N个选刊选过。益智说。
是吗?我还没看过这篇呢。我赶紧去看。……
K哥的作品标签太明显了,和其他作家风格迥异。写边防士兵,这一题材很有个性,很有写头。
还有一类是女性题材。
对,没错。
他的语言很有江苏作家的特色,语流感很强。
是,是。你看没看过那个叫《长空》的中篇?我最喜欢那个。还有《时间的海洋》。
……
我们就这样交流着。
有时,我们会把K哥早期的作品翻出来和新作进行对比,体会着他作品风格和写法上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聊K哥的同时不忘聊自己的写作,比如,益智说他又把他的哪篇作品传给K哥看了,K哥给了他很多意见。比如,我说我又把我的哪篇作品发给了K哥,K哥甚至向某某刊物作了推荐等等。无数个夏夜,我和益智两个人,我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却不能忍受停止对K哥的想象和构筑;无数个冬夜,我们忍受着寒冷忍受着饥肠辘辘,却无法忍受放弃对K哥的向往。
渐渐地,在K哥的指引下,我们俩都发表了自己的作品,我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改变。
现在,当K哥从我和益智的视野里消失的半年后,我们再次聚在一起回忆有K哥的日子,回忆K哥带给我们的一切。
我问益智,你还记得第一次和K哥聊天的情形吗?
益智说,当然记得。当时我为他写了一篇一万字的评论,通过QQ传输文件给他。我以为他看了会很激动,甚至会推荐到他任编辑的×杂志的文学评论栏目发表。你知道的,对于像我这样搞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能在那样一本刊物上发一篇研究论文得有多么了不起。可是,不想他看完之后就立即打电话过来说我把他写得太好了。他客气地向我表达了感谢,然后让我把那些不符合实际的吹嘘统统删掉。他让我懂得了做评论、做学问跟写小说一样,都得脚踏实地。
益智补充道,需要强调一点,他的声音很好听。
我说是啊,他的声音很柔和、很纯真。
益智说,你也记得他第一次和你聊天?
我说,当然啦!这辈子我都忘不了。那是我即将毕业离校的前一周的一个傍晚,我和寝室哥们L反锁着寝室屋门看毛片,另外两个哥们J和Q则围着电脑打着三国杀抽着烟。K哥打电话过来问,你给我的那个小说《到处是天堂》改得怎么样了?改完了吗?我当时蒙了,脑子一团浆糊。勤奋需要坚持,懒惰则永无止境。他对我提出修改意见后,我一直思考着如何修改却迟迟没有下笔。电话那头的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我们不是缺稿子,修改不了就算了,自己都对自己不负责别人怎么会重视你,他说。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一刻,仿佛突然到来的曙光将要熄灭,梦想的大门马上将要关闭,我害怕极了。我隐约觉得K哥有些生气了。他本来没必要生气不是吗?他并不认识我,我们没交情。
我离家来南方读大学后,第一次有人用那样的语气对我说话。我向益智解释,撒丫子惯了,惯出了一身毛病。
是啊!益智感慨道,K哥就像一座伟岸的山,时刻立在那儿。他的正直、他的认真、他不断奔跑毫不松懈的那股子劲儿——我们差远了。
曾经,K哥就像蛛网正中间的那只大蜘蛛,网着我们两只小苍蝇。我们心甘情愿地冲他扑棱着翅膀,乐此不疲。然而,我们尚未完全接近看清他的模样,他却突然长了翅膀飞出了我们的生活。蛛网残破,我们被蛛丝牵着,悬在半空。
4
曾经,网络的黑色大海中,K哥多数时间都像一片美丽的珊瑚,低调地隐藏着他的身影,隐藏在海洋的最深处。偶尔浮现出来,又像个孩子一样显摆着他的才华,这样的显摆带着强烈的戏谑性质,又经常是与文学无关的。在刚加他QQ时,可能因为已经有了之前论坛中的交流作铺垫,彼此也熟悉了,一次K哥向我发了个“偷笑”的表情,接着传来一曲他自弹自唱的《鸿雁》。
被重新编曲,用K哥的歌喉加以诠释的《鸿雁》,以悠扬的蒙古长调开头,让被霓虹灯围绕着的我一下子置身茫茫戈壁、茫茫草原之上。空阔辽远的大地上,一只鸿雁展翅翱翔,它的脚下,驰骋的蒙古骑兵——K哥,正快马加鞭奔跑过来。
虽然忙碌的K哥平时很少在线,但这并不妨碍我和益智对他的谈论,我们丝毫不懈怠地议论着K哥,成了每次碰头的功课。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K哥的新作以声波的速度在诞生,我们却用光速在谈论品评着,他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我们的速度。
在谈论过K哥的作品之后,我们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K哥这个人本身上来。我们知道的信息正如K哥的作者简介中提到的那样:1970年生,江苏籍。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西北部队服役17年,曾在边防站岗放哨。可是这些信息对我们的需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偶像,他的17年怎么可能就用一句“曾在西北部队服役”而草草概括呢?我们举双手反对。
有一段时间,我和益智不遗余力地去搜罗着关于K哥的信息,并且乐此不疲。某天,益智会突然揪出一篇K哥某年某月发表的博客告诉我,K哥某段时间曾在北京呆过;第二次,我又会根据某家报纸曾对K哥的一段访问告诉益智,K哥绝对在华中地区的某所以培养基层指挥干部为主的军校学习过;再比如,我们都从K哥的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中猜测K哥可能是专业兵出生,学的报务专业。益智还告诉过我,K哥应该是在北方的某片区域当过连队指导员,但是没几天他又会说,不对,他应该是当过宣传干事。可是,我怎么记得在哪看到他当过打字员呢?
我们交流的信息真真假假,只有部分我们通过直接给K哥留言询问或者从QQ聊天中得到的,我们才能准确地下定论。其他一概未知。
我们像两个追星追到发疯的狗崽子一样,恨不得连K哥有哪些生活习惯、作为一个部队文职干部军事技能如何这类问题都想知道。崇拜这种感情让我们两个大男人变得很三八。K哥像一个圆滚滚的洋葱,我们一层一层地剥。剥到最后,往往会刺得我们直流泪。
益智说,K哥太不容易了,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我应和着,是啊!又问益智,你说是不是正是因为K哥经历了太多,看淡了很多东西,所以才至今单身;又是不是因为他至今单身,他才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篇什?
没人能给我们答案。
我紧接着问,你说K哥那么温和、内向的一个人,他怎么经历过来的呢?
是啊,我也纳闷。——益智顿了顿。可是谁说K哥温和且内向的呢?
是啊。没人说。我发现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在臆测K哥,从他说话的含蓄,从他打电话给我们说稿子时的慢声细语,从他一向低调谦逊、从不张扬的态度,从他思想的非主旋律和无政治性,我们猜想,如果庄子活到今天,一定就是K哥这样的。
然而,庄子又怎么能在经过那么多的人生坎坷后呈现辉煌呢?现在,坐在办公室里看稿子的K哥较之驻守边防的K哥,难道不是一种成功、一种入世吗?这种入世的结果究竟是K哥主动争取来的还是被动接受到的呢?无数个疑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我们对K哥,总是有这样或那样无比深奥的疑问。这些疑问都快把我们变成神探了。
益智说,军队是最讲厚黑学的地方。
他说这话我就不爱听,好像“厚黑学”三个字侮辱了K哥。但是那么多疑问又确实困扰着我,使我无法把K哥的人生拼凑完整。
直到有一天,益智传来一篇自传性质的文字。
这篇文字按顺序叙述了K哥参军后那十年的经历。
那年,参加高考补习班的K在回家取行李的途中遇到了他们县人武部的C——他父亲的同学,在C的倾情动员下,K参军入了伍,成了一名海军战士。入伍是在辽宁大连,在海边一座座石头山的山坳中间,K成了一名学习通信专业的专业兵。
新兵结束后的K未循序干通信专业,而是去了胶东半岛的某部队,成了一名保密室的打字员。训练之余的K,在部队为备考军校的战士临时搭建的简易营房中学习了半年后,出乎所有人预料,成功考进了华中地区当时众所周知训练最严酷的两个陆军学校之一。在学员队里,由于K体重最轻,身高几乎垫底,所以靠他的笔杆子和他灵巧的歌喉在学校里谋了点职务,顺利毕业。
毕业后,K被意外分配到东北,在气温近零下二十度的操场上训练新兵。当时,疲于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的K,常觉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一度陷入人生的低谷。最终,他还是靠歌艺取得转折,开始了长达一年八个月的俱乐部干事生涯,组织晚会、在环码头部队官兵的歌唱比赛中示范演唱、多媒体教学,带电影组的战士放电影,用带着明显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当码头播音员等等。由于性格使然,受不了一成不变生活的K,最终在俱乐部主任多次暗示其将关系转到俱乐部时,突然要求回到原来的训练大队。
K军旅生涯中最不堪回首的时光由此开始,他遭遇了一段完全不被待见的时光。那年那月里,连个别自认为有关系的手下都敢对他歪嘴斜眼,使得他被“发配”至一个山沟沟里。那年深秋,境遇糟糕透顶的K就常在连队后那些连绵的坟场中转悠,他用不停的思考、用生理的恐惧抵销他内心的愤懑、烦躁。自此,他爱上文学,时常通过各种渠道搜来书籍在坟地旁阅读。
后来,K遇到一贵人,帮他调动,一年后,顺利调回胶东半岛。
写到这里,K哥感叹,假使那时未调出,一直呆在那个山沟沟里的连队,那么他无法想见今后的人生,极有可能就以一个基层部队指挥员的身份在那山沟沟里了此余生,结婚生子,与“作家”无缘。
读到此处,我心中纠结如刀绞,无法平静。
后来,K哥夜以继日发愤地写了几篇作品,投给军中某政工类杂志。那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他的文章。后来,工作再次出现调动要离开胶东半岛时,他专程去那杂志拜访编辑老师。老师想得极其周到,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于是,在新的单位中他顺利留在了机关大院。
……
至此,我们算是把K哥的人生拼凑完整了。后面的我和益智都知道,K下基层锻炼,因写作才能被调到北京某军报见习,后又调到西北,终因文才出众被调至西北某部的政治处任C刊编辑。
看过之后,我和益智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跟K哥相比,我们的人生悲惨得就像一张被团得皱巴巴的白纸。不,被团得皱巴巴的白纸尚且有颜色和体积,我们则没有。我们就是一层透明的保鲜膜,没什么重量,单薄得可怜。
益智说,我想去C城看看K哥。他说这话的同时,发了一张难过的表情。
5
我还是在QQ上问益智,你和嫂子怎么样了?
他“偷笑”着回答,和好了。
我“偷笑”着回复,早就猜到了。咱俩这素未谋面的网友都没分呢,你和你那如胶似漆的老婆还能就轻而易举地分了?
哈哈。他笑。
生活真是有趣,我和益智、我和K哥都是素未谋面的网友,仅此而已,却像是有根线将我们串联起来。世界之大,每天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分分合合,K哥跟我们的暂别仅是这其中的一种,也并不算特别,想想有些伤感。
而我和益智,之所以还联系着,完全要归功于K哥。
正如益智所说,他真的去C城看K哥了,这一度让我嫉妒不已。他去看K哥了,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去看K哥呢?在益智去西北的那半个月,我做了好几次梦,那不是梦,而是些回忆片段的拼凑。我梦到大学的网吧,梦到开着跑车的作家,梦到在坟头拿着手电筒读名著的K哥,还梦到“什么也没做”“提着裤子跑”的益智,最终这些梦定格在西北苍凉的夜空中,变成了那首《鸿雁》里的一个个音符,飘荡着、飘荡着……
从西北回到湛江后的益智在网上告诉了我三个让我无法相信的消息。
益智在QQ上对我说,我终于见到K哥了,但是有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你说。
说实话,第一,他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帅。他个子很矮,这是半身照片上看不到的。
我心想,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这对我来说,似乎早已不重要。K哥带给我们的震撼早已从外表突破至精神了。但是紧接着益智带来的第二个消息让我难以接受,他说,K哥的左脸完全毁容了。
简直难以置信。我无法想象毁容的K哥是什么样子。他定格在我脑袋中的一直都是那本杂志上的照片,精神抖擞的K哥漫步在茫茫海滩上,面庞洁净。在我的心中,我们的K哥是不该有任何瑕疵的。他快四十岁了,他还没找到另一半呢,怎么能毁容?
关于K哥单身的问题我和益智也谈论过。在我和某一女子定下婚约后,我在网上对益智说,本来我不该这么俗,可是,当我即将走向婚姻的殿堂的时候,我就愈发替K哥感慨。你说他为什么还不找另一半呢?我突然觉得他应该经历一切的一切,这一切里,自然包括婚姻。
益智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他选择单身那是他的选择,只要他自己开心。
我一直也是这样想的。可现在我要结婚了,我就觉得K哥也应该结婚。我左右不了自己不去那样想。K哥应该是完整的。
我追问益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回问我,你听过“12·5纳兰火灾”吗?去年12月5号。说着,他贴了一个网址给我。我点开:
12月5日中午,内蒙古纳兰旗发生草原火灾,当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上山扑救。下午3点10分左右,正在处理余火时,突起大风,部分扑救人员遇难。其中包括15名解放军战士,5名群众,2名林业职工。目前仍有200亩草原在燃烧。(×××报,2011年12月5日)
你是说——?
是的。益智打断我,K哥去采访了。本来他可以不去采访的,他好几个同事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去前线采访,可K哥说他懒得去构思那些理由,况且他又是单身,除了坐班外也没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就去了。
益智说,他遭遇了危险,二级烧伤。
第三个呢?
K哥年底就转业了。
转业?我不敢想,脱了军装的K哥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当我看到了他的那半部自传之后。我想,K哥自己也无法想象他脱掉军装是什么样子,就像那些演老革命军人的电视剧一样。我发现,我对K的想象,总是那么悲壮、那么浪漫,那么不具有这个时代的时代性。
然而益智对我说,转业是K主动申请的。
我看了看日历,距离年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我怕是没机会见到K哥穿军装的样子了。
我的伤感到了极致。
6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不知从何时开始,细究起来,或许就是从益智见到了K本人之后,我发现,我们不再聊K哥了,转而聊起了我们各自的生活。但我们都知道,K哥始终默默潜伏在我们的QQ好友名单里。
益智一度声称他被K哥的半部自传影响了,他说他想去经历那种惊涛骇浪式的波折生活,他说,我们的经历太少了不是吗,有点白活的意思。他说首先得从换工作换环境开始,他还列举了他的计划,比如从甲地到乙地再到丙地最后到丁地,到丁地的时候他说他就变成一个靠做小买卖赚钱的流浪者了。他的想法,我举双手赞成。但一个研究生,不干点正经事跑出去流浪,我又有点不相信。终于,他说完这话的一个月后,就找了女友,又没多久,他似乎就被乖乖地驯服了,甚至都不常上网了。
而我的生活,还是老样子。
K哥转业后的一年里,他没做什么除了写作以外的工作,我们网聊的频率已经很低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北漂了。而那时,我和妻子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我们的婚礼。听说我要结婚了,他很高兴,说要送我一盏台灯。他说我在京东网给你订了一盏台灯呦,愿它照亮你的写作之路。
我突然很伤感,距离我们认识K哥,已经四年了。四年后,我和益智都已经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作品,都在各自泥潭一样的生活中苦逼地挣扎着。我们紧绷着一根绳似的不敢懈怠,因为K哥。可K哥竟要去北漂了。那将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我想象不到。K哥说他去北漂了,我猜他就真的是去漂了。同样的事得看是从谁的口中说出,如果是从同学L口中说出,我会认为他是在放屁,这么些年,他说过他要出国,还说过他要出家,说过要买别墅,又说过要买奥迪。可是,到底一件也没落实。他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者。要是从同学Q口中说出,我只能当他是作秀。一个腰缠万贯、一向以物质享受为理想的富二代,吃穿不愁,去北漂?这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理想博你眼球的秀又是什么呢?可是,K哥却不同。他说去北漂,那就一定是去北漂了。
我把K哥送我的台灯摆在了我和媳妇的摊位上,下晚自习的学生们涌动着,我俩却跟空气一样被视而不见。K哥说要照亮我写作之路的台灯正照着一摞摞的贺卡。一万元的贺卡计划,我都不敢想,也不用想,我能做的也就是一张一张地卖。生活容不得我抱怨,它也不给我时间抱怨。卖贺卡的当儿,我闲着无聊去旁边的报刊亭翻阅某本选刊,再次看到了K哥的名字,是一篇名为《在长安街上跑步前进》的中篇被选载了。我手捧着选刊盯着灯罩发呆,灯光从灯罩边缘倾泻而下,打在灯下的书上。在长安街上跑步前进是怎样一种生活呢?从前我到过北京,到过长安街,我曾以出差、旅游抑或转车为目的路过那里,但它们对我丝毫没有意义,我像一片叶子,终究在那里找不到栖息的落脚地。可是现在却不同了,因为K哥在那。假使我再去北京,我想我心里一定会藏着某种期盼,期盼在马路旁、广场中心、天桥上或地下通道里,在行进中的下一秒猛然间就碰到K哥。那时,他或许成了一名通道歌手,或许成了一个行为艺术者,当然,他也可能成了一位企业家、一个名编剧或导演,总之,我相信他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我还没见过他呢。我期待着我们的第一次相见。
责任编辑 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