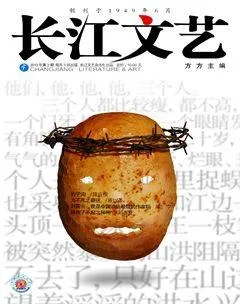叶村有事
我站了起来。
此时,
女眷们的哭天嚎地声,
跟丝弦崩断一样戛然而止;
表情由悲痛转换成淡漠,
也在瞬间。
我这才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们竟然不是表嫂和侄女们,
而是些陌生女人。
快到叶村时,我正纳闷四周的悄静,村里突然炸起铜管乐和鼓手班的嘈响,你吹你的调,他奏他的曲,把个叶村天空搅得跟打仗似热闹。我松下口气,庆幸总算没耽误给舅舅送葬,不然在村里失面子,明孝表哥面前更交待不了。现在,只待鞭炮和双响腾空而起,出葬时辰就到了。
我是昨天接到明孝表哥电话,才知道舅舅死讯及出葬时辰的。本来从容点,昨天我该回叶村的,一来今天不要起大早赶公交车,二来可看望妈,陪她老人家多说说话。说来惭愧,出来十多年,虽说县城到叶村只有一小时半车程,可每年除了过年和清明上坟,来去匆匆,我很少回叶村看望妈,更不用说看望舅舅了。一个农民,要在城里生存,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在乐队的嘈响声中,我走进叶村。村街已让花圈摆满,本来不宽的街道更加拥挤不堪了。我边走,边大致数数,花圈竟有四十之多,还有纸扎的高楼、小车、各种高档家用电器。两个纸扎美女,真人大小,屁股上写“保姆”二字,引来不少村孩围观嘻闹。人多,却没几个穿孝衣的,一看就是些帮忙人。秩序有点乱,他们吆五喝六的,正将花圈和那些纸扎东西往一辆辆黄包车上搬。认识的村人招呼了,彼此问候客气几句,其中许多人我竟然不认识。五月漫长的雨季过后,迎来第一个晴天,明亮的阳光驱赶走雨季的压抑,在村街上营造出一种蠢蠢欲动的活跃气氛。有人拿纸扎美女开了个粗野玩笑,把大家逗得像鸭子般嘎嘎大笑。这气氛,好像不是忙丧事,而是在聚会一个庆典。
“回来了,正松。”有人招呼我。
是叶根。他家与舅舅家老屋贴邻,老人平时多亏他关照。年青人大都走了,村里只留下老人孩子。叶根和我同龄,五十出头,属半截老,可这种年龄留在村里的,也不多。我递根烟给他,接着问我妈情况。他说自从你舅舅过辈,你妈身体不是太好。我忙问病了吗?他说也不是病,脑子想的,人好像一夜间衰老了许多。我听了,心里不好受。妈和舅舅兄妹情深,现在舅舅先走了,对妈的打击可想而知。
叶根问:“一个人回来?”
我有点挂不住脸,解释说:“媳妇刚生了孙子,老婆接她回家伺候月子,忙啊。我今天回村,她还得兼顾超市生意呢。儿子嘛,你晓得的,分开过了,在车站接手一间快餐店……店租贵呢;也忙,手下又雇了帮工,走不开。呵——,凑巧得很,女儿也要生了,就这几天的事……”
我没提老妹。舅舅的丧事,我跟老妹通过电话。老妹说哥,我做月嫂工钱二千三吃住在东家,请假开不了口呵。我说,那你家派个代表吧,儿子还是女儿,有一个回叶村,礼数要到。老妹半晌不语,后来解释说,他们打工的人,一碗饭不好吃呢。我明白老妹意思:代表也派不出了。虽说有理由,也情有可原,但毕竟情理上讲不过去。我不死心,劝说她一块回叶村,也看望下妈。老妹说哥,清明刚回过叶村,妈身体好着呢;我真的请假不了。接着问我送多少。我说你真的回不去,礼可要重点喔。老妹这番很决断,说哥,乡下丧事,一百加一副纸烛够了,你替我垫下吧。说罢关了手机。老妹这人,钞票看得重。不过也难怪,妹夫胃癌死后,欠一屁股债,她得还,说债还清后再攒点养老钱,免得老了向儿女伸手。因此拼命赚钱。我心里不是滋味,也无奈,只好一个人回叶村给舅舅送葬了。
叶根笑道:“城里人,忙是忙的。”
我怎么就成城里人了呢?就是脱层皮,我还是农民,在叶村有地有山有桔树,还有老人。打工赚了点钱后,我在村里盖了新房。明孝表哥更牛,盖了别墅。虽然都没住人,空着,可我们老了要叶落归根回叶村的。叶根这话,怎么听都像是挖苦。我哭笑不得,讪笑着说再聊吧,我先去舅舅家。
我想或许妈已在舅舅家。作为长辈,妈可能会主事他哥的丧事。
到舅舅家时,恰巧明孝表哥从屋里出来。他穿件皱巴巴不合身孝衣,戴孝帽,拦腰系根稻草绳,样子有点滑稽。四年前,回叶村过年我们见过面后,就再没见了。他现在发福了,腆个大肚,脸膛红润,眼睛小成一条缝,却透出精明和自信的亮光。见是我,他箭步上前,紧握我的手说,来了,好、好,我们兄弟多年没见面了。忙敬烟,又往我口袋塞了一包。我趁机解释老婆儿女以及老妹没能回村给舅舅送葬的原因,结结巴巴的,满是惭愧。明孝表哥通情达理,听完后诚恳地说,我们都是叶村出去做事的人,理解,理解!表弟来不就代表全家了!这态度,让我很感动,心里好受了一些。
明孝表哥朝屋里吆喝:“来■ ——!”
屋里立即响起女眷们的哭声。乡下风俗:客人来吊唁,女眷们必须以哭表达对逝者的悲痛。
在明孝表哥陪同下,我来到舅舅遗像前。一个活生生老人,现在再也见不着了,面对他的遗像,和摆在遗像前的骨灰盒,我心里难受。女眷们伤心欲绝的哭嚎,极具感染力,我的眼圈马上红了。她们一边哭嚎,一边大把大把地往烧纸盘里丢冥币纸锭,腾起的浓烟笼罩不散,熏得我微眯起眼睛。将礼金和纸烛交给理事后,我接过孝衣穿上,然后恭恭敬敬地鞠躬。想起舅舅的亲情,我不由滚下泪水,又跪下磕了三个头。
明孝表哥搀扶起我,说:“正松,起来吧。”
我站了起来。此时,女眷们的哭天嚎地声,跟丝弦崩断一样戛然而止;表情由悲痛转换成淡漠,也在瞬间。我这才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们竟然不是表嫂和侄女们,而是些陌生女人。目光扫过人群,也没见着她们身影。我觉得纳闷,张了张嘴,还是忍住没说出来。
明孝表哥说:“我们兄弟一边说说话去。”
昨天通电话时,明孝表哥说他是三天前连夜赶回的,第二天火化爹的遗体,今天出葬。我觉得舅舅丧事办得太仓促了。作为亲戚,我当时不便异议,可肚里总不是滋味。明孝表哥是何等机灵的人,大概通话时就感觉出来了。
退到一边,明孝表哥叹了口气,说:“是仓促了点。迷信这东西呵,你不信它,想怎么做尽管做去,一点没事。可你要是信了,不照着做,肚里难免存个疙瘩,担心万一……既然请风水先生挑好日子,图个日后平安吧,也就算了。”
原来是请了风水先生的,我有点理解了。
明孝表哥一笑,说:“不过,仓促但不草率。喜丧嘛,办隆重点,晚上再放两场电影,也算弥补了,对得起爹。”
我没搭话,明白他是想借丧事炫耀一下。人有这种心理很正常,哪怕在外头混得跌股,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不然在村里没颜面。我也一样。何况,明孝表哥确实混得不错。
明孝表哥说:“镇里有殡仪公司,一条龙服务,搞得很周到的。”
我明白了,原来那些“女眷”以及村街上不认识的人,都是殡仪公司的。
明孝表哥接着说:“三个都回不了家啊。打电话去,老大说飞机票买不到,老二说爹,日子挑这么紧,等我赶回家,你们不都散了?老三在欧洲旅游,说跟旅游团走的,爹你叫我怎么回?哎,你说气不气恼。”
我没吱声。我们叶村在县里小有名气,原因是外出经商的多,近在县城,远的跑到天津、东北。明孝表哥在上海郊区开小旅馆,三个儿女,一个在哈尔滨,一个在牡丹江,都是开超市的,老三跟老公做外贸,到外国像赶集一样方便。他们家是叶村最成功的农民。
都忙啊,理由也说得过去,可亲人去世没空回家奔丧,难免落下话柄。其实,一句话说白了,忙是推托的话。作为到城里打拼的农民,有赚钱的原因,也有赚钱难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人的亲情、人情,没先前浓了。我也一样,狠狠心将超市关门,叫儿子快餐店歇业,也不是办不到的事。钱财是身外之物,谁都会说,可临到头上,谁又都想不明白。我有些懊悔没有拖儿带女一家人回叶村给舅舅送葬。
我说:“怎么没见表嫂啊。”
明孝表哥说回来了,带孙子看你妈去了。第四代呢,太爷的丧事,必须到场。再说,也让他看看老家。
正说着时,风水先生进来催促,说赶紧奠酒吧。
于是把祭桌搬到村街中央,摆好遗像、祭品,开始奠酒。几年前奠酒,风水先生要唱,拖腔拉调的,丧家则在遗像前跪拜长哭,繁琐得很,却很有看头。县电视台说是“非遗”,还来录过像。现在风水先生偷工减料去繁就简,不唱了,只叫丧家按辈份依次下跪磕响头,将酒洒在地上完事。因孙辈都没回家奔丧,人少,奠酒很快结束。“女眷”们穿了孝衣,自然是“下辈”,也跪下奠酒,敬业精神令人感慨。都完了,风水先生才吆喝一声:
“出■!——”
双响鞭炮腾空而起;歇息过一会的乐队,此时吹奏出最高音。我听铜管乐吹奏的是《血染的风采》,很滑稽。乡下丧事都这样吹奏,热闹就行。等会还会换成《爱的奉献》。谁都没感觉滑稽,听习惯了。鼓手班吹老调,也听习惯了,却叫不出曲目。出葬队伍早已排好队等候,只待孝子到位,即可出发。
明孝表哥一手擎招魂幡,一手拎香火碗,走到队伍前头。先于他走的,是飘路纸的和开路先锋。前者肩挑阎罗锅,一路甩撒冥纸,逢村遇桥,点香烛插在路边,有借道与正告恶鬼勿挡道意思。后者即放双响鞭炮的,一路鸣放,也有镇慑恶鬼之意,颇有点威风。紧跟孝子后头的,依次是遗像、灵车。遗像自然是玄孙捧。有第四代了,是喜丧,所以玄孙穿红衣戴红帽。玄孙才六岁,一路由他奶奶也就是我表嫂陪护着。纸扎灵车里安置骨灰盒,因再没亲人了,由四个穿孝衣的殡仪公司人抬着。紧接其后的,依次才是铜管乐队、居士队伍、花圈纸扎冥楼等队伍、亲友队伍、鼓手班,最后是殿后将军——两个放双响鞭炮的大汉。出葬队伍浩浩荡荡,颇有声势,给五月的乡村平添了一道难得一见的风景。
经过我家老屋时,队伍停了下来。
我妈拄着拐杖在等候奠酒。门口摆祭桌,祭品有米饭肉水果等。其实,我老远就看见妈了,坐在家门口藤椅上,等出葬队伍到跟前,她才站起。站起时倚赖拐杖,腿脚不是很灵便。看着妈瘦骨伶仃弱不禁风的样子,我心里一酸,泪水夺眶滚出:老了,妈真的老了。我忙走出队伍,上前搀扶着妈。
此时,明孝表哥眼睛红了,叫声姑妈,跪了下来。
妈没搭理他,捧来一碗米饭,老泪纵横地看着舅舅遗像,咽不成声地说:“哥……吃饱饭再走吧,你吃,你吃饱呵……黄泉路上,呜呜呜……”
我觉得妈是糊涂了,搀扶她坐到藤椅上。
风水先生是机灵人,忙吆喝道:“奠酒结束,■!——”
明孝表哥这才站起来。出葬队伍断续出发。
到村口时,居士队伍站到了道旁,他们不送到山,在此目送出葬队伍过去。这支队伍很惹眼,戴黑帽,穿宽大黑袍,人手一串念珠,执丈二镶黄边黑旗,飘逸似仙,平添了丧事的隆重与穆肃气氛。叶根告诉我,这些广福寺居士,都是镇里、乡村的老头老太,哪家有丧事都聚集过去,给念经、送葬。我仔细看,果然认出有叶村的老太婆。叶根说,如今谁都想着法子挣钱呢,四五百一月没问题。果然,我见表嫂走上前去,塞过一只红包。表嫂交待说,十二点镇上富农大酒店吃长命豆腐,有大巴接送,都准时到喔。居士们点头不迭,说些客套话。说是丧宴,其实跟喜宴差不多,无非多一道叫长命豆腐的菜。
出村后,出葬队伍在柑桔林间迤逦穿行。十多年前,镇政府把我们乡打造成万亩柑桔之乡,漫山遍野的柑桔林,很引以自豪。跟村里人一样,我家的地,大都种了柑桔。可如今柑桔没人要,烂在树上,每年有关部门都发动单位和市民献爱心购买爱心柑桔,搞得人人都疲了。又心存侥幸来年柑桔会有好价钱,舍不得砍了改种其他。田野里零星的田地,大都荒芜,长满野草,看了让人说不出滋味。
之后是经过乡街,然后拐回,多绕个小圈,再到山边坟墓。听起来多此一举,其实是丧家主张,多走了二十来分钟。
到达山边坟墓时,风水先生看手机,说落冢时辰还有半小时。此时,黄包车夫们把花圈搬下,摆到坟墓周遭,将青山摊出白晃晃一大片。坟墓是双冢,舅母先已安息,如今舅舅也将在此永久长眠。纸扎高楼等要烧给舅舅。怕引发山火,已在距离坟墓十多米路上,辟出一片空地。风水先生交代一件一件烧。每烧一件,明孝表哥都要叨念:“爹呵,儿烧给你高楼咧,你收好啊”;“爹呵,儿烧给你保姆咧,你收好啊”……
焚烧着时,明孝表哥问我:“听说你盘下一个超市?”
我说:“是二手房,买下后改造的。城里房价贵,还欠十多万债呢。”
明孝表哥说没事,三五年还清,超市你就赚下了。我点头说是。超市是我的骄傲,标志着我进城打工的成功。明孝表哥说,乡下这些年好了些,可再好也没法跟城里比。我说是呵。明孝表哥说,呆在乡下是井底蛤蟆,没出息,还耽搁儿女。我点头,表示赞同。明孝表哥说,你看叶村哪家种柑桔发财的?没有。种葡萄也一样。有几户养猪的,猪肉暴涨暴跌,最终还是亏。我说是。明孝表哥叹道,你我这一代,总要叶落归根的。当初盖新房,是为创业,可现在想想,儿孙会回叶村住么?我说不会吧,他们不会种田了,也不想种。明孝表哥点头,说是呵,种田没出息,我们会希望儿孙没出息?他们不回叶村更好,说明有出息。我表示同感。明孝表哥说,城里的教育、医疗、文化,乡下怎么比?差距会越来越大。过去有句话,叫宁做大地方狗,不做小地方人,就是这道理。我说是啊,为了儿孙,你我这代人是骆驼命。明孝表哥说,我们吃点苦,应该。毕竟见过大世面,我佩服他的见解。
明孝表哥叹息道:“只是苦了我爹你妈,都老了啊。你妈健在,你要好好孝顺。别像我,后悔都没用了。”
我点头不迭,心里的苦衷却没法说出。我那超市不大,隔出一小间吃住,前面营业,从此我在城里不用租房,算是安家了。可是,把妈接到城里养老,怎么住?儿女未成家时,儿子每夜临时支钢丝床。妈来,儿子出去借宿,钢丝床让给妈。妈不常来,婆媳俩为些小事琐事,长年累月的,积怨深呢。我夹在中央,怎么也调停不了她们之间矛盾。最近几年,妈干脆不来了。妈越来越老了。掂量下老妹,也难,把妈推给她,我开不了口。妈是我一块心病。
明孝表哥说:“有个歌叫《常回家看看》……”轻轻地哼起来,带着点呜咽:“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眼眶里的泪漾漾欲滴。
我脑子里晃着舅舅和妈的身影,也跟着哼起来,泪水伴着呜咽声一个劲往外涌。
落冢时辰到了,风水先生叫我们过去。他将骨灰盒摆进墓冢,然后拉红线,看罗盘。折腾十多分钟后,才说好了,吩咐去找七颗子孙石来。
明孝表哥找来七颗小圆石,风水先生接过,边甩子孙石,边就唱开来:
子孙石掼得正,
生个儿子不捏锄头柄;
子孙石掼得响,
玄孙将来当市长;
子孙石掼得远,
儿孙钞票赚个亿万元;
……
风水先生的唱词与时俱进。我记得以前是唱当“乡长”的,现在改为当“市长”了;赚钞票“百万元”,改成“亿万元”。跟眼下人的期望值成正比。还投其所好,针对性特强,将明孝表哥的毛摸得熨帖。我见明孝表哥嘴角漾起微笑,低下头去,无限慈祥地抚摸着将来“市长”的头,一副欣慰模样。
风水先生唱罢,明孝表哥奉上一只大红包。
接着,风水先生拿起菜刀,将一只雄鸡宰了,拎着绕坟墓洒血,嘴里急促地念“天灵灵地灵灵玉皇大帝太白金星……”绕过三圈,将雄鸡往坟碑一摁,涂一片血,然后一扬手,远远甩了出去。
风水先生说:“好了,亲人脱去孝衣,洒净水,披红带,可以回了!”
都照着做了,由原路返回,把山上封冢等诸事留给风水先生。
心里想着妈,我走得比谁都急。
回到家,妈正在吃饭,菜很简单,就一碟咸菜。我见了不是滋味,说妈,到富农大酒店吃吧,有车接送。妈说,大鱼大肉的,我吃不了,也不想赶热闹。妈脾气倔,我知道说不动她,也就没勉强。清明回叶村上坟时,妈还精神,才一个多月,看上去妈真的衰老得快啊。我说妈,没有不轻爽吧。妈说没有,好好的哩。我们娘儿俩一时相对无言。
妈慢慢地吃着,忽然抬起头,说:“正松啊,你舅舅是饿死的。”
我大吃一惊,疑惑地看着妈。
妈肯定地重复:“你舅舅真是活活饿死的。”
我说:“没听明孝表哥说起呵,”
妈说:“村里都瞒着的。”
难怪,妈奠酒时不循常规,捧了碗米饭,呜咽着叫舅舅吃饱饭再走。
这是个石破天惊秘密。我真的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妈说:叶根跟我讲,半个多月前,他去看你舅舅,你舅舅病了,气色不大好。他问怎么啦?你舅舅说是有点感冒。当时你舅舅在喝芙朴。按他脑门,有一点点热度,也没当回事,就没给明孝打电话,交待过几句,也就回家了。巧的是,当天他老婆摔了,送到镇医院,说是腰椎摔裂了,得住院。叶根两个儿子你晓得的,都在城里打工。他只好留在医院服侍老婆,十多天后才想起你舅舅,不放心,回村过去看,门闩着敲死没人答应。转到窗前,隔着玻璃见你舅舅躺在地上。他慌了,跑来叫我。到你舅舅家,我叫他敲碎了玻璃窗爬进去开房门。我们进去后,发现你舅舅已经死了,也不知道是哪天断的气。
我说:“妈,这也不能断定舅舅是饿死的呵。”
妈说:“妈会胡乱讲?叶根也这样说。你舅舅死在地上,头挨着米缸,米缸盖滚在一边,地上撒了些米,嘴里也是米。估计你舅舅是几天没吃东西,饿昏了,屋里空空的找不出吃的,才想起吃米。结果,跌倒就再没起来了。还有,锅里浸着未洗的碗,都生了层水锈。你想想,你舅舅有多少天没烧饭吃了?他病得连路都走不动,更别讲到伙房烧饭了。”
这样的话,有道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
妈说:“病了,哪怕是喝点米汤水,人才会硬坚呵。老屋那么大,空荡荡就你舅舅一个人,谁帮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没饭吃,病更加重。归根结底,你舅舅是活活饿死的。”
舅舅快八十的人了,又病着,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援境地,这样的结果,我不相信也相信了。
妈呜咽着说:“断气这么多天,都没人晓得。要是在热天,早生虫了,让虫吃得剩副骨头了呵!”
我可怜的舅舅!
妈告诉我,叶根打去电话,明孝连夜赶回。料理后事时,发现草席下压着三百多钞票,枕头芯里藏有一张三万五存单。
妈悲戚地说:“三年困难时期,你舅舅吃野菜都挺过来了,想不到如今竟会活活饿死!手里有那么多钞票,却买不来一碗米汤水救命啊。”
我心里悲恸,一时无语。
妈不再说,低下头吃饭。吃得很慢,像是在数饭粒,泪无声地滚落在碗里。
妈肯定天天在想舅舅活活饿死的情景过程,由此,也想她的百年之日……有儿有女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会落个这般下场!我想,到这境地,换哪个老人都会这么想。妈是想苦了,也想得毛骨悚然,可是见到我,晓得我难处,也就没说,将苦和怕埋在肚里。
我不忍心看妈,心乱如麻,转过身偷偷抹泪。
手机响了。是明孝表哥催去富农大酒店,说车就等你娘儿俩了。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愣怔片刻之后,突然情绪失控地嚷道:
“不去,我陪着妈!”
责任编辑 吴大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