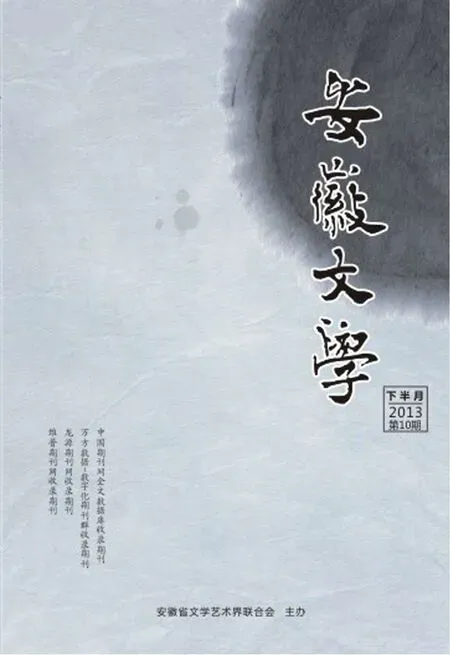魏晋文人的生命意识探究
徐海华
据《后汉书》记载,建安五年,最博学多才而且遍注群经,使经学今古文汇为一家的郑玄去世的时候,孔子曾托梦给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①他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旧的思想时代的彻底结束与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真正开端。正如宗白华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富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作为传统文明的儒家信仰日渐衰微,关怀人的生存自由、人格理想、精神解放的道家精神占了上风;儒道互补,开始由以儒家为内核的文化转向以道家思想为内核的文化。“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那种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人的生存价值并不在于社会的赞许而在于心灵的自由。”③此时,出现了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的玄学,文人性格、士人心态有了很多新的特点。最能反映玄学思想特质的“贵无”的本体论,与玄风熏陶下魏晋文人最显著的人格特点“任诞放达”成为解读玄学的关键。
“儒学传统中,最薄弱与最柔软的地方特别容易受到挑战”,③即关于宇宙与人的形而上的思考。汉魏之际,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对“宇宙与人的终极”这一经学回避的问题提出大胆的质疑;而最终由传统的宇宙论转向本体论。玄学本体论中以何晏、王弼之说——贵无论影响最大。二人在《晋书·王衍传》提出了关于贵无——以无为本的著名论述:“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此化生,万物恃此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他们为一切寻根,终于将“万物之体”推究到了“无”。王弼对贵无论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他的《老子注》、《易注》都贯穿了这一思想。他用“以无为本”的思想解释《易》大衍义,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特。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四十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韩康伯《易·系辞注》引)在王弼看来,大衍之数“四十九”和“一”的关系,就是“有”与“无”的关系;“有”之宗极根本在“无”,而“无”又通过具体的“有”体现。王弼注《老子》,更多地论及这一思想,如“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四十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老子》四十二章)以及他在《老子》十四章注中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讲的就是天下万物的归趣本宗只有“无”,因其没有任何局限而具有成为任何一个具体实有的无限可能性,故“无”为万物之本。这一思路的转换——“无”为本而“有”为末,就导致了生活价值态度的大转换——与“无”相应的自然秩序就处于与“有”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前,自然人性就处于社会人性之前。而现实生活中用以建构社会秩序,维系人际关系的法律、道德、习俗及相应的各种观念,即“名教”显然与“自然”出现冲突。于是,就有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著名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直言不讳地批判名教理法,对名教圣人明确表示鄙视。“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他非圣无法的惊世骇俗之论,也为魏晋士人的人生实践提供了合理的依据,继而出现士人中所谓的“任诞放达”。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专门记述当时名士生活中的任性自为,放浪形骸。《世说新语·任诞》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故而,《世说新语》评阮籍为“外坦荡而内淳至”。又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祥衣,诸君何为入我祥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阮咸与诸阮与群猪共大盆饮酒。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而光逸则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大叫。王澄出为荆州,其兄太尉王衍及时贤为之送行者倾路盈途,而他却全然不顾,性之所发,竟于此时脱去衣巾,爬上庭中树,于鹊巢中取鹊子,下而弄之,神色自若,旁若无人(《世说新语·简傲》六),桓伊善吹笛,时已贵显,遇王徽之出都于途中,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王徽之令人告桓伊:“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二人并不相识,只是一时兴起,便要人为他吹笛为乐,这实在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桓伊竟全不在意,即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主客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四十九),这实在是十分随便的事,主客二人都不拘细节,都任性而行。尽管士人们具体表现不一,价值评价也不一样,但后世仍为其行为中的任诞放达而称奇。
任诞放达这种纵情任性、蔑视礼法、醉心自然、不拘小节、我行我素的言行,若是脱去文化背景孤立起来看,着实令人费解、匪夷所思。唯其与魏晋时代的哲学思潮相联系方可找到问题的答案,正是由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生存自由的追求,对生命本质的苦苦探寻才使得魏晋文人的这种生命态度与方式为我们理解和接受,并不断地品味着它留予后世丰富的文化内涵。
注释
①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
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18,319.
[1]厦门大学中文系.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3]廖仲安.反刍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