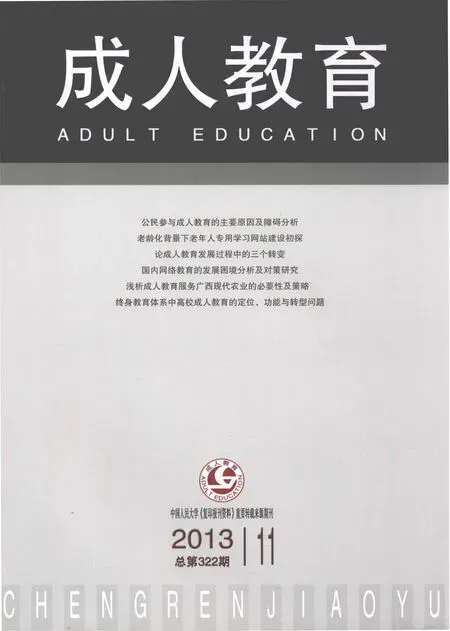论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三个转变
宋亦芳
(上海开放大学长宁分校、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院,上海 200336)
通常认为,成人教育是指为成人提供的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总和,其作用是使成人增长能力、丰富知识、提高技术,或帮助他们转向新的方向,使他们在个人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得到改变。然而,随着社会变革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深入,成人教育并不意味着仅仅将普通教育的体系、观念、内涵及方式方法等等照搬给成人,也不意味着成人教育就是局限于学校范畴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高志敏教授认为,成人教育“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才能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1]据此笔者认为,从成人教育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以更宽的视野全面认识成人教育内涵,并能走出教育看教育,重点是思考成人教育“三个转变”对成人教育发展的意义。
一、教育理念向终身学习转变
(一)规律探析:终身学习成为成人教育的必然趋势
纵观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通常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生产企业用机器代替了人工生产,生产方式的变革需要劳动者掌握更多新的知识和技能,而这有赖于工业劳动者的进一步充电。正是因为在种种需求的驱使下,出现了有组织的和多样性的成人教育,形成了一种趋于制度化和体制化的成人教育。
然而,真正推动成人教育全面发展的是人们对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因为面对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把成人教育作为不断提升自己的一种持续性要求。1919年,英国在《成人教育报告建议书》中就指出,“成人教育是永远的民众的需要,又是民众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具有普遍性和终身性”。二次大战以后,面对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受到终身教育思潮的影响,成人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步演变成一种满足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教育形式。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发展成人教育的建议》强调,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和学习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终身学习着重从学习者的主体性出发,强调个人在一生中应持续地学习,以满足个人在一生中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各种学习需求。”[2]
我国成人教育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全面发展的。解放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提出“要加强对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面对当时文盲占人口大多数、各类人才匮乏的严重状况,成人教育成为人们补文化、补技术、补学历的主要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人教育迅速恢复并蓬勃发展,基本满足了成人对文化、技术和各级学历教育的需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对教育多样化的需求,成人教育也面临新的选择和取向。因此,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提出了“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张,并指出要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引领了成人教育新的发展方向。
(二)思想演绎:终身学习成为成人教育的时代主题
成人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既体现了成人教育理念创新的作用,也反映了终身学习思想演绎的结果。194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第一届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召开,开启了成人教育新阶段,而以后的5届大会受保罗·朗格朗(Parl Lengrand)等人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积极传播终身学习理念。1972年第三届大会以“终身教育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为主题,使成人教育进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理念综合建构期;1985年第四届大会审议的项目《发展成人教育是实行终身学习的基本条件和教育民主化的重要因素:趋势与前景》认为,成人教育对实现终身学习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承认;1997年第五届大会《汉堡成人教育宣言》庄严声明,要确保终身学习在21世纪初更有成效;2009年第六届大会形成的《贝伦行动框架》指出,终身学习对于应对全球教育问题和挑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以包容性的、解放性的、人性的、民主的价值观为基础,对具有知识社会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3]因此,终身学习思想顺应了当今成人教育发展的时代潮流,反映了成人教育的最新主题。
关于终身学习概念,1994年在罗马举行的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指出,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任务、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在报告中提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1996年,时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雅克·德洛尔(Jacque Delors)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中指出,终身学习这一思想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并强调教育是建立在“学会认知、学习做事、学会共处、学习生存”这四大支柱之上的。[4]该报告对于引导新时期成人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在《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中指出的,“终身学习”这个词现在被更广泛地使用,这个转变传递出的信息不仅是语义的变化,它反映的是这个领域实质性的进展。[5]
(三)理论渊源:终身学习成为成人教育的研究取向
从理论渊源来看,终身学习思想一直存在于成人教育研究之中。20世纪初成人教育研究发端之初,桑代克(E.L.Thorndike)等人的研究就为成人是否具备学习能力找到了答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在任何自然生命周期内,年龄对于学习全然没有 否 决 权![6]20 世 纪 后 期,梅 里 安 (Sharan B.Merriam)和凯弗瑞拉(Rosemary S.Caffarella)对成人学习的支柱学说——自我导向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理论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许多学校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自我导向的终身学习者。[7]至于终身学习理论的正式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吴遵民教授认为,现代终身教育理论是从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成人教育委员会批准保罗·朗格朗(Parl Lengrand)终身教育提案开始的,而终身学习概念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基础的,也是终身教育理念的延伸。[8]当然,国际上终身教育(学习)理论发展时间不长,尚不成体系,且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也为成人教育在终身教育领域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20世纪末开始,我国成人教育研究重点也开始转向终身学习。其时,我国提出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叶忠海教授称之为“我国掀起了第三次现代成人教育研究高潮”。[9]在此期间,我国对终身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翻译出版国外终身教育研究成果、开展国际终身教育研究引进终身学习理论,代表作如《学会生存》(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1996)、《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吴遵民,1999)等;第二,结合我国实际开展本土化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代表作如《现代中国终身教育论》(吴遵民,2003)、《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陈乃林,2002)、《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设》(厉以贤,2004)、《创建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叶忠海,2005)、《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高志敏等,2005)等;第三,结合终身教育发展开展研究,代表性研究如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朱新均主持的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暨“十一五”重点课题以及专著《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朱新均,2010)、上海和山西等地开展的终身教育立法研究等。与国外相比,我国对终身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我国在终身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二、教学方式向支持服务转变
(一)理念深化:支持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基本内涵
支持服务概念是由英国开放大学大卫·西沃特(David Sewart)教授于1978年在德国哈根远程教育大学(FernUniversität in Hagen)发表的《远程学习系统对学生的持续关注》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最初将学生支持服务界定为“一种服务产业”,后来又将学生支持服务定义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学习者可以充分利用远程教育机构提供的各项功能。[10]大卫·西沃特的学生支持服务理论要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生支持服务的构成是“要素无限”;第二,学生支持服务的精髓是“持续关注”;第三,学生支持服务的归属是“服务产业”。2001年,大卫·西沃特在第20届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世界大会上阐述英国开放大学新时期目标时指出,要将整个教的组织转变为向学生提供支持和指导的组织。
大卫·西沃特对学生支持服务理论的认识、理解,是以其三十余年的远程教育实践工作为基础的。但这一理论不仅对远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对成人教育更具有深远的影响。从现代成人教育的现状来看,成人学习的目的更加多元化,学习的方法更加多样化,并且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学习时间更加碎片化,等等。因此,现代成人教育的教学方式越来越需要从“授课”转为“服务”。从这一理念出发,现代成人教育的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第一,成人教育是教育的实施者(如学校)提供的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包括管理、人力、智力、网络和资源等多方面的支持服务,体现“要素无限”;第二,成人教育的关键是要为学生提供全过程的支持服务,使学生在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交错中,能时时得到帮助和关怀,体现“持续关注”;第三,成人教育的立足点是从教学安排转为教学服务,形成完善的教育服务体系和服务方式,体现“服务产业”。总之,支持服务理论揭示出的成人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体现学习者的主体作用,为学生提供“学有所教”的教育服务。支持服务理论的本质,是实现支持服务下的成人个性化学习。
(二)研究追踪:支持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理论归因
在成人教育学及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中,并没有提及到“支持服务”这一概念,但支持服务理论可以从成人教育的研究中找到答案,因为在相关的成人教育的理论中,蕴含了支持服务的理念,包括针对成人学习者的支持服务的作用、方式等。这些都为成人教育的教学方式向支持服务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成人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诺尔斯(Malcolm S.Knowles)是西方第一位执着建构完整成人教育学理论的教育家。他在1970年的代表作《现代成人教育实践》中,提出了成人教育学理论的四项假设:成人具有独立自主的自我概念,成人拥有丰富多样并且人格化了的经验,成人的学习意向与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发展任务紧密相关,成人的学习活动主要以解决问题为中心。1984年和1989年又分别增加了二项假设:成人学习主要受内在动机驱动和学习者意识需要唤醒。他认为,“教师的责任是布置一个适合学习者学习的情境,以生活化为主”。有学者也认为,成人教育的教师需要更多地关注过程而不是所教的内容,教师宜扮演辅助者或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讲授者或知识分类者的角色。[11]
自我导向学习理论是成人教育的一个支柱学说,其研究可以追溯到1840年,而成为主要研究领域是1960年才开始的,其奠基人霍尔(Houle)及他的学生诺尔斯和塔夫(A.Tough)等众多成人教育家,都对自我导向学习提出过不同的理论见解。梅里安和凯弗瑞拉在《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一书中,基于众多学者的观点,对自我导向学习进行了追述和梳理,将自我导向学习过程归纳为三种模型:线性模型、交互性模型和指导性模型。线性模型强调学习者本身作用,交互性模型还兼顾到学习所处的不同情境等问题,而指导性模型注重在正规的课堂教学背景下,教师指导学生形成自我导向的能力以及学习活动的自我监控能力。其中,格鲁(Grow)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分层自我指导学习模型(SSDL),勾画了教师如何帮助学习者在他们的学习中变得更有自我导向性。因此,自我导向学习过程模型的不断演进表明,自我导向学习与“支持服务”下的成人个性化学习理念趋于一致。
(三)载体扫描:支持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信息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不断运用,支持服务体系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各种支持服务载体,促进了支持服务能力在成人教育中的进一步提升。上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在学校的日益普及,改变了学校教育中“教”与“学”的关系,成为现代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支撑。从我国开放教育的发展来看,50年代创建的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形成了我国远程开放教育的网络系统,而随着国家和地方开放大学的建立,这种网络系统正在转变成完整的立体化的支持服务体系。2006年,教育部设立教改项目《数字化学习港与终身学习社会建设与示范》,探索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和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更加广泛的社会人群的终身学习提供各项支持服务。近年来,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的出现和运用,更是对传统教学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支持服务的本质是什么?早在2001年,李克东教授就提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具有多种途径:资源利用的学习,自主发现的学习,协商合作的学习,实践创造的学习。”[12]2002年,何克抗教授也指出,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应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并不是技术与教学的简单“叠加”。[13]也就是说,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支持服务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简单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加强,也不是直接将传统教学方式与信息技术进行“叠加”,而是实现一种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一种基于支持服务的个性化学习。
《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信息化支撑服务体系”的目标。由此可见,国家政策层面对基于信息化的支持服务的建设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支持服务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机遇。如正在兴起的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是一种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未来不可或缺的学习模式。又如新近涌现的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MOOCs),使支持服务体系充满了遐想的空间。
三、办学职能向社会服务转变
(一)价值回归:社会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重要职能
广义的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而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14]在此,成人教育特指各级各类成人学校(成人学历院校、培训学校、社会培训机构、企业办学机构等)面向成人所开展的教育活动,也叫成人学校教育。成人学校是成人教育的主要力量,其社会服务职能是指学校直接为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提供的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活动。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学校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承担了其它机构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和职能。从古希腊人性教育、教会神学教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到资本主义的现代科学教育,西方教育实现了从单纯塑造人本身到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从依附于社会到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中国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修身养性教育到引进西学以“救国”图存、由私塾到近代大学的建立,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并逐渐确立了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成人学校社会服务的提出,是学校社会职能的重要体现,也是学校社会属性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外延上看是办学趋向开放。成人学校在从传统的封闭型形态向社会开放过程中,可以为社会提供各类教育服务,包括远程教育支持、教育资源开放、课程和资源配送等,其工作的触角可以向社会不断延伸,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各种学习的重要枢纽。其次,从根本上看是学校价值的回归。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存方式多元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在终身教育和学习成为人们迫切需求的现代社会中,成人学校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办班层面上,而是需要在提供广泛的与教育相关的社会服务中,充分体现出其在任何时候都是以培养人、服务人的核心价值上。
(二)重心转移:社会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必然需求
成人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变化过程,揭示了当今成人教育转向社会服务的必然要求,因为成人教育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我国成人教育发展来看,大规模的文化、技术、学历补习教育基本结束,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滞涨”时期,如占成人教育很大份额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此外,部分传统的成人教育的办学规模还略有下降。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字,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为719.07万人,到2012年达到2391.32万人,增长了232.56%。同期相比,2001年全国成人高校在校生总数为455.98万人,到2012年为583.11万人,增长了27.88%。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体现在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上,而成人高等教育规模并没有同步增长,这也代表了传统意义上成人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学习需求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成人教育,学习的目的和要求等都呈现多样化趋势,学习场所也不局限于学校范围,社区教育和各类社会化培训需求上升。比如,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我国老年人群体的比例呈上升趋势,社区老年教育也成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在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也面临新的职业选择,出现了以就业为导向的新的培训需求;再如,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培养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和更新人才的知识技能,这对成人教育在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等。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战略决策,也对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不只是在学校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时时、处处都能学习。因此,新的需求的出现,使成人教育面临新的选择和机遇。
(三)领域拓展:社会服务成为成人教育的广阔空间
成人教育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有赖于其能否融入到社会建设中去,在为社会建设服务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社会是一个大的教育市场,成人教育可以实行购买服务的形式,也可以运用市场化方式。关键是,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可以为成人教育提供新的途径。
一是基于参与文明建设的拓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的今天,我们需要发挥成人教育的教化作用,通过多形式的教育培训活动,促进市民更新思想观念和革除陈规陋习,发扬文明礼貌的社会风尚。同时,文明建设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长期任务,因此,市民文明素养的教育也将不断持续。此外,活跃在各条战线的文明志愿者,是推进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志愿者的文明素养及服务水平关系到文明建设的效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大的市民教育项目。
二是基于参与社会管理的拓展。近年来推出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以使社会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社会价值观缺乏共识,加上人口的大量流动、网络的无处不在,都对现在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而社会管理创新在推进过程中,对流动人口的教育问题,对特殊人群的培训、对网络的教育引导等等,对社会管理和各项措施可以起到有效的辅助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三是基于参与文化建设的拓展。参与文化建设、加强与文化融合,是成人教育发展的新途径和活力所在。“十八大”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成人教育与文化发展的结合,可以通过文化丰富教育,以教育提升文化,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学习产品,丰富市民精神生活。同时,在社会上存在着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化,很多是纯朴的草根文化,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过程,实现民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提升民间文化品质。因此,成人教育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将使成人教育更加充满活力。
[1]黄健.成人教育创新和学习型社会建设——4月国际论坛的回眸与评论[J].教育发展研究,2005,(7):79-83.
[2]雷丹.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与成人教育的功能[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6):20-2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六次会议成人教育大会文集[G].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4]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9.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M].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2.
[6]高志敏,宋其辉.成人学习研究考略——基于梅里安的追述[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6,(1):5-11.
[7]雪伦·B·梅里安(Sharan B.Merriam),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Rosemary S.Caffarella).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第2版)[M].黄健,张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5.
[8]吴遵民.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新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26.
[9]叶忠海.现代成人教育研究:历程和进展特点——为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J].成人教育,2009,(12):4-8.
[10]David Sewart.Continuity of Concern for Students in a System of Learning at a Distance[M].Hagen:Fern Universitt,1978.
[11]何光全.成人教育学的历史、发展与对话[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2,(3):5-11.
[12]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J].电化教育研究,2001,(8):46-49.
[13]何克抗.e-Learning的本质——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J].电化教育研究,2002,(1):3-6.
[14]叶澜等.新编教育学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