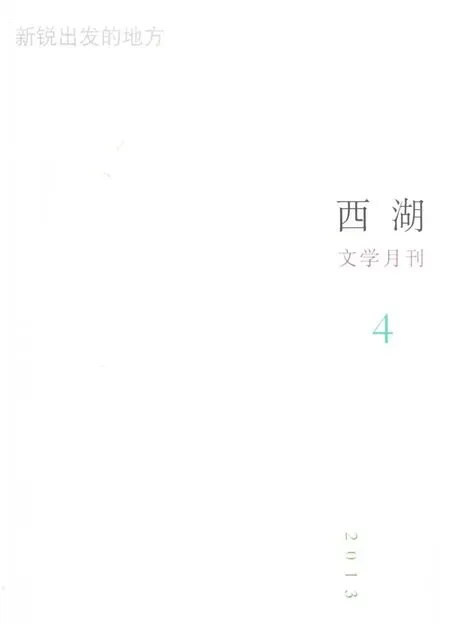隐藏的锋芒——读张祖文《拉萨河畔》
刘涛
一、关于“藏边体小说”
张祖文先生是四川人,四川师大毕业后即入藏工作,先是四处辗转当中学教师,后入西藏人大当公务员。“那个叫张祖文的汉人”入藏已有十二余年,有这么多年在藏区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肯定会有酸甜苦辣的感受,于是发诸笔端,写成了或长或短的小说,譬如《拉萨别来无恙》、《我在拉萨等你》、《你也叫卓玛》、《撑在露珠上的伞影》、《拉萨河的经幡》等。祖文把这些小说定义为“藏边体”,他大致这样解释这个概念:“藏”, 是西藏;“边”, 是边疆;“藏边体小说”即是有关边疆地区的西藏小说,就是站在内地在藏生活的人的角度来看西藏,主要反映内地进藏人员和受千年佛教熏染的藏族人民,在面对现代文明交融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援藏干部不断进入西藏,他们在西藏如何生活、工作,他们的个人情况、情感经历如何,他们经历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些主题一直鲜有文学去表现。祖文本身是“外省人”,他的“藏边体小说”即主要表现、描写这一群体。祖文自述:“我自己就是一个内地进藏人员。在西藏生活、工作了很多年之后,觉得竟然很少有以内地进藏人员在藏生活与工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感觉很遗憾。西藏的确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是在西藏出生,但却因为个人的梦想而来到西藏,在这里生活、工作。但他们因为远离家乡,不得不面对一些到西藏之后出现并给他们带来很多困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高原缺氧环境对身体的损害、子女今后的教育、因远离家乡而对父母或者其他亲人丧失掉的应尽的赡养义务,这是一些令人辛酸的问题。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觉得西藏这个地方不好,他们反而默默地在高原上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并将自己尽量融入西藏这个让他们有着无限感慨的美丽的地方。由此,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向世人描述这个群体生活万象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也没有任何政治的因素,纯粹只是自己觉得有必要书写他们的生命,记录他们的历史,让别人通过自己的文字明白这些人背井离乡远赴高原的生活现状,从而展示这部分人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个人梦想的执著追求。”这是祖文自道其志,也是他的抱负,几代援藏干部群体要借祖文之笔,写出他们的情况。祖文的《拉萨别来无恙》、《我在拉萨等你》和近作《拉萨河畔》等“藏边体小说”由此均可以得到理解。
因为西藏问题日益敏感,因为援藏干部本身的政治背景,所以描写援藏干部这一群体毕竟会有诸多禁忌,不能随意书写。祖文已经写了援藏干部这一群体,但他如何去写却不得不三思而后行,须谨慎小心。“藏边体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处理好这对矛盾,若完全被禁忌限制,小说就成了“歌德”;若过度触犯禁忌,小说可能遭禁。所以“藏边体小说”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不触犯禁忌的前提下,尽量客观、真实地写出援藏干部在西藏的经历、感受、心态等。祖文要开发一块处女地,尽管那里黄金遍地,但也荆棘丛生,希望祖文能够取中道,开发出金矿,但又不为荆棘所伤。
《拉萨河畔》之名很好,显得阔达。小说就是写拉萨河畔的众生,因此头绪繁多,但主要写援藏干部陈洛入藏工作之后生活、工作与情感经历,写入藏务工者巴尔干和腰子的遭遇,写藏族姑娘卓玛的经历与情感体验等。《拉萨河畔》扉页上写了两句话:“献给那些用生命守护这片高天厚土的人!献给那些以西藏作为自己灵魂归宿的人!”“那些用生命守护这片高天厚土的人”应是指藏族本土人,“那些以西藏作为自己灵魂归宿的人”则应是指如同祖文一样的入藏工作者。献词如此,也是祖文自明心迹。
祖文以电影《罗生门》式的叙述方法讲述《拉萨河畔》,他让各个主要人物均登台表演,读者可以完全了解其行为和内心世界。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条主要线索齐头并进,但也时有交叉互动,因此小说丰富而不凌乱。
《拉萨河畔》所处理的时间段为2003年非典前后,其时也是青藏铁路全面完工前期,祖文一方面写了这些具体人物,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那个时段西藏对这两个大问题的反应和反响,写出了其时的民风、民气。
二、如何描写援藏干部
陈洛是援藏干部,他是小说的主角,是两条线索的交叉点。陈洛在原单位的状态是“烦躁不安”,和妻子之间无激情可言,若即若离。从小说前面观之,他去西藏近乎逃避,逃避工作和家庭;可是陈洛入藏之后精神为之一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投入西藏的建设之中。陈洛入藏前颓废消极,是个昏昏沉沉的干部;入藏后意气风发,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要么西藏是陈洛的精神救赎之地,要么因为作者不得不遮掩他的阴暗面、只写其光明面,因为陈洛是援藏干部。小说花了较多的笔墨写陈洛入藏之后的工作情况,他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积极开发援建项目,一心一意为藏民谋福利。
除此之外,小说还浓墨重彩地写了他的情感历程。陈洛入藏后,逐渐和一个叫卓玛的西藏姑娘陷入爱河。卓玛为人善良,是一个名为“康定情歌”的小酒馆的经营者。小酒馆是公共空间,小说的诸多人物时常在此出现,诸多故事在此上演。由于奇特的相识缘由和日久见人心的接触,卓玛逐渐爱上了陈洛。作者对此问题处理得很含蓄,陈洛和卓玛之间的交往自始至终发乎情止乎礼。
陈洛和卓玛的故事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若如此,就关乎作风问题;这是一个有关真爱的故事,爱情自“五四”之后获得了重要的道德力量,故事只要关乎爱情,就有道德感和正义感。据说,爱可以超越时空,譬如《牡丹亭》可以使生者死、死者生,那么爱当然也可以超越民族的界限。电视剧《蜗居》也有类似的情节,作者态度暧昧,于是海藻和宋思明之间似乎是爱情关系;一旦如此,似乎二者都可以得到原谅,海藻不是小三,宋思明不是贪官。因为陈洛和卓玛之间是爱情,遂获得了护身符,所以尽管后来陈洛离婚,和卓玛走在了一起,读者非但不会批评陈洛,反而会为其高兴。
陈洛援藏期满,回到内地,小说自此出现了极大的空白,叙述速度飞速提高。陈洛再次回到西藏已是五六年之后,其时他不再是援藏干部,不是因公再来西藏。小说假陈洛之口说出,他已和妻子离婚,不是因为陈洛喜欢卓玛,乃是因为妻子以为和陈洛缺少感情,故主动离婚。作者处理陈洛和卓玛之间的关系,用心甚为巧妙,一定要经过诸般铺垫与解释,包括最终让陈洛因私来西藏,才敢安排他和卓玛走在一起。相形之下,小说中多多和大达瓦之间的爱情故事就简单了很多,直来直去,简洁明了,没有丝毫的缠绕。因为多多和大扎瓦是平民,而且都是单身,故可如此处理。
通过援藏干部这一群体看西藏或看这些干部本身,是一个极好的视角,而且鲜有人道及;祖文以此为突破口,确实可以切中肯綮。但从行文之中,我还是能够感受到祖文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心态,他不得不有所顾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洛这个人物显得前后不太统一,入藏前的陈洛似乎入藏之后就死去了,一个新的陈洛重生了。陈洛在西藏表现优秀,所做的唯一出格之事就是爱上了卓玛,可是经过作者扎实细致的论证与解释,读者可以判断他们之间是爱情,因此所谓出格之事也就不过如此了。
三、疾病的隐喻
《拉萨河畔》还触及到了劳资矛盾问题,具体到小说中就是巴尔干、腰子和白眼狼之间的矛盾,这是小说另外一个重要线索。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全面铺开,大量农民拥入城市打工,他们被称为农民工,于是劳资问题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有大量文学作品表现这个主题。《拉萨河畔》表现了西藏的劳资矛盾,但劳资双方皆是汉民(巴尔干是一个有趣的名字,但只是貌似少数民族之名,其实是汉人),不是藏人,如此这个主题才容易驾驭。
陈洛、卓玛和巴尔干之所以认识,起因在于巴尔干等打狗,卓玛奋不顾身护狗,后背被棍子重重击中。《拉萨河畔》由这一误会开始,随着行文的展开,他们逐渐和解:巴尔干之所以打狗,是因为工地伙食太差,没有油水;腰子之所以嫖娼,是因为年少气盛,新婚久别。主要人物在小说中均以第一人物出场,各道苦衷,所以误会逐渐消除。
巴尔干的妻子久病不能劳作、儿子读大学,所以他的经济压力极大。巴尔干开搅拌机已十年有余,没有防护措施,被查出得了尘肺病,于是陷入困境。但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之类手续,也因为老板白眼狼太苛刻,所以巴尔干一直没有钱动手术,只好一拖再拖。巴尔干试图抗争,他与白眼狼斗智斗勇,但敌强我弱,他遭到打击报复,抗争均以失败告终。陈洛尽管介入此事,试图帮助巴尔干解决问题,但无奈白眼狼过于狡猾,此事一直悬而未决。于是,巴尔干陷入绝境,坐以待毙。
其时恰是2003年非典之际,祖文就此着墨不多,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非典时期西藏的民情和民风。祖文设计了这样的情节,陈洛的太太欧可赴藏探亲,于是终止了陈洛和卓玛蠢蠢欲动的爱情之心,又安排她感染非典,在医院中隔离治疗。欧克患上非典,竟成为巴尔干起死回生的转折点,他偷偷溜入病房,与欧可待了一夜,于是感染非典。其时巴尔干的心态竟是如此:“而我的内心,则在瞬间就完全放松了下来。彷佛我现在得的不是病,而是整个世界。”巴尔干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上了非典!”巴尔干一患非典,身价倍增,当地政府和医院都不敢置之不理,于是迅速被转移到拉萨医院,数病并治。
《拉萨河畔》中解决劳资矛盾的途径竟是巴尔干主动感染非典。祖文如此设计,可谓神来之笔,但读来却让人痛心不已。巴尔干只有感染非典,才能获得关爱,才能付得起高额的治疗费用。祖文批判的锋芒终于掩饰不住,这是所谓“疾病的隐喻”:农民工巴尔干走投无路,得不到救助,只能以死相搏。劳资矛盾在今天愈演愈烈,似乎尚无解决方案;非典乃偶然事件,以非典解之,其实还是无解。
《拉萨河畔》高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旨,结局皆大欢喜。陈洛与卓玛有情人终成眷属,多多和大扎瓦过着幸福的生活,巴尔干及其妻子病愈,巴尔干儿子独立,腰子成了老板,普布医生当上医院院长,白眼狼身陷囹圄、资财散尽,其庇护者白局长被免职并判刑,矛盾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或许小说的结局不得不如此,但《拉萨河畔》中有两个事情——陈洛和卓玛的爱情,巴尔干主动感染非典——却一直疙疙瘩瘩,是光明中的阴影。祖文“藏边体小说”的困境或许由此可以得到显现,他的无奈与批判的锋芒也隐藏在疙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