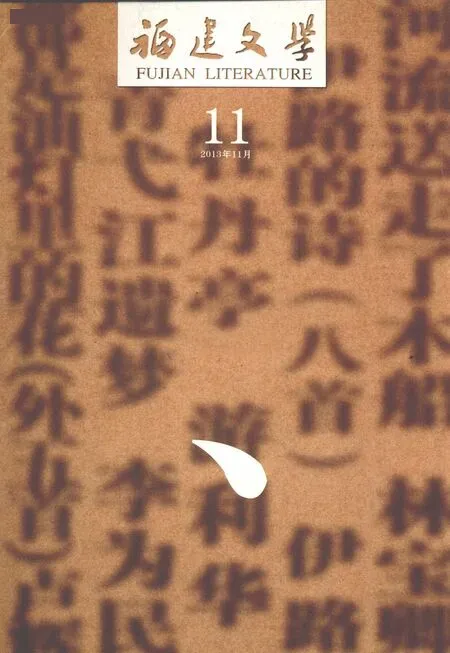诗歌,终极的诱惑(创作谈)
□卢 辉
我一直把诗歌当作彼岸的昭示,终极的诱惑,流动的驿站。这种神性的存在,不是玄学,更不是臆造的家园,它是时间的绵延和空间的扩张所呈现出瞬时的救赎和牵引。这正如当你早晨醒来,推开窗门映入你眼帘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界定的“常景”,另一种是流动的“变景”,要得到第一次的“鲜活”,取决于“变”的形态,而诗歌正是从此走出的,它无依无靠,无须染指,无须设定,更不便去装饰,它永远成为一种无极的趋向,在一次又一次的“可能”中完成近乎宿命的召唤。
诗歌总是从否定后的认定中开始的。是“第一次”,没有任何文化积淀的“唯一”的一次,一直处于否定中“发现”的一次,因而也没有一个界点的一次,正是这些无数个“第一次”组成心灵中短暂而新奇的景观,它永远只能是一种样态,而不能是一种凝固的结论。这正如生命的张狂,或是愚钝有时会与急剧上扬的理念巧合在一块,形成重构的虚妄,诗歌迫使这种虚妄既细切又坚韧,既粘连又脆薄,这是一笔怎样的“签约”?带着这种审视,使诗歌永远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而诗性永远在寻找中或明或灭。
也许一边是神性诱惑,一边是惨淡经营,二者注定成为一对“孪生子”,诗歌总以“废墟”为起点,无以圆满,无以归宿,只有挺住,这决定了为诗的根本:淡泊。当我一次又一次企图接近诗神的光芒之时,我才真正觉得:离无限最近的地方,心无比脆弱。然而,这种脆弱不是病态的,也不是体虚苦吟的一种,这是思接千载,心连浩渺时的恍惚,这是顿开茅塞前的无以皈依。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知命曰常,知常曰明。寥寥数语,集中国文化之大成,聚人生信仰之大义,汇千嶂万川之渊源,我试图聆听,试图俯仰,试图汲取,以展示我心空的茫远,以体悟斗转星移生命环复的轮回。于是,说不破道不尽的诗歌与极其有限的生命构成了“逆反”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文化的景观:缺憾中的行进,亏空中的弥漫,凹凸中的缠绕,这正是诗歌隐没升腾的气象,也是诗歌存在的理由。
在这个世界里,有很多问题引起我们的思索。生,是命定的吗?生下来在这个世界活着,现实早就等着我们,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面对。而我们流浪,我们安居,我们找寻,我们放弃,我们选择独踞一隅,我们奔向远方,这难道不是生命的历程吗?而诗歌就在其中,尽头呢?对人,是死;对诗,是思。生与死,爱和恨,内界与外界,超越与沉沦,哪一种才是生命的原生质?只有诗保留着生命复合体中两种质点的对峙。
天地间唯一值得在意的,便是生命丧失与呈现的对应互动:生命助长意志,意志点缀生命,生命占领意志,意志消耗生命,诗歌在这个二律悖反中滋长。可以断定,意志的真实换来生命的受难,这几乎是意志与生命邂逅而成的景观:诗人的生命空间和意志空间总是如实地流入“直觉”景观中,这是浑然的交响:生命在意志的支配下,呈图形展示出来。图形不是简单的画面排列,位移,晃动,它是生命与意志互为磨砺,妥协,激发的空间,诗歌就是生命空间向意志空间冲撞时留下的碎片。意志使上(天)与下(地)一分为二,生命使上下一片浑沌。人一直在完成着一场场寂寞与隆重的生死经历,庄严的产生也伴随着怪诞的出现,短暂的美引来永恒的意义和展望,这时,唯有诗歌成为生命与意志的资本。
诗歌是语言艺术。不过,无论你如何客观地,逼真地,富有启示性地表现世界,纸上写的太阳永远不会成为天上那个太阳。正是由于语言有语言的限定,也才有了弥漫性,这弥漫性便是诗人尽其智以有限的语言向无限的时空拓展而产生出来的永无极点的放射性,这里充满着有限的表现工具和无限的弥漫性之间的挣扎与魅力。试想一想,贝多芬创造音响,他成了一个不断发出各种音响的空间,然而文字不同于声音,每个字都有语义,你完全可以打破语义来组合它们,这不算什么,关键是,你永远无法消除个体的语义。因此诗人的杰出之处不在于反语义,恰恰在于以一堆词造成尽量大的弥漫空间,这是诗歌语言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