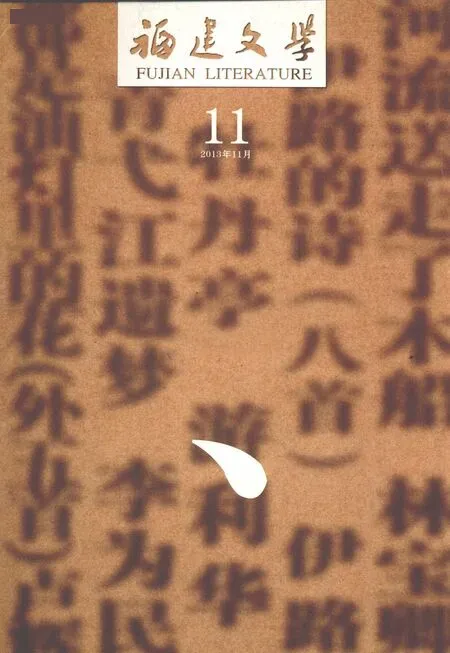被宠幸的人(创作谈)
□伊 路
出去走走,只是想散散心,活动活动腿脚。可有些东西却在等你,钻到眼睛里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无法跟没事一样,即使脚步没停下来,走过去大老远了,它还在那个位置抓你的脑神经,你就有了牵挂,心绪不宁,其实就是欠债了。这样还能撑多久?于是就出现了不得不把它写下来的局面。还得要写得妥帖,不然还别扭着,不乐意,非得把它给你的那种意思那份情意写尽写到位了才行,才完成了任务,身心才能安静下来。
这么说似乎有点嫌烦似的,其实主要责任还在自己,是应了那句“你如果无心怎会发现它有意”。而这心还是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和你的性情意趣交织在一起。像一座山,历时愈久,小路、密径就越多。虽然连那山自己也不清楚它们连系着什么。如今,它来了,实际是你对它有着隐形的期待,它就是生命本身的内容,你是欠自己的债,是你对这世界索求太多,或者也可以说成世界要给你太多,你是个被宠幸的人。
我的诗就是被如此地滋养滋补成长着,有的人总喜欢把自己放在现实的对立面,像一些很绝对的话我是说不出口的,因为我也在这样的现实里活着,靠它的一切过日子。世界之无穷自然包含黑暗和痛苦。但你如果老说自己如何孤独、如何厌倦和看不惯世俗,老是为了这点那点的不顺意在翻来覆去地表白抱怨发牢骚,那就得检讨自己的内心了。
人是伤不了世界的,只能伤自己。人太渺小,怎动得了大地的稳固,你在菜苗上撒了有害的化肥使它枯死,而山谷里草木旺盛得让昆虫吃到打嗝。种子到处都是,最荒僻的地方都能长出嫩芽,都有鸟儿的幼卵。人在世界里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怀抱里,人不见了怀抱依然,依然有永不会穷尽的生物和植物。
我从小随当乡村小学教师的母亲住在祠堂和寺庙改成的学堂里。记得有一个放神祖牌的阁楼,堆着学校多年积下来的童话书,星期天或放假时,我和姐姐妹妹就用课桌椅踮着爬上去看书。其实都被我们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了,如果找到一本没看过的时,我们就像被神灵关照着似的身心的幸福之门随之打开,和煦的阳光金闪闪……常常我们还用课桌椅搭成一座小屋子,把牙膏壳的上头剪下来穿进一条细绳做灯芯,套在一个空墨水瓶口,往里面倒一点煤油,就是一盏可以点亮的灯。虽然只能亮不多的时间,但也如同在宫殿里了……因为祠堂和寺庙多半是在村庄的边上,周围有大片的葱茏蓬勃而又荒凉忧郁的乡野,我也常常与其间的植物一样的状态迷失在里面……应该是在那时我就受到宠幸了。
我最好能像一座湖一样活着,但是不可能的,就像没有四周的悬崖绝壁或水泥石头围挡,湖也不可能形成。在烦躁严峻的现实中才能产生坚强的静。这样的静,得用工地的大锤、打桩机锤炼它,让它像金刚钻,有对抗、穿透、验证和被验证的能力。如果仅是静中的静,连成片的静,那只适合休息睡眠,经不起一枚小钉的扎。
为什么要写诗歌,有一点理由我很看重:世界呈现给我的覆盖在它的表面下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外部的心灵里的层出不穷的新气象、新意义,旁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我把它们写进诗歌里,这使我在创作时,心里能踏实平稳,觉得不是在做着虚无缥缈的事,没有白费时间和生命,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重要的事业。
或许我体会到的东西别人已经写过了,怎么可能避免呢,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啊,但这并不说明我在写之前先得想出怎么写得和别人不一样的办法,我就是要由着这个充塞着小金桶的自由之身把当时的情状老老实实地倒出来,它必定是我的,有着我生命习性的独特气味,技术手段也会像呼吸感应一样随之产生,自有其模样。事物瞬息都在因联系的变化而变化,人的感觉也是,一切都在互动中千娇百媚地变异闪烁,越神秘得难以说清就越渗透得细致入微,模糊一片。认真发挥了个人的作用,就是参与创造,参与变化。
一阵风使我感动震撼,那是因为它先经过了万事万物,我的微小的心思都连着那繁复隐衷,它们在触动我的秘密,电击般互相散射开闪闪发亮。
我说话不拐弯抹角,真诚直接,别具一格,因为那是在说你,是你使我这么说,我诗歌里的一个个字、一个个词、都是你的一滴滴水、一粒粒盐、一块块砖、一截截钢筋、一枚枚小钉,一寸寸闪电、星光、细雨、风暴、血管和神经,让我就这样慢慢挨近你,我是和你关系最密切的人。如果我越来越不经意地说出你,那是你越来越不经意地进入我的心里。
就这么一再地感应我,逼迫我,激活我,让我在孤独中繁荣充盈,我是被宠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