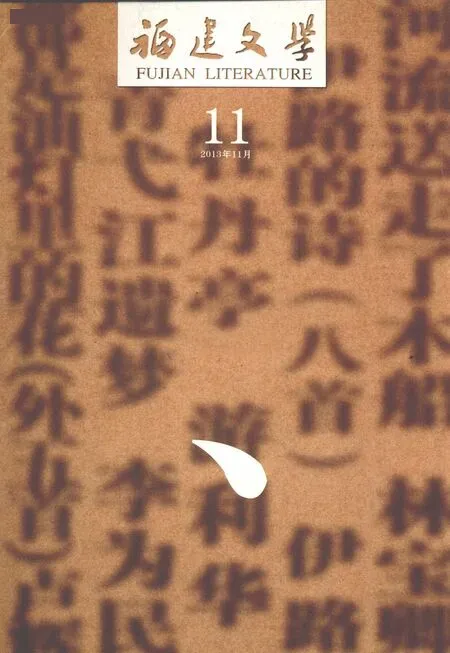美人胚子(外一篇)
□张建平
她在娘肚子里,便不知被男人偷看多少眼了。等她长成个一掐就出水的少女时,关里关外,那些臭男人的眼珠子,就成了暗影里的蚊子,逮着就猛咬一口,眼珠子就鼓鼓的。有吃不到葡萄的人,酸溜溜地说,不就是张画皮吗?也是个屎肚子!
她不施脂粉,冷若冰霜。一天上午,她坐到了修表店的橱窗里边,边接待顾客,边修表。那天很热,她从粉红半袖里露出的玉臂,汗毛都看得清。消息比腿跑得快,下午,修表店嗡嗡的,如蚊子团。他从公社骑车赶来,拿着父亲祖传的瑞士手表,候了半天,才挤到近前,撮着鼻子,吸了口气,将表递过去。她蹙眉冷脸,看不惯他色迷迷的样子,厌恶地朝后指了指老师傅。他摇头,让她收下,她摆手不要,拒绝了。他笑着赖在窗口,被后面心急的人撵了出去。她剜了他一眼。第二天、第三天,他又来了,她照样不理。却不知,他爱与美女打交道,他用刀子在心里比划了一番,为引起她的注意,情愿冒着被偷换零件的风险,也把表交给了老师傅。一星期后,他再次光临,对着她的窗口,咚咚咚,弹了弹硬硬的表壳说,值,值得!
两年后,他当了公社兽医站站长,她成了他的新娘。好奇的人,挠着头发,想不出个中道理。流行的版本是,他曾经大口应承,她必须每天化妆。
这有何难?化妆品,买得起的。她最初用雪花膏,后来是美加净,再后来,就连名字也想不清了。起初,几分钟就化完了,后来是半小时,再后来,就一两个小时了。衣服,早先,婚礼服装倒替着穿,挺显眼,后来,几个月买一套新的,走在路上扎眼球,再后来,几天一换,虽不昂贵,衬她苗条的身子,倒也天衣无缝。即使这样,去修表店,看美人的越来越少了,因为街上化了妆的美人,越来越多了,她掺在里面,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了。何况,她的年龄……有个恶作剧的人就说,那某某,后面看,馋死个人,前面看,起鸡皮疙瘩啊。
素颜就很好,何必折腾?他多次提醒她。
谁知,她一句顶一万句,干净,有罪?
难怪,她的爷爷生前做寿材,有人不小心冲着打了个喷嚏,便令人重新做了一副。刚结婚,他去前边院子挑水,进门时,屁股随风透了阵味儿,她就将后边那桶水泼了。
于是,他懒得管了,她也自得其乐。
不知哪一天,修表店关门了。下岗的她,半年后,在东关的一条巷子里,租了一间门头,重操旧业。生意却是十分清淡,大概只有一些老客户,知道她的手艺,才上得门来。新的主顾,多半是些中年以上的人,闲逛碰巧了,才来到这儿,看见门店拾掇得洁净,就耐心坐下来,翻看些旧的报纸杂志。偶尔抬头,瞟一眼她染得红红绿绿的手指甲。除了修各种电子表,放心来她这里的,修旧表名表的人多,不管多么珍贵的表,内芯外壳,修好后,完璧归赵。她清楚,当年老师傅,就将他那块表最贵的部件落下了,这使她不安,也为她不齿,从此再不登老师傅家门。她修表,尽量给人省钱,能用的零件,修旧利废,要换的,也征求了人家的意见。这就少了口舌,小小的店铺,竟得了诚信的名声。
女儿在北方的一个城市婚后生子,她惜别了转给别人的铺子,捎着一袋子鼓鼓囊囊的化妆品,坐上了北去的大巴车。
每天,她有两份课程,大部分时间照料外孙,有点小空闲,就安静地对镜化妆。女儿埋怨她,整天不出屋,不下楼,给谁看?
她不笑,也不反驳,没挪窝儿,照旧描眉画唇点眼影。
有一次,女儿回来喂奶,发现儿子躺在床上号啕,她却正往脚趾上涂抹,顿时火冒三丈,上来就将她的用品,一股脑扔到了垃圾桶里。女儿气愤地质问,我的妈,你……你想把我的男子汉,打小就熏成脂粉气?
她慌了,怕了,结巴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泪汪汪的。好几年,把心思,都放在了外孙身上。
外孙上学了,她呼出一口长气。她感到乳房胀痛,女儿陪她去医院,她坚决拒绝手术,不容许手术刀,毁掉自己身上完美的东西。
女儿哭了,买了价值不菲的化妆品,摆在她的床头柜上。
每天,她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静静地坐在床前,安详地仔细地化妆,似乎将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直到她不能起床翻身了,女儿醒后,先给她化好妆,才去上班。
一天,女儿回家发现,她的头垂在床沿上,额上有块血渍,已经没了呼吸。女儿哭泣着,最后一次,帮她补了前额上的妆,又在她的两个酒窝上,抹上了一层浅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