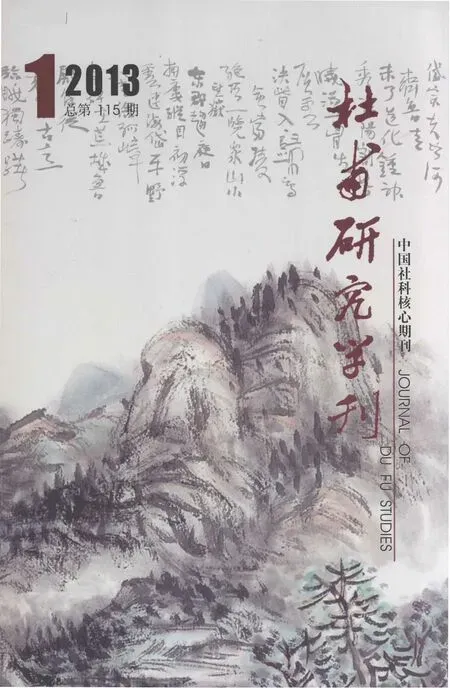比较杜甫《归雁》和韦应物《闻雁》——看《归雁》的张力艺术
雷文学
作者:雷文学,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350007。
杜甫有《归雁》一首: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
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
韦应物有《闻雁》一首:
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这两首诗有诸多类似之处:它们都是诗人因人生的不幸而远离家乡的思乡诗。在写法上,都是借飞过的大雁表达思乡之情。诗歌结构上,两首诗都是先用前两句铺垫,再用后两句核心意象将诗情引向高潮。从诗意上讲,两首诗用大雁的意象来传达思乡之情都达到了动人的艺术效果。但是,两首诗的艺术水准还是有较大差异:《归雁》显然表现了更深厚的情感,作者以更广阔的同情心对自己的命运给予了观照,诗歌给读者的冲击力更强,《归雁》的艺术水平更高。这种效果的造成,来源于《归雁》的作者在诗中充分地制造了张力;相比而言,《闻雁》的张力就显得薄弱得多,尽管它在艺术上因为有动人的意象也可算是优秀的诗篇。
“张力论”是英美新批评重要理论之一,在诗歌的文本分析中起到相当作用。“张力论”为美国现代诗人、批评家艾伦·退特提出,他说:“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张力最初的含义与逻辑术语“外延”和“内涵”相关,退特加以发挥,把它变成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外展”和“内包”这两个词有些拗口,但它们还是基本指出了张力所涉及的两个基本要素:诗歌所展现出来的外在意义及这些外在意义所包含的内在思想情感。外展和内包相互对立而又能使对方得到强化:外展充分必定加强内包,内包的充盈也必定衍化出更丰富的外展。张力论后来被其他新批评家扩展到诗的内容与形式、构架与肌质、韵律与句法等诸多对立范畴之间,成为这个派别文本细读的有力工具。
《闻雁》和《归雁》都是五绝,我们不妨以词为单位,把诗句切割为最小的意义单位,这样,两首诗都可以切割成12个语义单位。切割后的《闻雁》是:“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这首诗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韦应物由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刺史后不久所写,它表达的是:诗人身处异乡,乡关之思郁郁,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恰遇孤寂的秋雨之夜,一只从北方家乡方向飞来的大雁飞过自己高楼上方时凄凉地一叫,乡关之思被一下啼破,显得格外感伤。作家为了表现这样的思乡效果,采用了先铺垫再用一个动人的意象将诗情推向高潮的手法。这是高明的,它使诗歌的浓度在短短的篇幅里迅速加强,而在一点集中爆发,从而造成一种较强烈的艺术效果。显然,诗歌的精华集中在后两句,尤其是第三句,这一句五个字三个词,每一个词都有力度。“淮南”体现了环境的变幻,暗示了诗人心境的不安定。“秋雨”渲染了凄清的氛围。“夜”暗示了环境的孤寂。下一句中有表现力的是“高斋”一词:身处高斋,听闻雁叫声有更清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古诗中向有登高楼而远眺的传统,很多表现的是孤寂的幽思,因而,“高楼”“高斋”总为一种特定的孤寂的氛围所笼罩。在这种氛围中,诗人雨夜独处高斋、闻雁叫而翘首北望的画面在读者的想象中也特别动人。“闻”、“雁来”两词均只起点题的作用,没有更多的暗示意义。同样,诗歌开始的两句主要只起铺垫的作用,“渺”可暗示家乡遥远,但不具体,仅仅告诉读者诗人远离了家乡,对家乡很思念,为下文的抒情作铺垫。一、二两句的六个词几乎没有暗示意义很强的;全诗有表现力的词集中在“淮南”、“秋雨”、“夜”、“高斋”等四个词语上,这四个词制造了这首诗逻辑学意义上的“外展”,暗示了思乡这个“内包”,形成诗歌的张力。这里,思乡之情这个“内包”所到达的浓度完全取决于上述四个词所形成的“外展”所到达的强度。
《归雁》可切割为:“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这首诗是杜甫结束在四川九年漂流中相对安宁的生活,于大历三年(768年)出峡沿江东下,继续向东南漂流的路上写下的。在写法上,这首诗与《闻雁》一样,都是先铺垫再通过“雁”这一意象将诗情引向高潮,只不过这里是看到的雁,向北飞向家乡的方向;《闻雁》是听到叫声的雁,从北方的家乡方向飞来,但同样引起思乡之情。在这一总体框架结构类似的情况下,《归雁》在用词上表现了独到的特色。上述《闻雁》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主要集中在后两句的四个词,前两句几乎只起铺垫作用;但在这里,几乎每一个词语都有自己独到的作用和表现力。“东来”写行程的方向,这种方向的转变暗示了诗人内心对前程的茫然感。需知杜甫自安史之乱爆发,从长安流落四川,在四川又辗转成都、梓州、夔州等地,辛苦飘零,思家不得,现在又东去万里,不知流落到何处,茫然感可想而知。“万里”是夸张又不似夸张,从他离开长安辗转至今,行程离万里已不远。这种看似夸张的手法写出了辗转的艰辛、离家渐行渐远的痛楚。“客”写出辗转异乡的生疏感。“乱定几年归”应理解为:还有几年才能平定叛乱,我好能归家呢?“乱定”写出了诗人对叛乱的厌恶、对平定叛乱的渴望;其中又自然暗示了多年乱离的社会现实。“几年”写出诗人的渴望,同时也写出了诗人隐约的不安和绝望:需知杜甫此时已57岁,身体不好。就在写这首诗的前一年,他在《登高》中写自己“百年多病独登台”、“潦倒新停浊酒杯”,即是因肺病严重不得不戒酒。因而,即使安史之乱几年后能平定,自己还有没有生还家乡的可能呢?还有,这种对未来的渴盼还暗示了诗人已经飘零了多年,以及在多年的飘零中一次次地渴盼成空。“归”则直奔主题,用在此处,似普通,实则力度不凡。
有了上述铺垫,诗人在流浪的旅途忽见一只大雁高高北飞引起的“肠断”之感也就自然而然,因而在第三句开头诗意的转折处下一“肠断”,不但贴切,而且将读者的感受跳跃性地导向痛楚感的深处!大雁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就很有力度;不但如此,诗人在“雁”字前似不经意加一个修饰词“江城”,这种其实是有意的指称不但标明了写作此诗的地点,而且通过一个具体的异乡地名再一次强化了诗人流浪之途的空间变幻感,他似乎在心里轻轻地说:“这就是江城啊,我来到江城了啊!”诗人在“飞”字前加了两个状语“高高”和“向北”,“向北”所暗示的情感指向不言自喻,读者仿佛能感觉到大雁的翅膀每向北扇动一下,诗人的痛楚就加深一次。“高高”尤有神韵,这种重叠的词语有高不可及、自由自在的感觉,大雁能躲过人间的战乱和一切不幸,自由地飞向北方的家园,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向往,也暗示了作者归家不得的绝望,其中包括一幅动人的想象图画:万里楚天之下,一个穷困的诗人,抬头远望一行北去的大雁,久立不去,这是可以叫人叹息而至于泣下的。
由此看来,本诗几乎每一个词(除了“雁”和“飞”两个指示词以外)都有充沛的意义,都在诗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构成了诗歌的“外展”。外展充分总能极大地加强内包,由于本诗整体的思乡“内包”由众多富有表现力的“外展”撑起,这些外展从多方面对内包进行了开掘和强调,因而形成极大的张力,使得这首诗的情感极为饱满。相比而言,《闻雁》外展的强度及其所形成的内包的浓度就要逊色得多。具体说,两诗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差别:
第一,从词语数量上看,《闻雁》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是4个,《归雁》是10个。《归雁》全诗几乎每一个词语都有作者情感和心理的深深刻痕,每一个词都有充分的暗示,整体上造成一种强烈的张力。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实不仅如此,优秀诗歌中每一个词都是情语。这是杰作的魅力。
第二,从词语的表现力来看,可以把两诗各自12个词分为4类:表现空间的、表现时间的、指向心理和情感的及纯指示性的。纯指示性的词《闻雁》有4个:方、闻、雁、归思,《归雁》有2个:雁、飞,表现力均较小,可不论。
表示空间的词《归雁》有5个:东来、向北、万里、江城和高高,这些词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强调天涯异乡的感觉,空间又指向不同的方向和地域,极为开阔,情感极为开张。《闻雁》表示空间的词也有4个:故园、何处、淮南和高斋,故园和何处能起到开张空间的作用,但不够具体,表现力不强;有表现力的是淮南和高斋,但限于一地,故整首诗空间的开阔远不及《归雁》,其实反映的是作家的情感不如《归雁》作者的博大。一个情感博大、境界高远的诗人总是下意识地选用那些能表现博大空间感的词语。“高”(高斋,高高)的感觉是两首诗的精华,都能表达翘首凝望、怅然若失的深沉的思乡感,但两诗境界大不一样:《闻雁》是在“高斋”闻雁声,空间较小;《归雁》是在江城看到大雁,且高高北飞,有一种以天地为背景的气概,境界的不同显而易见。且《闻雁》的作者是在“斋”中,有寄寓之所;《归雁》的作者在江城看雁,处流浪之途,人生的感受自有深浅之分。因而,同样是在感受高处的大雁,但两诗感情的开阔和深厚程度显见不同。
表示时间的词《闻雁》有秋雨、夜,只是一个特定的凄清孤寂的时刻;《归雁》只有一词:几年,但如上所述,这个时间既指向将来也指向过去,暗示了作者长期的心理焦虑和对未来的渴盼与绝望,时间的跨度及其所包含的情感浓度自是《闻雁》无法比拟的。
由东来、向北、万里、江城、高高所形成的宏大的空间和“几年”所形成的久长时间撑起《归雁》巨大的时空感,这种纵横的时空暗示了在一个乱离世代里一个诗人乱离的生命历程及其中蓄积的巨大情感内蕴,《归雁》因而有诗史的品格,这比《闻雁》的一时(秋雨夜)两地(故乡、淮南)所形成的时空感,自有境界大小不同。
指向心理和情感的词《闻雁》有两个:渺和悠哉,它表现的是对家乡的渺远感,情感相对悠然平静。《归雁》有三个心理和情感指向明显的词:客、肠断和乱定,这几个词情感强烈,对人的心理冲击力均极强,是作者身世受到环境强烈刺激的产物;特别是在思乡心理中暗示了乱离的时代背景,表现力也非《闻雁》所比。
第三,从诗歌结构上讲,《闻雁》的前两句基本只起铺垫的作用,在前诗中的地位是服务性的,张力很弱,本质是散文。《归雁》的前两句也起铺垫作用,但同时它也是自为的,在服务中有自主,撑起饱满的张力,本质上是诗。故而《归雁》整体情感效果远胜于《闻雁》。新批评派理论家兰色姆提出“构架—肌质”理论来解诗,认为一首诗有一个中心逻辑构架(构架),也有丰富的个别细节(肌质),并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肌质而不是构架。从这种理论来看,《闻雁》和《归雁》均以大雁来表达思乡之情,均采用先铺垫再以“大雁”将诗情引向高潮的手法,构架可谓相同;但两诗在细节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导致两诗的艺术效果不同。这印证了“构架—肌质”理论的合理性。
第四,从音韵效果上看,《归雁》5个表示空间的词东来、向北、万里、江城、高高共10个音调大部分都是平声字,特别是5个词的末字,没有一个是逼仄感的去声字;甚而全诗整体的音节感饱满、舒缓、开张,这种音韵效果,与诗人深沉宏大的情感相一致,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所鼓张的结果。这是杜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如“风急天高猿啸哀”、“巫山巫峡气萧森”、“千家山郭静朝晖”等诗句绝大部分用平声,打破平仄相间的常规格律,很恰当地抒发诗人博大开张的情感。而三个表示心理和情感指向的词:客、肠断和乱定,末字则一律用急狭的去声字,这种语感则与诗人沉痛和烦乱的心绪相一致。相比而言,《闻雁》音韵平缓,情感相应也不甚强烈。这是两诗在音韵上的张力差别。
这些就是《归雁》堪称经典而《闻雁》虽优秀但尚不能称为经典的原因吧。
注释:
①退特:《论诗的张力》,见《“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②有大气魄、有沉着之致的诗歌往往如此,如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起句“钟山风雨起苍黄”气魄雄浑,整句诗七个字有六个是平声字,很好地表现了这一雄浑镇定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