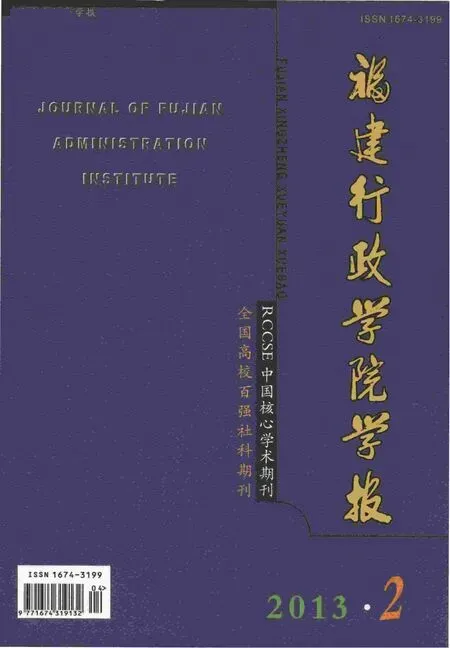中国婚姻挤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基于普查数据的时期分析和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
邹艳辉,黄匡时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100871)
一、导 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我国生育率逐渐下降,而出生性别比却日渐升高。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引起学者们对其形成机制和婚姻后果的广泛关注。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于出生性别比升高而导致的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现象日益得到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婚姻挤压,又称“婚姻拥挤”、“婚姻压缩”、“婚姻紧缩”、“婚姻剥夺”、“婚姻排挤”等,是指由于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在同期群中出现的数量失衡而导致男性和女性择偶关系的紧张或找不到配偶的现象。婚姻挤压表现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婚姻领域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失衡。因为一个人一旦进入婚龄后,就会身不由己地置身于婚姻市场之中,被纳入到婚姻配偶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体系之中,然后在这个婚姻市场和供求关系中进行比较、选择或被选择和匹配。[1][2]2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体制下,由于婚姻市场供需失衡,即婚姻市场可供选择的男性和可供选择的女性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由此导致了男性或女性不能按传统的偏好择偶,婚姻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我国传统生育文化中男孩偏好影响深远,在我国一直是男性婚姻挤压严重。当然,最近也有研究发现,高学历、高收入和高年龄的女性也遭遇婚姻挤压[3],由此,“剩男”“剩女”之词频繁出现于媒体、学者,甚至大众之口,成为婚姻社会学和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关于婚姻挤压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一是针对婚姻挤压的成因和后果的理论性研究。Avigdor Beiles认为,在不考虑国际迁移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出生人数的变化和夫妇年龄差三个因素可以解释婚姻市场不平衡:出生性别比决定了在生命的初始阶段男女的相对比例,而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影响了出生后的人口存活到进入婚姻市场的数量;在现实社会中,男女结婚年龄和年龄差的分布趋于分散,所以出生人数的变化和夫妇年龄差对适婚年龄的男性和女性相对平衡也产生影响。[4]郭志刚和邓国胜认为,广义的婚姻拥挤影响因素包括出生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人口迁移、夫妇年龄差偏好、年龄结构变动、再婚、历史婚姻拥挤的传递和个人性格相貌与社会经济条件;狭义的婚姻拥挤影响因素只包括出生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人口迁移、夫妇年龄差偏好、年龄结构变动。郭志刚和邓国胜还提出了婚姻市场理论的基本假设: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是影响婚姻市场最为直接的两大人口因素;夫妇年龄差既是影响婚姻市场的原因,也是婚姻市场变化的结果。这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婚姻市场变化的内在动力。[5-6]社会经济因素(包括文化、政策因素)是影响婚姻市场变化的外生变量,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影响夫妇年龄差模式间接影响婚姻市场,而婚姻挤压的出现也会促使人们做出积极的反应。李树茁等人认为,影响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因素主要包括: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孩死亡水平;出生人数不断缩减和传统的男大女小婚配模式;急速上升的离婚率和再婚水平。[7]225-226
不少文献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后果进行了系统研究。Hudson and Boer等的研究表明,婚姻拥挤不仅对终身不婚比例、初婚年龄和夫妇年龄差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大量的非自愿单身男子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单身未婚者本身的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婚姻及家庭的稳定性问题、非婚生育与私生子问题、独身者的养老问题、色情业和拐卖妇女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危害社会稳定,从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安全问题。[8]Li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所反映的女性短缺,本身所反映的是女性的出生权和生命权这样的最基本的权利被剥夺,侵犯了女性的生存、参与、保护和发展的权利,阻碍了生产力、效率和经济进步,损害社会与人口的整体福利,危及中国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9]
针对我国婚姻挤压的实证性研究,主要关注过去、目前和未来婚姻挤压的总量和相对量。郑维东和任强研究认为,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婚姻挤压是男性挤压型,1950年到1987年之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50~1960年低水平波动时期、1960~1970年第一次高水平波动时期、1970~1980的第二次更高水平的波动时期和1980~1987年较低水平的波动时期;而在1990~2050年,最高时婚姻挤压指数将达0.034(大约在2020~2030年之间),最低时也在0.001以上,其中婚姻挤压指数平均在0.02左右,即相应于每100对男女初婚,将会有两名“额外”男性终身丧失结婚机会。[10]33郭志刚和邓国胜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婚姻市场常常处于失衡状态,只是不同时期失衡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2]520世纪60年代我国出现的婚姻拥挤则是建国以后我国大陆婚姻拥挤程度最高的一次,而20世纪50年代出现在我国台湾省的婚姻拥挤也是世所罕见的。而伴随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老龄化加剧以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多重作用,2015年和2020年大陆的初婚市场可供选择的男性比女性分别多11.37%和15.98%,婚姻拥挤程度比建国后婚姻拥挤程度最高的60年代要高一些,但比1955年我国台湾省婚姻拥挤程度要低得多。Tuljapurkar等人认为,中国每年新增百万在本国找不到配偶的过剩男性。[11]874陈友华的研究表明,2015年20~49岁男性过剩人口超过2000万,2025年超过3000万,2035年超过4000万,在2040年左右达到4400万人。[12]Poston and Glover研究认为,中国1978~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300万人。[13]121李树茁等人研究发现,未来中国婚姻市场每年有10%~15%男性过剩人口,达到120万人。[7]217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20~45岁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14]潘金洪预测,到2050年婚龄人口性别比高达117.17,男性婚配富余比高达14.66%,2050年婚龄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5298万人,调整后的数据为5394万人,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婚龄人口男女之差多出3143万人,增加1.4倍。[15]22姜全保等人的研究认为,从2000年开始,中国会面临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2016~2046年平均每年过剩男性在120~150万之间,2060年之后每年在50万之下。[16]45Poston等人的研究认为,估计中国在2020年前后将出现5000万到5500万光棍。[13]136此外,也有少数者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统计值偏高所导致的婚姻挤压问题的严重程度提出过质疑[17-19],尽管出生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婚姻挤压现象已经成为共识。
不同学者对中国婚姻市场上男性过剩人数和比例有不同的结果和发现,有的甚至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不同。在数据上,已有研究主要使用2000年普查数据[7]213和1990年普查数据以及1982年的普查数据[20]25[21]3;有的将婚姻挤压限定在不同的年龄范围内,比如Tuljapurkar等人把初婚频率的年龄区间限制在50岁以下,[11]874李树茁等人则将年龄限定在14~60岁;[7]211郭志刚和邓国胜只关注22~36 岁的男性和20~34 岁的女性[2]5;陈友华等关注20~49 岁的男性和女性[21]5[22]58;有的将婚姻挤压限定在初婚市场[2]16,有的综合了初婚市场和再婚市场。[7]218在研究 方法上,不同学者大多采取不同的测量指标。Tuljapurkar使用度量潜在的两性相对规模差异的潜在初婚比指标来研究中国的未来婚姻挤压问题[11]875,李树茁等则将基年的性别比纳入到Tuljapurkar1995年的潜在初婚比模型[7]212,姜全保等设计了初婚频率标准化模型和初婚频率去进度化模型[16]42;顾宝昌、彭希哲、于学军、郭志刚和邓国胜等使用初婚市场的婚配性别比或相对性别比指标来研究中国的婚姻拥挤问题;[2]3[20]26[23]郑维东和任强使用Robert Schoen[24]的婚姻挤压指数(Marriage Squeeze Index)对我国1950~2050年的婚姻挤压进行研究[10]29;陈友华等用相对性别比、单身性别比、单身与未婚人口比例、单身婚配性别比、15岁时的平均期望婚姻寿命和婚姻寿命指数等指标分别对中德两国的婚姻挤压进行了对比研究[21]6[22]59;潘金洪使用同期群婚龄男性性别比和数量差来测量中国的婚姻挤压。[15]22
不同的方法各有优缺点,而且都没有针对性地对每年的富余男婴进行队列分析和依据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六个时期点对富余男性人口进行队列和时期分析。本文将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次普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时期分析和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利用出生性别比、同龄性别比、富余男性人口等指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市场情况,并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预测未来40年人口变化趋势,然后分析未来中国婚姻市场的变化情况。

图1 1950~2011年我国出生性别比和出生率演变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数据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基于六次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婚姻挤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趋势。在对1950~2010年的婚姻挤压分析中,主要采取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重点利用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过去和现在中国的婚姻挤压状况。在时期分析方法中,主要采取同期群婚龄性别差的方法来获得分年龄男性剩余人口,然后将婚龄男性剩余人口加总并获得某一时期的男性剩余人口总量。本研究认为,所谓男性剩余人口是指进入法定婚姻阶段的剩余男性,包括尚未去世的老年光棍。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对于结婚年龄的规定是男20岁,女18岁。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婚姻法》根据当时的国情确定了将婚龄提高两岁,即男22周岁,女20周岁。此后,男女两性的法定婚龄一直没变。因此,本研究将1953年人口普查和1964年人口普查的男性剩余人口的计算年龄范围限定为20岁以上,而将1984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剩余男性人口的计算年龄范围限定为22岁及以上。
时期分析中每年男性剩余人口规模可以表达为:

其中,x 为年份,Sx指的是某一年份的男性剩余总人口,i指的是年龄下限,j指的是年龄上限,通常每年的男性到一定年龄后会少于女性,j指的就是这个年龄。pmi指的是i 岁的男性人口,pfi指的是i 岁的女性人口。
在未来预测中,本研究主要使用队列分析方法,重点关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出来的男婴对未来的婚姻市场所造成的挤压。首先,根据每年的出生率和总人口获得每年的出生总人口,然后根据性别比获得每年的新出生的富余男婴。其次,根据当年出生的男性死亡率假设该年出生的男性遵循出生年份的分年龄别死亡概率能进入22岁及以上的男性剩余人口。而未来某年的男性剩余人口总量是22年前及更早时期的富余男婴的存活人口。由此,本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每一年度的男性剩余人口总量,而且可以获得每一年度的男性剩余人口的年龄结构。最后,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假定:(1)未来出生性别比从2010年的118.06以每年相同的速度(斜率)降低到2030年的107并且以后基本稳定在107;(2)未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63以每年相同的速度(斜率)降低到2030年的1.60,并稳定在2030年的水平;(3)未来男女两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1.75(男)和75.32(女)逐年稳步增加到2050年77.34(男)和81.32(女),然后预测未来40年每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包括每年的富余男婴及其存活到22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
在队列分析中,每年的剩余男性人口总量可以表达为:

其中,x 为年份(x≥2005),Sx指的是某一年份的男性剩余总人口,Lx-19831983指的是1983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x-1983)岁的存活男性,同样地,Lx-19841984指的是1984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x-1984)岁的存活男性,L23x-23指的是(x-23)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23岁的存活男性,同样地,L22x-22指的是(x-22)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22岁的存活男性。比如S2005=L221983,指的是1983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22岁的人口数量,又如,S2050=L671983+L661984+……+L232027+L222028,指的是从1983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67岁的人数加上1984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66岁的人数,依次类推,一直加到2028 年出生的剩余男性活到22 岁的人数。
在队列分析中,由于难以获得每年的男性人口的死亡率,本研究假定1983~1988年的富余男婴遵循1984年人口普查时的男性年龄别死亡率,1989~1999年的富余男婴遵循1990年人口普查时的男性年龄别死亡率,2000~2009年的富余男婴遵循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男性年龄别死亡率,2010~2050年的富余男婴遵循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男性年龄别死亡率。
由此可见,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有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在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对剩余男性进行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二是将焦点放在剩余男性和富余男婴上;三是考虑富余男婴的年龄别死亡率;四是针对每年的富余男婴进行队列分析,这一方法不仅可以获得每一年度的剩余男性人口的总数,而且还可以获得每一年度的剩余男性的年龄结构。
(二)研究数据
本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数据:一是历次普查数据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含分年龄性别比)和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包括1953年人口普查、1964年人口普查、1982年人口普查、1990年人口普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10年人口普查。二是历年出生率、总人口规模和出生性别比数据。历年出生率和总人口规模来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1950~1959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1960~1979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顾宝昌、许毅的《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1980~1987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88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1989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1990~2011年出生性别比数据来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三是2011~2050年人口预测数据。本研究将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国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平台和国际通用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 对未来中国40年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预测。为了简单起见,本研究采用中间方案来设置死亡参数、生育参数和出生性别比参数,预测未来40年每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包括每年的富余男婴及其存活到22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
三、研究结果
(一)中国婚姻市场的过去和现状
以往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婚姻市场男性挤压型失衡是常态,只是不同时期失衡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通常认为,1960~1970年是建国以后我国大陆婚姻拥挤程度最高的一次。[2]5也有研究认为,1970~1980有第二次更高水平的拥挤。[10]33本研究通过六次人口普查时点数据观察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婚姻挤压时期:一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整个60年代高度拥挤时期,这个时期的男性婚姻挤压是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婚姻拥挤时期;二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整个80年代的中度拥挤,这20年的婚姻拥挤是60年代的继续;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轻微拥挤,它是60年代和70年代以及80年代婚姻拥挤的余波。
第一,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拥挤期。从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1964年有1200万婚龄男性剩余,占整个婚龄男性的8.5%,在六次人口普查时点中剩余男性比重最高。从两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一时期的婚姻挤压主要是50年代之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的。1953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37~1950年出生的3~16岁的年龄组中的出生性别严重偏高,平均性别比高达114,其中1939年出生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20。这些群体在4年后即进入婚龄期,由此导致从1957年开始我国出现建国后的首次婚姻拥挤期。从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从4~42岁的年龄组都出现性别比偏高,尤其是24~38岁这个黄金婚龄期的性别比都在110以上。可见,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婚姻挤压最为严重。此外,1964年普查显示的4~14岁年龄组的高性别比将会使60年代的婚姻挤压延续到1976年。
第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度拥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婚姻拥挤主要是受到60年代的影响。首先,60年代已经进入婚姻年龄阶段但是尚未结婚的男性将不得不推迟结婚,由此导致70年代乃至80年代的婚姻拥挤。从1964年普查数据来看,28~42岁这个年龄组的男性到1982年普查时性别比依然很高。尽管他们在1982年已经处于46~60岁的年龄组,但是他们依然处于婚育年龄阶段。其次,20世纪60年代尚未进入婚龄阶段的富余男孩或富余男婴进入70或者80年代之后正好处于婚龄阶段,他们构成70年代或者80年代主要“剩男”人群。尽管1982年“剩男”的总数比1964年多800万,达到2000万,但是由于总人口在增长,所以其占整个婚龄男性的比重只有8.36%,比1964年的8.5%略微低些,但是依然比重很高。可见,70年代和80年代的婚姻挤压也是比较严重的。与1964年的婚姻拥挤相比,1982年的“剩男”主要是32~60岁的中高年龄群,而22~31岁之间的黄金婚龄期的男性富余人口并不严重。
第三,20世纪90年代的轻微拥挤。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男性剩余人口总量达到2200万,创历史新高,不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人口增长惯性导致,男性剩余人口占整个婚龄男性的比例只有7.33%,比前两次要低。1990年主要是40~60岁之间的男性多于女性,而其他年龄组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正常。这主要是60年代和70年代以及80年代的婚姻挤压的余波。
进入2000年之后,我国的婚姻拥挤基本不存在。不过从2005年开始,由于80年代以来的高出生性别比影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严重的婚姻拥挤时期。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并不处在婚姻拥挤期。2010 年我国剩余男性只有1400万,占全部婚龄男性的3.13%。不过,由于我国从80年代中期至今持续的高出生性别比,这些富余男性正在迈向“剩男”。而且从1983~2011年,我国正在以每年增加131 万富余男性的速度在增加。一个婚姻拥挤的时代即将来临。
(二)中国婚姻市场的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婚姻市场将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剩男”峰值将达到4141万。如图4所示,从1983 年以来多生的男性积累到2043年将达到峰值4141万。此时,男性剩余人口占整个婚龄男性的比重达到7.6%。图4还显示,在未来的30年内,我国剩余男性将快速上升,在21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呈下降趋势。然后到2070年左右,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到2030年多生出来的“剩男”将下降到100万以下,所占比重也将不到2%。
第二,七成“剩男”已经出生,未来新增“剩男”将减缓。根据估计,从1983~2011年间出生并将存活到22 岁的“剩男”占1983~2048年出生并将存活到22岁的“剩男”的71%,而且在1983~2011 年的29 年间平均每年以131万的速度增加;从2012~2048年的37年间,每年平均新增“剩男”43 万,不到过去29年新增“剩男”的1/3。可见,绝大部分“剩男”已经出生,正是目前处于青少年时期。未来的30年里,这些人将陆续从富余男孩或男婴进入“剩男”。
第三,2043年“剩男”六成处于结婚黄金年龄。图6 显示,2043 年 的4141 万“剩男”中,60%处于25~45岁的黄金结婚期,而只有20.5%的“剩男”处于51~60岁之间。从形状上看,图6像一座高原图,即大部分男性剩余人口集中在黄金结婚年龄段,而且最高比例在30岁的结婚高峰年龄。
第四,老年光棍数量庞大而且比重越来越高。如图7所示,50岁及以上光棍总量将从2033年的68万开始日益上升,到2054年达到1784万,占全部剩余男性的51%。此后老年光棍逐渐增多,到2070年老年光棍达70%。图8还显示,60岁及以上光棍总量将从2043年的61万开始日益上升,到2058年达到968万,占全部剩余男性的33%。此后60岁以上的老年光棍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多,到2070年老年光棍达47%,几乎接近一半。如此庞大和高比例的老年光棍将来照料问题值得关注。

四、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建国以来的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采取队列和时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市场进行分析。与前人研究相比,本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并得出了一系列新的发现或结论:
第一,本研究在对深入观察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拥挤进行了阶段划分,基本结论和前人研究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本研究不仅区分了三次婚姻拥挤的基本特征,并对三次婚姻拥挤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本研究认为,1950 年以来我们存在三次婚姻拥挤期,其中20世纪60年代最为严重,70~80 年代其次,90 年代最轻。而且70~80年代是60年代的继续,90年代则是前两次的余波。1964年的婚姻挤压属于黄金婚龄组的挤压,而1982年则是中高婚龄组挤压,1990年却是高婚龄组挤压。
第二,本研究在对1983年以来每年出生的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的基础上,不仅考察了当前我国婚姻挤压现状,而且对当前人口规模和结构特征对未来男性挤压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认为,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里,我国并没有存在明显的婚姻挤压。但是,这20年却是未来新一轮婚姻挤压的生成期或潜伏期。从1983~2011 年已经出生了未来70%的“剩男”。这些出生的富余男孩将会在未来20年内每年以131万的速度加入到“剩男”队伍中。不过,未来新出生的富余男婴将会减少,2012~2048年大约以每年43万富余男婴的速度在增加。

第三,本研究将关注点放在从1983年以来所新增加的剩余男性人口队列上,这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和准确。本研究发现,大约在2028年,我国剩余婚龄男性将超过3000 万,此时剩余男性占整个婚龄男性的5.6%;在2043年达到4141万的峰值,此时剩余婚龄男性占整个婚龄男性的7.6%;而且在2057 年我国剩余男性才低于3000万,也就是说,我国有3000~4000万的剩余男性的时间持续30年之久。本研究对未来剩余男性的总量估计和陈友华的总量估计比较接近[13]136,不过,本研究不仅仅限定在20~49岁的年龄组,而是包括22岁以上的所有年龄组的男性剩余人口。由此可见,Poston 等人断言未来中国会在2020前后有5000~5500万剩余男性显然夸大了。[13]138当然,由于本研究假定未来出生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在2030年之后趋于正常化。如果未来出生性别比保持在2012年水平或者在2030年之后依然偏高,这样剩余男性的数量将会增加,也许数量会更多。但是在2020年前后有5000万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未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也许在2050年左右会达到5000万,甚至更多。
第四,本研究通过对富余男婴的队列分析方法获得了每年剩余男性的年龄结构,这是本研究在分析婚姻挤压上的一大创新。这使得关注剩余男性的年龄结构成为可能。本研究发现,从203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50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光棍,这些人群的比重逐渐占全部光棍的50%以上;而且从2043年开始,1983年出生的剩余男性将陆续进入60岁,到2058年60岁以上的老年光棍达到968万,占全部剩余男性的33%。此后60岁以上的老年光棍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多,到2070年老年光棍达47%,几乎接近一半。如此多的老年光棍的照料问题引发关注。这些群体没有组建家庭,只有通过养老院等社会方式来养老。更重要的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加入鳏寡孤独群体中的“鳏”(老而无妻)、“孤”(无亲无故,父母或兄弟姐妹健在的不多)、“独”(老而无子女)中的三大类,这使得整个社会的老年照料问题愈加突出和严重。
第五,本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市场的考察和分析,引发一个重要的思考:既然20世纪60年代我国男性剩余人口占全部婚龄男性的8.5%,如此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尚且经历过,未来我国男性剩余人口占全部婚龄男性的比重均没有超过8%,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必要担心未来婚姻市场上的男性挤压问题?还是我们应该从数量上来判断?如果从数量上来看,1982年和1990年以及2000年的剩余男性总量均超过2000万,如此庞大的剩余男性人口也经历过。难道超过3000万或者4000万就一定会产生婚姻市场上的乱像吗?当然,也许乱像不会产生,也许会出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确实会形成所谓的婚姻挤压现象。当然,是否存在婚姻挤压的警戒线(或临界值)或者说如何将婚姻挤压分类定级,这值得未来进一步的研究、观察和思考。
[1]Lamanna,M.A.and A.Riedmann.Marriages and Families:Making choices and Facing Change.Fourth Edition[M].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1.
[2]郭志刚,邓国胜.中国婚姻拥挤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3):18-26.
[3]唐美玲.“剩男”与“剩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挤压[J].青年探索,2010(6):5-10.
[4]Avigdor Beiles.A buffered interaction between sex ratio,age difference at marriage,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humans,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sex ratio evolution[J].Hereditary,1994(33S):265.
[5]郭志刚,邓国胜.婚姻市场理论研究——兼论中国生育下降过程中的婚姻市场[J].中国人口科学,1995(3):11-16.
[6]郭志刚,邓国胜.年龄结构波动对婚姻市场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1998(2):1-8.
[7]李树茁,姜全保,费尔德曼.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Hudson,V.and A.M.den Boer.Bare Branches: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4.
[9]Li,S.,Y.Wei,Q.Jiang and M.W.Feldman.“Female Child Survival in China:Past,Present,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J].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PED2CICRED2INED Seminar on Female Deficit in Asia:Trends and Perspectives.Singapore,2005(12):5-7.
[10]郑维东,任强.中国婚姻挤压的现状与未来[J].人口学刊,1997(5):27-35.
[11]Tuljapurkar,S.,N.Li,and M.W.Feldman.High Sex Ratios in China’s Future[M].Science.1995:267,874-876.
[12]陈友华.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Poston,D.L.and K.S.Glover.Too Many Males:Marriage Market Imp lications of Gender Imbalances in China[J].Genus.LXI 2005(2):119-140.
[1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
[15]潘金洪.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7(2):20-25.
[16]姜全保,果臻,李树茁.中国未来婚姻挤压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3):39-47.
[17]刘成斌,风笑天.“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J].人口与发展,2008(2):36-47.
[18]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09(4):3-10.
[19]翟振武,杨凡.夸大还是低估?——基于不同来源数据的出生性别比水平分析[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1(2):2-10.
[20]于学军.论我国婚姻市场“挤压”的人口学因素[J].人口学刊,1993(2):23-28.
[21]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德婚姻市场供需情况的比较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0(5):1-10.
[22]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J].人口研究,2002(3):56-63.
[23]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J].人口学刊,1993(1):86-95.
[24]Schoen R.Modeling Multigroup Populations[M].New York:Plenum Press,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