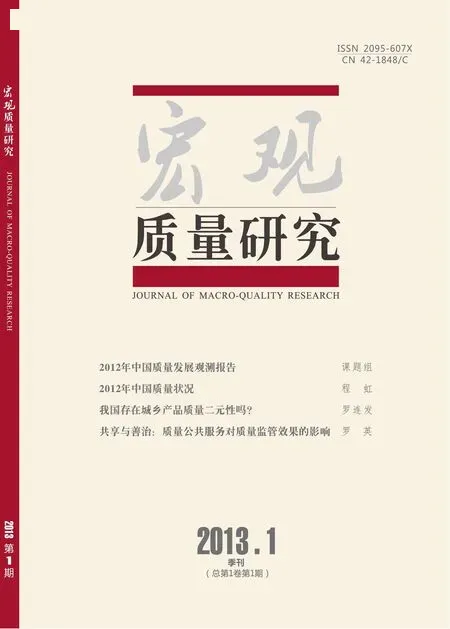中国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消费者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李 酣
一、引 言
在目前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当中,质量安全责任是一种“混合责任”,即这种责任体系的构成和平衡需要政府监管、企业、消费者及其社会组织三方的共同参与(程虹,2010)。这就意味着,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下,生产者要履行市场主体责任,同时,消费者责任、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责任也要发挥作用。
但是,从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各种媒体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消费者对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的履行和效果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关注,而且多是对监管部门的履责效果大加抨击,认为这些机构“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部门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然而,以上也仅仅是一种粗略的感性判断,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撑。消费者到底对监管部门的责任履行是一个怎么样的评价呢?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8个地区进行了基于消费者评价的质量观测,从观测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到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的数据。

图1 中国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认知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图表和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者在对国内和国外质量安全风险产生原因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反差。多数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重要原因,这一比重甚至高于认为企业不诚信是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比重,前者的比例达到了68.12%,而后者为61.49%。也就是说,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重要的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要比认为企业不诚信是重要原因的高出约7个百分点。而对于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虽然也有相当多的消费者认为国外政府监管得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更多的消费者认为企业更诚信是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比重分别是43.27%和51.57%。从理论上说,政府当然不是质量安全问题的制造者,所以不应该是质量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而企业是产品的生产者和市场交易经营的主体,是理所当然的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主要来源;而从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来看,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发生了逆转,或者说消费者对于中国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认识并不符合科学规律,不是理性的。那么,什么原因会影响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选择,导致中国的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评价呢?这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除引言之外,文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文献综述;其次是消费者性质特征与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之间关系的统计描述;第三部分是对影响消费者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有三类。第一类文献从理论上证明了政府监管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类文献不仅为消费者或者居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构建了理论基础和评价体系,还采用不同的样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三类文献分析了消费者属性因素对于消费者评价结果的影响。
在经典经济学中,有关产品质量安全责任的文献并不认为政府监管是解决这一市场运行障碍的可供选择的手段,而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和法律救济回复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Viscusi &Moore,1993)。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学者们认识到,质量安全是一个典型的由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问题,不对称的质量安全信息对各个主体会带来外部性影响,因而质量安全领域需要政府规制。Shavell(1984)最早指出,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控制过程中,企业所面对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政府监管必须保持平衡。然后,Rose-Ackerman(1991)界定了政府规制的适用范围,而Robert Innes(2004)和Sebastien Rouillon(2008)等学者都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规制与法律责任体系如何共同作用,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路径。在国内学者方面,程虹、李丹丹(2009),程虹(2010)从宏观质量管理的角度对质量安全责任体系中政府责任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科学划分,限定了政府监管的范围和履责的方式。而其他国内学者,则强调了政府在农产品或食品安全中实施监管的具体方式,从而给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加强质量安全责任领域中的政府规制(周德翼、杨海娟,2002;徐柏园,2007;张朝华,2009)。
第二类文献研究了政府职能或者政府治理的消费者评价。其中,一些学者分析了对政府职能及其履责的绩效进行公民评价的理论基础和评价的体系。周志忍(2008)对中国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为政府绩效评价的公民参与构建了一个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徐友浩、吴延兵(2004)通过对政府管理部门绩效评估的案例分析,说明了用顾客满意度评估政府绩效的特点和可行性。蔡立辉(2003)总结评议了西方国家政府评估的理念和方法。另外一些学者对政府履责的效率或者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Tony Saich(2006)研究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对政府绩效的总体评价,他的研究表明,这种评价会随着政府级别的降低而下降,另外,他还研究了政府供给特定公共品(如道路建设、医疗保险等)的居民满意度。而Tang &Parrish(2000)则具体研究了公民的文化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的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三类文献研究了影响消费者的评价结果的相关因素,包括消费者主观因素和消费者的内在属性因素。Flynn J.,Slovic P.&Mertz C.K(1994)认为性别和人种可能影响消费者对于风险的判断。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行为和选择偏好可能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职业性质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何小洲等,2007)。Biljana J.&Anthony Worsley(1998)、冯忠泽和李庆江(2008)的实证研究证明,消费者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认知水平与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规模有关。而马骥、秦富(2009)利用对北京市城镇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消费行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消费者的购买经历、消费者的学历、家庭中是否有儿童和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性担心程度等因素对于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评价的影响。
以上这些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政府职能的居民或消费者评价,也检验了消费者属性因素对政府绩效评价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地,具体到政府的质量安全监管职能,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论述了政府监管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还没有从消费者评价的角度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履行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统计描述和计量检验,并运用计量方法探讨影响中国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安全责任履责效果评价的因素。
三、消费者属性与其对质量安全责任的判断——描述性统计
从本文所做的文献分析来看,消费者行为和选择偏好可能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职业性质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何小洲等,2007),从而消费者个人的内在属性,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安全责任承担效果的评价。再有,消费者的家庭结构、家庭收入或者家庭支出等家庭背景因素,也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偏好函数,进而影响消费者对这一问题的选择和评价。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中的调查问卷,通过消费者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基本信息两栏收集了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民族、户口类型、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工作职位、家庭结构、家庭月收入和家庭月支出等有关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消费者属性的信息,对影响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的因素做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首先,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评价是否受地域差异的影响呢?为了分析这一问题,我们按照中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区域划分方法①对于我国区域,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划分方法。我们这里采用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对于中国经济区划的划分方法。这样,本研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

图2 不同样本区域的消费者对中国政府和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认知

图3 不同样本区域消费者对进口产品政府和企业质量安全责任的认知
那么,这三个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认知有什么差异呢?首先,从消费者对政府监管在质量安全风险产生原因中作用的认知来看,各个区域的消费者的评价与全国样本基本一致,即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产生重要原因的选择比例,都超过了50%,同样也高于认为企业不诚信是质量安全风险产生重要因素的比例。但是,在这三个区域,这些比例在数值上还是有所差别。中部地区的消费者更多地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的产生原因,也即在质量安全监管中没有承担好相应责任,这一比重超过了70%;东部地区消费者中持这种认识的,相对中部,也相对西部消费者要少,比例分别是64.01%、76.94%和66.26%。

图4 不同性别消费者对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判断

图5 不同户籍消费者对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判断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消费者所处的地域差异会对消费者对于中国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评价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使这种认识发生根本的转变。与之相对照,消费者多认为正是由于国外的企业更为诚信而且政府监管得力,才使得国外的产品更加安全。同时,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消费者中,选择企业更诚信是进口产品安全原因的比例要显著高于选择政府监管得力是其原因的消费者的比例。但是,面对这一问题,中部地区的消费者选择政府监管得力的比重还是高于选择企业更诚信的比重。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的性别差异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评价和判断。那么,这一因素会不会影响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判断呢?从图4看,将样本数据按照性别分组,男性消费者相对于女性消费者,更少将政府视为质量安全风险的来源,而女性消费者在认为政府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外政府监管得力是进口产品更安全原因的选择比例上,要高于男性。但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消费者,都更多地选择企业更诚信是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大大超过他们选择政府监管得力是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

图6 不同文化程度消费者对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判断
户口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评价。Tony Saich(2006)在他的文章中将研究对象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户口差异会带来居民对于政府绩效评价的差异。同样的,户口因素会不会影响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政府和企业责任的评价呢?从图5的数据来看,拥有城市户口的消费者更多地认为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是企业更诚信,要比农村消费者选择该项的比重高出近8个百分点。但是,这一差异对于消费者认为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是政府监管得力的选择上几乎没有影响,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消费者选择这一项的比例分别是43.35%和43.22%。此外,城市户口的消费者选择质量安全风险因素是政府监管不力和企业不诚信的比例都略为高于农村户口的消费者。
Tang &Parrish(2000)等学者的观察表明,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常常对政府的评价较低。在不同教育水平下,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比例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从图6可以看出,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消费者持这一观点的比重为73.6%,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如高中以下和高中文化水平的消费者选择这种评价的比例分别为67.85%和64.19%。但是,具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做这样选择的比例则是最低的,仅为62.50%。
最后,消费者的支出水平与消费者认为政府应该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选择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在对支出数据取对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那些支出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更为密集地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也即做出这一选择的比例也较高。
以上,我们根据消费者的属性特征,如地域、性别、户口、文化程度和家庭支出,对样本涉及的消费者进行了分类,再看每一个具体的组别中,消费者对于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认知。从上面的这些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来看,分类样本中的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判断与全样本中消费者的评价和判断大致相同。但是,在不同的分组中,组内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对这一问题的判断还是有差异的。
四、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依据反映消费者属性的不同变量对消费者进行分组,在不同组别中,消费者选择政府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比例存在数量上的差异,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属性变量是否显著地影响了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评价。要想判断到底哪些消费者属性变量会对消费者的这一评价产生系统性影响,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计量检验。
由于要分析消费者的内在属性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评价影响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而且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中,消费者对政府责任的评价是二元选择变量(Binary Choice Variable),所以我们选用Probit模型进行计量检验。根据上面的分析,本文所使用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有三种情形:
1.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产生质量安全的风险因素之一;
2.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产生质量安全风险因素且认为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是国外政府监管得力;
3.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产生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但不认为企业不诚信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
上式(1)中,εi为随机扰动项,Xi是影响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判断的可能因素,根据数据集的特点和上一节的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消费者所在的区域、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工作单位性质和家庭支出等变量。
(二)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本文实证分析所需全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变量名称、变量符号和定义。由于实证分析的数据来自抽样问卷调查,在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先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利用SPSS18.0软件对以上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数据的效度通过了KMO和Bartlett检验。Cronbach信度系数α为0.5496,尽管没有达到非常可信的0.8及以上,但仍然在可信范围之内①台湾地区学者吴统雄(1985)认为信度范围小于0.3即为不可信的,0.3以上都是可信的范围,只不过取信的程度由低到高依次排列。。所以,选取的数据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方程1中的被解释变量表示消费者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重要因素的概率,对消费者支出取对数以无量纲化处理②以下的实证分析都采取了对消费者支出用取对数的方法以无量纲化。,对该方程的检验结果见表2。
虽然本文第二部分的描述性统计表明,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政府是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选择比例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但是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区域因素对于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消费者的年龄、户口、婚姻状况、工作单位性质这些消费者的属性特征,对消费者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性别、文化程度和家庭支出水平对消费者的这一判断的影响是正显著的。也就是说,在这些消费者属性因素影响之下,消费者会更多地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的产生因素。通过OLS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最小二乘法)检验该方程,计量结果是稳健的。

表1 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表2 方程1的计量检验结果表

续表2
在表2中,我们用消费者属性变量对消费者进行分组,然后对这些属性因素设置虚拟变量进行回归,以反映组内其它类型的消费者相对于作为参照项的消费者对这一问题进行选择的差异性。回归结果表明,具有本科文化程度的消费者相比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消费者,更有可能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因素,这一结果是显著的,这也证实了前面描述性统计中,本科文化程度的消费者会更多做出这一选择的经验判断。此外,在外资或者合资企业任职的消费者做出这一选择的概率,要显著小于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消费者,因为变量前面的系数为负数。
进一步地,如果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且认为进口产品安全的原因是国外政府监管得力,这不但表明消费者错误判断了质量安全风险的真正来源,而且对政府在质量安全治理中的履责效果的评价更为负面,我们以此作为方程2的被解释变量,表3给出了该方程计量检验的结果。

表3 方程2的计量检验结果表

续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全国样本的回归中,消费者的这些属性因素并不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选择政府监管得力是进口产品更为安全的原因,以及同时做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判断。换言之,这些消费者的这种对于中国政府质量安全责任更为负面的评价不受消费者属性因素的影响。通过用OLS方法检验该方程,计量结果是稳健的。
不过,如果同样用消费者属性变量对该样本中的消费者分组,再进行虚拟变量回归,会发现,36-50岁的消费者相对于更年轻的消费者,做出这样评价的概率要显著低一些。同样,来自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或者合资企业的消费者相对于来自政府机关的消费者,更少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消费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相对更不符合质量安全责任的科学规律。
如果选择政府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已经表明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风险的真正原因没有科学的认识;那么,不选择企业不诚信,而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则说明做出这样选择的消费者,对于这一责任承担问题的看法更为不理性和极端。在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的数据中,有多达452位消费者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么影响这些消费者做出如此极端判断的原因是什么呢?方程3中的被解释变量表示消费者认为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的风险原因,但不认为企业不诚信是质量安全风险的原因,计量回归的结果见表4。

表4 方程3的计量检验结果表

续表4
从上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首先,只有性别因素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的这一判断,而且使得消费者更多地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履行做出这种极端负面的评价。OLS回归的结果表明这一结果是稳健的。其次,用消费者属性变量对该样本中的消费者分组,再进行虚拟变量回归,会看出这一样本中的女性,相对于男性消费者会更多地对中国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履行做出如此评价。另外,来自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消费者,相对于来自政府机关的消费者做出这种选择和判断的概率更高。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理论研究和本文的文献分析表明,政府在质量安全体系中对于企业的监管,是建立均衡的质量安全责任体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同时,质量安全责任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对消费者负责,为消费者提供质量安全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是判断责任体系健全与否以及这一体系的绩效的唯一标准。那么,这种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履行的效果评价应该由消费者来进行。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者对目前监管部门质量安全责任的履行存在较大的非议,甚至很多消费者完全错判了质量安全风险的真实来源及真正的责任主体。此外,从对这一判断可能会产生显著影响的消费者属性的因素来看,不管是性别、文化程度还是家庭的消费支出,这些消费者属性因素的变化都无助于他们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履行做出科学的判断。不过,从按照不同属性将消费者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来看,在各个组别的内部,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判断随着消费者的组内差异的变化会产生显著的变化,某些类别的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认知,相对于本组中的“参照项”有着较为科学和理性的评价。
本文首先对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在全样本中,消费者群体对于中国政府在质量安全风险中的作用,即其监管责任的承担有总体性的负面和非理性的评价。所以,需要从整体上加强对消费者群体质量安全责任的宣传和教育,扭转消费者对政府质量安全责任的不科学认知,以便改善中国质量安全治理的舆论环境,最终促进质量安全风险状况的好转。
同时,本文中按照消费者的属性因素进行分组检验的计量结果,有助于我们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手段应对这种困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计量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会对消费者的这种非科学判断和评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本科学历的消费者,选择政府监管不力是质量安全风险因素的概率高于较低学历者,而研究生学历的消费者是所有这些消费者当中,对这一问题看法最为科学和理性的,所以,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尤其是在本科层次的教育中,加强有关质量安全责任方面的消费者教育。此外,女性消费者相对男性而言,做出这样判断的概率更高,所以更需要针对女性消费者群体进行质量安全责任的科学教育。再次,在合资、外资和私营企业中从业的消费者对中国政府在质量安全责任体系中履责问题的看法相对符合质量安全风险的科学规律,而政府单位和事业单位的消费者对政府监管责任的看法更为不理性,也需要对这类消费者加强质量安全责任的宣传。
虽然,通过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消费者的一些属性因素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质量安全风险原因的认识和判断,从而混淆了政府和企业在质量安全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但是,本文并没有分析这些消费者的属性因素是通过哪些可能的路径影响其做出这一判断的,这将是作者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1]蔡立辉,2003:《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2]程虹,2010:《宏观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研究——一种基于质量安全的分析视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3]程虹、李丹丹,2009:《我国宏观质量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中国软科学》第12期。
[4]冯忠泽、李庆江,2008:《消费者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7省9市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5]何小洲、刘姝、杨秀苔、Edy Wong,2007:《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来自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调查》,《中国软科学》第1期。
[6]马骥、秦富,2009:《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认知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城镇消费者有机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7]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质量观测课题组,2013:《2012年中国质量发展观测报告》,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
[8]吴统雄,1985:《态度与行为研究的信度与效度:理论、应用、反省》,《民意学术专刊》第2期。
[9]徐柏园,2007:《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问题分析》,《宏观经济研究》第3期。
[10]张朝华,2009:《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下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重构——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
[11]周德翼、杨海娟,2002:《食物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监管机制》,《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12]Tony Saich,2006:《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民意调查》,《公共管理评论》第12期。
[13]Biljana,Juric,Anthony,Worsley,1998,“Consumers’Attitudes towards Imported Food Products”,Food QualityandPreference,Vol.9,Nov.,pp.431-441.
[14]Chen,Jie,2004,PopularPoliticalSupportinUrbanChina,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5]Flynn,J.,Slovic,P.,Mertz,C.K.,1994,“Gender,Race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RiskAnalysis,Vol.14,May.,pp.1101-1107.
[16]Innes,Robert,2004,“Enforcement Costs,Optimal Sanctions,and the Choice between Ex-post Liability and Ex-ante Regulation”,InternationalReviewofLawandEconomics,Vol.24,Mar.,pp.29-48.
[17]Li,Lianjiang,2004,“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China,Vol.30,Apr.,pp.228-258.
[18]Rose,Ackerman,Susan,1991,“Regulation and the Law of Tort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Papers andProceedings,Vol.81,May.,pp.54-58.
[19]Rouillon,Sebastien,2008,“Safety Regulation vs.Liability with Heterogeneous Probabilities of Suit”,InternationalReviewofLawandEconomics,Vol.28,Jun.,pp.133-139.
[20]Shavell,Steven,1984,“A Model of the Optimal Use of Liability and Safety Regulation”,RandJournalof Economics,Vol.15,pp.271-280.
[21]Tang,Wenfeng,Parrish,W.,2000,ChineseUrbanLifeunderReform:TheChangingSocialContra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Viscusi,W.Kip,Michael,J.Moore.,1993, “Product Liabilit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Innov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1,Feb.,pp.16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