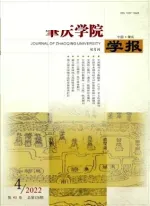广东出土两晋南朝墓砖铭文考察
马启亮
(佛山市南海区文体旅游局,广东 佛山 528200)
一
在墓砖上模印或刻写文字,是古代流行的丧葬风俗。这种墓砖一般称为“铭文砖”,通常为长方形,部分为楔形及刀形,文字一般见于砖的侧面,也有少数在端面或正面。字体主要是隶书和楷书,工整程度不一。铭文多帶有纪年,故又通称“纪年砖”。铭文砖流行于东汉至唐的中国南方地区砖室墓中,尤以两晋南朝时最为盛行。
广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南朝砖室墓数量众多,以广州、韶关、曲江、始兴、深圳、肇庆、德庆、梅县、揭阳、博罗、阳江等地较为集中,多属当时的交通要冲或州郡县治所在。据笔者统计,这些墓葬中近四分之一见有铭文砖,从形制简单的小型长方形单室墓到结构复杂的大型多室墓中都有所发现。从纪年来看,以东晋墓最多,西晋及南朝前期(宋、齐)墓次之,未见南朝后期(梁、陈)纪年。砖铭内容对研究两晋南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风俗等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纪年文字更是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
二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材料,以下对广东出土的两晋南朝墓砖铭文内容进行归类分析。
(一)纪年类
此类铭文数量最多,一般以阳文形式模印烧制而成。从文句结构上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纪年部分。一般置于句首,完整的纪年包括年号和年份。但也有省略年份的,如德庆马墟M7的“大明年造”[1]、乳源泽桥山ⅢM11的“元嘉年八月十日”[2]84。所见年号有:西晋的太熙(290)、永嘉(307—312)、建兴(313—316);东晋的大(太)兴(318—321)、泰(太)宁(323—325)、咸和(326—334)、咸康(335—342)、建元(343—344)、永和(345—356)、泰(太)和(366—371)、泰(太)元(376—396);南朝宋的永初(420—422)、景平(423—424)、元嘉(424—453)、大明(457—464)、义嘉(466);南朝齐的建元(479—482)、永明(483—493)、建武(494—498)、永元(499—501)。
这些纪年铭文中,“太”字无一例外的都以“泰”字替代,如韶关65韶西黄M1的“泰元二年宜日”[3]、始兴赤西M12的“泰和六年囗月十九日作囗”[4]、肇庆坪石岗晋墓的“泰宁三年正月十五日立”“泰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五月壬申立大吉昌”[5]等。另外,“大”均被“太”替代,如韶关小茶山M13的“太兴二年七月十四立作”[6]。这些都是同音或形近的借字,在出土文献中较常见。“泰”字含吉祥之寓意,故除了造砖者的随意性外,“泰”替代“太”更可能是反映死者家属的祝愿。上述借字情况亦屡见于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地区,如“太康”、“太宁”、“太和”、“太元”均写作“泰康”、“泰宁”、“泰和”、“泰元”[7],应是两晋时铭文砖制作中的普遍做法。
曲江曲河M1的“建元一年七月十日”[8]、英德含洭EH-M6的“齐永元一年大岁己卯”[9]则反映了另一个独特现象:以“一年”替代“元年”的写法。日本学者谷丰信则提出了另一种说法:“一”仅表示重复前面的“元”字,作为重复符号[7]。查看原报告墓砖拓片,“一”较短而不自然,更像是符号,而非独立成字。故笔者认为此说较可信。
第二,干支部分。很多铭文砖在年份后带有该年的干支,通常表达为:“(纪年)太岁在(干支)”、“(纪年)岁在(干支)”、“(纪年)(干支)”、“(纪年)(干支)岁”这几种格式,如肇庆坪石岗东晋墓“泰宁三年太岁在乙酉”[5]、广州桂花岗M5“永嘉五年岁在辛未”[10]、广州孖岗晋墓“永嘉六年壬申”[11]、新兴南朝墓“元嘉十二年乙亥岁”[12]等。另有加在日期之后的干支,如57西皇M31“永嘉三年四月廿日戊子”[13]、新兴南朝墓“八月八日壬辰作之”[12]。日期干支在广东两晋南朝墓发现较少。
第三,日期部分,即“×月×日”或“×月”。铭文中出现的月份频率如下表所示:

images/BZ_53_192_1692_1042_1817.png
显然,这些月份多为农历七月和八月,即秋季。反映了造砖时间和建墓时间集中在秋季的七到八月。
(二)记事类
记事性质的铭文不外乎两类:造砖与立墓。一般与纪年文字一并出现,构成完整语句,以表示造砖或立墓的时间。
造砖记事的文字,如广州桂花岗M4“逋蓝海造”、M5“永嘉五年陈仰所造”[10];广州孖岗晋墓“永嘉五年陈仰所造”、“永嘉六年壬申陈仲恕制作砖”[11];57西皇M31“永嘉三年四月廿日戊子于赤岸造”[13];广州黄埔姬堂M2“永嘉元年正月十五日张秀士家作砖”[14]等等。这些记录造砖一事的铭文,蕴含着造砖时间、造砖者、造砖地点等信息。尤其是造砖者方面,可以注意到以下这几个人:广州桂花岗M5的“陈计”、“陈仁”、“陈仰”(陈仰也见于广州孖岗晋墓中)等,加上孖岗晋墓中同时出土的“永嘉六年壬申陈仲恕制作砖”,似可表明,在西晋末,该陈氏家族是广州地区造砖行业的代表之一。
立墓记事的文字,如曲江曲河M1“咸康八年七月十八日孝子李立”、“咸康八年七月廿日孝子邓立作”[8];65韶西黄M2“覃氏立”[3];广州狮子岗晋墓“建兴四年七月立作”[15];始兴农虎 M1“李氏立”、M5“伍天立”[16];韶关刘宋墓“宋元嘉十七年庚辰立砖吕氏记”[17];肇庆坪石岗东晋墓“泰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五月壬申立大吉昌”[5]等等,均带有“立”字,蕴含墓葬建成时间、立墓人姓名等信息。比较特别的是65韶西狗(未编号)的“咸康八年八月作寝”[3]和德庆东晋墓的“惟晋咸和六年太岁在辛卯孟秋八月上昭吉日甲申立此坟墓良会在参富贵宜子孙谨琢甓以记之”[18]。
另有一些铭文仅有“作”、“造”字样,难以断定是表明造砖还是建墓事件的,如广州72北牌M002“大兴二年七月三日造之”[19];曲江南华寺M15“景平元年作”[20];韶关S.S.G.-10“建元一年七月十日作此”[21]等等。
(三)吉祥语类
此类铭文也很常见,有单独成句的,也有与纪年文字组句的。其中最常见的有:
1.“宜侯王”。见于广州桂花岗M4[10]、65韶西黄M5[3]、肇庆坪石岗东晋墓[5]等。
2.“宜子保孙”、“子孙千亿皆寿万年”。皆见于广州桂花岗M5[10]及广州孖岗晋墓[11]中。孖岗晋墓中另见“皆寿百年”、“富且寿考”,都与祝福子荫有关。
3.“大吉”。如肇庆坪石岗东晋墓“大吉昌”[5]、韶关刘宋墓“大吉”[17]、乳源泽桥山ⅠM1的“大吉羊道”[2]87。
另外,“康”、“千年万岁”、“王土田亩”、“太安乐宜”、“六合”等吉祥语也有零星发现。比较特别的是孖岗晋墓中的“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其中的“皆宜价市”是目前所见唯一与商业有关的砖铭。
(四)人名类
除了上述记事类铭文中出现的造砖者或立墓人名外,尚有单独出现且含义不甚明确的人名,如曲江曲河M2的“朱武子”[8]、广州狮子岗晋墓的“孔子”[15]、曲江南华寺M1的“周氏”[20]、始兴晋墓中散见的“李、齐、黄、明、平、吉、光、田、徐”诸姓氏[4];广州72北牌 M002 的“周世”“周夏师”[19];广州先烈南路M3的“田、白”姓氏[22]等。其中始兴晋墓、先烈南路M3中不止一个姓氏出现于一座墓葬中,这些姓氏应是代表造砖者的。其余的尚难断定是造砖者、孝子或是墓主人的名讳。
(五)墓志砖
见诸报道的广东两晋南朝墓葬中尚未见有墓志,但发现了初具墓志性质的墓志砖。广州下塘狮带岗M6东晋墓的“甄寿亡亲、解夫人墓”砖[23];肇庆坪石岗东晋墓的“高囗囗囗广州苍梧广信侯也”[5]也带有墓志砖性质。两例墓志砖铭文皆阴刻,与常见的墓志相似。
(六)反映社会现象
仅见于广州。广州孖岗晋墓“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广州南郊敦和乡晋墓“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等[11],反映了西晋末年北方战乱动荡,南方特别是广州安稳和平的局面,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七)其他
如广州狮子岗晋墓的“作此与众异”、“右”[15];曲江南华寺M14的“六舆”、M16的“太壬”[20];65韶西狗M4的“五田五”[3];广州黄埔姬堂M2的“九百”[14];始兴始赤电M1的“主人”、M2的“名时”[24];始兴缫丝厂M4“悼土兴子”[25]等等。狮子岗晋墓中的“右”字铭文砖仅一块,与南京地区的“中、下、左、右”等铭文一样,表示此砖的特定位置,“作此与众异”亦仅见一块,置于左棺室后壁,形状比一般墓砖大,与南京地区的“正方”、“中斧”等铭文相似,表示该墓砖形制的特殊性[26]。这种表明特定位置和形制的铭文砖都出现于大型墓中,同一般中小型墓葬相比,其墓室的营建,从设计到施工过程中,对墓砖的选用、烧制、排列、堆砌等都有严格的要求。狮子岗晋墓是前后室带甬道的砖券墓,总长9.6米,为广东规模较大的六朝墓葬,这一点上与南京地区无异。
三
广东出土的两晋南朝砖室墓铭文砖,集中见于广州地区、以韶关为中心的粤北地区和以肇庆为中心的西江地区。粤东地区仅揭阳一地有铭文砖出土,粤西南地区未发现铭文砖。广州地区、粤北地区、西江地区三地砖铭各有其区域特征,略述如下。
广州地区:最具地域特征的铭文当属“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西晋末年的铭文,仅见于广州。其次,能窥知具体造砖者的铭文,也只见于广州地区,计有“逋蓝海”、“陈仰”、“陈计”、“陈仁”、“陈仲恕”、“张秀士”。再次,吉祥语中,“宜子保孙”、“子孙千亿皆寿万年”等祝福子荫的铭文,只见于广州。另外,孖岗晋墓的“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反映商业的铭文,亦只见于广州。
粤北地区:前述曲江和英德墓葬中的“建元一年”、“永元一年”的特殊纪年方式,为粤北地区所独见,亦未见于省外同时期的墓葬。立墓类记事铭文,绝大部分发现于粤北,如“咸康八年七月十八日孝子李立”、“李氏立”、“永嘉六年六月立”一类;且能窥知立墓人姓名的铭文,全都出现于此区。单独姓氏的铭文砖,此区发现较多,广州、肇庆等地罕见。另外,乳源泽桥山的吉祥类铭文全是“大吉羊道”,不见于其他地区。
西江地区:德庆东晋墓的“惟晋咸和六年太岁在辛卯孟秋八月上昭吉日甲申立此坟墓良会在参富贵宜子孙谨琢甓以记之”及肇庆坪石岗东晋墓“泰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五月壬申立大吉昌”两处铭文砖,纪年、日期、干支、立墓、吉祥语等俱备,内容详尽,为本区所独见。
三国吴永安七年(264)“分交州置广州”[27]1162后,番禺(今广州)一直作为广州州治及南海郡治。吴甘露元年(265),以“桂阳南部为始兴郡”[27]1164,直到隋灭陈后并入南海郡,始兴郡在整个六朝时期一直存在。除了梁、陈两代曾分设阳山、清远等郡外,始兴郡在吴末至南朝齐的辖境,均包括粤北铭文砖分布的韶关、曲江、乳源、始兴、阳山、英德、连州等地。并且,始兴郡长期不隶属于广州,“晋武帝平吴,以属广州;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广州;三十年,复度湘州”[28]1133,南朝齐均属湘州。可见,铭文砖出土地的广州地区与粤北地区,六朝时期分属不同的州,文化面貌有所差异,从铭文砖内容上可窥见一二。
至于铭文砖出土地的德庆、肇庆、新兴等地区,吴及西晋同属苍梧郡;东晋时德庆地区设晋康郡,新兴地区设新宁郡,肇庆地区除南朝宋、齐时曾属南海郡外,吴、晋时属苍梧郡,梁、陈属高要郡。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三地的文化面貌相似,与今广州所在的南海郡中心地区有所差异,因此,结合铭文砖的内容,西江流域的德庆、肇庆、新兴等地应自成一区。
四
铭文砖上的纪年往往是墓葬断代的重要依据。但是,如前所述,纪年铭文往往与造砖或立墓记事同时出现,因此便存在造砖时间与立墓时间的区别。造砖时间应较立墓时间为早,立墓时间则为墓葬的准确年代。而在实际情况中,因缺乏明确的立墓纪年,并且存在挪用早期墓砖、年份滞后等情况,所以采用纪年砖断代时必须慎重,最终要结合墓葬形制及典型随葬品的演变来确定墓葬年代。
曲江曲河M1出土三种纪年砖:“咸康八年七月十八日孝子李立”、“咸康八年七月廿日孝子邓立作”及“建元一年七月十日”[8]。咸康八年是342年,建元元年是343年,后者虽不能确定是立墓时间还是造砖时间,但前者为立墓时间无疑,却时间在前。韶关65韶五劳M1出有“永嘉四年七月一日立”和“咸康三年”纪年砖[3],前者是310年,后者是337年,立墓纪年明显偏早。这些应是混用了早年墓砖的现象。
广州黄埔姬堂M3西晋墓,出土“熹平四年”纪年砖。熹平四年是175年,其发掘简报称:“M3墓砖除西耳室皆采用晋砖外,其余各处均用东汉旧墓砖砌就。”除了“熹平四年”外,“君宜官秩”、“用官大吉”、“大吉囗囗”等铭文砖也是东汉砖[14]。这是晚期墓葬采用早年墓砖砌墓的典型例子。
此外,有些纪年的年份带有滞后性。广州孖岗晋墓同时出有“永嘉六年”和“永嘉七年”的纪年砖[11]。永嘉为晋怀帝年号,只使用六年(307—312),而313年则应是晋愍帝建兴元年。《晋书·怀帝本纪》载“(永嘉)七年春正月……丁未,帝遇弑”,同卷《愍帝本纪》载“建兴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怀帝崩问,举哀成礼。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29],可知永嘉年号用至313年正月,至四月改年建兴。该墓出土很多带“永嘉七年”的墓砖,除可能是313年一月至三月,即建兴改元前立墓的,更可能是由于广州地处偏远,虽已过了四月,但仍不知中央政府已改元。
还有使用了特殊年号的现象。德庆马墟M7出土两种纪年砖:“大明年造”及“义嘉元年吉日”[1]。“大明”是宋孝武帝年号,自457年至464年。而“义嘉”则比较特殊,它是南朝宋刘子勋的地方政权年号。刘子勋为宋孝武帝之子,封晋安王、江州刺史,驻寻阳(今江西九江)。《宋书·明帝本纪》载:“泰始元年(465)冬十二月……镇东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二年)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平定之,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同党皆诛服”[28]155-158。《宋书·刘子勋传》载:“泰始二年(466)正月七日,奉子勋为帝,即伪位于寻阳城,年号义嘉元年”[28]2060。由此可知,“义嘉”年号只使用了一年,即466年。《宋书·明帝本纪》又载:“(泰始)二年春正月……令孙、孟虯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曇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叛逆”[28]156。可知广州也曾归顺了刘子勋政权。当时德庆为晋康郡,属广州,故也受刘子勋政权的统治。德庆马墟M7这件“义嘉元年吉日”铭文砖,表明该墓立于466年,其铭文印证了刘子勋政权范围曾达至广东地区的史实。
以上对广东出土两晋南朝铭文砖内容进行了归类分析,并总结其区域特征及纪年铭文与墓葬年代的问题。至于铭文砖的烧造工艺,年代特征,以及与墓葬形制、等级的关系等问题,则要在对墓葬进行更深入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地展开讨论。本文仅对铭文砖内容本身,进行初步的考察、分析。
[1] 古运泉.德庆县马墟公社古墓葬发掘简报[J].广东文博,1985(1):39-41.
[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乳源泽桥山六朝隋唐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3] 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集刊(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0-196.
[4]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3-133.
[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肇庆市博物馆.广东肇庆市坪石岗东晋墓[M]//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深圳博物馆.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48-264.
[6]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韶关市曲江区马坝人遗址博物馆.广东韶关市小茶山墓葬群发掘简报[J].南方文物,2008(2):49-53.
[7] 谷丰信.中国唐以前纪年砖铭文之考察[J].东方博物,2004(4):44-52.
[8]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曲江东晋、南朝墓简报[J].考古,1959(9):469-471.
[9]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J].考古,1961(3):139-141.
[10]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西北郊晋墓清理简报[J].考古通讯,1955(5):43-49.
[11] 麦英豪,黎金.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J].文物参考资料,1955(3):24-34.
[12] 古运泉.广东新兴县南朝墓[J].文物,1990(2):53-57.
[13] 区泽.广州西郊发现晋墓[J].考古通讯,1957(6):43-44.
[14]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晋代考古的重要发现——黄埔姬堂晋墓[M]//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文物考古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316-319.
[1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沙河镇狮子岗晋墓[J].考古,1961(5):245-247.
[16] 始兴县博物馆.广东始兴县老虎岭古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0(12):1080-1086.
[17] 毛茅.韶关发现南朝刘宋纪年铭文砖[J].文物,1998(9):91.
[18] 尚杰.德庆县东晋墓葬清理简报[J].广东文博,1986(1-2):37-39.
[19]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晋墓清理简报[G]//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60-64.
[20]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曲江南华寺古墓发掘简报[J].考古,1983(7):601-608.
[2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J].考古,1961(8):435-441.
[22]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先烈南路汉晋南朝墓葬[M]//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9-71.
[2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下塘狮带岗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6(1):36-45.
[24] 始兴县博物馆.广东始兴县晋、南朝、唐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0(2):116-122.
[25] 廖晋雄.广东始兴县缫丝厂东晋南朝墓的发掘[J].考古,1996(6):30-36.
[26] 华国荣.六朝墓文字砖的归类分析[J].南方文物,1997(4):70-77.
[27]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9]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