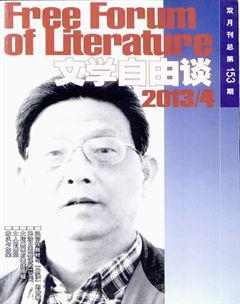文人的名利观
毛志成
对名利的认识和理解,称之为名利观。世界上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几乎都有对名利的追求。从小孩子到老人,从贱民到贵人,从文盲到学士,从匪寇到君子,都有对名利的不同认识和表现。为什么要格外去说文人的名利观?只是因为文人是社会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他们对名利的解读往往比芸芸众生有高明之处(不论真假)。
总之,专门谈论中国文人的名利观不仅值得,也很有必要。
古今中国的文人,尤其是古代,很多时候是没有“名利”这个词的,最乐于使用的是“功名”一词。参加科举考试,雅称就叫作“博取功名”。这里边一个是“功”,一个是“名”,很少去谈(甚而避谈、羞谈)“利”。一辈子混得甚好,叫作“功成名就”,而不称之为“名利双收”。看来中国文人比外国人很有精神品位,也雅得多,标志之一就是只看重“功”、“名”而很少去谈甚而不谈“利”。更何况有孔圣人的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更显得中国文人的不凡。
到了后来,连“名”也羞于去谈了,只讲求成功不讲求成名。到了再后来的革命年代,也包括将革命异化为极左的年代,文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行为都立足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党”,“一切为政治服务”。一涉及名利,就与“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甚而“不革命”、“反革命”沾了边。
不过中国文人对“功名”的认识、理解、体现,其最大的愚昧和虚伪之处,又恰恰在于两点:一,为功而功,为名而名,有时全然不理会那样的事有无实际价值。有的人为了争某些“功”和某些“名”,苦了一辈子甚而殉身,无非只是为了得到某种并无实际意义的虚夸而已。对此我们只能叹息一声:“愚哉!”二,在贪功、沽名的背后,其实对“利”又看得格外重。古代科举中以忠君、治世、述政、献策为大题目的文章,大多数人的本意也无非是对升官发财的追求而已。
即使新中国建立后,一时间作家、诗人也曾成为许多人的追星者、争取者(很像今天争当歌星、影星、笑星的人如蜂似蚁),原因之一也在于那时国民的经济来源除了工人有限的固定工资和农民可怜的固定工分之外,惟一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说来说去,利也。
“文革”时期取消了稿费,一心想当“红文人”的人也不乏,有的还成了火爆的名人,为什么?政治利益所致也。
必须承认,将主要的心趣投入文化本身而对名利淡然处之的人也是有的,古今中外都不乏。中国古代从屈原、司马迁直至曹雪芹,以及后来代表“民族魂”的鲁迅,另如俄国十九世纪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一群虽然身为贵族但一生以写作为主业的作家,他们对“利”大都无兴趣。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对上述的人我们无须刻意学样,因为他们付出的人生成本太超量了,而且有时与各种磨难形影不离。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有名而无利甚而还要久久陷在磨难中,只能说明社会不正常,有病态。
但是话说回来,文人将出名视为第一位的事,而出名又只是为了谋利(包括物质利益或地位利益),也是社会的一种不正常,最终也会导致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本身的不正常。也就是说,为名利而发烧、发疯的文人写出的作品(包括讲演稿)也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无论是德育功能还是智育功能,也无论是感性体验的生动性还是理性认识的深刻性,都很难挣脱俗陋或虚浮。
作家自称百分之百地为国为民而写作,或是要求作家这样做,丝毫不计名利,这都是不可信的,也是虚伪的。相比之下,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和提高名利观的品位更有益些。作家的出名,作品的出名,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能量;写出的书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稿费也拿得多些,这也是一种价值显示,理应被社会予以特殊尊重。但是相反的现象也是有的,如有的作家(特别是拥有某种特殊头衔的作家)很有名但作品却不出名,甚而不知道他写过什么,或是他的书出版之后(尤其是被吹捧过甚)但被人一读才觉得只是哗众而已,无论是见识还是文采都实在稀松。有的将浮奢当深刻,有的将俗鄙当生动,都近于无聊。
在这里,我倒想起了一个名词、一个称谓:匠。什么是匠?俗称手艺人(不同于特殊的誉称“巨匠”),即专门从事某种手艺且又喜欢并精通该手艺的人。这种人的特点是:一,首先是平民,不是上层人物;二,又不同于各式各样的外行、混子,对本业之所以内行,首先在于他苦练过基本功并且达了标,由一般的初学乍练者升成了“把式”、“师傅”;三,在一业中总得有点名气,否则无人认可;四,他的基本目的只是为了谋生,即为了利。
具体到文学来说,我们最缺乏的不是“家”而是匠,即文匠(也称文字匠)。什么是文匠?就是通晓并善于运用文字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包括能教、能写、能编、能审、能印发等等)。这样的文匠,不仅文字的基本功扎实,而且在同业中或其它行业中一看便承认其确有文字技艺,是内行或内行中的不平庸者,有一定名望。这样的文匠并不一定崇高,也有实实在在的利益需求。这样的名利观就是正确的,至少是正常的。远比连匠的级别都未达到而疯狂地追求当“家”、当“名家”要可敬得多。当然,果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名家”、“大家”也很好,甚而更好。但无论是匠还是“家”,都应当从名与实、利与义相统一入手。
说来说去,文人名利观的正确和优质化是十分重要的。
文人之所以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从事的专业主要从属于精神专业,以影响社会、影响他人为基本活动,因此名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影响力,一种促动力,一种宣传力。无论是作家、诗人、理论家,还是教育界的各级教师,在一业或一校中默默无名,只像一个空洞符号而无生动具体的形象,只能说明他不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但“名”是个大概念,涵义很广,包括名字、名号、名气、名声、名望。仅仅名字四传但谁也不知他有什么具体行为,仅仅名号吓人(如级别高)但谁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高于常人的德智,仅仅名气很大但谁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真正的可爱、可贵、可敬之处,仅仅名声很响但未必享有美名甚而不乏恶名,这样的有名不如无名。
真正具有正能量的出名叫名望,即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至少在同业中)感受到此人可爱,此人可贵,此人可敬,这才是实现了名的优质化。
当名人并不难,难的是当名士。比成为名士更难的是成为名流,因为真正的名流首先是清流,是真君子和真才子的共同组合。
文人的名利观是否能真正实现优质化,根本的一条是与“利”有关的心思和行为如何。谈到这个问题,不必讲些漂亮的虚言,至少做到一点就可以了:从事文业之前、之中,只是专心去做,一切灵感、冲动、激情都基于文业本身,不理会利。而获利、发财,只能是事后的事。获了利、发了财之后,高兴一阵子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但切切不要发烧,不要成了“烧包”,应当“放下”,继续使文心、文绩的品位更上一层楼。为什么要这样做?只因为文人是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