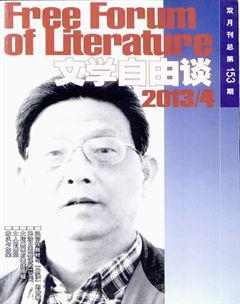多年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堆废纸
唐小林
在贾平凹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的今天,一个叫孙见喜的人也开始如日中天,日益红火起来。这位自称为“当世为贾平凹立传第一人”的贾平凹的商州乡党,数十年来,用一种锲而不舍,见缝插针的钉子精神,先后撰写出了《贾平凹之谜》、《鬼才贾平凹》、《贾平凹的道路》、《中国文坛大地震》、《贾平凹前传》、《危崖上的贾平凹》、《废都里的贾平凹》等多部有关贾平凹的传记文学作品。孙见喜在其《危崖上的贾平凹》一书的后记中说:“我跟踪贾平凹的创作几十年,累是不必言的。”有记者问孙见喜:“您从三十八岁写到五十四岁,您用一生中最有创造活力的一段生命来为一个成长中的作家作传,你认为值得吗?而且据我所知你是搁下手头的长篇小说来优先写这本书的,倘以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您可以出手两部长篇小说吧?”(笔者按:此采访中的人称代词忽而用“您”,忽而用“你”,极其混乱。)孙见喜回答说:“恐怕还不至(止)两部吧。我用一生中的黄金时段来写贾平凹这样的作家,我不后悔。把自家的馍放到后边蒸是想多攒些柴薪。”记者又问:“1984年,贾平凹才三十二岁,您当时就着手写他不觉得有些冒险吗?是什么吸引您用了青壮年的大半时间来研究这个作家?”孙见喜回答说:“一是出于感情,我和平凹同喝丹江水长大,他父亲教过我初中语文;二是他的文笔最对我的口味;三是他笔下的商州生活、文化风习我最熟悉,他将生活变为作品的过程研究起来对我的创作有借鉴价值;四是这个贾平凹有文学天才,将来能成大器。”为此,孙见喜不无自豪地说:“我从1975年开始读贾平凹,1981年开始追踪他的创作足迹。目前全国各出版社出的研究贾平凹的各类专著有二十多部,这些专家几乎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匠,我没有学力和他们对话。但他们几乎都参考过我写的《贾平凹之谜》和《鬼才贾平凹》,我的书是他们的素材源之一。”然而,这些学者和广大读者却没有想到,他们居然被孙见喜这些换汤不换药的“纪实文学”忽悠了。
最近,孙见喜撰写的贾平凹“纪实文学”的亲历者健涛先生,以《如此“不实”的贾平凹“纪实文学”》为题,在《文学报·新批评》发表文章,对孙见喜所谓的“纪实文学”进行了批评。健涛指出,关于贾平凹在镇安县的采风总共写了将近九千字,其中前边六千多字写了贾平凹与何丹萌独自去了深山野岭,时间长达五天四夜。“瘦小娘子”唱山歌、逛“鬼洞”和“玉皇炉”,黑夜里迷了路宿在一座残败凄凉的破庙,发现墙上有“抗日必胜”标语和“五百三十八年”前题于“景泰三年”字样的壁画等等耸人听闻的造假描写“完全都是子虚乌有!”但据笔者所知,此段描写并非始自健涛先生所说的《贾平凹前传》第一卷第十四章的《商州逛山》,而是最早出现在孙见喜对贾平凹进行神话的滥觞之作《贾平凹之谜》。该书出版于1991年2月,同年8月第二次印刷。也就是说,这是孙见喜在贾平凹传记中大量想当然地杜撰,对读者进行忽悠的初战告捷,同时也是孙在传记中制假造假的甜蜜幸福之旅。孙见喜在搭乘贾平凹的顺风车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而十年之后孙见喜大炒冷饭,捣鼓出版的三卷本《贾平凹前传》,可以说是孙见喜大肆神话贾平凹的登峰造极之作。健涛在文中引述的《贾平凹前传》中的《商州逛山》,恰恰就是孙见喜摘抄自其旧作《贾平凹之谜》中的第十三章《走商州》。
健涛在文中爆料说,早在二十多年前,贾平凹前妻韩俊芳就对“我”讲过,见喜一进门她就赶紧把平凹书房门锁上,得像防“贼”一样防着他,不然他进去了看见啥都往本本上记。贾平凹也曾对“我”讲过,孙见喜“看见啥就往本本上抄,凭着只言片语就弄出一大堆来。我啥话都不敢给他说,他啥也不知道,写出来出了问题还要我负责。我弄得里外都不是人,被动得很”。健涛先生说:“我不敢说孙见喜和何丹萌关于贾平凹纪实文学中的全部情节都是这么写的,但是从其文字叙述的形式与格调,已经显露出他们是在用写小说的手法写纪实的东西,虚构和想象超出了必要的底线。”在我看来,孙见喜倾其一生的黄金年华,无怨无悔地为贾平凹树碑立传,并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其贾平凹研究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在孙见喜看来“平凹是块碑,碑文篆隶真草,苍劲隽永,却是块悟不尽的无字碑。常人读平凹著作,容易走样,而寡淡,而偏拗,这只是误会。知音觅贾氏,能见真的高山流水,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千古风流的脉动;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意蕴;有‘花开半看,饮酒微醺的幽玄……读深了,平凹就成为刻于心灵的兵马俑;夜冥里,会梦入古拙的《静虚村》,远远鲸汲一口油泼辣子的火香,品它饱含的一个淡泊人轰轰烈烈的情与爱”。在我看来,孙见喜的贾平凹研究,一开始就误入歧途,陷入了捕风捉影的怪圈。为了吊足读者的胃口,孙见喜甚至不惜采用地摊文学的招数,大量暴露贾平凹的隐私,挑逗和撩拨读者的“性趣”。在其早期的《贾平凹之谜》中,孙见喜竟然如此写道:“平凹欲伸手动她(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却又不敢,自己把自己的双手藏到身后,腰却不由躬了下来;他低下头来,和她脸对了脸;他悄悄地用她的五官来丈量自己的五官,眼对眼、鼻对鼻、口对口……不由得,他长长地伸出了舌头。可是,该他舔的地方没有瞄准,她就从梦呓中苏醒了,第一句话是:‘闻你那气,快去漱口!”想想看,作为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看到孙见喜这样的文字将会是怎样一种尴尬?作为韩俊芳的丈夫,贾平凹怎么能够将夫妻之间的隐私轻易就告诉孙见喜,让其昭告于天下?因此,我以为,孙见喜这样的做法,至少对韩俊芳和贾平凹缺乏的是最起码的尊重。在《危崖上的贾平凹》一书中,孙见喜又以贾平凹的好友和研究权威自居,大爆贾平凹与其前妻韩俊芳离婚的内幕,称贾平凹的前妻怀疑其“与人有染”,并借用友人的训示告诫贾平凹不该过早地暴露和夏女士的关系,这样离婚便有喜新厌旧之嫌,有损先生道德形象。表面上看来,孙见喜是在维护贾平凹的道德形象,但事实上却是在帮倒忙,极大地损害了贾平凹的形象。试想,孙见喜犹如“狗仔队”手法,用专门捕捉明星“桃色新闻”的八卦来做卖点,写出的贾平凹传记,怎么会得到贾平凹本人发自内心的认同?为此,孙见喜的所谓贾平凹“纪实文学”早已经将贾平凹搞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孙见喜始终是抱住贾平凹这棵大树死死不放。在今年初,孙见喜又大炒冷饭,弄出了一本贾平凹研究的“新”专著《废都里的贾平凹》。孙见喜不管贾平凹愿意不愿意,这辈子都是要吃定贾平凹了!对于孙见喜这样的做法,有评论家甚至怀疑,孙见喜只不过是为了多弄稿费,其对贾平凹的“研究”,根本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孙见喜的贾平凹研究至少陷入了以下误区:
一、盲目的个人崇拜。可以说,孙见喜在撰写贾平凹传记时,从来都是跪在地下,五体投地,以仰视的目光来神话贾平凹的。在孙见喜的眼里,贾平凹简直就是神。正因如此,孙见喜的《贾平凹前传》才不惜以“鬼才出世”、“制造地震”、“神游人间”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神仙界”的书名来将贾平凹推向神坛。在《贾平凹前传·制造地震》一书中,孙见喜直接将对贾平凹的个人崇拜推向了世界最高峰。孙见喜写道:“1989年,小马到长庆油田谋生。在一座高山的职工食堂当炊事员,工作之余,少不了谈论贾平凹的小说。这期间,他如醉如痴,几乎买全了贾平凹的所有小说。有一部介绍贾平凹创作道路的书,小马说:‘我一连看了十遍,看后大为感动,发誓此书不外借,要存千古作祖业。他说:‘恰好一位姑娘登上门来办事,死活要看这本书,急得我失去了男子汉的稳重,竟开玩笑说,你看了这本书必定要给我当媳妇。姑娘当然不信,她急切切拿去读了。结果,书中有情,书作媒缘,她果然爱上了他。后来姑娘也成了贾平凹迷,小马站在职工食堂的高山上,仰天长叹:崇拜贾平凹,却老是没见过贾平凹,贾平凹你在哪里?”在孙见喜的书中,贾平凹不仅是神,甚至贾平凹的书也成了灵丹妙药。这种把读者当弱智的神话,亏孙见喜先生才想得出来。如果贾平凹的书真有如此的奇效,那些未婚的孤男寡女们,只要人人买一套贾平凹全集反复阅读,就不愁找不到对象。在孙见喜的笔下,一个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不但读完了贾平凹所有的小说,并且将有的书反复读上了十遍还嫌不过瘾。在他看来,读者读贾平凹的书,简直就像当年那些学习“毛选”积极分子,越读心里越亮堂,贾平凹的书,甚至胜过了当年全国人民追捧的“红宝书”。如:“一次,我在从成都到重庆的火车上,因为四川打工妹下广州,列车超载,十几个小时我没吃没喝没小便,人挤人几乎无法出气。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见一个姑娘手持平凹的《人迹》迷读,问她何故如此,她说:‘挤死我也要读。”难道贾平凹在书中下了什么迷魂药?我不知道,贾平凹看到孙见喜如此地神话自己,究竟是该笑还是该哭?孙见喜的这种贾平凹传记,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美化贾平凹,实际上却是在用一种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肉麻文字妖化贾平凹。孙见喜应该知道,气球吹得太大,很快就会破的。越是把贾平凹捧上了天,贾平凹就会摔得更惨。正因如此,贾平凹的前妻韩俊芳才对孙见喜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犹如防“贼”一样的战术。吊诡的是,这么多年来,韩俊芳和贾平凹越是想摆脱孙见喜,孙见喜就越是对贾平凹穷追不舍,死缠烂打,并美其名曰对自己的贾平凹研究“无怨无悔”,以致使贾平凹不得不无助地哀叹:“写出来出了问题还要我负责。我弄得里外都不是人,被动得很。”
二、捕风捉影,充满编造、无聊的文字。如:“转过山岩,我们立时惊呆:一片麦苗青青中,一位女子正在观望我们,目光相遇,四个男人被惊呆了。她穿着件水红衫子,头发丝丝绺绺飘拂,面色白里透红,眸子轻柔如水。我们和目标相距十几米。我想起那户人家的厦房门上,贴着新婚的对联。我注意到平凹的表情:目光被扯直了,嘴唇僵硬地张着。其他二位正当年轻,我不便表述他们的失态。是她漂亮吗?不能这么说。是她清纯吗?不能这么说。是她内秀吗?不能这么说。四个男人落荒而逃,上了一座高硷,人家还在那麦田里采摘什么。若干年后,我们四人又在商州相遇,谈起这位女子仍不知我们何以败得这么惨? × × 说,论这女子长相,若放在城市,也只算中上,只是因为我们在深山野岭上,突见这样的女子并和环境的巨大反差之下,她的漂亮,便凸显出来,且孤独地立于麦地,便有了神秘的魅力,我当时就不相信是真人。现在想起来,如果我认准是真人,我敢过去拉她的手。”“平凹说,见那女子,我就先感觉有一种气扑面而来,接下来就糊涂了。我说,这女子只能用美丽两个字来形容,用‘漂亮不准确。‘漂亮是外在的;‘美丽是丰富的,‘美是内质,‘丽是外表,这就形成了一个由内而外透射的三维力,再加上环境的陪衬,就产生巨大的‘场,处在这个‘场中,男人十之八九要乱了方寸。我一生只认可两个美丽人,一位是电影《五朵金花》中那个女主角,再一个就是这个女子。”在谈到《贾平凹前传》的写作时,孙见喜曾告诉记者说,他强调的是该书的“亲历性、目击性、共行性”。至于这“三性”对研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孙见喜则语焉不详。如像以上这样一段纯属几个色迷迷的男人荷尔蒙分泌失控的文字,最多只能增加该书恶心人的程度而已。孙见喜以为,一般人玩女人就是下流,一旦成为了文人和名人,则变了性质,只能算是令人羡慕的艳福和风流。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自得,在孙见喜的贾平凹“纪实文学”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对漂亮女性的意淫和玩赏心态。如:“十一时,四川彝族舞蹈团一行八人表演节目。之后,六位女演员高唱‘劝酒歌为诸位敬酒,平凹不胜酒力,竭力推脱未果,由 × × 代为饮之。 × × 说:‘云南宁朗县一位负责人给我说:平凹是伟大呀,连文化部都派人到云南给他找药!”酒池肉林,美女侑酒,历来是许多中国男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孙见喜在文中所写的,更像是《世说新语》中的暴发户石崇斗富,“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的翻版。只是不知真假。但想来这种十有八九“天方夜谭”的故事,不过是孙见喜充分发挥了自己编故事的特长,虚构出来的。在孙见喜的笔下,贾平凹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大师,而且是一个令女性们神魂颠倒的魅力无穷的男人。“但凡文学界开会聚首,他免不了要受到许多女性崇拜者的包围。她们朝他拥挤,常常把热烘烘的胸偎着他的身,常常把湿漉漉的气吁在他的脸;她们要听他说一句平常的话。”如此的场景,那些古代的皇帝们若是地下有知,恐怕都会羡慕死了贾平凹。
三、海阔天空,不负责任地颂扬。在孙见喜颂扬贾平凹的一本又一本的“新天方夜谭”中,贾平凹早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坛的无敌之神。贾平凹的伟大简直是无与伦比,举世无双。在孙见喜看来,“要读懂《废都》必须知道人性是什么?要知道人性是什么,就必须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这样才可以知道《废都》在当代文学中的位置,这是第一;第二,要进一步解读《废都》还必须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了解中国全部的小说史,你须知道中国本来的小说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中国小说的美学传统是什么?下来你要知道什么是外国小说并将之与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比较,从中找到差异;此时,用《废都》进行比照,看她是中国的纯种还是西崽?或是两者杂交?第三,须了解当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形态,了解中国目前社会转型期人们心态和行为模式,从而定准庄之蝶与四大文化名人及几位女士所背负的符号学意义,并由此切割中国社会隐秘的一角做标本,以存照后人,体证‘史的真正的声音”。按照孙见喜这种天花乱坠,不着边际的逻辑,我敢说,中国的读者几乎就没有人有资格读贾平凹的《废都》了。既然贾平凹的小说如此的博大精深,古今中外,如此地包罗万象,以孙见喜现有的知识结构又怎么能够读懂《废都》?既然孙见喜自己都没有读懂《废都》而又出来大谈《废都》,这还不等于是盲人摸象?为了确立贾平凹世界文学的大师地位,孙见喜甚至不惜拿世界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大师来为贾平凹垫底,将他们统统都踩在脚下。在孙见喜的眼里,贾平凹的小说,不仅能够打败福克纳和格拉斯,而且轻而易举地就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扔进了爪哇国。在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大师“打败”之后,孙见喜便兴奋地宣称:“中国作家由此而不再仰视拉美文学,一个真正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上的艺术之林将复现于东方!这对西方正在寻求文化奶娘的后工业文明而言,无疑是一次新的启示,全新的人类文化或许由此而种下胚胎。”
诸如此类的贾平凹神话,不但没有对人们了解贾平凹及其作品起到丝毫的帮助,反而对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贾平凹,理解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贾平凹对孙见喜的微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孙见喜这些不被贾平凹认同,同时又被读者广泛质疑的传记,无疑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大忽悠”。在我看来,孙见喜并非没有写作的才华,令人惋惜的是,孙见喜的才华一开始就用错了地方。试想,倘若孙见喜不是将那种写小说的才华和方法错用,并且避免一条道走到黑地去发挥想象,或许孙见喜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真的可以写出一两本像样的小说。人生不可以重来,但却可以反思。但愿孙见喜能够暂时停下手中的笔,抽时间来好好想一想,这几十年的时光耗在“贾平凹研究”上写出的那些曾经挣过一些银子的文字,多年以后,究竟会不会变成一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