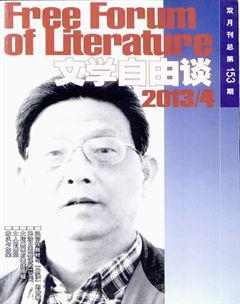放了一把火,再加一把柴
陈冲
关于王蒙新近出版的长篇旧作《这边风景》,我已经放过了一把火,那就是发表在2013年6月27日《文学报》上的《你从“这边”看到了什么“风景”?》。如果说那篇文章主要是对小说原著做了一点文本分析,只是捎带着对某些过甚其词的阿谀奉迎有所批驳,那么下面这些文字,就要对这些谀词的出产地——“《这边风景》研讨会”做一点解析了。一个时期以来,遍地开花的这个作品那个作品的研讨会(最近更有一个被郑重其事地冠名为某某作品的“学术研讨会”),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种种非议,虽然笑骂由他笑骂,研讨我自会之,毕竟其名声和实效,已呈江河日下之势。下面将要解析的这个,无论是会议的规格,主办者的“级别”,还是与会专家的“地位”,都堪称国内最高档次的作品研讨会了,以此为“标靶”,解而析之,大略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种东西是在怎样地败坏着整个文学批评的风气,败坏着一些批评家既有的好名声,甚至注解着某些批评家的文品乃至人品。
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读了这个研讨会的实录,我未必会豁出去放那把火。王蒙是位很会写小说的作家,即使某个作品因为某种原因写砸了,也能砸出个模样来,至少不失其丰富性复杂性,让你做文本分析的时候,须得费点心思,动点脑子,静下心来,把手洗干净了再做。咱又不是干这个的,轻易不愿揽这种活儿。而“特地”去阅读这个实录,却是因为接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一位老友的电话。这位老友是位“读书界人士”。近些年来的怪事之一,是每年都有“世界读书日”活动,活动来活动去,不知为什么,却把“读书界”给弄没了。早年不搞读书日的时候,还有一个“读书界”。要言之,该界人士就是那些纯粹出于爱好而喜欢读书的人。读得认真,亦常有会于心,但并不以此去出席研讨会拿红包,或写文章换润笔。读到好书,觉得是一次享受,记住这个作者,下次遇到他的书,还读;读到烂书,权当是一次消遣,也记住这个作者,下次遇到他的书,不读了。就是这样一位老友,打来电话,说问个事儿。原来他因事先见了预告,从网上即时收看了那个研讨会的“图文直播”,但是那第一位做主旨发言的领导就让他中断了收看。他说那个发言让他产生了两点困惑,其一,他虽然还没有读过小说原著,但是发言只听到一多半,竟然让他觉得那位发言者没有读过、至少没有读完那部小说。他问:这可能吗?然后他又问:其二,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你们那一行里最高层面的人士竟在这样的场合做了这样的发言,可能吗?我当即给了他一个回答:一般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不接受。他说你不是早就退休了吗?又没什么正经事,花点时间,给我个有说服力的回答。
于是我学习了那个文字实录。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所以先读的是那个主旨发言。原来做这个发言的不仅是领导,还是颇有名声的品牌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所以,在仅仅根据这个发言的文字实录来判断他是否读过作品时,我还是相当慎重的,所以我的结论也是慎重的:我不能断定他没有读过作品,但是我得到的印象是,即使没读过作品,也能做这样的发言。
还是以文本为据。发言开宗明义便有个交代:“这两天我把这本书读了。”这是个很含糊的说法,表面上看他讲的是这本书他“读了”,实际上看他想告诉听众的是这本书他“没读”。这本(其实是两本)书七十万字,七百个页码,两天能读完?就算每天十小时,这十小时里不吃不喝不上洗手间甚至连眼都不眨,平均下来每小时就要读三十五页,或每1分42秒就要读一千字,那得怎么个“读”法?您知道的。
然后李先生谈到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基本上全是空话,不过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讨论。毕竟,空话之外,他也谈到了作品中的一些具体优点,比如其中一处说:“这部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生活。南疆的热情、勇敢、善良的人民,缤纷多彩的民族,生活情境,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让我们深深为之感动,为之沉醉。”这能不能算李先生在公然昭示他没有读过这部作品呢?也不必“读”过,哪怕只是“翻”过,但凡“翻”得稍微留意一点,也能记住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是伊犁河流域,不是南疆。在小说里,作家只是在为了更鲜明地突出伊犁河流域的地域特征时,作为对比,才偶尔写到南疆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那么,或许是李先生“翻”得实在太粗疏了,大量写伊犁河流域的篇什都没看见,偏偏极其不幸地刚好“翻”着了写南疆的那几笔,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悲剧性的误会?可是,这部小说里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涉及边民外逃事件,李先生没注意到他们是逃往哪里的?他们是往北跑的呀。南疆的边民怎么会往北跑呢?
但是,为了慎重,我仍然愿意承认,这些并不足以坐实发言者没有读过作品。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足够的客观证据,足以完全排除这些不靠谱的情事是出于发言者的口误,或纪录者的手误。不过我又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如果我们不是太强调发言者是否存在主观故意,而是着眼于接受的一方,那么我想更重要的,应该是向发言者们认认真真地提个醒:你读没读过作品,人家是能听出来、看出来的!虽然这里面确实有冤假错案,比如我就确定无疑地了解,有些研讨会的发言者,是真读过作品的,正惟其读过,才无法从乌有处说出作品的这好那好来,只得凌空蹈虚,离开作品说一些空头好话,结果反倒让人觉得他没读过作品。这样的冤情,您说怨谁?
按这个方法或标准,读过这个研讨会的实录之后,我的判断是,在所有发言者当中,至少有一半没有读过或让人觉得没有读过作品。我说的是“读”过,“翻”过的不算。恕我不指名道姓,反正谁没读过谁自己清楚,我只想说,这是能够听出来或看出来的。但我更想说的是,这毕竟是个最高档次的研讨会,情况要算是比较好的。相比之下,那些档次、级别较低的,尤其是那些所谓“地方上”的,或地方上“专程晋京”召开的研讨会,会上那些“外请”的专家,几乎全都没有读过或让人觉得没有读过作品。好了,现在您知道我想说什么了。这种研讨会有两个很奇怪的机制,一是培养了一批没读过作品也能滔滔然讲上十几二十分钟的专家,二是造就了一批读过作品也让人觉得没有读过的专家。总而言之,这是一些没有或假装没有读过作品的专家在那里研讨作品的作品研讨会。
但是,既然要“研讨”,总得说点什么,哪怕并不真研讨,起码得有“研讨”状。也不是什么都能说,得说好话,最多在那之后加一点“美中不足”。这也罢了,俗话说得好,拿了人家手软,吃了人家嘴短。近日报载,某地一贪官落马,当地企业界对他的评价是:“拿钱办事,作风扎实。”何况我们的专家都是有学养的人,纵是说好话,也知道底线在哪里,不会太离谱。不幸的是,我们的此类研讨会,还有第三条更怪的机制,就是涌现出一批敢于主动打破这种底线的专家。经内行指点,我才约略明白了这种机制能够起作用的原因:只有能把好话说“到位”的专家,方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另一些虽然说了好话,但说得不“到位”,渐渐便门前冷落,终至无人问津了。
有利益就会有竞争。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最终自会产生出类拔萃之辈,其中就有一位,凡是好评如潮的作品,在各种好评当中能给出最高评价的,总是这一位。很荣幸,“《这边风景》研讨会”也请到了这位弄潮儿,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陈教授对《这边风景》给出的评价是:“这部作品我们怎么高度评价都不为过。”上不封顶呀,您还能做出更高的评价吗?不能了。为了使这个至高无上的评价能够成立,就不能拿常识以内的批评标准来衡量这部作品了,所以这位教授单为这部作品设定了一个新标准,而支撑这个新标准的则是一个新概念,叫做“历史的前进性”。
什么是这个新标准?陈教授说:“这部作品应该放在前苏联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以及后来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个谱系中来理解,不再是‘现实主义这个纲领底下来阐释,而是要直面‘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个大概念来阐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就称之为“研讨会话语方式”吧,用老百姓的大白话来形容,就叫“满嘴跑舌头”,逮住什么说什么。他说“应该”如何如何,那就是只能如何如何了。至于为什么“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是概不涉及的。比如,为什么应该放在《母亲》、《在人间》、《静静的顿河》的谱系中来理解,而不“应该”放在《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的谱系中来理解?最起码,前一个谱系是外来的,后一个谱系是本土的;前一个谱系讲的都是革命前和革命中的事,后一个谱系才和《这边风景》一样,讲的是革命胜利后继续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事。事实上,如果把《这边风景》视为这个谱系的最后绝响,说不定还真有点东西可以研讨一番,因为它恰好验证了“物极必反”这个普遍真理。再比如,“现实主义”是个什么“纲领”?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批评实践中,什么时候使用过不带副词的“现实主义”去“阐释”过任何作品?没有呀!我们把所有不带政治性副词的统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而与之相区别、相对立的,先有苏联人发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有经我们改造过的“革命现实主义”,然后很快就过渡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最后则得到了一个更简单也更贴切的命名:“伪现实主义。”区区孤陋寡闻,从来没听说有过一个叫“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概念,更没有听说过——甚至压根儿就无法想象,怎么《母亲》、《在人间》、《静静的顿河》居然构成了一个叫“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谱系!您这不是想替俄罗斯改写苏联文学史吧?当然,我们欢迎陈教授为新的批评标准提出新概念,但是您总得让我们知道一下您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新概念的吧?比如,您这里的“社会主义”指什么?“革命”指什么?就是那个“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又是“社会主义”,又是“革命”,八亿人斗来斗去,还能有“文学”的立锥之地吗?但是陈教授显然不屑于理睬这些细枝末节,而是继续满嘴跑舌头,一跑就又跑出了一个新概念:“历史的前进性。”什么叫“历史的前进性”?是不是历史总是在前进,从来就没有倒退或出轨的时候?不知道。反正一旦用“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来阐释《这边风景》,这个小说就获得了“历史的前进性”,并且由于“创建”了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正面积极‘新人形象”,也有了“历史合理性”。反正怎么说都可以,只要是好话,尽管逮着什么说什么。但是,满嘴跑舌头的陈教授显然让舌头跑得太溜了,忘了征求一下小说作者王蒙先生的意见。依我猜,王先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不可能同意把他打成右派属于历史的前进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陈教授提个醒儿: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今天,说“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一直在创建一种前进的、正面积极的叙事”,只能是——对不起,为了我那饿死在劳教所里的一百七十多位“同学”,我实在忍不住要说一句粗话了——纯属扯淡!
出类拔萃之辈终归是少数。我当年所在的劳教所管这种角色叫“少数个别人”。绝大多数发言者还都是比较温和的,有一些发言甚至还提出了一些有点意思、有些意义的问题,比如张志忠、雷达、施战军等人的发言;即使是另一些发言者,也因为心里知道有点不靠谱,有点超出了底线,便尽量往虚的、含糊的地方说,比如在主旨发言的引导下,好几位都说到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按版权页上的标示,这部小说出版于2013年4月。就算它在4月份的第一天已经在各地书店上架,而研讨会召开的日期是2013年5月18日。王蒙再伟大,谈论他的一部面世刚刚四十八天的小说,张嘴就说它的“文学史意义”,总让人有一种荒腔走板的感觉。于是就时时提到它的写作日期,甚至说它是一件“出土文物”,以唤起人们悠远的历史感,仿佛它已经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的检验,正好用来填补半个世纪之前那段文学史的空白。虽然这倒挺符合巴甫洛夫的心理暗示学说,可是一想到这都是些顶级的专家,就觉得这些话不像是认真说的,倒是更像在以接力的方式,联手创作一篇意识流穿越小说。专家们想必知道,中国的传统是隔代修史。这是一个好传统,也是好规矩,从有史以来,以迄于清,没有一本被承认的史,是由本朝修定的。你这个朝代的功过是非,是个好朝代还是坏朝代,你自己说了不算,要后代人说了才算。按一种理想,我们现在这个朝代,是要传到千秋万代以迄永远的。如果那样,中国自清以后将不再有史。或者某个时候历史因为失去了前进性而不慎出了轨,自有那时的人来考虑如何修“文革”那段时间的文学史。它应该或不应该是“空白”。不是,拿什么来填补这个“空白”;是,又用什么来解释这个空白,都是那时候——也就是千秋万代以后的人,才有资格考虑的事,咱们现在就瞎吵吵这种事儿,那不是咸吃罗卜淡操心吗?果然专家都是聪明人,既然明知说了白说,不说就是傻瓜了,不说白不说呀。怎么说都随便嘛。反正等到正史出来了,无论那上面提没提到《这边风景》,或者提到时又是怎么个说法,终归是千秋万代以后的事了。斯时也,你再想找咱们这些专家秋后算账,肯定早没地儿去找了。
但是,如果我们并没有专家们那么聪明,或者我们就心甘情愿当一回傻瓜,再或者改变一下规则,把专家真当专家对待,你既然是专家,专家的话说了就不能白说,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出一个很要命的问题:“文学史”就是这样被写出来的吗?“文学史”上的“空白”就是这样被“填补”成鼓鼓囊囊模样的吗?果如此,这个“文学史”还能唤起我们哪怕一点点的敬畏之心吗?它不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街头小妞了吗?去年,因为吴义勤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批评界的一种新趋势,即有些批评家敢于在“第一时间”进入“当代文学史”,当时还误以为他在提倡一种不靠谱的治史方法,现在看来,这恰恰暴露了我自己的孤陋寡闻。吴先生常出席此类研讨会,自然见多识广,想必在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上,经常听到各路专家们对好好坏坏的刚出版十几、二十几天的作品做出“文学史意义”上的研讨。那么他其实并不是“提倡”什么,只是对当下批评现状的实录了。现在我明白了,没读过或假装没读过作品而又要把空话说“到位”,最好的话题就是谈论文学史。至于会不会因此败坏了文学批评的风气,至少在研讨会上,就顾不得许多了,拿钱说好话,至少落个作风朴实与扎实吧。
最能体现专家们的批评智慧的,无疑要首推对这部作品的局限性的超越。这个局限性是那么明显又那么巨大,要完全回避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超越。实现这种超越的办法说难也不难,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它确有局限,再话锋一转,“真正重要”的、最能体现作品价值的不是这个,而是……什么什么。一下子就有了发挥的空间,专家们各显身手,说到原汁原味的生活,说到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风情民俗,说到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说到人情人性,直至说到“温暖”、“感恩”、“和解”。总之,那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不是作品描写的对象,只是一个载体,用来装载上面所说的内容。当然,这种话也都是以标准的“研讨会话语方式”,或者说“满嘴跑舌头”的轻巧说出来的,只说是这样、是这样,决不对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进行论证。然而有时候也会发生例外,比如在众多的大智若愚之外,偶尔出现个别的弄巧成拙。其实还是太老实,总觉得光给出结论,一点儿都不论证,似乎太对不住专家的身份了,岂不知他这一论证,就把所有的大智若愚者们全都给卖了。这回干这傻事的是张柠教授。为了论证那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确实只是个载体(张教授的原话是“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过是小说结构中的‘地基”),是用来装载诸如“温暖”、“和解”等内容的,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强烈的历史感和超历史的生命感”。而更不幸的是,他还具体谈到什么才是那个居然能超历史的生命感,原来就是“大量的味觉(食物)、视觉(颜色和风景)、嗅觉(气息)的描写”,而这些“才是现实主义的真谛”。为什么?因为那些斗争都是人鼓捣出来的,而这些味觉视觉嗅觉,却是“上天赋予感官世界……的初始功能”。上天高于人,所以生活感就超越了历史感。这就沾点儿糊弄人了。但这样的理论还是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到了这样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只能大智若愚,稍微一有小聪明,立刻就会露马脚。所以我预测,这种研讨会再开下去,用不了多久,连这样的论证也不会有了。
当然,更好的选择,可能还是不要再开这种研讨会了。这种会太难为我们的专家们了。他们不得不抛开原本值得骄傲的学养,假装看不见文本中一眼就能看见的问题,把心思全都用在怎样从“缝隙”里找出可以说的好话,然后再努力把好话说到位。您说这是图什么?就为那点出场费?须知自欺之余,难免欺人,即如在《这边风景》为什么会尘封三十余年之后又得见天日这样一个与文本无关,却又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上,不说实话是有过错的。所有人都知道,这部小说在1978年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是很难出版的,因为按那时的标准,它的政治是不正确的。不能出版政治不正确的作品,是党的一贯政策,这个政策现在并没有改变,如果用一些含糊的词语去造成某种错觉,似乎现在已经可以出版政治不正确的作品了,那肯定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误导。所以,三十多年前不能出版的作品,现在能出版了,表明的决不是政策的变化,只能是标准或者说“形势”的变化。这一点,只要看看围绕焦裕禄引发的争论就足够清楚了。对焦裕禄的宣传究竟是怎么回事,至少对于我来说,早在1980年就有了一个当时的结论。那时我住在保定,一天从工厂下班回家,路上遇到一位乞讨者,自称是兰考来的,说给点钱吧,能给点粮票更好啦,有钱没粮票也买不了吃的呀。我给了他五斤粮票,条件是你得如实告诉我,为什么要主动讲自己是兰考人。他说,全国人民都知道焦裕禄啊,知道焦裕禄,就知道兰考穷,兰考人民吃不饱啊!我想了想,决定认同这位兰考农民的结论:在对焦裕禄的宣传中,除了焦裕禄的个人品德确有令人肃然起敬之处,就只有兰考穷、兰考人民吃不饱是真实的了。这就是那个时候,或者说思想解放浪潮下关于政治正确的标准:焦裕禄在兰考县委书记任上主要做的那些事,并没有、也不可能让兰考人民吃饱。不管黑猫白猫,他不是抓住了老鼠的那只猫。但是,在又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我们看到了新拍的电影,然后是电视剧《焦裕禄》,我们都知道那是比文学作品更加守土有责的领域,是绝对不会对“政治不正确”讲“包容”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容易明白,在吃饱了肚子之后,又需要那些不抓老鼠的好猫了。这不就是当年难见天日的《这边风景》,三十多年以后得见天日的原因吗?可是,就是这么显而易见的道理,所有发言者都心知肚明的事实,到了我们这种研讨会上,却上不得台面了。即使是不愿太过自欺欺人的专家,也只能像石头缝里长出的小草,挣扎着长出来了也是歪的。比如我一向尊敬的贺绍俊先生,就在发言中表示要“大声质疑‘政治正确”。能有这样的勇气,使我对贺先生更增加了敬意。但是,这样的大声质疑会有怎样的结果,您知道的。
最后我还必须向王蒙先生表示我的敬意。发言结束以后,主持者请王蒙讲话。相比于这个很长的会,他的话讲得格外短,总共只有三百四十个字。这里面真正用来表明他的态度只有三十五个字,即“这部书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很痛苦”,和“没有想到它的局限性形成这么一个特点”。占十分之一吧。最后他用了一百二十个字讲到那些出逃的“哥们”,说他们“生活得不好”,“所以我仍然保留对他们的关心”。这番纯属“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竟占到了整个讲话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做个猜想,他坐在那里听着一个个发言,以他的学养和智慧,当然听得出谁个没读过作品或假装没读过作品,当然也听得出那些发言里一处又一处的言不由衷,当然更听得出那些临时被猛然间无端创造出来的新理论、新概念,是怎样地无法自圆其说和无法定义。我想他确实“很痛苦”。
那么,谁需要这样的研讨会呢?古井集团?乾盛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