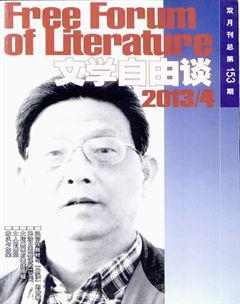文人的感觉
李国文
要知道,越是难解难分的谜,越有吸引力,越是众说纷纭的谜,越耐人寻味。谜在未解之前,那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体会,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绰绰的印像碎片,那感觉得到,可捉摸不住的浮云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纵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美之享受吗?
·作者·
感觉,很重要,就文人而言,尤其重要。
文人的感觉,分两类,一是为文时的感觉,二是做人时的感觉。前者很重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后者更重要,却未必是很多文人真正知道的。
从文学角度看,前者压倒一切,再正常不过,你连文学感觉都没有,即使加入作家协会,也不过徒有虚名,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而已。至于扎一锥子放不出一个屁来的文学感觉迟钝者,麻木者,或者根本连一个文学虫子也算不上的凑热闹者,尽管非常努力,写作品多少部;尽管非常刻苦,出文集若干卷,说了归齐,在文学史的眼光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菜鸟一个。
我从来相信,一个作家,没有迅捷灵敏的文学感觉,没有举一反三的联想能力,没有丰富充沛的反射思维,没有望风扑影的虚构功夫,这四个“没有”统统付之阙如,哪来灵感迸发,哪来创作冲动呢?一句话,文学这个职业,还真有点特殊,大概得有一点天赋。这样说,颇有点唯心论,但事实摆在那里,每朝每代都有存诸史册的皇帝,但不等于每朝每代都有垂誉千秋的作家。说得吊诡一些,能捧文学这碗饭吃,三分努力,七分天赋。没有天赋,你十分努力,十二分努力也白搭。所以,想搞文学和能搞文学,是两回事,爱好文学和擅长文学,是两回事,从事文学工作(哪怕你当上了文学总司令)和从事文学写作,也绝对是两回事。而不能混为一谈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有没有文学天赋?你有没有文学感觉?这是为作家最起码的刚性需求。
因此,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拥有差的文学感觉,大概也就只能写出滥竽充数的作品了。至于那些文学大师,无不因为拥有超好的文学感觉,才写出存世不朽的超好作品。然而,翻开文学史,拥有好的文学感觉者,未必拥有好的做人感觉。结果,为文甚佳,为人失败,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很多。曹丕在短短的《典论》里,还说到两位东汉文坛大佬,班固和傅毅掐架的故事。“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什么叫“不自见”,就是对自己失去感觉,麻木不仁;就是用放大镜看自己的长处,用显微镜看他人的缺失。“自见”者,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别人几斤几两,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自见”者,既不知己,更不知彼,光看到别人的不足,看不到其实自己更狗屎,摇头晃脑,神气活现,感觉失灵,贻人笑柄。这种“不自见”的现象,颜子推在其《颜氏家训》中,举了不少例子:“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杨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覆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疎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
颜子推正统一点,正派一点,因而对以上这些名流大家,责切言厉,刀刀见骨。这是当下那些红包文学批评家,绝对做不到的,并非他们眼拙,也并非他们胆怯,而是有钱使得鬼推磨。批评家心中的那个鬼,看到人民币,立刻没了脾气,立刻敬礼鞠躬,立刻伸出舌头,立刻溜舔金主。颜老先生活着的南北朝时期,没有作品研讨会,推介会,首发式,没有这个奖,那个奖,自然也就没有饭局,没有红包,没有整版唱赞歌的文章和大把大把的奖金。因而颜子推心中坦荡,上溯秦汉,下至魏晋,批了一溜够。还应该看到,从上古到中古,文人并不太多,再加之造纸术很落后,印刷术不发达,作家相当有限,颜老先生就有可能综观上下数千百年,做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结论。要是颜子推从棺材里爬出来,看到如今作协的省市会员成千上万,出版的文学作品成千上万,发出的文学奖金成千上万,养活的批评家也成千上万,恐怕再写《颜氏家训》的话,对于当下那些分明狗屁不是,却颇洋洋自得,“得瑟”没完没了,发飚无休无止,不知东南西北,不知天高地厚,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在话下的轻薄文人,要进行批评的话,就非上面那三百零五个字而是三百零五万字也未必能概括得了的。
看起来,文人的这两种感觉,非同小可,马虎不得,缺一不可。
如果说文学感觉有高低之分,那么做人感觉则是优劣之别。前者的高和低,不过程度上的差别,后者的优和劣,则是本质上的不同。文学感觉的高低,体现在作品上,无非好差之分,做人感觉的优劣,表现在处世上,则是是非之别,这也是做人时的感觉要重要于文学感觉的原因。遗憾的是,很多古往今来的文人,文学感觉好了以后,做人感觉不知为什么就差,甚至很差?颜子推文中提到那位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诗写得那个好,好到无人敢贬一词,人做得那么差,差到无人敢道他一个好。毛泽东读其诗《登池上楼》,批注曰:“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可见这位诗人,其做人的感觉是多么差劲了。老子曾经说过,“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难道人望高了,名声响了,就一定要走向反面吗?一些大佬,前辈,权威,要人,上了年纪以后,不顾令名,不拘小节,不知轻重,不识大体,而为人诟病,而被人非议,无论过去,还是当下,都是文坛上断不了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缘故。毛注中的“晚节造反”四字,虽系指诗人最后弃市广州的结局,但言简意赅,深意存焉,也许这是所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人士,值得记取的。
按《明史》所说,明代的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也是一个在文学感觉上,为人感觉上,逐渐离谱的大人物。因此,归有光“诋王世贞为庸妄巨子”,汤显祖“至涂乙其四部稿,使世贞见之”地加以攻讦,而稍后的公安三袁,则“乘其弊而排抵之”,屡出不敬之词……《明史》遂有“晚年攻者渐起”的贬笔。然而,按其毕生的声望行状,等身著作,不朽价值,深远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堪称有明以来的第一文人,这是当之无愧的。犹如我们谈论文学史,说到唐朝,首先想到李白,说到宋朝,首先想到苏轼,那么,说到明朝,首先就会想到王世贞。他不但是大家公认的文坛盟主,同时还是人所共允的史学巨匠;特别是在才俊辈出,云蒸霞蔚,文章璀灿,风流尽显的明代文坛上,他成为一个拥护者甚众,追随者甚众,反对者不少,诋毁者更多的焦点人物。
一致看好的作家,未必真好;一致看坏的作家,未必真坏,这大概也称得上是真理了。王世贞的文学成就,如日中天,但王世贞的为人处事,却臧否不一,惟其有人赞,有人弹,有人捧,有人棒,才是值得刮目相看的真作家。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也持这样的观点:“王世贞与李攀龙齐名而才实过之,当时娄东历下狎主文盟,奉之者为玉律金科,诋之者为尘羹土饭,盛衰递易,毁誉迭兴,艺苑纷呶,终无定说。要之世贞初时议论太高,声名太早,盛气坌涌,不暇深自检点,至重贻海内口实。逮时移论定,向之所力矫其弊,以变为纤仄,破碎之习者已为众所唾弃,而学者论读书种子,究不能不心折弇州,是其才虽足以自累,而其所以不可磨灭者,亦即在此。今其书具在,虽未免瑕瑜杂陈,然举一时之巨擘而言,亦终不能舍世贞而别有所属也。”
而王世贞能够到达《明史》所称的“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的名望高度,乃形势造就,乃潮流推动。也是蒙元帝国摧毁中原文明,灭而不绝,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深厚渊源,将他推涌到这样一个尊崇的位置上。中国文化之起复兴衰,多因入主中原的边夷民族,自身文化低下,而生出的弱势心理,势必要采取黑暗至极的野蛮手段,对先进文化的地区和人民,实施其恐怖统治。蒙元征服中原后,除了进行掠夺,抢劫,蹂躏,践踏外,人分十等,九儒十丐,屠灭文人士子之斩草除根,抵制文明文化之不余遗力,根除传统思想之干净彻底,否定历史渊源的全面虚无,实施全面的反文化,反文明的精神荒漠化运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试想一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浩劫,仅仅十年工夫,造反派和红卫兵,将整个国家搞到濒临破产边缘的地步。由此可知,从公元1206年到公元1368年的一百六十二年间,蒙元统治者等于一口气进行了十六次文化大革命,能不造成华夏崩毁,神州陆沉,文化断绝,一劫不复的下场吗?
民国初年的柯劭忞,著《新元史》,在《文苑传》中写到:“然蒙古初入中原,好问之学不甚显于当世。”这是对野蛮民族杀灭文化的委婉说法,其实,这一百多年的统治,使整个中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公元1109年(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为两千零八十八万,人口约一亿一千二百七十五万,到公元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全国户数为一千五百万,人口约七千五百万。在遍地尸骸,触目血腥,朝不保夕,杀人如麻的日子里,中国人(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民族)都快死光光了,文学还能有一丝生气吗?所以,明代出现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以后的又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乃时与势的必然,既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屡兴屡灭的强韧,也是中国文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坚定。结果,时代的造就,形势的必然,王世贞应运而生。
如果不是朱元璋这个心理变态的农民,也许轮不到弇州先生享此殊荣。在中国,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有在意识领域中,在文化状态上,处于劣势的民族、阶层、群体、个人,对于文明,会有一种心灵的恐惧,对于文化,会有一种情感的拒绝,对于文人,会有一种偏执的忌畏,对于所有上过学的,读过书的,有知识的,有学问的士人,会有一种非我族类的隔膜。朱元璋就是这样一类冥顽不化者,一旦拥有权力,必然要泄愤,要报复,要整肃,要收拾,等到君临天下,坐稳江山,唯辟作威,唯辟作福,必然要焚书坑儒,大开杀戒。这个流氓无产者,不但杀尽了一大批在元蒙统治下勉为其难的知识分子,也杀光了一大批与新朝合作并且卖力奔走的知识分子,最后,连与他一起打江山比他多识几个字的革命同志,也被他消灭殆尽。有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在中国非正常死亡的全部文人中,只有两个人受到腰斩极刑,一为秦朝的李斯,一为明朝的高启,李斯只被拦腰铡了一刀,而高启却从头到脚,铡成八段。文学这东西,胆小,怕惊吓,哪禁得起朱重八这种将文人剁成肉糜的歹毒?于是,本应在明初出现的这场文艺复兴,一直到正、嘉、隆、万,才姗姗来迟。
斯其时也,明代文学史可谓兴旺发达,花团锦簇,继杨升庵之博,文征明之雅后,就是王世贞的风头了,加上李攀龙的复古,李卓吾的异端,何心隐的侠游,唐顺之的史著,归有光的制艺,李时珍的本草,汤显祖的惊梦,屠长卿的风流,徐文长的孤绝,吴承恩的《西游》……一直到万历年间《金瓶梅》问世,明代文艺复兴运动,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写作,心境很重要,而心境取决于环境,环境决定于气候,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作家很难静下心来执笔为文。在这样一个各展丰姿,各呈异采的氛围里,王世贞异军突起,独领风骚。由于他出身官宦之家,受到良好薰陶,博览群书,勤奋为文。所以,嘉靖年间,他是一个文章脱俗,令人一新耳目,议论出众,左右社会舆情,唱和应制,无不得心应手,才华横溢,目为一时之秀的时代先锋。他这一生,虽说不上顺风顺水,一路鲜花,但也少有波折,无大罣碍。只是“嘉靖三十八年,父忬以滦河失事,(严)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忬竟死西市”,受到打击外,到了隆庆朝,他该有的全有,该得的全得。甚至连《金瓶梅》这部天下第一奇书,著作权也算到他的头上。
这则奇谈怪论,是发生公元2013年春天有关王世贞的最新新闻,我也不知道应为王世贞喜,还是悲,同样,我也不知应为中国出版业喜,还是悲?
将《金瓶梅》的作者,认定为王世贞,犹如给断臂的维纳斯装上另外一支胳膊,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我颇诧异中国的一些好事者,这种自作聪明,弄巧成拙的行径,所为何来?近些年来,《红楼梦》被糟塌一个够后,现在又来算计《金瓶梅》了。我也记不得哪位研究者,哪家出版社,在新出的《王世贞全集》中收进《金瓶梅》,并饶舌不已地,颠三倒四地,强词夺理地,无中生有地,说兰陵笑笑生即王世贞,将一个五百年来在文学史上给读者留下无数暇想的谜坐实,真是太煞风景了。
本来,中国人就是一个不大具有想象力的民族,现在,连这一点点想象余地,也极其武断地被扼杀,真让人感到痛苦。退一万步,如果《金瓶梅》确实出自王世贞手笔,至少也应尊重他不署自己真名,而偏要署兰陵笑笑生的本意吧;如果《金瓶梅》果然不是王世贞的手笔,而兰陵笑笑生另有其人,那王世贞岂不是窃取他人知识财产的贼吗?英国有个莎士比亚,我还曾到艾玛河畔斯特拉斯福镇上,参观过他的故居。但一直不断有消息传来,英国很有些研究者相当认真地考据,这个小楼里住过的莎士比亚,不是写出几十部戏剧的莎士比亚。人家那里在将实证虚的时候,制造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这里却将虚坐实,将读者当作阿斗。
五百年来,至少有五十种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神圣的推断,这不很好吗?至少说明在明代这场文艺复兴的大潮中,有五十位可以写出《金瓶梅》重量级文学作品的巨匠,留下这样的群星闪烁的谜,何其令人神往,一定要解开吗?有必要解开吗?拿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将兰陵笑笑生和王世贞画上等号吗?我始终认为,一个能被王锡爵女儿昙阳子的邪教,迷得魂不符体的,简直浅薄得可笑的王世贞,这样的作家人格,与兰陵笑笑生笔墨中那份冷静,那份严竣,那份清醒,那份睿智,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刻洞察,对于那个社会的辛辣批判,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如果,也许是王世贞在天才爆发的情况下,写出这部不朽之作,他自己不愿坐实,五百年来无人坐实,那继续让维纳斯断臂下去,不也是一种残缺的美,遗憾的美吗?这又能碍着谁呢?
要知道,越是难解难分的谜,越有吸引力,越是众说纷纭的谜,越耐人寻味。谜在未解之前,那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一二体会,那神神秘秘的,影影绰绰的印像碎片,那感觉得到,可捉摸不住的浮云流水,那接近破解,然一纵即逝的吉光片羽,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美之享受吗?我想到梁启超怎样去读李商隐的《锦瑟》了,他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后来,我悟到了一些,也许,一部足本的对性描写未加任何删节的原本《金瓶梅》,用这种附带有奖赠品的方式打开图书市场,其商业行销促售的苦心孤诣,我也只好无语。
回到万历朝的王世贞,他的同年张居正,当上首辅兼帝师后,对他而言,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在旁人眼里,这可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虽然《明史》说“张居正枋国,以世贞同年生,有意引之,世贞不甚亲附”,但实际上,从张的文集中所收录的给这位大文人的回信来看,还是关照有加的。而王世贞写给张的信,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字未留,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张居正最后完蛋了,清算了,怕沾包,怕惹事,偷偷地销毁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王世贞小人,至少他在做人上,有点不够意思。无论如何,嘉靖二十六年,王时年十九,张时年二十,相差一岁的两人,如兄如弟似的联袂应进士试。榜发俱中,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这份情谊,何等难得。同年,在科举社会里,可比如今同学会、校友会的关系更铁。王仰仗这位年兄,张拉扯这位年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张一任首辅,马上就提拔他为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张是政治家,王是文学家,张从来不染指文学,王却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但想在文学上开一片天地,在政治上也要大踏步前进,而且迫不及待。因此两人常常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居正积不能堪”,就对他说,老弟,你是一把莫邪干将式的宝剑,可不是随手可使的大刀片子,金镶玉嵌的宝剑,应该存放在锦匣里,只供赏鉴,不能使用,那就只好请阁下恕我敬谢不敏了。
两人从此分道扬鏕。不久,到了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起初卧床还要处理政务,后来实在支持不了,熬到六月,呜呼哀哉。随后,神宗朱翊钧这条白眼狼,对自己老师发起满门抄斩式的清算,所有张居正的敌人也趁此跳出来踩上一脚。在这场大清洗中,王世贞对他的同年有没有落井下石,不得而知。但是,他绝不厚道,他不够朋友,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张居正病根在“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的绯闻透露,对于张居正巴结大太监冯保,竟在帖子上卑称自己为“门生”的嘲讽揭发,口诛之,笔伐之,相当不讲义气。这与他对待张居正前任首辅高拱的轻薄,如出一辙。因为高在隆庆年间,任首辅,权高位重,说话算数,但迟迟不给他父亲王忬一案平反昭雪,让他记恨在心,等到他撰写《嘉靖以来首辅传》时,字里行间,足足将他丑化了一顿,因而颇为时人疵议。“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凡请弇州作传志者,虽中才亦得附名,未请传志者,虽盖代勋名节义,亦所不载。后之耳食之言,未可以为之定案云云”……但是,时已五十八岁的王世贞,认为即将一甲子的人,真正的老爷子,允许自己可以不在乎,或者,不必在乎了。
这种感觉错位,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生涯上。他未中进士前,即以诗文闻名,出道后,则更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相唱和,继承“前七子”复古理论,史称“后七子”。据《历朝诗选》,起初,有一个叫李伯承的举子,在京会试期间,组诗社,邀同好者参加。“伯承未第时,诗名籍其齐鲁间,先于李于鳞(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后来,“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本来,王世贞年轻时得以侪身诗坛,其引路人为李伯承,与李攀龙结识,其介绍人亦为李伯承,然而,作为诗坛新秀的王世贞,进得诗社,拉帮结派,联手才气并不高,野心却很大的李攀龙,将创社元老李伯承挤兑出诗界。接下来,又将当时诗名胜于他俩的谢榛,逐出这个圈子。据《明史》:“迨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谢)榛为长,攀龙次之,后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攀龙遂贻书绝交,世贞辈右攀龙,力相排挤其名于七子之列。”据称,谢榛眇一目,凡有这等身体缺憾的人,俗称独眼龙,都有强烈的自尊意识和挑战心理,后唐的李克用,那个沙陀人非要把黄巢赶尽杀绝的狠劲,即是一例。于是,谢李之间,产生龃龉。
文坛,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江湖。而按江湖的规矩,第一论胳膊,第二论辈份。胳膊代表力量,辈份代表资格,谢榛有理由不买李攀龙的账,你算哪根葱,你来当一把手。但王世贞愿意这个虚荣心重,而才气有限的李攀龙为首,却不愿意那个独眼龙领袖群伦,于是,王世贞联合他人抬李压谢,从此,谢榛只好成为离群的孤雁,云游天下,老死他乡。可王世贞也并不因此高看李攀龙,清人朱彝尊说过,“元美才气十倍于鳞”,他也许觉得自己百倍于这位同行,他奚落李的作品,“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极尽挖苦之能事。明代诗坛的这份乱象,明代文人的这份德行,不觉眼熟,似曾相识。敢情,五百年前一台戏,五百年后接着演,看来,文人的感觉,无论古今,无论中外,大概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里说过:“当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坛坫争雄之日,士大夫奔走不遑,七子之数,辗转屡增。一时山人墨客,亦莫不望景趋风,乞齿牙之余论,冀一顾以增身价,诗道之盛,未有盛于斯时者;诗道之滥,亦未有滥于斯时者。”现在,攀龙殁世,王世贞独操文柄,此刻,可是真正的老太爷了。据陈继儒的《狂夫之言》,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闰九月重阳,在他的弇园里缥缈楼请客,应邀者甚众,终身不仕的陈继儒,也在座。这个有点体制外意思的文人,对王世贞,崇拜是有的,但不迷信;朋友是做的,但不佞从。他是松江华亭人,王是太仓人,同乡之谊使他敢于口无遮拦。
“酒间,座客有以东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尝叙东坡外记,谓公之文虽不能为我式而时为我用,意尝不肯下之。余时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东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东坡生平不喜作墓志铭,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较似输老苏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论及光武、高帝,先生云还是高帝阔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后,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后却与故人子陵严先生同卧,较似输光武一着。公更大笑,进三四觥,扶掖下楼。”
席间闲话,概属戏言,但看似无心的话,就怕有心人听,文学感觉和做人感觉双输的王世贞,也就只好借着酒喝得高了点的理由,退席。
由此可鉴,文人的感觉,相当重要,而对于上了年纪的文人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