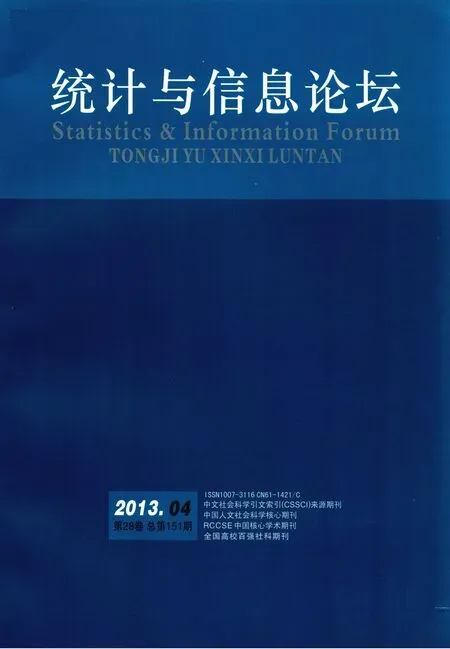集聚经济与中国城市体系优化──跨省迁移视角的研究
余吉祥,段玉彬
(1.安徽科技学院 财经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2.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一、引 言
城市体系的演进方向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效率[1-2]。但是,在不同国家,促进城市体系演进的动力机制存在巨大差异,并由此导致城市体系演进方向显著不同。有学者认为,影响一国城市增长的主要是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知识积累、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市场机制主导的集聚经济是掌控城市体系演进方向的基础动力[3-5]。但是,在很多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制度因素在塑造城市体系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大量研究显示,在这些国家,政府采取的城市化政策往往是主导城市体系演进的基础动力[6-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0.55%提高到2010年的49.68%。然而,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扁平化”演进趋势[10-11],这导致了经济增长无法利用城市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1-2]。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府大量设置的县级市是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12],也有研究将其解释为户籍制度约束下“迁移本地化”引致的“分散城市化”[6]。一个共识是,由政府主导的中小城市偏向的城市化政策扭曲了中国城市体系本该有的规模结构,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政策有了重要调整。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也删除了先前“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条文。在最近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不再有明显的中小城市偏向,这为发挥集聚经济促进中国城市体系演进的作用提供了条件。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在中小城市偏向型的城市化政策下,城市体系的演进主要受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政策影响,并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但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城市体系演进更多地受集聚经济的影响,并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已有的扁平化城市体系因此得到优化。那么,中国城市体系优化所需的经济集聚力来自哪里?从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经济的集聚力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在城市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内部以及城市群的城市之间的溢出效应是集聚经济的源动力。因此,沿海城市提供的集聚力将提供城市体系扁平化演进趋势的反制力量,这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经济基础。
为了检验上述假说,本研究使用跨省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度量指标,分析集聚经济在促进中国城市体系优化中的作用。由于跨省迁移要承担高额的成本,因此,促进跨省迁移的动力只能来自城市强大集聚力所提供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的相对规模实际上体现了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大小。
二、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表现:从扁平化发展到集中化发展的转变
(一)数据简介
已有研究主要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市区非农业人口”来度量城市的人口规模,并基于这一指标来描述城市体系演进的特征。但是,由于“市区非农业人口”是基于户籍人口口径统计的,不包括迁移人口,因此严重低估了城市的真实规模。本研究使用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城市人口规模,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将迁移人口包括在内。城市人口规模度量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依据“城市实体地域”来统计。由于城市行政辖区内通常包括了大片农村地域,因此,如果使用城市辖区内的总人口指标,会高估城市的真实规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周一星和于海波的方法,通过汇总城市街道人口数据得到相对真实的城市人口规模[13]。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来自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以及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提供的“六普”地级市人口数据资料。本研究样本确定为1990年、2000年、2010年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应有的样本量是1990年188个,2000年263个,2010年287个。需要说明的是,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广东河源市、云南东川市无街道人口,因此,1990年的样本量为186。而在《中国乡镇街道人口资料》中,2000年浙江丽水市,广西贵港市、玉林市,四川眉山市、巴州市、资阳市,云南保山市,宁夏吴忠市无街道人口数据,因此,2000年的样本量由263个下降为255个。
(二)样本描述
为了描述中国城市体系的演进情况,本文适当借鉴了《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分类方法,按城市人口规模的大小将城市划分为五个等级,20万人口以下的为小城市,20~50万人口的为中小城市,50~100万人口的为大城市,100~300万人口的为特大城市,300万以上人口的为超大城市。1990、2000、2010年各等级城市的数量和各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见表1和表2。
1990—2000年间,城市数量增长了69个。表1显示,城市数量的增长主要分布在小城市和中小城市等级,达到43个,占城市增长总数的62.3%。而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数量只增长了9个,仅占7.2%。与此对应的是2000-2010年,城市总量增长了32个,但是,仅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就增长了32个,小城市的数量在此期间明显下降,中小城市的数量也仅增长了6个。

表1 各等级城市数量分布表 (单位:个)
从城市人口规模分布上看,1990-200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 359.8万人。其中,小城市和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了1 292万人,占全部城市人口增长的24.1%。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增长了2 936万人,占全部城市人口增长的54.8%。而这一比例在2000-2010年分别为0.1%和88.7%。可见,2000-2010年,新增城市人口的绝大部分集中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十分有限。特别是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在2000-2010年大幅下降,这与1990-2000年城市人口增长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表2 各等级城市人口分布表 (单位:万人)
表1和表2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的城市体系在1990-2000年间和2000-2010年间有着显著不同的演进趋势。前期的城市增长主要以中小城市为主体,城市体系变得更加扁平化;后期的城市增长主要以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体,城市体系朝着集中化方向演进。因此,中国扁平化的城市体系在2000年以后逐渐得到优化。
(三)Zipf回归
通过Zipf回归获得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这是判断城市体系演进趋势的另一个更为常用、更为精确的方法。国外学者利用该方法探讨了世界各国城市体系的演进趋势[14-18]。也有学者使用该方法研究了中国城市体系的演进趋势,研究结论一致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体系变得越来越扁平了[10-11]。
Zipf回归方程为:lnRit=lnAt–atlnSit+eit。式中,Sit为t年标准化了的城市i的规模,通过将各城市规模除以样本城市平均规模得到,Rit为相应的位序。我们可以根据at的变动趋势,判断城市体系演进方向。如果at变大,则表明城市体系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当at为无穷大时,所有城市规模相同。反之,城市体系向集中化方向发展。已有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at显著变大了,因此,中国的城市体系向着扁平化方向发展[10-11]。但是,本研究在样本描述部分提供的结果说明,这一结论只在1990-2000年间成立。

表3 Zipf回归结果表
本研究使用Zipf回归方法获得了1990、2000、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Zipf指数,结果报告见表3。从回归结果来看,调整的R2值三年中均未低于90%,且回归系数at三年里均和1相差不远,这与“齐夫法则”的预测十分一致。最重要的是考察“Zipf指数”的时间趋势。1990-2000年,“Zipf指数”估计值从0.992 2增加到1.068 3,因此,在此期间,中国的城市体系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而2000-2010年,系数估计值从1.068 3大幅下降到0.964 6,表明此期间中国城市体系的演进趋势发生了反转,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两种分析结果一致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国的城市体系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但进入本世纪后,大规模城市发展迅速,城市体系朝着集中化方向发展,先前扁平化的城市体系逐渐得到优化。那么,导致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基础动力是什么?我们认为,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市场机制主导下的集聚经济是导致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基础动力。
三、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成因:集聚经济的作用
对于2000年以前中国城市体系扁平化发展的成因,已有研究一致认为与政府采取的中小城市偏向的城市化政策有关[8][12]。但是,对于2000-2010年间城市体系演进趋势出现的反转,已有文献并未作出任何解释。本文认为,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市场机制在城市体系演进中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大城市更强的经济集聚能力得以发挥,这是中国城市体系在2000年后朝着集中化方向发展的原因,也构成了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基础动力。
为了检验这一假说,需要寻找到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以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集聚能力进行比较。本文认为“跨省迁移人口的相对规模”是个合适的选择。这是因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人口的自由迁移受到了户籍制度的约束。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就业机会、工资福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均未获得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迁移成本高昂。对于长距离的跨省迁移来说,迁移人口所承担的成本更高。面对高昂的成本,促进迁移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城市强大集聚力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报酬。基于这一推断,一个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的相对规模是判断城市集聚能力的合理指标。
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并且在此基础上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重要城市群,因而会产生强大的经济集聚能力。因此,可以从两个层面论证集聚经济在促进中国城市体系优化中的作用:一是从地区层面分析跨省迁移人口在沿海和内地的分布情况,二是从城市层面分析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的相对规模。
(一)地区层面的分析
利用2010、2000、199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4汇总了沿海地区吸引的来自内地的跨省迁移人口的规模①沿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粤等9个省市。。结果显示,1990年有399万人跨省迁入了沿海地区,只占到了全部跨省迁移人口的36.06%。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跨省迁移人口并不主要是流入沿海地区的。但到2000年,流入沿海地区的跨省迁移人口规模增长到2 784.3万人,在全部跨省迁移人口中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到65.64%。至此,内地作为主要跨省迁出地,而沿海地区作为主要跨省迁入地的地位得到确立。到2010年,内地流入沿海地区的人口规模进一步上升到5 770.2万人,在全部跨省迁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一步上升到67.19%。
表5显示,1990-2000年间,流入三大经济带的跨省迁移人口规模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环渤海地区增长了近2倍,长三角地区增长了4.2倍,珠三角地区增长了11倍。三个地区跨省迁移的总规模由448.8万人增长到2 855.4万人,占全国跨省迁移人口的比例从40.56%上升到67.32%。分地区来看,环渤海地区相对地位有所下降,长三角地区增长了近6个百分点,珠三角地区增长了24个百分点。因此,在1990-2000年间,中国的跨省迁移与其说是向沿海地区集聚,倒不如说是向广东省集聚。
但是,2000-2010年间,跨省迁移人口在三大经济带间的分布有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地区显示了持续且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长三角地区吸引了32.81%的跨省迁移人口,为三大经济带最高。环渤海地区吸引了13.32%的跨省迁移人口,与1990年基本持平,而珠三角地区吸引的跨省迁移人口的比例则下降到了25.03%。

表4 按来源分沿海地区吸引的跨地区迁移规模表

表5 三大经济带吸引的跨省迁移人口表
(二)城市层面的分析
由于经济集聚能力的主要载体是城市,因此地区层面的分析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结果。为了对集聚经济的来源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下面的分析将从城市层面展开。
2010年内地、沿海以及三个主要城市群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规模、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的平均规模以及跨省迁移人口占比见表6②该数据由国务院六普办公室提供。由于无法获得2000和1999年城市跨省迁移人口的数据,因此,此处的分析仅就2010年展开。。数据显示,2010年沿海城市的平均规模为175.91万人,而内地城市的平均规模只有72.22万人③沿海城市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粤9个省市共100个城市,其余省区、市的187个城市为内地城市。。而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平均城市规模又显著高于沿海城市的平均规模④这些地区平均的城市规模均超过了200万人。。这表明中国的大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

表6 2010年不同区域城市规模及跨省迁移规模表
表6数据还显示,不同区位的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规模显著不同。珠三角城市最高,为81.14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7.06%。沿海城市平均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也达到了41.5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23.59%。但在内地城市,跨省迁移的规模非常小,仅有3.99万人,仅占城市全部人口的5.53%。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城乡人口迁移受到了户籍制度的严重制约,因此,城市所吸纳的迁移人口,特别是跨省迁移人口,是反映城市经济集聚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沿海城市的经济集聚能力远远超过了内地城市。
表6显示的是城市区位和经济集聚能力之间的关系,表7则进一步显示了城市规模与经济集聚能力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人口超过300万的超大城市的平均规模为642.02万人,而这些城市平均吸引了159.62万的跨省迁移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24.86%。这一比例在100~300万人的特大城市中下降为13.89%。在50~100万人口的城市中,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18%。每降低一个等级,城市所吸纳的跨省迁移人口比例下降10个百分点。这表明城市规模与人口集聚能力正相关。
表7数据还显示当城市人口规模低于100万人时,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大致稳定在4%~5%之间。在这个区间,城市规模的增长对提升人口集聚能力并无多大益处。只有当城市规模超过100万人时,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才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显著提升。因此,着力建成一批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能够有效地提高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表7 2010年不同规模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的比较表(单位:万人,%)
上述分析表明,沿海地区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城市具有更强的人口集聚能力,是导致中国城市体系在2000年以后朝着集中化方向演进的原因。
四、对中国城市体系未来演进趋势的预测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体系的演进是有阶段性特征的。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在考察和总结欧美国家城市化的基础上,将城市化进程划分为缓慢发展的初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10%~30%之间)、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与稳定发展的后期阶段(城市化水平超过70%)。并认为,在城市化的初期和中期,现代工业发展对集聚效益的追求使人口和生产活动不断向大城市集中,推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城市在数量和人口总量上的增长快于中小城市,整个城市体系趋于非均衡发展。但城市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当达到一定规模后,集聚不经济的逐步增强将削弱集聚经济的作用,降低大城市的吸引力[19]24。因此,当城市化进入到后期阶段时,大城市增长速度放缓,中小城市的增长加快,城市体系日益均衡化,将呈现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态势。
保罗·贝洛克总结了1800-1980年间发达国家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的演进过程(见表8和表9)[20]154,从中可以发现,在1800年到1950年城市化发展的初期与中期阶段,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人口规模上,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了中小城市。具体表现为,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52个,增长了51倍,人口则从100万人增加到了12 550万人,增长了近125倍。而中小城市的数量和人口规模仅分别增长了19倍和23倍。这表明城市体系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会朝着非均衡化方向演进。1950年以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陆续进入到了城市化的后期阶段。在此期间,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数量增长了112%,但人口规模却出现了负增长。10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的数量增长了82%,但人口规模却增长了92%。因此,此期间城市体系日益均衡化。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干预的色彩一直十分浓厚。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城市化采取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分散城市化模式。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本地就业问题,但这种人为的干预也扭曲了城市化本该有的进程,使得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快于大城市的增长,背离了城市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政策进行了调整,政府力量逐渐退出。在这一背景下,大城市的经济集聚功能得以发挥,城市体系逐渐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但这一统计数据包括了“镇人口”,如果将“镇人口”排除在外,中国城市化水平则要低一些①这里的数据是城镇化率,并不是城市化率。城镇人口不仅包括了“市人口”,还包括了“镇人口”。如果将镇人口排除在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其实更低,见周其仁(2012)的讨论[21]。。因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目前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再加上城市化政策调整后,市场力量逐渐主导了城市化的进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发展速度还将快于中小城市,城市体系将进一步朝着非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表8 发达国家城市数量分布的演进趋势表

表9 发达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趋势表
五、结论及启示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四普、五普数据资料,本研究从两个角度描述了中国城市体系在1990-2010年间的演进轨迹。无论是对样本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的分类描述,还是使用更为精确的Zipf回归方法,结果均一致显示,中国的城市体系在1990-2000年间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然而,2000-2010年间,城市体系扁平化演进趋势得到扭转。主要表现为大城市在此期间获得了更快的增长,城市体系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扁平化的城市体系在近期得到了优化。
已有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一种分散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模式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集聚功能的发挥,是一种低效率的城市化。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随着城市化政策在20世纪末的调整,集聚经济在推动中国城市体系演进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先前扁平化的城市体系开始得到优化。使用跨省迁移人口的相对规模作为经济集聚能力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沿海100万人口以上的大规模城市是经济集聚力的主要提供者,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沿海大城市。
进一步的国际比较显示,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城市体系的演进趋势显著不同。在初期和中期,大规模城市增长较快。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规模不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大规模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下降,城市体系演进将实现从集中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分散的城市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就因政策干预而提早到来,这显然违背了城市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不过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沿海大城市强大的人口集聚能力开始纠正传统城市化模式形成的扁平化城市体系问题,中国城市体系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正逐步优化。
然而,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在优化中国城市体系中的作用,还有一系列的制度障碍需要突破。主要是因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彻底,迁移人口承担的高额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掉了城市集聚经济带给迁移者的收益,降低了城市集聚经济在促进人口迁移上的作用。因此,中国城市体系的优化除了要继续减轻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外,还需要给迁移人口以市民待遇,努力降低迁移成本。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务院“六普”办公室的数据支持,在此致谢!
[1] 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2] Au C C,Henderson JV.How Migration Restrictions Limit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0(2).
[3] Glaser E L,Kallal H D,Scheinkman J A,Shleifer A.Growth in Citi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6).
[4] Eaton E,Eckstein Z.Cities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7,27(4-5).
[5] Black D,Henderson V.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2).
[6] Henderson J V.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与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07(4).
[7] Henderson J V,Becker R.Political Economy of City Sizes and Form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0,48(3).
[8] Fan C C.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pansions of China’s City System[J].Urban Geography,1999,20(6).
[9] MacKellar F L,Vining D R.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New Evidence[D].IIASA Working Paper.1994.
[10]Song S,Zhang K H.Urbanisation and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n China[J].Urban Studies,2002,39(12).
[11]Anderson G,Ge Y.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5,35(6).
[12]Chung J,Lam T.China's‘City System’in Flux:Explaining Post-Mao Administrative Changes[J].The China Quarterly,2004,180(12).
[13] 周一星,于海波.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重构(一)[J].城市规划,2004(6).
[14]Rosen K,Resnick M.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An Examination of the Pareto Law and Primacy[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80,8(2).
[15]Krugman P.Confronting the Mystery of Urban Hierarchy[J].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10(4).
[16]Gabaix X.Zipf’s Law for Cities:an Explanation[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114(3).
[17]Black D,Henderson V.Urban Evolution in the USA[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3,3(4).
[18]Soo K T.Zipf’s Law for Cities: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5,35(3).
[19]Northam R M.Urban Geography[M].New York:John Wiley&Sons,1975.
[20]保罗·贝洛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21]周其仁.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N].经济观察报,201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