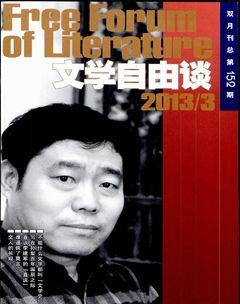写在孙犁百年诞辰之际
金梅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十五年间,孙犁写了百余篇读书记。其所读之书,除很少一部分为近现代著作外,多系古籍;其所记所论,则多为所读书籍的作者,或书中涉及的人物,即所谓文人、文士的心态、生态、性格特征、人生遭际及其结局,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等等。在对历代文人命运所作的剖析中,孙犁归纳、引申出不少值得后人记取的人生或文学的规律与经验。
孙犁在《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中说,当他面对那些名家名作时,他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有感于颜之推,“用寥寥几个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过其实之处”,孙犁表示,“文字之事,实难求是也”。他作读书记时,为了“求是”,总是把文人的行事、为人与为文,置于文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生活情景、人际关系之中加以分析、论述。这就是他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知人论世”的治学方式。
本文略去孙犁对几位汉魏六朝文人的具体分析,先看看近现代著名文人、学者王国维的悲剧结局。关于王国维投湖自尽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疑案。从孙犁相关读书记的分析来看,上述那些古代文人的结局,虽也有其个人性格、品性的因素,但更由于客观因素(政治之因)所致。而在孙犁看来,王国维之死,主要是他个人主观上的原因。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再次东渡日本留学,并听从罗振玉的劝阻,在学术上,走上了一条从新学退回到复古的路径。罗的识拔、资助、教诲,使王国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家”,但“在政治上,却把他推到了一个死角,带到了一个绝境”。这中间,王国维或有“携家相从”,在生活方面要仰仗罗氏的难言之隐,但主要是他个人缺乏坚定的思想和意志软弱的表现。孙犁说:“从这件事,我初步看出王国维的性格,有些病态,即所谓‘狂易,这对他后来的结局,是一脉相连的。”
王国维何以要投湖自尽呢?袁氏称帝,张勋复辟相继失败之后,就连那些粗野的军阀、无知的政客,都已看出,在中国已不可能再行帝制。“像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烟消火灭的‘清室?”孙犁这一设问的意思是,不能像罗振玉似的,把王国维之死,简单地归结为这是他“援主辱臣死之义”的表现,而应该从更深层次、更多角度上进行追问与研究。以王国维的知识、文化背景(他曾多年涉猎西洋文化,从事英文、日文报刊翻译),从理性上,他不会不知道世界大势,也不会不知道中国社会历史已不可逆转。然而,正如当今流行的俗话所说,屁股决定脑袋,王国维先是由仰仗复古派代表人物罗振玉,一头钻进故纸堆和老古董之中,后又和清朝遗老罗振玉,先后入宫侍奉逊位皇帝,溥仪则给了他相当的恩惠。这就使王国维在是变换立场、与时俱进,还是原地踏步、继续围着逊位皇帝转,以及在旧学与新学之间如何选择等问题上,思想纠结、心态失衡、情绪失控。尽管不能说,王国维的投湖而死,是在“援主辱臣死之义”,但缺乏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王国维,在罗振玉推入的“政治死角”和“绝境”,以及由此造成的病态、心态中不能自拔,却是事实。以此,孙犁说,王国维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他所学的“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说”,又“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以及与疾病缠绕相伴随的情绪抑郁,等等,“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所以说,“王国维的死因很复杂,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个人的悲剧因素,即心理与病理的因素”。
如果说,孙犁以知人论世的研究方式,在谈论古代文人的悲剧结局时,侧重点在论世上面,为不幸者给以更客观的评价;那么,他对王国维评论的要点,更多地放在了其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弱点上面,为的是从中得出一些可供后人汲取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呢?孙犁说:“学识,学识。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就以为既有过人之学,就有过人之识。这是会害了自己的。……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以上见《买〈王国维遗书〉记》这里所说的“识见”,是指对时务的认识、见解与践行之谓也。终其一生,王国维始终处于不能辨识与选择、处理时务之中。
联系历史环境、具体情景、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某个人物,是孙犁知人论世、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人的方法论之一,而不以人废言,不以时废言,则是其方法论之别一方面。
关于不能以人废言,孙犁在《读〈宋书·范晔传〉》中,说得更直接、更明确。范晔,出身官僚世家,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宋书》本传中说,范曾任尚书吏部郎。元嘉元年(424),因在太妃殡葬时饮酒,并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范在无聊“不得志”中,“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唐章怀太子李贤,从众家《后汉书》中选定范著并作注,遂使范著《后汉书》成为古典、“前四史”之一,誉贯青史。范晔后为宋文帝宠幸,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要。但他依然没有满足,便于元嘉二十二年(445),与孔熙先等谋立彭城王义康,不料被人出卖,事败下狱,不久被处死。关于范晔的为人,出卖他的人徐湛之说他“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说他“意难厌满”,他哥哥说他“此儿近利,终破我家”。由此看来,范晔那样结局,也是咎由自取。范氏一生行事,除了编著《后汉书》,无可称述。但他在狱中写给甥侄的一封信,却值得称道。孙犁很喜欢这封信。他在摘录其主要内容后说,这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著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范晔在这时,“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后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于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这就是说,不要因某人品行不端,就废弃其内容正确的文字和特定情景中出自肺腑的话语。
所谓不要以时废言,意思是:不要因时代的推移,就废弃时代人物抨击时弊,变革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话语和文字。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贯穿于孙犁文论和读书记。而在《买〈饮冰室文集〉记》中,显得尤为突出。
《饮冰室文集》的作者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人物。戊戌变法,康、梁并称。袁氏称帝,为了不让梁启超发表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馈送他十万元巨款,另附其他贵重礼物,他一概拒绝。孙犁说,梁启超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字千金了”。梁的思想,曾主导过一代思潮,影响过一代青年。但到五四运动后,当“思想界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来吸引青年一代”,梁启超成了“过时人物”,青年人对“这位文豪,就非常漠然了”。梁启超是个很谦虚和有自知之明的人。当有人打算编辑他的文集时,他说“不好不好”,他写文章,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意思。他写文章,是“应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时势变化很快,“转瞬之间,悉为刍狗”。所以说,他写的文章,只能披之报刊,供一时的参考,起一时的作用,过后就拿它盖酱瓿好了。他还说:“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况乃丙申丁酉间(引者注:1896~1897)之作,至今偶一检视,辄欲作呕,否亦汗流浃背矣。”但当编辑告诉他:“虽然,先生之文,公于世者,抑已大半矣。纵自以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间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适于彼时势之言也。”他也就同意了。就内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把梁启超的文章,称之为“时作”。
孙犁在介绍过梁启超的情形之后说:“无论谁写的文章,都不会认为一定就是传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于当世当地有利,更何望于千百年后有用?所以古往今来,应时之作,总是有的,而且数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少作,一概摒而不录,不只抹杀了文章当时的功能,后世读者又从何处考见当时的社会风貌、当时的文坛风貌?”所以说,“梁启超后面表示的态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是实事求是的。孙犁又进一步指出:“人非圣贤,哪能一贯正确?写文章,也常有一时一地的情况,为公为私的目的,个人的私心杂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诚,所有这些,并不一定影响文章的传世。相反,文章最怕虚伪掩饰,这种用心,才真正是文章传世的大敌大患。梁启超的文章,对于当时当地,是充满热情的,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文章,行文流利,善于辩论,吸收外来的东西,迅速而虚怀,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虽都是过时的文字,有心人今天读之,还是会有所体会,并有所收益的。”如果我们把梁启超的文章,与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所抨击的鼓吹大跃进的那些作品相比,就更可看出两者的差别了:前者能够传世,关键在于作者“出之坦率真诚”,“为国家国民设想”,有“由衷的热忱”;而后者,则是作者“虚伪掩饰”和“赶浪头”的私心杂念的表现,这类文字,就只能去盖酱瓿了。
梁启超不是文学家,他对文学还有些偏见,但他是一位文章大家。孙犁说,梁氏“犀利的文笔和善于辩难的文风,长期影响了以后中国报纸的社论和政论。但后人写的政论,说理明辩者有之,能像他那样富于感情的,就很少见了”。在当时,梁启超是一位先进人物,但“这一天才,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命定要随时代而消亡”,其所写“时作”,也逐渐会被人们所淡然视之。然而,孙犁又充满敬仰地说:“展读其书而念其人,于我心虽不无戚戚,然忆及海禁初开,国家危亡之际,仁人志士,爱国心切,忘我无私,声嘶力竭,又不胜其感激追慕之情也。”这是说,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上看,人们不该、也不会遗忘梁氏其人,也不该、不会遗忘其“时作”所起的作用与历史价值。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孙犁说,他对白氏的主张“是信奉不疑的”,并尽力实践之。他还反复讲过,作家是时代的产物。当然,孙犁也是时代的作家,只是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艺术处理方式。但有些研究者,却把孙犁视为时代的“边缘作家”,好像孙犁是远离时代中心,他不是为时代创作似的。笔者以为,孙犁之写作上述《买〈饮冰室文集〉记》一文,不只是在肯定梁启超及其文章的时代作用、历史价值,也是对某些误读自己作品者的一种间接的回应。
孙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写的读书记中,反复地谈论着文人、文学(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这是有原因的。其因之一是,1979年3月间,孙犁曾对来访的韩映山等说:“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写东西别投机,别媚世,别图解政策,艺术要离‘政治远一点,但不脱离政治。”(韩映山《孙犁的人格和作品·日记摘抄(续)》)在这句话中,尽管前有三“别”的前提,后又有“不脱离政治”的限定,但此话传出,还是被人曲解和断章取义地理解成“孙犁主张写东西脱离政治”。孙在一年多后的长篇谈话《文学和生活的路》中,又将他的本意详细申述了一下,但误解与误传依然存在。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孙犁在多篇读书记中,反复谈论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申述文艺是不能、也不会脱离政治的。其因之二是,以史为鉴,启示后人。其因之三是,面对现实,有感而发。
孙犁所谈文人,几乎都与政治有关。这里所说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学(文章)与政治的关系,或文途与仕途的关系。孙犁说:“古代没有‘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也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是间接服务,而是直接服务。也没有人讳言或轻视为政治服务。文人都是自觉自愿的。这说明,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文学和政治的这种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很自然的。”孙犁在《读〈后汉书〉卷七十四·班固传》的题目之下,特意加了一个副题:《一个为政治服务的文人》,上引这段文字,就出于该文。孙犁又说:“作品的高下,不在作品里有没有政治,浓淡如何,而在于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通篇都是政治,却是千古的名文。”1987年,孙犁在上引《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中一段文字的同时,又写道:“我们的文坛,在过分强调政治若干年之后,出现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为政治体现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了淡化生活。”对于这种情形,孙犁讥讽道:“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来越浓化之势。”
关于文途与仕途的关系,孙犁则说:“古时文人,并不忌讳政治。历代作家,没有和政治发生纠葛或牵连的,几乎没有。他们以居官为荣,立功立德并重。”又说,在中国“古时,官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做官。……唐宋以前,文学大家,都有官职。一边做官,一边写文章。文章好,官声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为人贵重”。还说:“唐朝文士(引者注:不只唐朝,自有科举以后的文士均如此),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子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巅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孙犁在《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和《读〈旧唐书〉》中,分别以扬雄依附王莽、蔡伯喈依附董卓、陈子昂依附武则天,柳宗元、刘禹锡等依附王叔文的结局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孙犁说:“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据自身的才能。”(《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意思是,文人在文途与仕途之间,有个根据自身情形进行选择,或两者得兼、保持平衡的问题。但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易的,于是也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生态与结局。孙犁说:“余晚年读史,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于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孙犁还有更具体的描述:文人“做官不成或不顺,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无聊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做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读〈宋书·范晔传〉》)。唐之宋之问,依附武则天、张易之、武三思,后又“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宋虽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但因其言行卑劣,只能说是一个“文学混混儿”、“卖卖名气而已”的典型。在官场受挫后,退得快的,最数白居易。他能“宦而隐”,“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他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文学创作,还自编诗集,分送佛寺,保存得法,使后人才能看到一部“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官场受挫,遭遇不幸后,被动退回文场而有大成者,可以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和宋代苏东坡为代表。柳宗元等遭遇不幸,出乎他们的意料,也不是他们甘愿承受的,但无论从文学史长河中去考察,还是对他们本人,其最终结果,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关于柳宗元,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者。”柳之长期被贬,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如果他不是长期处于被贬之境地,穷极潦倒,中间有人举荐重回朝廷要地,他就不可能在文学辞章上下功夫,从而传之后世。这中间的得失,定会有人辨之者。用孙犁的话来说,“八司马事件”,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没,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大幸欤!”刘禹锡与柳宗元一样,长期遭到贬逐,而这一遭际,也“大大地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以上见《读〈旧唐书〉》)关于苏东坡,苏辙在为乃兄所作墓志铭中,亦有类似的说法:“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读〈东坡先生年谱〉》)意思也是说,如果苏东坡能够稍微韬晦谨慎一些,即使不能为相,也能避祸,但他还能是文学史和书画史上有大成就的苏东坡吗?
柳宗元、刘禹锡、苏东坡等,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艺术上有大成就者。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政治上受挫,文艺上有成”的过程。孙犁在《读〈旧唐书〉》等读书记中,延伸与发挥了韩愈与苏辙的论说,把柳宗元等在文艺上获得大成的过程,视之为不幸中之大幸,当然不是在肯定历史上的政治迫害,而是说,柳、刘、苏等古代文人,在遭遇不幸之后,即使是被动的,却使他们有了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的过程,从而在文学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就。(《读〈旧唐书〉》中谈论刘禹锡的话)这是一种由负面转化为正面的效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事变为好事的过程。孙犁则用这种效应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提醒当今的文艺家们,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深入生活,体察民情,了解民间艺术,何等地重要!
《旧唐书》王勃传中说:“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贵显。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在裴行俭这段话后,撰者说:“果如其言。”孙犁则在《读〈旧唐书〉》中,谈过“初唐四杰”令人遗憾的结局后,引述了上述裴行俭的相关评语,进而引申出了一个如何看待所谓“神童”(“初唐四杰”中的杨炯,中式的就是“神童举”)和少年成长的问题。他说:“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如此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即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又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孙犁由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上述话语,值得当今急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以及当今在文坛上“早年成名”,惟以快捷量多为骛的年少作家们深思之。
(本文由磊石协助完成)
2013年4月18日,于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