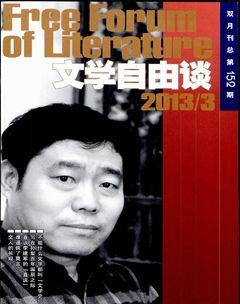不能什么文字都叫“文学史”
唐小林
读罢2013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唐德亮的文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错谬》,笔者不禁暗想,作为该书主编的学者陈思和究竟怎么了?我以为,该书谬误百出,无论怎么说,陈思和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么是陈虽挂名主编,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认真审阅和校订过该书,要么就是陈虽然认真仔细地审阅过该书,但确实未能发现书中如此之多的错谬。倘若是前者,陈思和的治学态度就大为值得怀疑;倘若是后者,陈思和的学术功力就显得大欠火候。
事实上,当今许多披着“文学史”外衣的书往往都不堪细读。例如,被某些作家飙捧为“先锋中的先锋、作家中的作家、编辑中的编辑”(见《一个人的文学史》腰封)的程永新所著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尽管被书商们称之为“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文学史的翻身解放,80后的‘文学补课教材”(见《一个人的文学史》腰封),但仔细读罢,它与“文学史”毫不相干。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某些作家们的功利心和下作状,是他们对手中拥有发表权力者的朝圣般的顶礼膜拜和肉麻的吹捧,而不是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客观研究和准确描述。
自大和自吹自擂是中国作家身上常见的毛病,例如,马原在写给程永新的信中,就曾这样自我吹嘘:“当我自想是写出好诗来的时候,我真要抖起来,哼哼小调。可不是在发头条的时候。我的《星期六扑克》是一首绝唱,不信你出声音地读两遍!只要读两遍就够了”,“我是个天才诗人,只不过生不逢时,这不是诗人的年代”(《一个人的文学史》第34页)。马原真的是天才的诗人吗?我想,这样的问题只有儿童才能够回答。程永新将马原与自己这种无厘头的通信展示出来,丝毫没有让人感觉到其中真有多少文学的品质,反而让人看到了大量的无聊和肉麻。作为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程永新自然会受到那些想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的逢迎,甚至吹捧,这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是,程永新竟然把对自己的无聊吹捧,当成了资本和宝贝,私下欣赏嫌不过瘾,还要拿出来到处炫耀,甚至以这样的“资料”为素材,写了一本煞有介事的“大作”,名之曰:《一个人的文学史》。我们看到,在该书中,作家们对程的吹捧,简直就像吹牛大赛一样登峰造极,一个比一个更投入和离谱。例如,余华这样写道:“程兄:刊物收到,意外地发现你的来信,此信将在文学史上显示出重要的意义,你是极其了解我的创作的,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来说是定音鼓。”“你的长篇快完成了吧?我充满热情地期待着读它,我预感到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这是从对你的了解后产生的。你肯定会成功的,这是命中注定的事。”(第46、47页)贾平凹这样吹捧道:“我一直认为里程(程永新笔名)的小说肯定是好小说,但我读完《穿旗袍的姨妈》后还是震惊。”又说:“里程的阅读是中国作家里最为丰富的一位,对于新时期小说革命他是最早的鼓吹者和参与实践者,正因为如此,《穿旗袍的姨妈》里现代小说的手法足够的圆熟。”“对于我来说,他写得太洋了,洋得让我喜欢而嫉妒!”(第145页)北村的赞词是:“而程永新是先锋中的先锋,作家中的作家,我认为在他心中一定有一种比作家更广阔的先锋意识,又有一种更完整的成熟的力量来把握当时的先锋文学潮流。我们作家像演员,而他则像导演。所以,批评家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遗漏这样优秀的编辑家是奇怪的事,他甚至比批评家更贴近那个时代的文学的胸膛。”(第147页)李洱送上的礼物是:“没有程永新,1985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就会是另外一副模样。”(第275页)丁伯刚的谀辞是:“我看的第二篇小说是《迷失》(程永新的小说),看后完全被那样一种精神涵盖力震住了。在中国的当代小说中,这无疑是最优秀的一篇。”(第73页)
看罢以上这些喷口水不上税的无聊吹捧和集体表演,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些常常宣称要有“全球意识”的作家们拍起高级马屁来是多么的心潮起伏,毫无节制。贾平凹说程永新的阅读是“中国作家里最为丰富的一位”,这样的事实依据是从何而来的呢?试问,鲁迅先生算不算中国作家?钱钟书先生难道是外国作家?难道程的阅读比鲁迅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阅读真的还要丰富?果真是这样的话,程就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牛人”了。恕我直言,就小说的品质而言,程永新的小说最多也只能用“稀松平常”四个字来形容。
试问丁伯刚先生,汪曾祺的《破戒》和《大淖记事》是不是当代小说?韩少功的《爸爸爸》是不是当代小说?程永新的那些小说拿什么来与汪曾祺、韩少功这样的作家相比?丁伯刚不知为了什么,把话说满,将程的小说吹捧成为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篇”,并宣称不但自己爱读程永新的小说,其老婆也爱读程永新的小说,甚至连他的朋友们都对程永新的小说喜爱有加。如此肉麻的颂扬,本身就是笑话。可是,程永新“花椒树上挂猪头”,不但不嫌肉麻,而且还要拿出来示人,我真佩服他把肉麻当有趣的勇气。
作为被贾平凹称之为中国作家里阅读最丰富的程永新,至少应该读过《战国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一篇文章。面对别人无聊的吹捧,作为一个生活在遥远的战国时代的古人,邹忌尚且都知道对别人的吹捧去仔细反思:“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与之相比,我觉得程永新似乎还缺乏了一点邹忌那种面对无聊的吹捧“暮寝而思之”的清醒。
程永新将其书名称之为《一个人的文学史》,在我看来,这颇有点类似于赵本山小品中小沈阳的裤子“跑偏了”。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书中这样的文字,究竟有多少文学史的意义:“那时的程永新只有二十九,其英俊、其潇洒、其谈吐之风趣无人能及,是《收获》编辑部的宋玉,巨鹿路的潘安,外滩的丘比特,黄浦江上空的阿波罗”,“如今我们都已年过四十,程永新的机智风趣更胜一筹,他的俊美却正在成为传说。”(余华语,见该书第130页)“一位熟悉程永新的女士向旁人介绍他时说:程永新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这种来自女性的判断和推崇无疑是令人愉快的,更何况它是恰当的。”“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却又迷恋于优美的法国语言的小伙子确实是风流倜傥儒雅浪漫。”(孙甘露语,见该书第139页)“您真谓性情中人,潇洒名士,又含而不露,有浑然之美质。”(贾平凹语,见该书第93页)诸如此类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文字,在程永新的书中不断往外冒。
对于余华们的吹捧,程永新早已是心领神会,并且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知恩图报的投桃报李。尽管余华的《兄弟》写得很糟,其中李光头和刘镇的人们整天都在消费着小镇美女林红的屁股。这种不厌其详的夸张和煽情描写,使《兄弟》早已经沦落为地摊文学,但程永新却信誓旦旦地忽悠读者说:“《兄弟》绝对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你难道能够设想文学史写到世纪后可以不提《兄弟》,可以没有《兄弟》这一章节,可能吗?绝不可能!”(第190页)由此看来,程永新所谓的“文学史”,就是其与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这帮文坛哥们姐们的交情史。反之,倘若谁与其发生了龃龉,程永新断然忘不了在他的“文学史”中对其进行曝光和羞辱。程永新如此出韩东的洋相:“他们(朱文和韩东)俩喜欢来事,却又缺乏搞运动的素质,像是发育不良的侏儒”,“我第一次给他(韩东)发了个很短的短篇,纯属是帮忙性质,严格的意义是人情稿”,“严格说,这篇东西按照苛刻的标准,是不一定能在《收获》上发表的。但是出于情面,还是想帮他”。(第180、181页)如此的睚眦必报,可以说是程永新对不愿俯首称臣的韩东进行的一次阴暗的羞辱和“脱光”。
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程永新还总是忘不了借他人之口来为自己做广告。在书中,那些哄抬程永新的作家们不是对程永新的小说感到“吃惊”,就是感到强烈的“震撼”,或者被“震住”,仿佛程永新就是中国文坛的核电站和震中区,无论其写的是什么小说,都会对中国的文坛形成巨大的震撼和冲击波。如一位编辑说:“这个小说的阅读过程是让我不断受到震撼的过程,小说大量密集的精彩细节要是落到别人手里说不上可以掺多少水呢,而且对人性、历史的书写有许多难得的突破。通篇的文气从容,情绪饱满,笔触自然,颇有普鲁斯特的韵味。还有宗教情怀。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遇到可以赞美的小说了。”(第177页)这位编辑对程永新的赞美,简直胜过了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的甜言蜜语,那么抒情,那么温馨,那么的情深意长。在这种友情吹捧中,程永新的小说就理所当然地有了大师的韵味和宗教的情怀。当代中国的小说中恐怕很难找到第二部程永新这样可与普鲁斯特的小说比肩的经典了。又如:“你就是好评论家。可惜这样的评论家中国好像几十年没出一个了。”(第310页)难怪在程永新的书中居然出现了“《收获》有个程永新”这样令人笑掉大牙的高级马屁。据笔者所知,近年来,在中国文坛,诸如此类的高级马屁可说是不绝于耳。如像什么“广东出了个 × × × !”仿佛程永新们就是中国文坛的红太阳和大救星。除了别人的吹捧之外,程永新还常常忘不了自大地贬低同行:“其实中国真正懂小说的人,刻薄一点说,没有几个人。”(第208页)我真佩服程永新站在世界之巅,俯视众生的勇气。一个十多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文学期刊的编辑,那么多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和学者,在程永新的眼里通通都成了饭桶和白痴,通通都被踩在了脚下。一个人狂妄到这样舍我其谁,一点都不把同行放在眼里的地步,这确实是需要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的。
俗话说,上帝都有打瞌睡的时候。可是程永新自我标榜,他当编辑这么多年,完全看走眼的,自信就没有过。一个编辑究竟对其审阅的稿件是否看走眼,哪有自己说了算的?王婆卖瓜,也没有这样卖的。以笔者对《收获》杂志的观察,一般的作家,即便是有再好的稿件,也早已被程永新认定的大师们给挤在了门外。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目中无人的狂妄,程永新才敢随心所欲地将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某些作者打包批发成为大师,将他们的作品美化成为经典。倘若谁要不认同他的这些经典,程永新就会在自己的“文学史”中发泄一通。
由此可见,程永新的“文学史”,的确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最多,再加上那些与他结成“利益同盟”的写手们。这种三姑六婆,张家长李家短的“杰作”,只可归入《古今笑话》一类,哪里称得上是什么“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