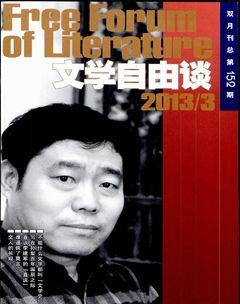“写书有稿费”对文学史的左右
李洁非
去年《环球人物》十月号上,有诺文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吃相凶恶》和《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以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本文非莫言专论,故不就此展开,而只借为由头,去作一项文学史的考察。
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实际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没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稿费,实属误会。“润笔”本意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于稗乘野史,主流的诗文从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基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事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内“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住房、医疗等,就是变换了形式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
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问题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生存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1917年,陈独秀倡文学革命,“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这实在不是他要排斥这样的文学,而是这样的文学在排斥他。贵族、古典(用典)、山林文学得以存在的理由,是文学不必用于世。大多数情形下的古代文学,是士大夫官余之物,为之仅在心性,非为稻粱之谋。何况文学通往社会的途径也根本没有打开,就算你不为自己而写,为社会写作,也毫无需求与市场。而现代的职业化背景下,则颠倒过来,文学已被定义为面向社会的写作。不是不可以只为自己写、只依自己趣味写,但这样的东西,已不受“文学”概念认可,不入其序列以及文学史范围。“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1934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迟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老舍自然是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他心中盘旋着这字眼,掂量沉吟,无非缘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处,是当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做“职业写家”却两次辞职。我们或许会想,明明不必如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何不可?实则那种状态,不在其间体会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欢教书,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从事文学创作,非得处于职业的意识和姿态,假如游移依违,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压力,对于创作终归是客串的心态。近年有与老舍相反的若干男女,从职业作家改行当大学教授,释放了职业作家的压力,也释放了职业作家的进取心。
鲁迅的故事,则与老舍截然不同。鲁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这最后的上海时期,鲁迅脱离公职,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工资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身份渡过。此前,从1912年到1927年4月,鲁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学任职,而俸酬极高。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处任教兼职,亦为一笔收入。另外,还有稿费。其弟周建人忆此,称:“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当时,对鲁迅恭执弟子礼之许钦文在某杂志谋得一职,“十八块钱一个月,在我,比六块、八块一月的稿费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时候。”可为鲁迅收入水准的参考。同文说到,鲁迅与周作人分家后购阜成门内西三条屋基(即今鲁迅故居),花费四百元;此大约仅相当其月入。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月薪高达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薪水远逊厦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公职收入外,还有写作收入。鲁迅成名早,影响大,而又笔耕不辍,报刊稿费与出书版税皆甚可观。
老舍迈向“职业写家”的犹疑、退缩与艰难,我们犹然在目,转眼面对鲁迅1912年以来的持续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著名评价,以及胡风《鲁迅先生》在刻画鲁迅峭拔形象时稍带表达的对茅盾、郑振铎等人的鄙视。胡风称郑振铎“资本家和文坛重镇”,称茅盾“资本家的代理人”或“资本家帮闲”。主要的意思,是讽郑、茅等人同势利现实苟且甚至合污。鲁迅毫无奴颜和媚骨,旁人对现实却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内中诚有个性之根由、品质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场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设若如老舍那样,“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大抵很难有足够底气傲视所有的奴颜与媚骨。
当时作为职业作家,蒋光慈更加成功。说来难以置信,这位以无产阶级文学为鲜明特色的作家,在资本主义上海却竟然以这种作品大红大紫、称富文坛。其小说《少年漂泊者》“出到十五版”;《冲出云围的月亮》“曾创造文学出版界的奇迹:它在1930年1月出版后当年的八个月中,就共再版八次”;余如《野祭》、《菊芬》都再版多次。蒋的成就和收入,显示左翼写作在上海不仅可以存在,甚至是文化与思想的时尚,这恰也是他为何不忍放弃写作去搞什么街头政治的实际原因。其实后来(即夏衍所称1932年后的“左联成熟期”)左联其他成员也渐知个中滋味,在文学、电影、戏剧创作上“四面出击”。蒋光慈不幸先行一步,而竟遭开除党籍。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称他“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说他对《丽莎的哀怨》不听劝告“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又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
实则如先前所陈,“现代”条件底下,文学不可能置于商品交换关系以外,或者说,它必以“出卖”的样态而存在,纵然是“无产阶级写作”亦无他途。从文学中否认、鄙弃金钱或收入,实际是做不到的。不过,在这方面,由于义理上先期对商品经济取批判立场,造成态度上多年摇摆不定。
职业化,就是专仗笔墨吃饭,以文谋食。文与食挂钩,文学变成谋生手段,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历史格局已经如此,就算有人仍抱“为文学而文学”之想,现实也毫无余地。所以“现代”以来,的确没有与吃饭无关的写作,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作家”,还是“无产阶级作家”,“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某种意义也可以说,你不吃“资产阶级文艺”这碗饭,就吃“无产阶级文艺”这碗饭;总之是吃饭。从吃饭角度看百年文学发展,很多问题能够删繁就简。
前左联书记徐懋庸,忆到延安后的感受:“我第一次在延安时,还兼了鲁迅艺术学院的一点课程,另有每月五元的津贴费,此外还有一些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1942年《解放日报》曾有一文《“吃”在延安》,说:“不管你工作和休息,总会有饭吃,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吃饭是受人‘恩赐,或者象外面一样有吃‘下贱饭之感。”在延安,“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
所以,即便在延安,文学与吃饭亦属题内之旨。其形式,如徐懋庸已提到的,包括稿费。《解放日报》及《文艺战线》、《文艺月报》等征稿启事,一般都有“一经揭载,当奉薄酬”之类表示;又如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稿所云:“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明示千字计酬及稿费标准。但这并非延安特色。在延安,文学“收入”与独特政治制度结合,又有新的创造,开启新的分配模式,而垂乎至今。这才是延安文学的特色。党对文艺队伍采取养起来的办法,不像资本家那样只注重眼前利益——不出活即不给饭吃,出了活不够好也不给饭吃——而是着眼于“组织”,亦即政治挂帅。重要在于形成一支队伍,将作家身份转变为服从党的领导的文艺干部,解除作家后顾之忧,让他们觉得从此不再为吃饭而写作,而永远是坚定跟党走的一名光荣文艺战士。这种“组织”层面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文艺队伍确切可管可控,乃延安“养士”亟欲收取之效,作家或文学生产的效率问题虽应考虑,但较此远居其次。
组织起来,是延安及日后共和国文艺队伍建设的真谛,亦是随之而来的一种全新文学收入分配政策之底蕴。自此往后,左右文人之欢愁而又体现资本主义文学生产调控手段的稿费、版税,意义和重要性大幅下降。供给制,或建国后结合了工资制的半供给制,实际是收入的大头。只要成为“组织”所接纳的“文学工作者”,生老病死几乎全由“组织”包揽,从住房到家具,都由“组织”提供而仅收取一点象征性租费。因此,进入编制,成为编内、在册的作家,比之于作为个体在市场上打拼、靠稿费吃饭,远为踏实、牢靠、旱涝保收。近来这种制度虽不再覆盖整个文学,面目亦不完整如初,但遗韵犹存,且仍是想要从事文学的人之心中首选。
建国后,供给制与工资制结合,将原来一部分“实物收入”或曰待遇、福利,折为工资。“组织”内文学工作者的收入随之转型,历史上首次出现以作家身份拿工资的人群。对此新生事物,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作为从事文学所得收入,理应客观地符合或反映文学的价值;曩往以稿费、版税形式发生的收入,是基于作品质量高低、读者或市场认可度,故与作品价值的关系直接,而工资很难求得这种关系,尤其它还固定不变,一经确定,无论作家具体劳作表现如何,都按月付与。正因此,作家的工资并非针对传统上理解的“文学”的付酬。它的着眼点与目的,是构建、定位文学的行政秩序,包括文坛内的领导关系、长幼尊卑,从而保证文学事业与党和国家整个政治的一致性。1955年工资改革,把干部分为三十个行政级,专业领域也各建其等级系列,以级阶之差,将人有效序列化,明其上下前后之意识。
这种本有利于政令贯通的阶梯关系,施诸文学和作家管理,客观效果就是促其官僚化。虽然古来官宦能文者甚多,但作家身份官僚化却是当代所独有。纳入行政级别的不必说,茅盾行政四级即正部级,周扬、丁玲行政七级即副部级,孙犁行政九级、赵树理行政十级即正(或副)局级……对于非行政的专业级别,制度规定也允许与前者品秩相换算(如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八级),在专业作家与官员身份之间形成类比,不单取得那种心理体验,也包括实质性享受同等物质条件(就医、配车、安装住宅电话、交通工具乘坐等级及出差食宿规格等等)。作家的官本位意识,还特别被级别系列中某些内嵌导向而强化,例如行政十三级以上称“高干”,看文件、听报告等政治特权惟相应行政级方可。五十年代作家定级时赵树理等人的选择就很说明问题,他们若定文艺级工资本可更高,然却宁愿少拿几十元,去“靠”政治待遇更高的行政级。
“现代”文学收入的传统来源与稿费、版税,与当代意识形态及文艺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允许其在现实中存在——从当时广泛的收入水平看,且丰厚足以令人侧目,《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热销小说,收入都可至累万,而国家领导人月工资亦不过四五百元,工人一般仅三四十元,因此在五六十年代,有成就的作家确可说已跻身最高收入人群。但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收入,作家虽纳于怀中,却始终没有底气,内心纠结、七上八下。因在革命义理中,货币、金钱、资本(这几个字眼互相沾亲带故)含有“原罪”,“资本主义”来源于此,剥削、剩余价值因它而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对于作家为稿费、版税而写作,革命义理怀有天生嫌厌。很早的时候,蒋光慈在左联的公然叛逆,即被解读为版税——金钱腐蚀的结果。
然而,道义上的耻恶并非稿费、版税遭忌的惟一原因,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隐秘、不会直接提及的原因,即货币本身的活跃性、自由性,令因之以致厚赀的作家,思想容易产生离心力,从而影响或销蚀党对文学的领导。当然,这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仅在文学和作家中才发生。有关金钱能够松懈革命意志乃至使人背叛革命的告诫与宣传,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一直没有中断。对作家来说,个人生活得之党的赐予、国家俸酬,还是自己卖文售书所得,以及这两者比重孰高孰低,被担心将无形中破坏其归属感。后来,果然发生了刘绍棠的例证。刘作为急速升起的文坛红星,数年间以稿费、版税致富而购置房产,据说他本人也公然提出“为三万元稿费奋斗”。1957年反右,刘被打成右派时,对于他的批判着重渲染了稿费问题。
随之在大跃进中,对稿费的抨击被强烈提诸报端。当时工人喊出口号“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作家张志民遂稍加变化,移植为“要红旗不要稿费”,称“对于纯洁我们的创作队伍,对于创作人员的思想建设,都有极大好处,没有半点坏处”。冯德英宣布,把小说《苦菜花》及改编电影所得八千元稿费“全部捐献给山东胶东地区,支援家乡的生产跃进”,他解释他做法的原因:“他所以能写出这一部小说,首先归功于党,和家乡人民的英勇斗争”。侯外庐等则认为“高稿费报酬的制度的不合理,在今天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束缚人们共产主义风格的东西了”,“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登报倡议“减低稿费报酬”,称稿费可使作家“迷失了方向”。同时,他们正确和客观地指出以当下文学体制,稿费确实可以说是“多余”的:
我们估计一下,目前实行减低稿费,对于作家的生活影响不大。中国作家协会及各分会两千会员里面,大多数是业余作家,他们一向靠工资生活,稿费多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影响。至于专业作家,实在是数目很少。而且专业作家中,有好多人在各省市,都担任有一部分职务,在必要时也可以拿部分工资,生活也不会成问题。总之,担心生活困难与作家叫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家早已是党和国家所养的“国家干部”,有职务有工资,稿费多少对于生计并非关键。
终迄于“文革”爆发,稿费立刻废除。“文革”十年,前五年没有文学创作,自然无谈稿费;后五年创作恢复,稿费却不见踪影。这一点,笔者恰好有所亲见。其时,家父偶有文章在刊物发表,所得报酬只是一些书籍,其中有一本《马克思与燕妮》,或类似书名,在当时算是印制精良,至今还记得对上面的燕妮像注目颇久,觉得发表作品能换来这么漂亮的书,亦颇值得。
其后至今,文学收入在中国,又演为一种或系世间独异的状态。我们未遑察问俄罗斯、东欧及越南等是否如此,但知目前的中国文坛,同时存在吃公家饭和自家饭两种作家。亦即,一面是文学已向市场打开,一面是体制内生存仍得维持。后者较三十年前国家的大包大揽,缩水不小,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极富吸引力,多数想以文学为业者,求之而不能得,真正自甘其外的少之又少。
上世纪八十年代,围绕“坚持”与“自由化”曾有反复而激烈的拉锯,最终结果却是互相妥协。“坚持”论尺度有所修正,对“新潮”人物不再拒门外。而后者何尝不如是?“八五新潮”一代,本悉数身在体制外,逮于今日,未入“彀中”者百不及一。考其原因,实不在理念、取向等,惟生存(广义的收入)可解,比如莫言所坦承“吃饱肚子”的问题,生计之有所靠、生老病死之有所托,没有人会敬谢不敏。
近年文学分野那样大,“严肃”与“庸俗”各自判然,人每从道德、精神上有无理想求之,实则却是生存、收入情态使然。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这种“一文两制”收入格局,十分有趣。它其实是百年来文学体制递替的产物,也是一种暂时的调和,不久或将有变,我们从出版的企业化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动向中,略见端倪。那时,文学免不了又有一番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