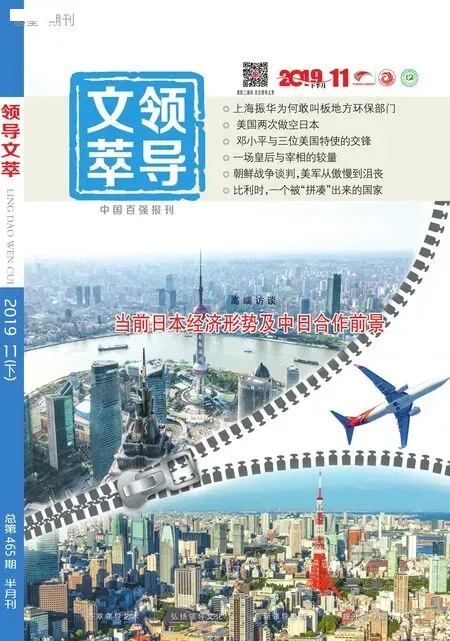胡乔木“最好的一面”
□虞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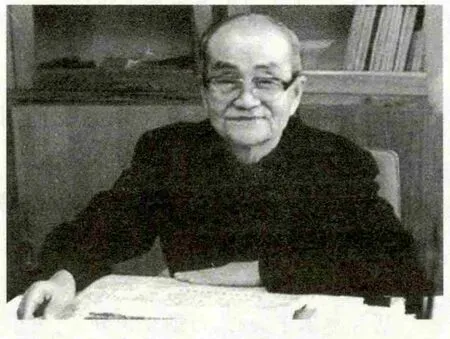
胡乔木复出后,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在《胡乔木书信集》中已见一斑:
1980年9月,巴金向胡乔木当面提出俄国文学专家汝龙住房被占问题,希望他帮助解决;次年9月,巴金致信胡乔木,希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解决”。12月1日,胡乔木致信巴金:“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
1981年7月,梁宗岱病重,胡乔木接其妻“甘少苏的一封来信,要求有所帮助”,当即致信广东省省委书记吴冷西、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请你们两位酌情处理”。据甘少苏说,胡乔木还曾亲自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请他们照顾这位老教授”。
1982年8月2日,胡乔木接新华社关于《著名老翻译家张友松工作条件需要改善》的材料,次日即致信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韦君宜,希望帮助解决这位年近八旬老人的苦境。当时张友松的子女均在外地,身边无人照顾,且蛰居十平米小屋,根本无法工作。
1983年5月,胡乔木致信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梅益,希望解决文学所特约研究员夏承焘在京工作、生活、就医等诸多不便。当时年已八十有三的夏老,全家三代六口人蛰居三十余平米的两居室,且上下四层楼梯。
……
胡乔木乐于关心、帮助知识分子,更乐于同知识分子交流、交友,而这,应该也是胡乔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最好的放松。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我觉得他到我家来,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会儿。他是给自己放放假,所以非常愉快。
乔木同志常来找钟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钟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据说,当时胡乔木常住在钓鱼台,离钱先生的寓所很近,到钱先生家时还常穿着拖鞋。由此也可见胡乔木与钱钟书私交之好。
对此,杨绛在《我们仨》中有一段精彩的如是说——
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这也就是说,如果说胡乔木向钱钟书夫妇展示的是其“最好的一面”,那么钱钟书夫妇则依照自己“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的阅读习惯,“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这种建立在彼此“知道自己的身份”基础上的“契合”,实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只要一方稍有不慎,这种“契合”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就记录了这样一次“意外”:
1982年6月,胡乔木将其七十岁生日前写的四首七律《有所思》寄请钱钟书指正,没想到钱钟书在上面做了很多涂改批注。胡乔木犹豫着一边拿给李慎之看,一边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李慎之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6月12日,李慎之“来到钱先生家里,充当‘说客’”——
我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的《正气歌》太道学气就不收的,以钱先生的绝顶聪明,几乎不等我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后面说的就是他6月18日致乔木信中的话:“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可见,“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文化人之间要建立深厚的私交的确是很难的,正所谓“契合”难得,这从胡乔木与聂绀弩的交往过程中也可见出。
1982年7月4日的拜访,胡乔木面对整年斜躺在床上的绀弩先生,不但竭力赞扬他的诗,而且夸奖他“思想改造可得一百分”,并又一次展现了他“最好的一面”:帮聂家解决照顾他们的一外地亲戚的北京户口问题,托人从香港购买治疗哮喘的好药送给聂绀弩。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
胡聂之交,至此应该说还是蛮“顺畅”的。遗憾的是,聂绀弩“知书”却不“达理”:
胡乔木主动替人作序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但聂绀弩却因“胡序”耽搁了出书进程,全然忘了“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竟于7月21日致信催稿——
顷闻人民文学出版社人言,您要为拙诗写一序,该集正候尊序排印,想系真事,不图暮年打油,竟逢此殊遇,真放翁所谓“丈夫不死谁能料”也。惟年事既高,且复多病,朝不虑夕,深以能亲见此序为快耳。
信的意思很明显:“既然是您要写序,那就请快些!再耽搁下去,我至死都见不到书了……”明知胡乔木是个位高权重的大忙人,却作如是说,大概也只有聂绀弩了。
或许,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聂绀弩虽然欣赏胡乔木的才华,也认为胡乔木同志的序说我对生活有诙谐感……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但终究不愿与他走得太近。原因可能有二:其一,两人的思路有“错位”而无“契合”。曾替聂绀弩在香港刊行《三草》的罗孚说:“绀弩最怕人提起这序,怕人家以为是他找了什么门路求来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不愿“高攀”,而胡乔木大约也自以为他来作序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没想到偏偏就有绀弩这样被迫张吞苦果的人,两人就这么“错位”了。其二则是“胡序”说对他(聂绀弩)的生平却并不熟悉,令聂绀弩非常不满。在10月25日致舒芜的信中,聂绀弩写道:
乔序说对我的生平不熟,其意极明:“此人如有历史问题,我不负责!”否则何必提此?
文人深交本来就难,更何况身份、地位、秉性迥然不同的两位大文人。不管怎么说,胡乔木与钱钟书、聂绀弩的交往都是极为难得、真情实在的文坛佳话,都体现了胡乔木“最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