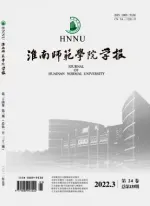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之心理背景研究
沈幼平
(安徽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经由鲁迅的译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影响巨大。鲁迅在《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上倾尽心血,远远超越了译者与译著的关系。这一现象早已被研究者关注。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鲁迅对《苦闷的象征》文艺思想的赞同与推崇。但这似乎只是部分原因,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时的心理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动机,也应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对于翻译《苦闷的象征》的动机,鲁迅自己一直没有言明。他在《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中说:“……因为这于我有翻译的必要,我便于前天开手了,本以为易,译起来却也难,但我仍只得译下来,并且陆续发表。”
遗憾的是鲁迅没有明确说这“必要”究竟是指什么,于是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研究界对鲁迅热情移译《苦闷的象征》的动机解释各异。除前述的文艺思想“赞同与推崇”论外,还有观点认为:厨川白村提出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鲁迅当时的整个精神状况,因而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然而“共鸣说”更适用解释鲁迅欣赏《苦闷的象征》的原因,而不是积极传播与阐释的深层动机。笔者认为,鲁迅如此热情译介《苦闷的象征》。深层动机之一是借《苦闷的象征》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这种苦闷直接产生于鲁迅当时的特殊心理背景。
实际上,“苦闷”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心理的基调。“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身处新旧交替,民族内忧外患,看不到个人前途,作为‘弱国的子民’,烦闷苦恼和悲观绝望之情更是盘旋心胸,无以解脱。”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苦闷更是成为社会问题。
和知识青年“单纯”的“苦闷”不同。年逾不惑官居教育部佥事,又是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的鲁迅,此时内心感受的则是多重复合的苦闷,是一种深隐的大苦痛。
以往的论者多着眼于时代给鲁迅造成的苦闷,是社会性的苦闷云云。实际上,鲁迅的苦闷更多来源于自身。他在开译《苦闷的象征》后的1924年9月24日给李秉中的信中坦承:“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①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1页。
从少年时代起,鲁迅的气质里就打上了苦闷的印记。他对人生的洞察使他对于“人间苦”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力。于是青年时代的鲁迅就陷入无边的孤寂之中,感觉在人群却如置身于荒漠:“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①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7页。这种由寂寞而生的苦闷,是鲁迅一生的心理背景与基调。
除了对人生的悲剧性认识的苦闷基调,在决心翻译《苦闷的象征》时,鲁迅的还体验着更加具体而切肤的苦闷。
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之初,饱受孤寂之苦的鲁迅就渴望在家庭生活中找寻一丝慰藉。1919年底,鲁迅出面购置的八道湾11号住宅修缮完成,他们全家终于又团聚在一起。兄弟三人围绕着母亲,过起其乐融融的大家庭生活。鲁迅先前极度的内心苦闷大为缓解,文学创作力全面爆发。小说集《呐喊》中的主要作品,都写作于八道湾居住时期。然而,和睦热闹的大家庭生活只维持了3年多。1923年7月,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兄弟失和”。8月2号,他带着妻子朱安搬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自此,刚刚回暖的心境又堕入冰谷,鲁迅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
“兄弟失和”已然打击沉重,更令鲁迅陷入绝望的,是他要第一次和毫无共同语言的,名义上的妻子朱安共同生活。搬入砖塔胡同61号,鲁迅即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从搬出八道湾到决定翻译《苦闷的象征》,这一年里,鲁迅的心情几乎是在绝境中的。他甚至说过:“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②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0页。
婚姻悲剧带给鲁迅的痛苦,是他苦闷的另一重要来源。妻子朱安被他称作“母亲送给我的礼物”,鲁迅对比自己大3岁的朱安,除了责任,毫无一丝夫妻感情可言。自结婚之日起,鲁迅实际就过着独身生活。情感的缺失和性的苦闷纠缠一起,象毒蛇一样围绕着他。以前不在一起生活还稍好一些,现在两人单独生活一起,这种悲苦更加放大。
在这种苦闷到绝望的心境下读到 《苦闷的象征》,鲁迅又怎能不发生最强烈的共鸣?他的内心的苦闷突然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对《苦闷的象征》激情地传播自是必然的结果。形象地说就是:唱别人的悲歌,抒自己的苦闷之情。
两性相悦自是人之常情,鲁迅随教育部迁北京后的很长时间里,绝少有和年轻女性接触的机会。所以,除上班应酬外,鲁迅就寓在会馆里抄古碑看佛经,以压抑自己内心的苦闷。然而,这种强迫压抑自己的状况随着鲁迅在大学任教而被打破。特别是译《苦闷的象征》前一年的1923年秋,鲁迅开始在女师大任教,和年轻女性的接触骤然增加。此前被强行压抑的情欲逐渐在鲁迅内心滋长。此时正值“兄弟失和”后,鲁迅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61号。一方面是对正常男女情爱的渴望;另方面是被世俗力量的压制。此刻的鲁迅比绍兴会馆时期更加感到苦闷。
在《苦闷的象征》出版之际,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开始相恋。从两人当时的往来书信可以看出,难以摆脱的人世间的苦闷,一直是他们最多探讨的话题。仅1925年3月至7月的41封往来信件中,直接出现“苦闷(痛)”一词就达32处之多,其他类似的表达也几乎充斥于每篇信件中。例如:“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等等。③由于种种原因,1933年初版及以后再版的《两地书》对信件存在大量删改,难见书信原貌。本文数据均采自: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与公开传播的文字有别,私人性质的书信有时更能反映人的真实内心。仔细研读鲁、许二人此一时期的往来书信可以发现,“苦闷”正是鲁迅翻译、传播《苦闷的象征》时的精神基调。
恋爱是美好的,但世俗的力量和对朱安的责任心,却加重了鲁迅内心对未来生活的疑惧。刚刚收获亲密感情的鲁迅,又体味到更为复杂的人间之苦。他的这一时期的《伤逝》等作品,就明显流露出这种苦闷和疑惧。这就不难理解,鲁迅1927年在国民革命大本营的广州,还在向青年学生倾情推荐《苦闷的象征》。④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1页。苦闷是鲁迅终生难解的,甚至鲁迅的美学思想亦可径称为“苦闷美学”。
因此,在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期,鲁迅的内心被多重复合的苦闷所充溢。《苦闷的象征》里的那些文字,就似从鲁迅自己的心的深处喷涌而出:
“一面经验着这样的苦闷,一面参与着悲惨的战斗,向人生的道路进行的时候,我们就或呻,或叫,或怨嗟,或号泣……这发出来的声音,就是文艺。
人类创造生活的欲求和从社会机体来的强制压抑之力相冲突,即产生苦闷懊恼。
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
正因为有生的苦闷,也因为有战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生的功效。
有如铁和石相击的地方就迸发出火花,奔流给磐石挡住了的地方那飞沫就现出彩虹一样,两种的力一冲突,于是美丽的绚烂的人生的万花镜,生活的种种相就展开了。
人生的深的兴趣,要而言之,无非是因为强大的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懊恼的所产罢了。
倘不是将伏藏在潜在意识的海底里苦闷即精神底伤害,象征化了的东西,即非大艺术。”①以上均见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有谁能怀疑,以上这些文字不是发自鲁迅内心的最深处?
一般而言,翻译作品的成败和翻译者是否是著名作家关系不大。比如几乎所有鲁迅翻译的外国小说都不是被以后的读者接受的译本。但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却是个例外。从译本的接受史角度考察,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一直被公认是最权威的版本。
《苦闷的象征》在当时就有多个译本,除鲁迅译本外,还有丰子恺的全译本,以及明权 (孔昭绶1876-1929)和樊仲云的选译本。但鲁迅的译本一直被公认为最传神的。当时的文艺批评家张若谷曾撰文高度赞扬鲁迅的翻译:“就我个人看来,要算他译的《出了象牙之塔》与《苦闷的象征》两部书为最佳……因为我有些迷信,好像厨川白村的作品,只有他的译笔可以逼肖原文的风味。”②张若谷:《关于我自己》,《文学生活》,上海:上海金屋书店,1928年,第51页。此外,据日本学者工藤贵正考证,1950年代后 《苦闷的象征》在台湾又出现多种新译本。至今共有:徐云涛译本(台南市经纬书局,1957年12月第 1版);慕容菡译本 (台北市常春树书坊,1973年出版);顾宁译本(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76年 3月出版);林文瑞译本(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9年 11出版);吴忠林译本 (台北市金枫出版社,1990年11出版)等译本。③[日]工藤贵正:《厨川白村著作在台湾的传播》,《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然而,尽管在台湾存在这么多的新译本,鲁迅译本的地位却无法替代:“……鲁迅译本《苦闷的象征》被当成“世界文学名著”,并为许多大学和研究所收藏,鲁迅《苦闷的象征》的译文成为公认的范本。”④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为什么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如此持久的魅力?因为鲁译本在直译原著的同时,却又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一种语言和情感上的原创作。鲁迅是在借厨川白村的文字宣泄积郁胸中无法排遣的苦闷,激情抒发自己的心声。字字句句皆为鲁迅自己真实内心的写照,这自然比单纯的翻译更为传神。
宣泄内心苦闷是鲁迅翻译并热情传播《苦闷的象征》的深层动机之一,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