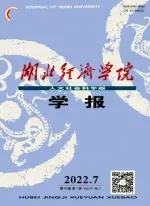香港内地武侠片文化背景比较
陈 希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文化传播系,山西 太原 0300031)
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下,武侠电视剧的拍摄自由度在文化的转型中逐步扩大,但仍然要面对多种文化的纠葛和影像阐释的困境。它始终处于高端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大众文化,民间意识取向与官方意识导向,时代精神的人文关怀与艺术的真实性遵守,忠实与背叛等多重矛盾之中。改编自金庸小说的武侠电视剧虽然运用相同的文本,表现力却大不相同。以《笑傲江湖》为例,1984年香港无线电视台首次对《笑傲江湖》进行电视剧改编,在今天看来,此剧节奏缓慢、动作简单、制作简陋。台湾紧随其后,于1985年也制作了该剧,但只是对香港1984年版进行了复制,对小说的精神主旨也很少顾及。1996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对《笑傲江湖》进行了再度改编,本版本力图还原小说内容与精神内涵,并与香港的时代背景结合,充满了通俗化娱乐化。2000年新加坡也开始对《笑傲江湖》进行电视剧改编,此次改编受到徐克夸张化改编手法的影响,对小说内容进行了大量更改,让观众难以认同。2001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改编,本版《笑傲江湖》终结了天马行空的改编风格,回归到相对忠实于小说内容的改编。
一、香港武侠电视剧文化背景
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96年对《笑傲江湖》进行的再度改编,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它所表现的内容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在通俗文化背景下迎合了观众消遣娱乐的心理。
(一)商品性
(二)通俗性
通俗文化是指流行于民间,通俗易懂并且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化。香港文化中的通俗性体现在排斥与放逐深刻的思考,制造文化消费。香港电视剧作为香港文化的一个载体,具有鲜明的通俗文化特征。此类作品对观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大多没有深层次的含义,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体现出一次性消费的特点,是现代人类的“快餐文化”。所以通俗电视剧主要是指“以反映大众的世俗生活和情感为主要内容;以一定的程式化和模式化为主要形式;以给大众提供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明白晓畅、浅显易懂、便于接受的大众文化文本。”②中国的武侠文化作为通俗文化中的代表,武侠小说也正符合了电视剧通俗化的改编要求。香港无线电视台对金庸武侠电视剧的改编正是以观赏性的武打动作、角色夸张的人生际遇、主人公波折的情感经历作为主要表现方面,历史地理背景与权利的争斗作为次要表现方面。这样使香港金庸武侠电视剧在结合高度商业化制作和传播机制的同时,又兼具传奇浪漫的基本要素,成为通俗电视剧中的典范。观众可以在茶余饭后享受轻松愉快的剧情,而不需要费神去思考故事内容的深刻。
在武侠电视剧制作过程中,通俗性表现在对叙事节奏的把握上。为吸引观众,适应市场,制作者通常把电视剧的叙事节奏加快。“这种明快跳跃的叙事节奏吸收了中国传统白话章回小说的特点:大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小段落模仿好莱坞的叙事风格:三分钟一个小高潮,十分钟一个大波浪,令观众紧张得透不过气。”③在香港无线电视台版的《笑傲江湖》中,就运用这种快节奏叙事与悬念的更迭吸引观众不断地去猜测谜底。为了突出节奏,香港电视剧制作方通常很重视开头,以凶案现场、古时战场、皇宫全景等这种牵动人心的开头居多。香港无线电视台版的《笑傲江湖》在开头即展开宏大铺排的记录,率先表现了武林正派与魔教之间,武林正派盟主之间的比武过招。在剧情展开之前,先让观众体会到武林正派与魔教两方的庞大气势。
(三)自我认同性
武侠电视剧的繁盛成为香港通俗文化自我认同的标志之一。武侠电视剧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苏,维持了十几年的繁荣状态,一直以来是香港文化样式中最为发达的领域之一,与同时期其它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地区与国家相比,香港武侠电视剧也拔得了头筹。武侠电视剧之所以在香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首先,因为香港的殖民地性质,它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的同时被现代西方文化冲击,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交汇下形成了相对开放而且高度发达的文化市场;其次,庞大稳定的读者群在视听时代又迅速转化为忠实的收视后盾,所以武侠电视剧成为电视剧市场中最具价值的产品之一。
金庸武侠电视剧的流行,还包括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当电影电视随着时代发展成为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时,包含浓重东方色彩的武侠电视剧正好充当了当代华人的怀旧寄托。“电视剧制作者利用现代拍摄技巧的发展与特技手段的更新,加上灵活运用各种镜头,以及数字特效的进步,将原本武侠小说中传统的文化资源、诗情画意的意境、激烈的动作场景,都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的形象符号,直接刺激观众的感官,形成震撼的视听效果,给观众在放松中带来金庸武侠电视剧的全新体验。”④
(四)受众的主动消费性
电视剧作为一种最为典型的视觉文化产品,它必须满足各个社会阶层的需求才能最大程度地扩展审美主体的范围。香港的观众由于其生活节奏紧张,忙碌的工作之后需要的是享受生活。香港的武侠电视剧内容结构通俗易懂,人物塑造善恶分明,满足了大众从中寻求消遣、娱乐和放松的心理。从电视社会学中的电视社会消费来看,他们对于香港电视剧的消费方式是主动消费。“主动消费便是指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收看符合主观的收视愿望。”⑤香港无线电视台版的《笑傲江湖》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感情经历的离奇曲折,满足了观众通过电视剧观看人生百态的消遣心理。
同时,观众希望在武侠电视剧中看到与自身单调的现实生活相异的充满刺激与激情的侠客生活,观众在接受过程中,希望编剧和导演用紧张的剧情和激烈的矛盾冲突绷紧自己的神经,在刺激的氛围中使自己的思维紧紧地跟随故事的节奏进行转换,想想自己也在经历剧中江湖侠客的快意人生。在多变的故事情节中,体验到他人的生活趣味。所以,武侠电视剧总是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视率。电视剧作为最典型的电视文化产品,其目的之一就是拉近观众想象的空间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杰姆逊认为“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它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⑥“武侠电视剧通过它直接诉诸人的视觉优势,激烈的矛盾冲突将观众这个审美主体的情感与理智紧紧抓住,从而削弱了观众对电视剧本身的审美批判能力。”⑦强化了观众对武侠电视剧的娱乐欣赏心理。
二、内地武侠电视剧文化背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内地在文化转型中开始掀起改编武侠电视剧的热潮,中央电视台决定首次拍摄金庸武侠电视剧《笑傲江湖》。由于拍摄理念与观众诉求形成差距,使本剧处在了尴尬的位置。
(一)主旋律性
由于电视逐渐发展为当前我国第一大传媒,电视剧也随即成为最富影响力的现代文化载体。从内地电视剧的发展来看,四大名著早已搬上荧屏,并且广受好评。而一些具有典型的中华武打元素的影片在海外的播映与获奖,也为中央电视台在制作古典文学后转向制作通俗文学提供了契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中央电视台用制作严肃历史剧的方法制作武侠电视剧,其实蕴含了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国人的审美意识形态通常是崇高的,是具有明显现实反省和批判特色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本身就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往往会通过对艺术题材的选择,对艺术表现方式的构建以及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批评来影响艺术。这样,艺术与意识形态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交流:意识形态作用于艺术构思、创作、鉴赏的全部过程,而艺术也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力投射出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优秀的艺术作品通常能达到意识形态和艺术之间的黄金中庸距离,因此能成为精品甚至经典。国家广电总局曾指出“广播影视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⑧
互联网 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苏联卷入了古巴导弹危机,核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个国家都在考虑核攻击后的情景。兰德研究员保罗·巴兰(Paul Baran)试图解决核攻击后的一个问题:在核袭击造成毁灭性后果后,如何保持官方沟通渠道的畅通。他的答案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框架。
在金庸武侠小说作品中,《笑傲江湖》表现了诸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观:“提倡在精神上要诚实做人反对暴力;揭示了正义的美好,野心的危险,暴力的愚蠢;对爱情的忠贞,对亲情的渴望,对友情的珍惜。”⑨与香港极力表现金庸武侠作品中的浪漫传奇元素不同,中央电视台版《笑傲江湖》虽然也极具视觉美感,但是这种美感是积累在长镜头的长篇累牍应用上;在节奏缓慢的场面调度中;在绵延悠远的镜头流动中,剧作呈现出了一种现实主义历史剧的拍摄风格。制片人张纪中曾明确表示拍摄此片是走主旋律风格路线,意图弘扬英雄主义精神与正义永存。因此中央电视台版的《笑傲江湖》是力图去表现和回归金庸小说中的儒家侠义精神,优秀的文化传统,希望将武侠电视剧变成一个当代的文化寓言,符合国家的话语需求。
(二)被动消费性
武侠电视剧因为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和对现实的关照,所以呈现出虚幻的特点。在以武力统治的世界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挑战与颠覆,也因此成为人们寄托对现实不满的一种途径。“由于中国古老文化中对‘侠义’的渲染,以及人们内心深处对远古时期神力的崇拜,”⑩中国内地武侠电视剧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该类型剧主要表达了对英雄主义和侠客行侠仗义的歌颂,对真、善、美人性的歌颂。在内地特有的文化进程中,武侠电视剧的制作虽有起伏,但因观众的喜爱,未曾断绝。
目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事业日益深化,经济增长率迅速提高的阶段。当代通俗文化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并席卷内地。中央电视台版《笑傲江湖》制作方以主旋律理念制作该剧,让观众看到一部严肃的历史武侠电视剧,这与观众期望欣赏通俗化武侠电视剧的想法产生较大差距。从电视社会消费行为看,这造成了观众在欣赏该电视剧时被动的消费行为,“被动消费行为不仅是指观众被迫强制性收看电视节目,也包括电视节目中夹杂隐含的与主体审美心理,主观愿望相悖的、主体所不愿接受的一些部分”。輥輯訛这种制作方与接受者的矛盾将中央电视台版的《笑傲江湖》推向了一个尴尬境地。
三、结语
日前,于正工作室对外发布要重新对金庸武侠电视剧进行再度翻拍,而《笑傲江湖》也已投入拍摄当中,在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新一轮的三地合作版金庸武侠剧又将笑傲江湖。
注 释:
①彭宏:《影像怀旧身份确认与文化工业——金庸影视热的心理机制和商业动因》电影文学,2008年版第15期,第14页。
② 高鑫:《电视艺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页。
③刘旭东:《如何去说香港的故事——香港电视剧的叙事学研究》电影评介,第15页。
④彭宏:《影像怀旧身份确认与文化工业——金庸影视热的心理机制和商业动因》电影文学,2008年版第15期,第13页。
⑤ 胡申生:《当代电视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期,第48页。
⑥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⑦ 闵云童:《香港电视剧叙述模式与观众接受心理研究》电影评介,第2页。
⑧ 孙莉:《论21世纪中国电视剧的多元意识形态整合》新闻知识,2010年版第8期,第36页。
⑨ 陈浩:《意识形态下的金庸武侠剧》大舞台,2009年版第3期,第51页。
⑩ 张艳艳:《浅论中国内地武侠电视剧的艺术流变》文教资料半月刊,2010年版第6期,第91到92页。
輥輯訛 胡申生:《当代电视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期,第53页。
[1]彭宏.影像怀旧身份确认与文化工业——金庸影视热的心理机制和商业动因[J].电影文学,2008.15.
[2]胡申生.当代电视社会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9.
[3]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陈浩.意识形态下的金庸武侠剧[J].大舞台,2009,(3):51.
[5]张艳艳.浅论中国内地武侠电视剧的艺术流变[J].文教资料半月刊,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