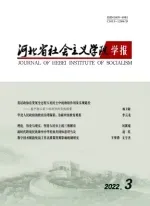“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基石
贾丽云 王丽欣
(1.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河北石家庄050051;2.石家庄市九三学社,河北 石家庄050011)
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所在。在这个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也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这种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成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绝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搞一党制”。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多党合作的问题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要使党外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在“进京赶考”途中,毛泽东特意交待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要“用大位置好好安置”。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成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基石。
一、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建立了“三三制”这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这一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贯彻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方针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
1935年,中共在《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中,“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在乡、区、县、边区各级实行普选,选举产生各级政府,8月,《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普选的原则。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根据地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此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严格贯彻和体现了“三三制”原则。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9名常驻议员,其中共产党员3名;选举18名边区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讨论,以党外人士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作了讲话,批评了党内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作风,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力。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重申:“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此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形成了这个时期多党合作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经济上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实行空前广泛和充分的民主。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很好地坚持了这一政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指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提出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并纷纷致电表示拥护这一号召。中共中央对此表达了欢迎态度,并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在中共有关部门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一大批民主人士陆续从北平、上海、天津、香港和海外秘密来到解放区,同中共商定有关召开新政协和起草《共同纲领》等问题,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初形态。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新年献词中庄严宣布:“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甚至在“进京赶考”途中,毛泽东还特意向周恩来交待,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要“用大位置好好安置”。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体政体的这个意见和构想,被写进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概括起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是这个《共同纲领》,使得多党合作的实践才有了法理上的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科学地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他明确指出,新中国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光靠一个党派,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二大将其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此后历次宪法修正案都予以重申。
事实表明,中国的政党制度安排,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
二、“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的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而各民主党派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反蒋抗日这些根本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一致。也正是因为如此,“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共同治理国家便成为了中共党内的共识。
一是吸引了大批社会精英加入到争取民主自由、建设强大中国的行列。人才是保证一切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联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从而吸引了大批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知识分子汇集到延安开展救亡图存运动。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全面展开,国统区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爱国运动,形成了新的革命高潮,展现了光明的前景,极大地推动和吸引着民主党派,形成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革命力量大联合。以开国时期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为例,在一届政协会议选举产生的6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在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民主党派有20人;在全国政协5位副主席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人;在政协全国委员会180名委员中,有民主党派60多人;在组成政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各委员会主任和各部部长27人中,有民主党派9人,另外还有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在各部门担任了要职。“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充分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团结奋斗的积极性,也为多党合作奠定了群众基础和制度基础。
二是奠定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所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这种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极大拥护,纷纷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做好妥善安置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开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新中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从此被确定下来。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由全体人民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团结精神的光辉典范。
三是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建立。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时局变化最剧烈、政治斗争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也是各民主党派发展的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适时地与民主党派相互磋商、紧密配合,凸显了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并由此得到了众多民主党派的认同,纷纷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1936年,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各民主党派中的爱国民主人士逼蒋抗日,毛泽东分别给宋庆龄、章乃器、沈钧儒、李济深、许德珩、何香凝等爱国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写信,希望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威望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联合36人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结束党治,增强抗日力量;皖南事变后,宋庆龄、彭泽民、何香凝等人在香港联名发出《为皖南事变致蒋介石书》,提出了“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护各种抗日党派”的强烈要求;1943年7月,在国共两党矛盾又一次激化的形势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要求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正是在中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维持到抗战胜利。尤其到1945年7月,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位参政员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举行了三次会谈,就国共谈判、联合政府、“国民大会”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停止“国民大会”;二是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正是这些合作,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成立。
三、“大位置”起用党外人士的现实意义
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与多党合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是有利于人才聚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凝聚起来。由于历史原因,各民主党派成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共同纲领》制定之后,各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修改自己的章程,逐步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各民主党派为进一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形成了人才集聚新模式。
二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以新政协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通过为标志,民主党派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一支合法的民主政治力量。在合作建国的过程中,共产党始终注意倾听民主党派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演进本身就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民主化实践。据不完全统计,至2009年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有党外人士18万多人,各级政协委员中有党外人士35万多人,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中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3.2万人。就石家庄市而言,目前担任市级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5人,其中人大1人,政协4人,担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有99人。这一制度,拓宽了民主渠道,能充分反映社情民意和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
三是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充分信任、相互协商的传统和机制。早在延安时期,民主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就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采纳,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主人士意见的典范。这个传统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仍然得到发扬光大,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都要认真听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据统计,从2002年11月至200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142次。自2005年至2008年底,各地中共党委共召开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1003次。从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各省区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提意见建议中,共有1112条被中共党委和政府采纳。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西部大开发、以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极富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环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吸取和弘扬了我国“和合”文化,强调执政党和参政党合作共事、求同存异、民主协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在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上,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团结协作、共同奋斗,从根本上消除了政党攻讦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内耗,维护了政治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
五是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多党竞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同时也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通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执政党的监督,使得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更多地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随时听到不同的意见,有利于克服和纠正官僚主义,及时改正工作中的错误,防止执政党内出现腐败现象。近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聘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参加党风廉政建设检查,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工作不断加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自身建设,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