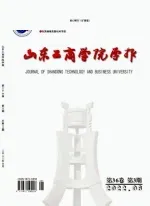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探析
郑小娟,张淑芳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250014;山东工商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山东烟台264005)
明清时代的徽商群体,被不少人称作有儒商之风。所谓儒商,即儒与商的结合,是商(贾)但却好儒。对于徽商何以能以儒商知名,本文试图从思想根源上,即从徽商中流行的“贾儒相通”的观点入手来进行探讨,以期形成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徽州人的“贾儒相通”观
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儒风浓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从学、致仕、为官,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有识之士坚定的价值取向与普遍的道路选择。但宋元以后,随着徽州社会逐步陷入生存危机,徽州人也不得不面临痛苦的思想转变。他们认识到:“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1]”但是,弃儒崇商这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叛逆思想,又是朱子故里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结果,在经过了苦苦的探求和思索后,徽州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折衷之道,即为商为学的不矛盾性,这就是“贾儒相通”观[2]。
用徽州人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贾儒相通”观有3个基本点:
1.儒求宦,商求利,功名相通振家声。徽州人认识到,从儒的目的在于仕宦,仕宦则是为了变寒门为望族以“亢吾宗”。然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3]”而且,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时代,望族的标准也变了,“素封”和以诗礼承家的文人高士一样,都已被世人看作为望族。所以,儒求仕宦,贾求厚利,这两种“功名”实际是相通的,都可以“大振家声”。在这种情况下,是从儒还是从贾,完全可以视具体情况二择一,即:“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3]”不少徽商就是这样考虑的,如歙人许太明携赀商游西湖时就曾慷慨立言:“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4]”又如婺源人李大祈“惧堕其先世业,遂愤然曰:‘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弃儒服,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业骎骎百倍于前,埒素封矣”[5]。
2.难为儒,先为贾,千驷万钟叠相求。汪道昆指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6]”他的这段话是在强调,有志者不应拘泥于读书求功名的陈规,而要善于变通:如果治儒求功名的路走不通,就“弛儒而张贾”。这里的“弛”与“张”,是用弓上弦或下弦来比喻事业的兴废。也就是暂时放弃“儒”,转而去经商。待到经商成功后在“飨其利”时,为了子孙后代的前程,就“弛贾而张儒”,把经商得来的钱去培养子弟读书,求取功名。这样“一张一驰,迭相为用”,其结果就是不成为享有“万钟”食禄的高官,就可能成为拥有“千驷”实力的巨贾。这一点,在“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往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的时代[7],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所以,由文献中不难看到,不少徽州士人的做法就是:“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5]。
3.商重利,士重义,商人士行义为利。一般来讲,商人重利,士子重义,似乎两者是对立的。但是徽州人却看到士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商人同样可以做到重义。正如《黟县三志》卷一五《舒君遵刚传》载:“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吾少有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我们从文献中可见,徽商在经营活动中“以义为利”的事例不少。如歙商黄玄赐在义礼之邦的山东经商,他“临财廉,取与义”,得到齐鲁之人的评语:“非惟良贾,且为良士。[8]”《沙溪集略》卷四载歙人凌晋,“虽经营阛阓中,而仁义之气蔼如。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或讹于少与,觉则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乎益殖”。由此,汪道昆总结说:“司马氏曰: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9]”
二、徽商践行“贾儒相通”观的几个事迹例说
由于是以“贾儒相通”观突破了阻挡徽人从商的思想障碍,所以徽州商帮从一开始出现就带有儒宗的鲜明烙印。我们从徽商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体现他们践行“贾儒相通”观的记载,兹举其中记载较为详明之三人事迹为例。
(一)吴良儒
明人汪道昆的《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中记载其事迹:
“歙之西故以贾起富,其倾县者称‘三吴’。三吴出谿南即谿阳里长公,曰继善。是举丈夫子五人,其四以倾郡闻。季君无禄,早世居其诎。季日自富,孺人戴乃代有终,戴以刘姬进。季君有三息子,长即处士,名良儒。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受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岳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未亡人从梱内而相形家,得而父兆吉,直将树衡霍而夷泰华,日几几于孺子望之。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处士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
于是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余三千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毋即巨万何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恶用远游?’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脱或堪舆果验,无忧子姓不儒。’…
人言诸吴固多上贾,而处士之贾也良。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计赢得,如取诸外府;其发也,如贾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
乃处士中年折节,谢侠少游:‘吾少受命于亲,不自意儒名而贾业,幸而以贾底绩,吾其儒业而贾名。’暇则闭户翻书,摹六书古帖…尝言:‘母氏夺吾儒第,以吉兆卜吾后,吾业未毕,固当为后图。’乃课诸子受经以成先志…处士捐馆武林,盖春秋六十有八。”
(二)程锁
《太函集》卷六一的《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中记载其生平事迹:
“长公(即程锁)始结发,从乡先达受诗,无何,父客死淮海,长公哭踊且呕血,则饮泣以安母心。乃趣奔丧,父故资悉贷他人所。故竖窃资亡匿,秋毫无以为资。客请捕亡而后发丧,长公不可,‘仁者不忘丘首,孤不能以一朝居,如使急亡命而缓亲丧,无宁匍匐往矣。’…既终丧,病骨立,屏居一室,三岁不出户庭,少间,则挟策读书不辍业。母谓:‘孺子病且无以为家,第糊口四方,毋系一经为也。’长公乃结举宗贤豪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久之业骎骎起,十人者皆致不赀。”
长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予平价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
县大夫召长公为植城休宁…宗人某子甲有难色,县大夫顾问长公,长公跪曰:‘某贫,宜不胜任,锁幸有余力,毋以一夫烦君候,请代之。’费五百缗而告成事。会城溧水,长公亦费五百缗。既则举宗梁渐江,费亦称是。…
长公以身起富,中分产,独胞弟铨,遇铨怡怡无德色。…以遗言命三子:‘吾故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问仁、问学,业已受经;即问策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吾倍尔曹,尔曹当事自此始。毋从俗,毋用浮屠,毋废父命,吾瞑矣。’…
余惟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长公是已。…季年释贾归隐,拓近地为菟裘,上奉母欢,下授诸子业。暇日,乃召宾客称诗书,其人则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其书则《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迄今遗风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长公尝奉诏助工,授鲁藩引礼,卒不拜,乃今仲伯受国子业,而冢孙亦学为儒。”
(三)李大祈
婺源的《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中记载其事迹:
“(大祈)于是弃儒服,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知留都为江南要据,爰居积于市,权子母以便民。又谓淮以南淮以北盐盬半天下,煮之不啻可以给私家,亦且可以供边饷。于是转徙维扬,出入荆楚,鹾艘蔽江,业骎骎百倍于前,埒素封矣。”
时故居积久欲颓,公倡大义,率二三昆弟鼎而新之,曰:‘吾匪以怀安,将以联子姓,聚而群处,以无废前人可矣。’故同舍数千指,靡不佩公之遗爱,而雍雍有张公艺家风云。生平犹好行其德,邻里之急,辄应之恐缓。至于驾桥梁、辟道路、建梵宇、备赈仓,类多争先义助。尝有客负廷琇公(祈父)千金,湖阴某子甲负百金者,公怜其家不克偿,遂焚券。曰:“毋以是慁我后人。”维扬有某子甲以事罹覆家之祸,公扼腕为之不平,遂锐身捐千金为解,俾其家得保累巨万之富。人以是多其交谊。远近有质成者,得公一言,即立输平…
治家故尚俭勤,家虽饶,而恬淡自御,食不兼味,衣不重彩,泊如也。惟是羞宗庙,飨宾客、延师傅,则必极丰腆。每以幼志未酬,属其子,乃筑环翠书屋于里之坞中,日各督之一经,而叮咛勖之曰:‘予先世躬孝悌,而勤本业,攻诗书而治礼义,以至予身犹服贾人服,不获徼一命以光显先德,予终天不能无遗憾。然其所恃善继述、励功名、干父蛊者,将在而诸子。’以故诸子发愤下帷,次第尉起,或驰声太学,或叨选秩宗,翩翩以文章倾人耳,皆足以慰公之望也。…金栗斋曰:‘…如松峰公者(李大祈别号松峰),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庶几终身之慕矣。’”
以上3个例子在徽商中是非常典型的。通过观察,我们实际可以总结出徽商践行“贾儒相通”观主要的3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表现是身虽业贾,但却能尽扫市井俗态,有翩翩士君子之风。我们在徽州当地的方志、族谱以及文人笔记中可看到甚多这样的描述。如明万历年间的大学士许国,曾为本族商人许文林号竹石者写过一篇《竹石先生像祠记》,谈到许文林在一个“舟车辐辏,廛市栉比”的市镇经商,但在他身上却没有小商人的俗态:“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又如婺源《湖溪孙氏宗谱》载,徽商孙大峦,“好与文人学士游,多闻往古嘉言懿行,开拓心胸,故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风焉”。再如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墓图志》载徽商郑作“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楚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第二方面,是在业务上,能够以儒术助“治生”,并获得成功。从历史上来看,在这方面春秋时代的子贡(端木赐)堪称徽商们的楷模。子贡是孔子的门徒,《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他学成以后,不愿意做官而去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虽不甚赞同,但在事实上,孔子能够周游列国,享誉四方,却与子贡的大力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子贡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是司马迁说的一句公道话。子贡的事迹为徽商们所仰慕,所以不少徽人常把业商称作“端木生涯”,还有把这四个字镌刻成牌匾悬挂在店堂里[10]。文献中关于徽商以儒术助“治生”,并获得成功的并不鲜见。如《旌阳程氏宗谱》载休宁程声玉弃儒经商,“寓经济于废著之地”,以致“获利如操左券”,“所求无不遂,所欲无不得”。《张氏通宗世谱》载张光祖“少习进士业,受春秋三传,领会奥旨”,后经商,“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甚多”。又如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便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丰南志》的《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记载他:“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很快成为巨富,而且“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可见他不仅是自己获利丰厚,而且还助人致富。这样的人物还有歙商潘汀洲,其早年习贾,从商之后,“虽托于贾人而儒学益治”,他以儒术助“治生”,“或用盐盬,或用橦布,或用质剂,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为此,他曾自矜地说自己“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11]。
第三方面,是在对经商挣得财富的使用上,是否能实践儒家“仁者爱人”和行善积德的思想。在文献中,常可见到一些徽商在经商致富后,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抚孤恤贫,兴水利筑道路以及救荒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有的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这带有长远投资的性质),但有的就可以说只是出于“仁爱”和行善积德的目的。像歙人黄长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载他“不效啬夫,徒为自封已也。人有缓急,赴之皇皇如不及。凡阨于饥者、寒者、疾者、殁者、贫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办翁。翁辄酬之如其愿乃止”。另外还有“嘉靖庚寅,秦地旱蝗,边陲饥馑,流离载道。翁旅寓榆林,输粟五百石助赈。”当时地方官奏报朝廷,要赐给黄长寿四品爵,授予他绥德卫指挥佥事的职衔,但是黄长寿“谢弗受”。他的理由是:“缘阿堵而我爵,非初心也”。也就是说他出钱做好事,并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出于本心的行善动机。清时婺源商人詹文锡“承父命往蜀,至重庆界,洽合处有险道,名惊梦滩,悬峭壁,挽舟无径。心识之。数载后,积金颇裕,复经此处,殚数千金,凿山开道,舟陆皆便。当事嘉其行谊,勒石表曰:‘詹商岭’”。他能将此事放在心上,几年后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主动出资修建,其本心也当是为了行善,以方便过往行者,而非带有功利的意图。光绪《婺源县志》的《人物孝友》部分中详细记载了詹氏的这一事迹。
三、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分析
如果说徽人服贾,“贾儒相通”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徽州商帮本身就是带着“贾儒合一”的追求而出现的。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经过“贾儒合一”的过程,实现由商入儒,彻底转变的目的。即为儒是目标,而从贾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徽人对“贾而好儒者”是分析得相当仔细的,将其分为2类:一类是“贾名而儒行”的“儒贾”,是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的;另一类是“以儒饰贾”的“贾儒”则是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的。徽人提倡做“儒贾”,而认为“贾儒”不足取,至于原因,正如前引《太函集》卷六一的《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中评价程锁时说的:“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即儒贾是符合正确的儒化发展方向的,会把一个人培养为儒士;而贾儒借助于儒术来经商,只会让其为商做得更加成功,不会促使其转化为儒,即不可能实现儒家以德教化育人的目的,对其来讲,儒的外观犹如蝉蜕一般,用完之后便会褪掉了。
由此观察,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应是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的,其经商也是在创造儒化的环境,寻求使子孙为儒,仕宦的结果。对不少徽商而言,只要有可能,他会让自己的后人,甚至自己放弃已经营的较为成功的贾业,而改去读书治儒。在徽商文献中,不难看到这方面的例子,如《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载:“仲君故事儒,藉宗庙之灵,从舅贾而起富,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受经矣,幸毕君志而归儒。”同书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中也谈到歙人吴良儒在经商累“巨万”后,自豪地称:“吾少受命于亲,不自意儒名而贾业,幸而以贾底绩,吾其儒业而贾名。”他“暇则闭户翻书,摹六书古帖…乃课诸子受经以成先志”。
其实,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商人,要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下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成功,他势必要为自己披上一层儒化的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学界所提到的明清众商帮都有个儒商化的问题,只不过儒化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徽商应该是儒化程度最深的,在一个极端上;而晋商恐怕是截然相反,在另一个极端上。比如,雍正二年刘于义在奏折中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朱批谕旨》卷四七中记载了雍正帝对此的批示,他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在最高统治者眼里,晋商这个群体就是非常轻视读书仕宦的,这大概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评价。
[1](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二[M].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万历十九年刻本.
[2]汪雷.论徽商之崛起[J].财贸研究,2002,(2):14 -19.
[3](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M].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万历十九年刻本.
[4]歙县许氏世谱明故青麓许公行实[Z].隆庆抄本.
[5]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Z].万历刊本.
[6](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M].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万历十九年刻本.
[7](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M].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民国七年刻本.
[8]歙县竦塘黄氏宗谱黄公玄赐传[Z].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9](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二九[Z].范长君传,万历十九年刻本.
[10]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40.
[11](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四[M].潘汀洲传,万历十九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