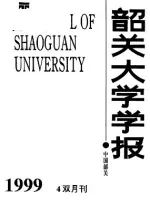爱的魔力——以《一串葡萄》为中心
(开封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著名文学流派白桦派的中坚作家,也是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贯穿着对人类的爱,他写人生中美好明朗的一面,也写丑恶阴暗的一面,鼓舞为爱与理想而生存。《一串葡萄》是有岛武郎应《赤鸟》杂志主编铃木三重吉的邀请而创作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发表于大正9年(1929)。取材于作家幼年时的生活体验。
作品讲的是,主人公“我”就读于西洋小学,每天经过美丽的海港,“我”喜欢画画,想画出海边漂亮的景象,尤其是那种几乎透明的海水的蓝色和一种浅红色,可是“我”却没有那么漂亮的水彩笔。而“我”的同学吉姆恰好有,“我”想要那两种颜色的水彩笔,想啊想啊,想得不得了,想到胸口发疼,终于忍不住偷偷拿走了吉姆的水彩笔,但是被同学发现了,并被送到了“我”所喜爱的女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没有呵斥“我”,而是摘了串葡萄送给“我”,还嘱咐“我”第二天一定要来上学。第二天,“我”犹犹豫豫地来到学校,可完全出乎意料,在校门口等着的吉姆竟然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让“我”和吉姆握手和好,又摘了串葡萄送给我们。从那以后,“我”变成了一个比以前好一点的孩子,好像也不那么胆小怕事了。
故事很简单,写了一个少年的小学时期的一段经历和对老师的美好回忆,从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爱及爱的魔力。当然,这里所说的爱,不是狭义的男女之爱,而是广义的爱。这里所说的爱和爱的魔力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少年喜爱绘画,太过执着而至于偷拿同学的颜料,做出错事。属于偏执的爱,造成了不良的结果。二是老师出于对学生的真爱,恰当处理,使矛盾双方都有所收益,有所长进。是真正美好的爱,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一、“我”对颜料的爱是偏执的爱
作品中的“我”喜欢画画,喜爱漂亮的颜料,爱到痴迷,爱到着魔,爱到不能自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以至于偷拿别人的彩笔。在这个不长的故事里,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描绘港湾迷人的美景。“蔚蓝色的大海上军舰、海轮等排得满满的。烟雾从烟囱里袅袅升起,世界各国的国旗悬挂在一根一根桅杆之上,美得令人目眩。”[1]这景物色彩斑斓,动静有致,层次分明,少年从心底里喜欢,热切地希望把它们真实地呈现出来,可是无论怎么描画,怎么涂抹都展现不出真正景致中看到的那种颜色,达不到自己的预想效果,仔细想想,感觉是由于自己没有描绘这美丽景色的水彩笔。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么选择放弃不画不涂了;要么用自己不够理想的水彩笔凑合着涂涂画画就结束了。
可是,“我”不一样,“我”那么想画出来,那么想涂出好看的颜色。于是,“我”要想方设法,弄到颜料。然而,“我那时候不知怎地性格胆小,没有央求爸爸、妈妈给买的勇气。”众所周知,有岛武郎的父亲有岛武是萨摩藩邸家臣,明治维新后曾任大藏省书记官,家庭非常富裕,买一些高级颜料,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我”没有向父母说明,也就是说,从正面渠道解决难题的方法就不存在了。作者这么写,是从他成人后的角度出发的,而在当时的状态下,我们认为,少年的“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要父母去买的问题。因为当“我”画不出那种颜色的时候,“我”立即想到了“我”的同学吉姆,而不是自己的长辈,吉姆有西洋水彩,“他的水彩是上等的外国货。十二种水彩像小墨棒似地被压成四方形,在轻便的小木盒里排成两行,无论哪种都很美丽。特别是蓝色和浅红色,更是美得惊人。即便是吉姆蹩脚的画,只要涂上那种水彩,也会漂亮许多似的。”从那时起,“我”就想得到吉姆的水彩棒。
想啊想啊,怎么也忍耐不住。每天只是闷在心里想着水彩的事。终于在一个秋日的中午,和老师、同学一起吃过便当(指当时日本学校的学生自己从家里带的自备午餐,大概都是白米加一点菜)后,当“我”想那水彩想到心口发疼的时候,就独自一人走进教室,经过紧张、矛盾、痛苦、恐惧等种种激烈的思想斗争,在下午上课的预备铃敲响之后,做梦似地把那两根水彩棒揣进了自己的兜里。这一段,作者运用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和对比手法。“天气是冬天来临前的秋季里常有的好天气,晴空万里,仿佛能看透天空的最最深处。我们和老师一起吃午餐盒饭,即便是在吃得最高兴的时候,我的心也总是平静不下来,和那天的天气截然相反,心绪黯然。”对于小学生来说,午饭时间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光了,可以身心放松,可以吃美食、侃大山等等,可是“我”却因为心怀鬼胎,始终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在看到吉姆笑着和别人说话时,也觉得是在嘲笑自己,在说:“你们看,那个日本人肯定想要偷我的水彩。”独自在教室时的感受写得也很形象逼真:“我感到脸在发烧,不由得把头扭向一边,可是又忍不住马上斜眼去看吉姆的课桌,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痛苦极了。虽然一动不动地坐着,却像在梦里被鬼怪追赶一样惊慌失措。”就是在这样紧张、恐惧的情况下,“我”偷来了自己“心仪”的东西。
这就是“爱”的魔力。按一般道理来讲,“我”那么胆小,连买画画颜料这么正当、平常的小事,都没有向父母要求的勇气,竟然独自一人在灰暗的教室里,在脸发烧、心乱跳的情况下,偷走同学的东西。这不能不说“爱”的魔力惊人。这里对颜料的“爱”,是出自本能的欲求,与其说是爱,是对东西的深挚感情,倒不如说是欲望,是对自己认为美好东西的迷恋和占有欲,是对某种事物的贪恋和偏爱。这种爱,是偏执的,无规则的,若任其泛滥,定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老师对学生的爱是美好的爱
其实,这则故事重点描写的是老师对学生的爱。年轻美丽的女教师,在“我”万分沮丧地被其他同学作为窃贼连拉带拽地带到办公室的时候,她虽然有些惊讶,有些不悦,但却很平静地让其他同学都回去后,才轻轻地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紧紧地抱住我的肩膀,小声地问:“水彩已经还他了吗?”等“我”使劲点头后,她又轻轻问:“你认识到你做的事不对吗?”这一句话使“我”再也忍不住了,作者写道:“尽管我使劲儿地、使劲儿地咬住哆嗦得无法控制的嘴唇,但还是哭出了声,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当时我真想就那样死在老师的怀里。”
对于做错事情感到悲伤、孤独、极其后悔的“我”,对于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的“我”,老师却是平静地让其他同学回去,很好地维护了“我”的自尊,保存了“我”的颜面。老师更没有严厉的批评,呆板的说教,也没有恫吓与惩罚,却紧紧地抱着“我”,轻轻地和“我”谈话。这么善意、这么爱心的处理方法令人赞叹、使人佩服。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理技巧”,只是出于老师对学生的爱,发自内心的喜爱和爱护,就那么自然地做了。后来,老师让“我”呆在她的办公室里,还摘串葡萄给“我”吃,她就去教室上课了,当“我”迷迷糊糊睡着被她晃醒时,她交代说:明天一定要来上课,否则她会难过的。就这样让“我”回家了。
第二天,“我”万般无奈、疑虑重重地来到学校,却是出乎意外,首先是吉姆主动、亲热地把“我”拉到老师的办公室,接着老师笑眯眯地说吉姆已经原谅了我,以后还要做好朋友,并且又从窗口探出身体,摘了一串葡萄,从中剪断分给“我”和吉姆。故事没有讲吉姆为什么可以把一切都当作没有发生过一样,还高高兴兴地牵着“我”的手,主动示好。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应该是老师找到吉姆,谈了话,做了工作吧。吉姆被偷了东西,还能原谅对方,主动和对方修好,需要多大的度量、多高的情操。这对吉姆来说,也是一种修养的提高和进步吧。主人公“我”呢,从那以后,“我变成一个比以前稍好一点的孩子,好像也不那么忸怩羞怯了。”
老师的作用多么厉害,不声不响地、四两拨千斤似的委婉处理,就把一件坏事变成了好事,而且使两个孩子都有了很多的进步。作品还写了“我”对老师的留恋。“尽管如此,我最喜欢的那位好老师去哪儿了呢。我虽然知道不可能再遇见她了,可是,即便是现在我也在想,老师如果还在身边的话该有多好啊!一到秋天,一串串紫色的葡萄又挂上了美丽的白霜,但是,我却无论在哪里再也没有见到过托着葡萄的、大理石般的洁白而美丽的手了。”老师美丽的手给少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这双手轻轻地抱过少年,为少年摘过葡萄,更因为手的主人——老师充满真情爱意的巧妙的处理方法,让“我”铭刻在心,永生不能忘怀。
老师对学生的爱就如家长给孩子的爱一样,给予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师只有真心付出爱,并且用较为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才可以启迪学生的心灵,唤醒学生的智慧,使师生之间产生情感共鸣。这样,学生才会从内心深处对教师产生亲近感和依恋感,“亲其师、信其师”进而“乐其师”,才会把对教师的爱迁移到对教师的尊重,接受教师的教育。
有岛武郎谈到自己的创作原因时曾经说过:“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第二,我因为爱着,所以创作……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2]作家把自己创作动机的50%归结为爱,他在实际创作中也践行了这一点,他的许多作品都饱含着暖暖的爱意。《一串葡萄》描写的主人公“我”对画画的热爱,老师对于学生的爱,都是爱的体现。既然是爱就会产生魔力,就会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我们要尽可能发挥爱的正能量,避免她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有岛武郎.蔟ふきのぶどう[M].東京:ポプラ社,1990:4-21.
[2]小川利康,王惠敏.关于汉译有岛武郎的《四件事》——从《现代日本小说集》所载译文谈起[J].鲁迅研究月刊,1993(8):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