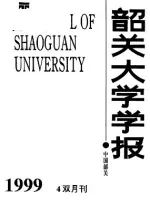试析《追忆似水年华》的独特时空结构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处,安徽 合肥231635)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给出版商的信中称,《追忆似水年华》是“一本完全不像传统小说的书”[1]223。因为,他不愿意像传统的小说家一样用整部小说叙述一个故事,表现一个主题,他要发掘的是他记忆深处最细微、最真实的“矿脉”,他需要表现众多主题和人生中的各类故事:追忆逝去的岁月,找寻失落的时间;追忆生命中的欢乐和痛苦。叙述者在永不停息的追忆同时,“事物、地方、岁月,一切都在他周围的黑暗中盘旋”[1]227,时间和空间在抑扬的节奏中,在充满诗意的韵律中,一一呈现在眼前。
一
《追忆似水年华》作为回忆录式的小说,叙述者总是处于叙事的焦点,叙述者既是回忆的起点,也是回忆的终结。风景、场景、环境等空间因素也都围绕叙述者而展开。这样,叙述者呈现出的空间就不仅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而且还能表现其丰富的精神世界。因此,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空间既是表现人物活动的场所,即结构空间;也是叙述者表达思想的容器,即主题化空间。
一般而言,结构空间在小说中只为人物提供活动场所和背景,它是故事的附属物。这种空间形态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俯拾皆是:大到一个城镇,像贡布雷、巴尔贝克、巴黎等,小到一个舞会会场、一个房间,只是作者对其描述详略不同而已。“这样一个容积之内,一个详略程度不等的描绘将产生那一空间具象和抽象的不同画面”[2]。
叙述者对贡布雷的描写,详尽、细致,如诗如画。高高的教堂,四周的原野,市镇上鳞次栉比的房子,古老的城墙和布局整齐的街道在视角不断转换中被显现出来。这里还有从附近田野里传来的自然气息,有早晨的清闲,宁静而温馨。“乍暖还寒时节的阳光,扑到炉火前来取暖”则充满着诗情、诗趣。而叙述者第一次到巴尔贝克时,对这里的描写就粗略得多,“这里,一列有轨电车,一家咖啡馆,广场上来往的人群,贴现银行分店……”[3]370留给我们的只有感观印象。
普鲁斯特不仅注意空间的详略描写,同时还通过空间的重复和空间的变化来揭示空间的关系。小说中的“两条路”,即斯万家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贯穿了整部小说,它们反复地出现在小说的不同章节中。不仅如此,在叙述者的眼中,原先无论是在实际的空间距离,还是精神层面上几乎相距甚远的“两边”,到最后距离彻底销蚀了。这样,空间不仅具有结构意义,而且还被赋予精神内涵。对维尔迪兰家的沙龙和盖尔芒行家的沙龙描写也是如此。
毕竟结构空间只能为人物活动提供广阔的舞台,但艺术不是展示,艺术是寻找真正的自我。而从记忆深处显示的风景、空间一旦进入小说中,它们便超越了单纯的结构形态,它们往往成为个人意志和自我的转喻或暗喻的形式,空间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这一点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极其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用微型舞台,窄小的房间和拥挤的住所表现巨大”[4]的空间,而普鲁斯特则以“卧室”、“旅馆的房间”和“客厅”来表现人物的情感和自我。贡布雷黑暗包裹着的卧室是叙述者“百结愁肠的一个痛点”;在巴尔贝克的旅馆里,塞满了器物,“我向他们投去戒备的眼光,它们也报我以戒备的眼光”[3]402,在盖尔芒特府邸,“普鲁斯特的所有人物都集中在同一大厅里”[5]96。它们或者表现人的孤立、无助;或者表现人对异己空间的排斥;或者表现空间对人生存在的限制。作者正是借助于这些空间表现人的精神状态。
二
普鲁斯特将小说定名为《追忆似水年华》,其主旨就在于强调时间的失落和追寻逝去的时间,所以,贝尔特认为,时间在普鲁斯特这里是“毁灭与拯救的双头怪兽”[5]8。
时间的毁灭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它“川流不息,永不回头”,时光总是在日起日落中,在寒来暑去的季节中悄然离去,另一方面则由于人在琐碎的事务中,在毫无意义的生活中消耗着时间。作者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和对社会的观察中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注定是痛苦的、孤独的,更令人感伤的是,在时间的洪流中,人将会衰老,也会死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开始了痛苦而艰难的回忆历程。
当回忆的闸门一打开,首先浮现出的是他童年在贡布雷的日子,它开启了小说的序曲,同时也拉开了人生的序幕。随着斯万的一次又一次拜访的铃声,“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母亲吻别的孤独的黑夜。孤独、无爱的生活是他生活的起点。
叙述者步入成年以后,对爱情充满着期待。他结识了斯万的女儿——希尔贝特,这场爱情对马塞尔来说虽然短暂,但却给他造成了无限的痛苦。而与阿贝尔蒂丝的爱情始于巴尔贝克沙滩的偶遇,在第一印象中,他感到阿尔贝蒂丝是个热情且贞洁的女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阿尔贝蒂丝好撒谎,并且是个性变态者,失望之余,他将她囚禁在自己的家里。
斯万、圣卢等人遭遇的爱情大致也如此,时间毁灭着他们的爱情。
《追忆似水年华》中另一个主题是:我们在时间中,随时都会死去。盖尔芒特家的聚会就是死神狂欢的晚会,时间的印迹刻在每个人的脸上。夏吕斯是个“两眼发呆、驼背”的老人;莱杜维尔公爵是大病初愈,显得老态;曾是充满朝气的外交官夏特勒罗公爵只残存有一点过去的影子;阿让库尔先生似乎是个老叫花子;而马塞尔早年相识的一个少妇,现在已白发苍苍,拱肩缩背成了凶狠的小老太婆。还有他们曾经相识的人,德·布雷奥、德·穆西、斯万等等一个又一个地仙逝,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会光顾他们,他们都隐隐地感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这种悲伤一般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作者一方面要表现韶光易逝,另一方面则想让时光永驻。而真正能唤回过去的是追忆,它将过去像地毯一样铺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细致地品味它、审视它。自主回忆“作为一种起唤醒作用的工具毫无价值,它所提供的影像与真实相去甚远。”[5]10这是由于我们受到了世俗的影响,再则,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理性的推理往往为生活幻想所迷惑,难以再现生活中的真。只有无意识回忆,它不受理性的控制,往往在某个“瞬间”产生,并向过去无限延伸,它是时间的绵延。为了表现非自主回忆是一种瞬间,而且是爆炸性的,作者在小说中刻意多次写到这样的时刻。第一次是在吃玛德莱纳小甜饼时,当马赛尔喝到第三口时,“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而这种感知在第七部《重现的时光》中达到高潮,马塞尔走在盖尔芒特高高低低的石板路上的感觉,餐巾纸的僵硬感、汤匙碰撞盘子的声音、水管里的流水声,即刻的感悟与遥远过去的感受,也可以说躯壳中的各种感觉同过去同类感觉联系起来,此时,他品尝到了瞬间感觉的生命力;它与时间无关,与现实成败无关,它体现的是事物的本质。整个过去的事件、人物在无意识回忆中浮现了出来。
“人生中有些出神入化的时刻,当前偶然获得的感觉使过去重现,于是我们快乐地感到自身存在的持久性;不过一个人一生罕遇这种时刻。”[3]8那么,如何将这种个人感受化成普遍的存在,“把它变换成一种精神的等同物……而这种在我看来是独一无二的方法,除了制作一部艺术作品外还能是什么?”[6]只有在艺术中,艺术家才能听从其本能,艺术是真实的学校和真正的最后审判。普鲁斯特认识到,作家的主要职责就是发现关系并将各种关系表现出来。
普鲁斯特首先赋予无意识回忆以超时间性,也即时间自由地被扩展或浓缩。有的瞬间似乎变成了永恒,如贡布雷,一个没有吻别的黑夜,在叙述者心中衍化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情感“战争”;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府上短短的一场聚会就出现了好几个时期的时间。然而有的时间又急如旋风,转瞬即逝,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被淹没在小说幽暗的底色中,几乎是被一带而过。人物的衰老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作品表现人物的衰老却很突然,第一次出现还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人,下次就变成了一个老人。作者既可将人物放在显微镜下细细地解析,也可以将人物无尽地放大,只给人一个粗略的轮廓,这正是时间在艺术中所表现出的神奇。
其次是运用对位法,这种结构方式是将相关内容并置,从而使小说结构和谐、整一,具有同时性。“两条路”是最具时间跨度的对位结构,斯万家那边“通向巴黎的犹太资产阶级世界”[5]120,盖尔芒特家那边 “通向巴黎,通向时髦的圣日尔曼区沙龙”[5]121。“两个‘两边’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和不同的社会生存视野。”[5]127从开始到结束,这两条线索都平行地出现在小说之中。
对位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同一事件、同一感觉放到小说的不同部分,人物彼此相似、相互重复,结果是叙述时间以重复作为节奏,而重复似乎消除了时间的进展,从而让时间获得了另一种生命力。
第三是结构上的呼应。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和第七部《重现的时光》除了两者所涉及的主题相似外,并且两者的结果也雷同。在第一部中涉及两种回忆:半睡半醒的状态和吃玛德莱纳小甜饼的感觉。第七部这种经验再次出现了。除结构的整体对应外,小说中的人物也相互呼应,斯万和马塞尔是对应的,斯万的爱情是马塞尔爱情的预演。
此外,普鲁斯特擅长用冗长的复合句,以“最细微的色调差异去表达个体对周围世界的心理知觉过程”[5]115。并且复合句的从属句“不仅把某一瞬间的内心体验,而且同时把环境、景色、体验发生于其中的情势统统纳入一个完整的句子”[5]50。
在时间的洪流里,普鲁斯特发现了艺术家自己:“我懂得了死亡、爱情和生命的意义,我明白了精神欢乐和痛苦的价值。”[5]127作者从厚重岁月中发掘的时间被艺术化了,这样也就找到了“想像中的时间”,时间和艺术一道成了永恒。
三
1913年拒绝接受《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的出版商,曾抱怨作者竟然花30页的篇幅来描写入睡前的情况,而这正是《追忆似水年华》的独特之处,普鲁斯特把我们带入的不是“单一的时间、地点和叙述中,而是被引入一个复合在一起的情境”。入睡前的辗转反侧是回忆的 “温床”,它“孵化并催生”了回忆;同时回忆将无限延展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联系起来,“这种记忆并非仅仅关系到我居于何处,而且涉及我曾生活于何处,以及我可能生活于何处。”[5]128所以说,《追忆似水年华》中时空是互融的:时间是空间里的时间,空间又是时间里的空间。
毋庸置疑,《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小说,同时也是关于空间的典范作品。而时间空间化,也即柏格森所称的“空间时间”,就是“用空间的固定概念来说明时间”[5]128。
就《追忆似水年华》作品本身而言,时间表现为两种时态:现在时与过去时。回忆将这两者贯串起来,特别是无意识回忆,由特定空间里的感知而开始,然后,回忆将叙述者带回遥远的过去,最后再回到现实中,简单的模式应该是:现在——过去——现在。不由自主的回忆使世界陌生,它将现实的房子和过去经验里的各类房间聚合到一起。在记忆的运动中,记忆有条不紊,“通常我并不急于入睡,一夜之中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追忆往昔生活,追忆我们在贡布雷的外祖父母家,在巴尔贝克、在巴黎、在董西埃尔、在威尼斯以及其他地方度过的岁月。”[3]6那么过去在回忆中又是如何获得独立的时间意义的呢?那就是事件之间的联系。如果舍弃了事件间的联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细节的陈述了,时间难以复活。这也是符合记忆特征的。如对斯万之恋的描写,将斯万对奥黛特的追求和迷恋细致地刻画出来,这样再现的不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事件,而是再现了特定时段的历史。这样在一个场景里,在一个个事件中,事件被突现出来了。
空间,在小说中表现为场景、环境等,它是人物活动和事件产生的场所和背景,换句话说,人物和事件是空间存在的灵魂和支柱,离开人物和事件空间的存在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而 《追忆似水年华》中,人物的时间化是极明显的。作者一方面利用人物的外貌将人物印上时间的印记,如枯干的躯体、失去光泽的面容、小心翼翼的步履等等,另一方面则利用人物的语言来表示人物的变化,如弗朗索瓦完全改变了她的外省腔调。
普鲁斯特虽然竭力将时间内在化,但对事件的描写仍然赋予了时间化的特征。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人物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来表现其时间性,因为时间改变了,人的观点也会随之改变。如德雷福斯事件在小说中通过盖尔芒特先生几次议论来表现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普鲁斯特在特定的时间框架中,以细微丰富的心理感受和深刻的辨析力,追忆着一个个事件,复活了一个个人物,从而构成了心理时间中一个漫长、辉煌的流动画廊,时间在空间里复活了。
[1]米歇尔·莱蒙.法国现代小说史[M].徐知免,杨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8.
[3]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上册[M].李恒基,桂裕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4.
[4]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M].陈永国,傅景川,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423.
[5]贝克特.普鲁斯特论[M].沈睿,黄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译本下册[M].周克希,徐和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