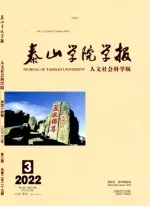2012年鲁迅作品研究中的几个亮点
崔云伟,刘增人
(1.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青岛大学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在历年来的鲁迅研究中,有关鲁迅作品的研究总是异彩纷呈,创意不断。2012年度的鲁迅研究自不例外。笔者在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基础上,特意从中概括、梳理出有关鲁迅作品研究的几个亮点。现述评如下,以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一、《呐喊》、《彷徨》研究
与《呐喊》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狂人日记》、《孔乙己》。
从《狂人日记》发表之初到上世纪90年代,鲁迅研究界围绕“狂人”是否真的发狂的争论从未间断。郜元宝[1]将之分为四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即:1、“不狂的战士”;2、“真狂的战士”;3、“作者寄寓其思想的普通狂人”;4、“作者寄寓其思想的半狂半醒者”。论者在显示鲁研界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风尚,重温50-90年代中国学者的读书之细、态度之诚、用功之深之后,继而将这一论争提高到“防破绽”与“忘破绽”的关系中来,认为第一种说法最接近“忘破绽”的境界,其他三种说法取的则是“防破绽”的态度。对《狂人日记》来说,中国学者数十年来“防破绽”的努力,其意义即在于帮助读者切实领略到了鲁迅(也是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的设想之奇崛与挥写之浑然。
作为《狂人日记》中的核心意象,“吃人”是如何生成的?李冬木[2]认为,“吃人”这一意象,是在日本明治时代相关讨论的“知识”背景下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明治时代关于“吃人”的言说为《狂人日记》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母题”。具体说来,鲁迅之所以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并继而创作出《狂人日记》,可能与他所“偶阅”到的日本明治时期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这部书大有关系。在芳贺的这部书中,提到了大量关于“支那食人“的记录,其中取自《资治通鉴》的有3例。如此一来,在关于《狂人日记》这篇作品的“知识”层面上,我们已经大抵可以领略到“周树人”成长为“鲁迅”的路径,或许还可将之视为“近代”在“鲁迅”这一个体身上发生重构的又一例证。
该文运用日本学者所惯用之实证法,不惜花费巨大力气,征引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其梳理之精深、之清晰、之透彻,都是很令人感佩的。这对当前一味凌空蹈虚、惟宏大议论是崇的浮躁文风未尝不是一种有力的纠偏。但该文在论述逻辑上亦有可商之处。最为关键一点在于,在鲁迅的文本中没有留下有关芳贺矢一的记载。如果论者就此打住,那么前面所进行的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要白费。这当然不是论者所想看到的。为了能够实现芳贺与鲁迅的对接,论者只能采取这样的逻辑。他说,不提不记不等于没读没受影响,那些“片言中语”少提或者不提的,可能反倒离鲁迅更近。让我们姑且先同意这种说法。接下来,下文在提到《通鉴》和鲁迅的关系时,却又有意对之进行遮蔽,说是在鲁迅的藏书目录中未见《通鉴》,《全集》中提到《通鉴》都是作为书名,没有涉及其中任何一个具体的“食人”记载。如果按照前面姑且同意的观点,鲁迅不提不记或少提少记《通鉴》也是并不等于鲁迅没读没受影响的,《通鉴》反倒可能离鲁迅更近。而在实际上,《通鉴》在中国名气很大,是一般文人都知道且会常用的,鲁迅看过并从中取典,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么,论者在这里为什么有意遮蔽《通鉴》呢?其原因即在于论者的目的是要引出并突出芳贺的《国民性十论》,以证明其对鲁迅《狂人日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样一来,同是鲁迅少提或不提的书,论者一方面断定《通鉴》离鲁迅远,而另一方面却又断定《国民性十论》离鲁迅近。论者的逻辑在这里岂不是有点不通?
《孔乙己》是鲁迅最喜欢的一部短篇小说。李宗刚[3]着眼于《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认为《孔乙己》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大陆及海外学者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该文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鲁迅<故乡>阅读史》在写作方法上极为相似,都采取了以小见大的方法,都力图从微观出发并进而把握宏观。通观全篇,论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它同时亦为考察鲁迅其他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分析。任湘云[4]则从金钱影响和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对《孔乙己》所描述的生存世界和孔乙己的悲剧意义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金钱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影响、制约着孔乙己所在世界人们的精神、身体活动甚至整个生活方式。同时,科举制度、长衫人物、短衣帮、酒店掌柜和小伙计等从不同角度形成无所不在的否定力量,不断粉碎孔乙己残存的生存梦想,使孔乙己生存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麻木、冷漠、无望的世界。在今天这样一个金钱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里,《孔乙己》又得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关联,这不但使该文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义,而且也再一次地证明了鲁迅小说的强大和永恒。
与《彷徨》研究有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在酒楼上》、《孤独者》、《肥皂》、《祝福》。
《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均为鲁迅描写现代知识分子的精彩篇章。汪卫东[5]将这两篇小说视为鲁迅“梦魇”中的姊妹篇,认为《在酒楼上》是一篇具有“最后”气息的小说。在这篇小说中,母亲成为吕纬甫最后行动的意义来源。这样,一个问题随之而出:如果这个“母亲”不存在了,他的结局会怎样?这一问题在一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孤独者》中有了答案。这篇小说以死亡开始,也以死亡结束,整篇写的就是主人公魏连殳的死亡过程。这一死亡过程正是从魏连殳的祖母——“母亲”的死亡开始启动的。这样一来,《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一个写失败之人的最后状态,一个写的就是他的崩溃过程,两篇小说连起来读,在逻辑和文脉上,则确实堪称姊妹篇。论者继而认为,这两篇小说写作之时,正值鲁迅处于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绝望”之时。鲁迅正是通过上述两篇小说,一方面对自我人生结局作了最悲观的预测,另一方面却又从旧我中诞生出一个新我,从而穿越了这“第二次绝望”的。
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认为《在酒楼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对此,齐宏伟[6]认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文本内容,又不符合鲁迅的思想实质。这篇小说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鲁迅刻意安排的观念冲突和人格类型冲突。也就是说,《在酒楼上》的文本内在张力乃鲁迅有意为之。其深意在于:鲁迅在小说中以西方线性史观批评中国传统循环史观,又以斗争型人格批判妥协型人格,在中西观念对比中,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批判及对新史观并新人格类型的弘扬。鲁迅这些观念受尼采等影响,有其重要价值。
“肥皂”是《肥皂》中的突出意象,以往论者多所忽略,吕周聚[7]则对其多重意蕴进行了细致解读。他认为,《肥皂》是一部用象征主义手法写成的作品。肥皂作为西方现代消费用品进入中国后,不仅带来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且带来了中国人审美观念、消费观念和性观念的变化。鲁迅通过一块小小的肥皂,设计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展示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复杂的心理世界。对四铭而言,肥皂就是性的象征,一块肥皂揭示出四铭的内心欲望与其外在行为之间的矛盾。对四铭太太而言,肥皂亦是爱与美的象征,一块肥皂唤起了她的爱美之心,也唤醒了她内心的性意识。该文构思独特,阐述透彻,发前人所未发,为近年来《肥皂》研究中的特出之作。
在一场“没有真正的被告和凶手,因而全部是被告和凶手”的鲁镇谋杀案中,祥林嫂是如何被吃掉的。在彭小燕[8]看来,祥林嫂是在一片“虚无—混沌”中“被吃掉”的。这一“虚无”世界有着四个基本的构成件:“我”、鲁四老爷、鲁镇人、祥林嫂。《祝福》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细腻、复杂的虚无世界:“我”的暧昧犹疑、消极自供、无为无奈;鲁四老爷们的抱残守缺、迷信装佯、无所作为;鲁镇人则在“空寂—无聊”的惘惘推动中愉悦地“畅饮”着祥林嫂的血泪人生;祥林嫂则被鲁镇的诸多合力逼进了“绝望—无靠”的死角,死于鲁镇这一“混沌—虚无”的人间世。《祝福》之“虚无四重奏”,“我”等三重都让人扼腕叹憾,唯独在祥林嫂这里,是如此地令人唏嘘落泪:遭遇绝望、吞咽虚空都不是她的错,而是整个鲁镇世界那貌似很有文化、无懈可击的无端逼压。这样的鲁镇是必须予以改变的,而这也正是鲁迅的期待:期待着全体鲁镇人能够“有所真为”“成其为人”。
从整体上对《呐喊》、《彷徨》作出精彩解读的是王晓初[9]。他认为,在《呐喊》、《彷徨》中,“鲁镇”、“未庄”、“S城”是以鲁迅的故乡绍兴为原型建构起来的一个充满浓郁的浙东水乡色彩的文学世界。鲁迅一方面揭示了闰土、阿Q、祥林嫂等越地底层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压迫下形成的精神病态,另一方面也力图去发掘他们追求解放的精神力量,从而开启与贯通了我们民族走向解放与新生的可能。由狂人、疯子、魏连殳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狂人”形象谱系凸显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谱系的镜像。他们争取个性自由与解放的冲动延续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同时又贯通了与底层民众的精神联系。他们致力于整个民族的觉醒与解放的愿望使他们在绝望中抗战而更加坚韧顽强。
二、《故事新编》研究
李国华的《行动如何可能》[10]探讨了鲁迅《故事新编》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文章认为,在这个关于“行动如何可能”的构建中,鲁迅始终是以生存、温饱、发展作为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的。因此,鲁迅为《故事新编》构建的主体生成逻辑即是,在普遍的生存、温饱、发展问题语境下,行动因为相互主体性意识、阶级论意识的存在及名实之辨、命名与历史书写、效验与位置的考量等方面的思虑,而变得可能。该文认识到“行动如何可能”成为后期鲁迅所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很有见地的,按诸《故事新编》文本实际,鲁迅确也在其中深入探讨了这一命题。但是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该文为了印证某项理论,却颇有牵强之处。如论者为了论证在《故事新编》中四类行动主体均缺乏所谓“相互主体性”时,这样论述《铸剑》,说《铸剑》中宴之敖者的“复仇即不复仇,不复仇即复仇”;又说复仇时,三个头混战在一起,无从分辨,最后只能合葬,这是“完全混淆了敌我,消解了复仇的价值”。这与笔者阅读这部优秀小说时的感受大相径庭。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铸剑》中的宴之敖者并非《起死》中的庄子。宴之敖者是一个真正的侠客,他很懂得人我之分、敌我之辨,要不他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复仇的意志十分坚决,恰恰因为他的复仇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人我之分、敌我之辨。而《起死》中的庄子则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持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圆滑观点的。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显然的。二,这三个头混在一起,并非是混淆了敌我,消解了复仇的价值,反而正是复仇的升华,复仇的意义及价值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我们读到这一段描写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愤怒和痛苦,所获得的只是一种狂欢的快感(莫言语,参见下文莫言谈《铸剑》)。这愤怒和痛苦的消失,并不是对于复仇的消解,而正是对于复仇的超越。消解和超越,一贬抑,一提升,这两者的含义是根本不同的。
徐鉞的《新编与新诠》[11]则是对《故事新编》的结构性分析。该文认为,鲁迅在《补天》、《奔月》、《铸剑》的创作中,更多地体现了对于“历史演义”文体及“现代性油滑”成分的探索自觉,而《理水》、《采薇》等后五篇的创作则主要是利用对这种叙述形态的掌握而集中做出的纯熟表现,其在“价值新诠”上的阐释意义已经大于其文本上的形式结构意义。论者具体展现了《故事新编》新编与新诠的演进过程。继之,指出隐藏在新编与新诠背后的是荒诞和绝境,即鲁迅是以八篇新编的故事诠解了否定与质疑的合法,呈示了任何一种“旧”的价值体系被消解、被再诠释的可能的。
莫言在与孙郁的对话中[12],谈到他对鲁迅作品的看法。他说他最喜欢鲁迅的《铸剑》,喜欢它的古怪。他觉得《铸剑》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黑衣人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也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真正的复仇未必是手刃仇敌,而是与仇者同归于尽。当三个头颅煮成一锅汤后,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我们读到这一段描写的时候,所获得的是一种狂欢的快感。这篇小说太丰富了,它所包含的东西,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而且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
《出关》发表后有所谓“自况”说。张钊贻[13]认为,持此说的基本上是“左联”内部一些人,如邱韵铎、徐懋庸等的看法。“自况”说表面上已为鲁迅所否定,但从文本和历史背景的分析,《出关》的确有“自况”的内容,而鲁迅的否定在逻辑上亦非完全彻底。《出关》部分关键的内容反映出鲁迅与“左联”一些人的矛盾,也体现出他对“联合战线”的怀疑。对《出关》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王学谦[14]。
三、《野草》研究
《野草》通过繁复的意象和梦境的营造,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意义世界,蕴含着鲁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哲学。王本朝[15]认为,在修辞风格上,《野草》追求语言的修饰和开掘,时有复沓、缠绕的笔墨,也不乏直白、节俭的语句。在曲里拐弯的表达里,呈现出他对文字的精准、文句的泊漾和虚词的迤逦的敏感和讲究。“然而”是《野草》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系连词。鲁迅对它有着恰当而巧妙的运用,无论是对情感和寓意的表达,还是形成语气节奏的转换与跌宕,都使《野草》多了一份意味深长的气势神韵。对“然而”的使用,有着鲁迅质疑和否定的思维特点,也呈现出鲁迅相反相对、矛盾并置的话语方式,由此,也可见出鲁迅对历史和现实的悖反与乖谬,生命存在的矛盾与紧张的独特感受。
鲁迅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孙玉石[16]认为,鲁迅研究的阐释空间的创新性是无限的,鲁迅学术阐释科学性规范的“度”是有限的。20世纪之后,先后有研究者另辟蹊径,从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视角,对于《野草》中或十余篇或全部的散文诗,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阐释。这种爱情视野的阐释的成果,为我们的思考既要如何打破习惯思维限囿,扩大鲁迅阐释的视野的同时,又如何做到坚持文学阐释方法论的科学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思考空间和进行学术研究方法反思的可能性。
李玉明《论<野草>的基本意识结构》[17]则认为,作为一种基本意识结构形态,《野草》是关于自我的,是自我对自我的究诘、拷问,是对自我的存在状态的探寻,而显现在这种究诘和探寻背后的精神趋向则是某种“抵抗”的行动,即鲁迅的“反抗绝望”。反抗绝望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凸显的是个体的精神自由或自由意志,它追求的是自我的某种超越性存在,是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地位的某种建构。
张洁宇[18]则将《求乞者》与“兄弟失和”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集中探讨了在鲁迅的写作中关于“社会之痛”与“个人之伤”之间的关系。论者认为,《求乞者》一文既是出自私人经验的一个非常隐晦的发泄,同时又是一篇内涵深邃而丰富的散文诗;其中,既有对那些在灰土颓垣中纷纷登场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尖锐批判,也有鲁迅自己以“无所为和沉默”与之对抗的倔强身影。
四、早期文言论文研究
以蒋晖对《科学史教篇》的解读[19]最为精彩。通过考证《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蒋晖引出了鲁迅研究中被忽略的几个问题:一是鲁迅早期思想的形成与英国维多利亚文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那个时期“科玄”论战的关系;二是分析他的历史哲学研究需要注意他对西方科技发展史的批判。该文同时具备重要思想价值和史料价值,体现了论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惊人的学术视野(张洁宇语),是近年来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研究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优异之作。
五、杂文研究
鲁迅文学的诞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事件。汪晖[20]通过对《呐喊·自序》的细读,重新解释了鲁迅文学的动力问题。论者深入分析文本中的修辞、故事及其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说明鲁迅文学的动力不是从绝望出发,而是从反抗绝望出发的。鲁迅的东渡学医,弃医从文,革命后的沉默,《新青年》时期的呐喊,均可以置于“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脉络中给予解释。这一脉络正是鲁迅的宿命。与其说是“回心”,不如说是“忠诚”,解释了鲁迅的那些“不能全忘却的梦”。“希望的文学”、“反抗绝望的文学”与“胜利的哲学”、“乐观的文学”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两组各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文学态度。鲁迅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是通过对于“希望的文学”的否定而确立自身的。这种自我否定正是这一革命世纪最为宝贵的遗产。
安德鲁·琼斯[21]则着意强调了《呐喊·自序》中的“铁屋子”意象。他认为有关“铁屋子”的这段寓言叙事,与两部晚期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两段情节相关。这两部小说分别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和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两部小说都在物质、技术的层面深入探讨了殖民主义式的自然—历史知识散播和新知识生产的制度性渠道。它们提供了全景式的窗口来前瞻充满进步和可能性的新世界,尽管如此获得的图景总是在叙事的扭曲中被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错位蒙上阴影。在这三个文本里,主角沉睡在铁做的密室里的状态,都出现在其进入某种乌托邦境界之前。但这不能保证,经过睡梦的囚禁,那些主角最终能获得自由。
杂文,是鲁迅倾力最多也是最受争议的写作。汪卫东[22]认为,鲁迅杂文之谜,关乎对20世纪中国最有成就的作家的评价,而且牵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入理解。鲁迅不是从既有文学规范出发走向杂文的,于他,文学是一种行动,既是参与国族现代转型的独立精神行动,又是生命意义上个人存在的抉择,这一复杂承担者,最终找到的是杂文。日本时期的“文学自觉”后,鲁迅先后经历了“小说自觉”与“杂文自觉”,“杂文自觉”是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发生于“第二次绝望”后,以《华盖集》为标志。鲁迅以其真诚、原创的杂文创作,冲击着固有的文学规则和秩序,同时带来并确立了新的文学性质素,丰富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学性建构。鲁迅杂文对20世纪中国精神现场的展示及其精神难题的洞察,显现了文学展示精神存在的文学性内核。
1933年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古物南迁”的政策,鲁迅表示过反对吗?符杰祥[23]通过对比鲁迅论及“古物南迁”的四篇文章,最终发现:鲁迅并没有对古物南迁发表专论文字,他所真正关心的也不是古物南迁,而是古物南迁以外的其他两件事情:学生逃难和政府抗日。概言之,鲁迅对古物南迁有所批评,而无意反对。鲁迅批评古物南迁这件事,只是借此和学生逃难的事作比较,来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和高压政策。至于古物本身应该不应该南迁,他并无明确表示反对的意思。
对鲁迅杂文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朱寿桐、陈欣瑶等[24]。
六、诗歌研究
1932年鲁迅作有一首《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杨义[25]认为,从这首《自嘲》诗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自嘲是一种解构性的思维方式,它解构了豪言壮语式或标语口号式的自誉,也解构了金刚怒目式或一泻无余的社会抗议,却将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社会抗议的坚定立场隐藏在游刃有余的曲笔之中,令人感慨多端,也令人回味无穷。这就使得这首《自嘲》诗成为中国历代自嘲诗的压卷之作。从这首《自嘲》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鲁迅的文化血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却又从这片土壤、这个根系中生长出生命坚挺的大树。他的文化哲学的反传统色彩,是属于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的;而文化哲学中对固有血脉的强调,则属于我们这个具有博大精深的文明根基的民族的。思潮与血脉的深度对话,正是鲁迅文化哲学的内在生命脉络。对鲁迅诗歌作精彩解读的还有张洁宇[26]等。
七、翻译研究
20世纪30年代,鲁迅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毁灭》,获得瞿秋白的高度评价。但两人关于小说中核心意思“新的……人”的翻译存在分歧,瞿秋白译作“新的人”,而鲁迅译为“新的人类”。薛羽[27]指出,在这里,鲁迅是带着“中国问题”的“联想”和“设想”,态度微妙地游移于这种“新人”在“目前”出现的可能,并通过把“新的……人类”“搬往将来”的设置,留出了“目前”的未知的斗争空间的。当然,鲁迅最后也认同了瞿秋白的翻译,但毋宁说在他那里,正因为多了这一层“误读”的曲折和执拗,才有中国语境下“新的人类”作为远景,“新人”作为现在空间的“不在场者”,更加需要革命的“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需要“其间的桥梁”了。姜异新[28]则认为,北京时期鲁迅的翻译是与其作为个人体验的“现代性”紧密相联的,鲁迅在北京时期的翻译,尤其是选材方面反映出他通过个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对鲁迅与翻译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任冬梅[29]等。
八、手稿研究
2011年,周楠本在《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中,认为《<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尽管由于其合同性质不好归入鲁迅文稿,但是可以归入鲁迅手稿,因为这是鲁迅的手迹。本年度叶淑穗[30]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仔细审视这件手迹的用笔风格和常用字写法,可以发现它和鲁迅手迹是有很大差异的。论者将六位《新青年》编委的字迹一一进行排查、对照,发现胡适的手迹酷似这页《<新青年>合同书》的手迹。为了证实这种说法,论者搞了一个《<新青年>合同书》手迹对照表,一边是鲁迅的手迹,一边是胡适的手迹,中间是《<新青年>合同书》手迹,三方对照,最终证实此《<新青年>合同书》应为胡适先生所书。至此,这一疑案得以告终。该文令人感佩之处在于:一,敢于大胆质疑,对前人说法进行适时纠正,进一步制止了以讹传讹;二,采用了实证手法,以事实胜于雄辩的力量,使得这一考证再无疑义;三,尽管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此手稿尽管并非鲁迅所为,却系胡适所书,无形中为胡适研究提供了又一则具体可感的史料。
在鲁迅稿本鉴别问题上,朱正曾经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原稿”与“清稿”说,认为有无作者署名和流水页码是辨别鲁迅手稿属性的重要参考。但是,符杰祥[31]认为对于所有鲁迅手稿而言,这两条基本原则却并非完全适用。他发现:鲁迅在上海最后十年的手稿很少有看到作者署名的,能看到作者署名的多是北京到广州时期的手稿。如果把这两个时期分为前期和后期的话,那么前期基本符合“原稿”的条件,后期则基本符合“清稿”的原则。这似乎不合常理,也很耐人寻味。这其中的原因即在于,鲁迅后期的写作环境险恶复杂,不能像前期那样将写作原稿直接寄送报刊,而多是请人抄写副稿寄送报刊发表,原稿则作为底稿用来编集出版。这样一来,鲁迅稿本的诸多疑惑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对鲁迅手稿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姚锡佩[32]等。
九、鲁迅作品整体研究(各种视角和层面)
(一)语言学视角
郜元宝[33]认为,语言问题在鲁迅那里乃是由无数语言细节组成的基本方法论。鲁迅思想学术的自觉是与他的语言的自觉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学习鲁迅的文体,不仅有助于现代文学的道路的确立,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化的学术语言。在今天看来,鲁迅的语言也许并不规范,却比所谓规范的现代汉语或许更有生命力。今天所谓“规范”的汉语,已经既不能容纳我们的先辈像鲁迅的现代汉语,也无力容纳西方或日本的语言。伟大作家如鲁迅的语言艺术是建立在自觉的语言疏离和语言投入相互交织的语言意识上的。他们对包括母语在内的一切语言的热爱都不只是单纯的沉湎和敬谨接受,而是灵魂的安逸和不安的纠缠在语言上的呈现。什么时候回避了这种矛盾和挣扎,委身于某种现成的语言“规范”,那么语言的探索和创造也就停止了。
徐桂梅[34]细致解析了鲁迅小说语言中的“日语元素”,她从鲁迅35篇白话小说中选出147句含有“日语元素”的句子,将其分成七类:(一)和制汉字词;(二)鲁迅自制汉日混血词;(三)汉日同形词;(四)汉日镜像词;(五)汉日同素词;(六)日化语法;(七)有日语特征的修辞等。在每一类中,论者都举出例证,详细分解,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继而认为,“日语元素”以各种可能的形态渗入了鲁迅小说的词汇、语法和修辞中,不仅大大丰富了鲁迅文学语言的词汇量和表现方法,也大大提高了表达的自由度和张力。鲁迅大胆引入“日语元素”,用新词语、新语法、新的修辞手段,不但营造了一个个陌生新鲜的文本,而且也让新鲜的域外之风长驱直入现代汉语语境。
(二)中学语文教学视角
钱理群[35]在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时认为,鲁迅不是一般的文学家,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民族思想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作品的语言具有装饰性、音乐性和游戏性三大特性,正是鲁迅把我们民族母语的汉语的特点和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鲁迅作品教学的意义,即在于给中学生和中学教育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支撑。它对中学生的一生成长所产生的“精神垫底”的特殊作用是别的其他作品的教学所不能替代的。教好鲁迅作品,则需要做到:第一,要寻找鲁迅与学生之间的生命契合点、连接点,构建精神通道;第二,要以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走近鲁迅;第三,鲁迅作品教学要删繁就简,要有所讲,有所不讲,不必“讲深讲透”;第四,要重视一个新的教育课题:如何运用网络新技术进行包括鲁迅作品教学在内的语文教育。
[1]郜元宝.“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围绕《狂人日记》的一段学术史回顾[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2]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J].文学评论,2012,(1).
[3]李宗刚.《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J].东岳论丛,2012,(4).
[4]任湘云.孔乙己的金钱、身体与身份[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1).
[5]汪卫东.“梦魇”中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与《孤独者》[J].鲁迅研究月刊,2012,(6).
[6]齐宏伟.《在酒楼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矛盾吗[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3).
[7]吕周聚.“肥皂”的多重象征意蕴——鲁迅《肥皂》的重新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2012,(12).
[8]彭小燕.“虚无”四重奏——重读《祝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
[9]王晓初.鲁镇、未庄与S城:鲁迅小说建构的文学世界——从越文化视野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J].孝感学院学报,2012,(1).
[10]李国华.行动如何可能——鲁迅《故事新编》主体构建的逻辑及其方法[J].鲁迅研究月刊,2012,(9).
[11]徐鉞.新编与新诠——《故事新编》的结构性分析[J].鲁迅研究月刊,2012,(9).
[12]姜异新.莫言孙郁对话录[J].鲁迅研究月刊,2012,(10).
[13]张钊贻.《出关》的现实寓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
[14]王学谦.鲁迅为何改写老子和孔子——从《出关》看鲁迅晚年心态的复杂性[J].文艺争鸣,2012,(5).
[15]王本朝.“然而”与 <野草 >的话语方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2,(1).
[16]孙玉石.鲁迅阐释的空间与限度——以《野草》为例谈鲁迅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2012,(1).
[17]李玉明.论《野草》的基本意识结构[J].东岳论丛,2012,(2).论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J].齐鲁学刊,2012,(1).
[18]张洁宇.鲁迅《野草·求乞者》考论[J].鲁迅研究月刊,2012,(9).
[19]蒋晖.维多利亚时代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诞生:重考鲁迅《科学史教篇》的资料来源、结构和历史哲学的命题[J].西北大学学报,2012,(1).
[20]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21]安德鲁·琼斯.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J].王敦,李之华,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2).
[22]汪卫东.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J].文学评论,2012,(5).
[23]符杰祥.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J].鲁迅研究月刊,2012,(2).
[24]朱寿桐.鲁迅的文学身份、批评文体写作与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前景[J].鲁迅研究月刊,2012,(8).陈欣瑶.舱、街道、客厅——鲁迅杂文中的“中介空间”[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25]杨义.鲁迅的文化哲学与文化血脉[J].鲁迅研究月刊,2012,(10).
[26]张洁宇.一个严肃而深刻的“玩笑”——重读《我的失恋》兼论鲁迅的新诗观[J].鲁迅研究月刊,2012,(11).
[27]薛羽.新しい人间:“新的人”或“新的人类”——鲁迅与瞿秋白关于《毁灭》的翻译分歧[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28]姜异新.翻译自主与现代性自觉——以北京时期的鲁迅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2012,(3).
[29]任冬梅.论鲁迅的科幻小说翻译[J].现代中文学刊,2012,(6).
[30]叶淑穗.对《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一文的质疑[J].鲁迅研究月刊,2012,(4).
[31]符杰祥.鲁迅稿本问题辨考——从《为了忘却的记念》说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7).
[32]姚锡佩.敬阅台静农藏《娜拉走后怎样》手稿长卷[J].鲁迅研究月刊,2012,(11).
[33]郜元宝.鲁迅与当代中国的语言问题[J].南方文坛,2012,(6).
[34]徐桂梅.鲁迅小说语言中的“日语元素”解析[J].鲁迅研究月刊,2012,(2).
[35]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J].鲁迅研究月刊,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