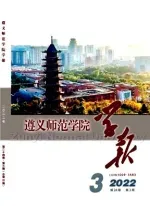自动写作:从布勒东到残雪
梁 波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00020)
正如著作醒目的名称一样,残雪在《残雪文学观》中直截了当地阐发了她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理想。因为书中多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访谈言论,难免予人以重复唠杂之感,不过其核心要义却不难把握:残雪在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一种她认为最高层次的写作方式——“自动写作”。虽然不知是刻意回避还是无意遗漏,残雪的这部著作中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过布勒东的名字,然而只要看到“自动写作”这个词语,我们无疑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位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巨子。那么残雪的自动写作与20世纪初布勒东倡行的自动写作之间有无联系,并存在怎样的异同呢?
一
要探求布勒东和残雪自动写作的由来,二者的精神资源是首先需要关切的问题。自动写作其实并不新鲜,在超现实主义出现前一百年左右,法国诗人内瓦尔就声称自己是在“超级自然主义”的自动写作状态中进行创作,西方的唯灵论者和东方的巫婆,也用同自动写作类似的办法传达神喻。布勒东坦承,“自动作用承之于巫师”[1]P51。真正使自动写作得以闪耀光芒的还是超现实主义。在布勒东那里自动写作最早是作为超现实主义本身出现的。1968年,曾经的超现实主义干将路易·阿拉贡回忆说,“人们所称的超现实主义实际上开始于1919年春末。我在1919年6月从部队回来后,布勒东来让我看苏波和他合作的《磁场》。我们当时使用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只是指人们后来称之为自动写作法的东西。”[2]P180虽然后来超现实主义逐渐走向音乐、绘画、电影等更为广泛的艺术、文化甚至政治领域,但在文学范畴内,自动写作一直是它最基本、最坚定的支撑。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对超现实主义的定义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他们正在从事的自动写作的写照:“超实现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发现象,主张通过这种方法,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2]P259从其中“纯粹的精神自发现象”、“思想的照实记录”等字眼,我们可以究寻到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是其最为直接的思想来源。布勒东也说,“这要感谢弗洛伊德的发现。根据这些发现,终于形成了一股思潮;而借助于这股思潮,人类的探索者便得以作更进一步的发掘,而不必再拘泥于眼前的现实。想象或许正在夺回自己的权利。”[2]P246
布勒东认为人们只有在潜意识状态中才可能避免思想在清醒时所受到的限制,其中最严重的限制是“对直接感觉的屈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残雪继承了布勒东的衣钵,她将潜意识视为写作最丰富、最恒久的资源与动力。在她看来,“潜意识的力量是很大的,这种东西已支持了我近二十年不间断的创作。”[3]P18最好的写作必须“一头扎进潜意识这个人性的深层海洋,从那个地方发动我的创造力。”[3]P8
布勒东和残雪自动写作对潜意识的推崇,实际目的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反抗,意图寻找他们认为更为本真的现实存在。对于传统现实主义,二者都无好感,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强烈的排他性。布勒东明确地说,“我厌恶它,因为它包孕着平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得。正是它,于今诞生着这等可笑的作品,以及那些没辱人格的剧本。它不停地在报刊上加固设防,对于科学、艺术的发展横加阻隔,却竭力去迎合一般舆论最低级的趣味:明白直捷到了庶近蠢笨,犹若描写猪犬终日之奔忙。”[2]P242-243在他看来,莫泊桑的作品也“毫无生气、枯操、平庸、不完整和没有深度。”[2]P192他指责现实主义态度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一切科学、道德、艺术进步的最大障碍,在精神上是平庸、仇恨的根源,在艺术上则是“迎合最低级的趣味”。而残雪在否定传统、否定生活现实上毫不逊色,她认为以现实主义为根基的“历来的中国文学在人性刻画上都是平面的,没有层次而幼稚的。”[3]P3而她本人的写作则根本不关注现实场景,也不以此为素材,“我要写的是更深层的东西,不是表面的现实,那个表面的现实跟我要写的东西没有多大关系。”[3]P67“我在写作时,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句子都摆脱陈腐的‘现实’的羁绊,插入核心地带。”[3]P87她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一再进行贬抑,而谈到当代作家时,对于“回归传统”的王安忆描述的现实也认为并不真实,“其实乡村和底层哪里是她写的那个样子?农民的苦、农民的悲她完全没有感觉。”[3]P17带着伤痛从一战战场上归来的超现实主义者,对战后现实的不满和破坏欲望使他们的文学理念有着一定的逻辑线索,而残雪对传统的一概否定就显得更多地是出自意图引起围观的偏狭与执拗了。
二
在时隔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残雪重新翻捡出布勒东的自动写作,我们要比较二者的异同,除对其精神资源进行查探之外,还有必要对他们写作的具体过程进行解析。通常情况下,很多作家都不会暴露自己是如何写作的,他们更愿意在一部作品完成后将之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看到读者的一脸惊诧,从而得到巨大的满足,而对过程则绝口不提;亦或只是对大致的写作状态透露一二,而对自己写作详细的运行方式语焉不详。但是布勒东并没有这样干,他将“超现实主义魔术的秘密”毫无保留的公之于众:“找一个尽可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然后把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弄来。尽你自己之所能,进入被动的、或曰接受性的状态。忘掉你的天才、才干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才干。牢记文学是最可悲的蹊径之一,它所通往的处所无奇不有。落笔要迅疾而不必有先入为主的题材;要迅疾到记不住前文的程度,并使你自己不致产生重读前文的念头。第一个句子会自动地到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以致于每秒钟都会有一个迥然不同于我们有意识的思想的句子,它唯一的要求便是脱颖而出。”[2]P262从这一段详细的说明中可以见出,布勒东的自动写作过程“没有任何理性的控制”,任由意识自然地流淌,甚至标点符号在他看来也成为完成作品的羁绊。作品是作者思想自然流淌的结果,理性思维没有充当任何的监护作用。与布勒东绝对的非理性、绝对的不可控相比,残雪对自己的自动写作有了新的阐释,“我的写作是理性和感性合一的产物。我必须肆意发挥,我又必须用强力控制。控制不是为了节制,而是为了更肆意地发挥”[3]P20,要“用一种很强的理性把自己控制在非理性的创作状态中间”[3]P70。对于残雪这略带禅宗意味的说明,要理解起来是困难的,甚至引起了更多的疑惑。这种通过理性去达成一种非理性的状态,真的有实现的可能吗?残雪具体是如何做到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在《残雪文学观》中并不能找到答案。尽管残雪也表示“理性只能站在场外监控,绝对不能跳进场内充当角色。”[3]P88但有一点必须加以确认,那就是如果有了理性的参与,这本身就已经不可能再是一种纯粹非理性的状态,因此对于残雪的自动写作就需要重新审视。要么,残雪进行的确实是一种自动写作,而她对外宣称的“理性控制”并不存在,只是一种对个人写作方式进一步的神秘化;要么,残雪的写作根本就不是纯粹的非理性的自动写作,只是一种可能的尝试,她还在向完全的自动写作靠近的途中。配方可以盗取,然而火候的拿捏只有师傅知道,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一门手艺的写作中,布勒东与残雪究竟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着他们自己所言的自动写作,还需要从他们的文学实践中寻找答案。
三
除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之外,布勒东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娜嘉》了,“这部小书是二十世纪法国现代文学中最杰出、最重要的名篇之一。”[4]P4虽然布勒东的意图是要通过作品营造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但有意思的是,《娜嘉》几乎是一部与作者生活进行同构的小说,作者基本上是将自己的思想与生活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书中。作品一上来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回答一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是谁?这可以看作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先驱的思想实录,布勒东把完全真实的自己当作了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的主干部分是布勒东与娜嘉从相逢到分手的爱情故事。对于娜嘉,布勒东一再向读者保证确有其人,这一点也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由此可见,《娜嘉》不是虚构,而是“完全的、彻底的真实”[4]P6。可以说布勒东自动写作的成果就是他“思想的照实记录”,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它与现实之间并无裂隙,它几乎就是现实本身。
而到残雪哪里,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以残雪认为最能代表她自己写作方式的《新生活》为例(“我觉得还是《新生活》最能代表我”[3]P33),可以窥得一二。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述遗的老妇人搬到一座高楼后所遇到的怪人怪事:爱吵架爱打听爱纠缠的老邻居彭姨、常常破坏电梯然后又把它修好的修理工、大楼里唯一的邻居神秘的黑脸汉子、七楼永远开着门的空房间、去过一次再也找不到的商业街,等等。小说被一种神秘的氛围所包裹,其中的人物与事件缺乏现实生活的支撑,明显可以看出“创作”的痕迹,而且这样的创作已经越过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边界。在残雪看来,“除了表层的社会生活,还会有个人的深层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有其独立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表层生活都要受制于她。”[3]P135-136也就是说,残雪的小说并不以还原“表层的社会生活”为目的,而是要展现所谓的“深层的精神生活”,并通过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式的虚构来完成这种展现。显然,残雪将“社会生活”定义为“表层”,将“精神生活”定义为“深层”,进而将二者截然区分且对立起来,并认为不通过“社会生活”就能表现“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有着“独立”的表现通道。这样的理念无疑已经走入她个人自我的文学密室中,要得到理解和认同是很困难的。
于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场景出现了,以超现实为宗旨的布勒东通过原生态现实的纸上再现,以彻头彻尾的复印真实来实践着他的自动写作。而声称要写出更为本真的“深层的精神生活”的残雪,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通常意义上的现实,另起炉灶营造出一个基本与真实生活无关的“现实”,来通达她眼中的“深层”。同样反感传统现实主义的两个人在自动写作的旗帜下,沿着不同的方向,走向了各自的极端。
除了与现实的关系,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二者作品中是否有理性和逻辑的存在,这是检验二者是否真正实现技术上的自动写作的关键。《娜嘉》虽然是布勒东本人真实生活的复述,但其中并没有连续的情节,鲜明的形象,有的只是作者浮光掠影、跳跃闪动的记忆片断。在叙述完一件事后,紧接着的并不是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而是莫名其妙地开始对另一主题发表一通“抒情的”思索,因而显得毫无逻辑,毫无结构,读者能捕捉到的只是一些优美的文字与意象的组合。而最终娜嘉被送进疯人院后的命运如何也没有交代。小说更是以一则与此前内容毫不相干的关于一架遇难飞机的电报结尾,真正让读者体验到了自动写作的非理性特征。对于自己的作品,布勒东如此评价,“很难恰如其分地估价呈现在眼前的各种素材;甚至可以说,初读之下,简直无法置评。即使这些素材是出自你本人的手笔,它们于你也一样地陌生,犹如其之于任何他人一样;所以你自然也对之不无戒意。”[2]P257可见,布勒东并不否认自己的作品缺乏内在的逻辑结构。然而残雪却正好相反,她一再声称,如果真正做到自动写作的话,“我写出来的这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里面一定有结构,只要有人有那么大的力气去研究,他就会找出来。”[3]P78其实,并不需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只要随着《新生活》诡秘的文字前行,就会自然摸索到故事的脉络,以及捕捉到那些个性怪异、生活中无法出现的人物的踪影。小说主人公述遗进入城市高楼后的多疑、孤独、迷惘在一个个事件中被连缀起来,这些事件虽无现实的根基,但却自成逻辑,有条不紊的演进着,明显可以看到“结构”的痕迹。
两相比较,从《娜嘉》反映出的断裂、错置,以及理解的障碍来看,有理由相信,主张完全非理性的布勒东,将自己的生活作为素材,不经过缜密的计划、结构,片断式的呈现出来。这种从自己的生活洪流中攫取一勺的办法,有着实现自动写作的更大可能。而残雪的《新生活》尽管背景虚无,缺乏生活的逻辑,小说最后的指向也模糊不清,但主人公述遗经历的搬入高楼、上下电梯、寻找商业街等事件,却有着自我独立的故事逻辑,如果只是“脑海空空坐在桌边就写,既不构思也不修改,用祖先留给我的丰富的潜意识宝藏来搞‘巫术’”[3]P61的成果的话,有些难以让人信服。
当然,文学最终必须以作品证明自身。布勒东以完全非理性的自动写作完成了“二十世纪对文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反动”[4]P6,它代表一种写作的向度,不过其作品本身的价值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淘洗后,已显苍白。《娜嘉》如今只留下一些优美的词句与意象,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转,而与大众渐行渐远。超现实主义者也几乎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完全放弃了自动写作。在自动写作沉寂多年后,残雪对它进行了自己的重新定义,在“非理性”之前加上“理性控制”的定语,难以避免模糊、混乱和矛盾的嫌疑。从其作品来看,在抽空现实生活之后,残雪笃信人的抽象本质的单独存在。她把表现这种“深层”的人的抽象本质奉为其写作的终极目标,并试图依靠“理性控制下的非理性”的自动写作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不以现实生活为基石,不通过“社会生活”就能进入“精神生活”的写作方式具不具备普遍意义,是不是有推广的可能,文学实际的发生进程早已给出答案。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引起人们对文学另一种可能的关注,从而以多样替代单一、以丰富替代贫瘠,完成对当代中国小说的充实。
[1][英]C·W·E·比格斯比.达达与超现实主义[M].黎志煌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
[2]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残雪.残雪文学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法]安德烈·布勒东.娜嘉·序[M].董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