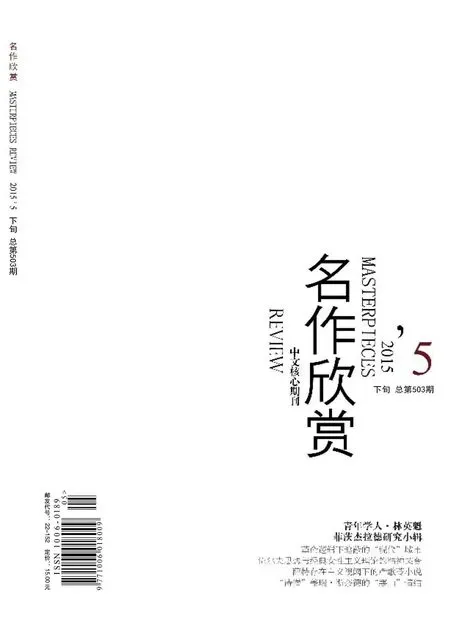利沃夫家族的挣扎与困惑
⊙姚秀娟[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作 者:姚秀娟,文学硕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文化。
一、引言
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迄今为止,已经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数篇短篇小说和回忆录,以及两部文学批评。很多作品被寄予极高的荣誉,例如美国全国图书奖、美国国家书评、福克纳奖等。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候选人。他眼光犀利,视角独特,将美国犹太人作为小说当中叙述的对象。而何谓美国犹太人?史克金(Ira M. Sheskin)在“美国犹太人”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犹太人是具有犹太信仰或族裔特征的美国公民。”①可以发现,犹太教对于犹太血统和犹太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仅仅针对犹太人,而且指向生活在美国的美国犹太人。事实上,美国犹太人源于犹太人,而且相当一部分美国犹太人在成为美国公民之前是具有流散经历的。他们来到美国追寻的是“应许之地”。没有任何生活根基的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犹如勇于开辟新土地的拓荒者。不过只是拥有勇气不足以克服生活中的种种苦难,犹太人向来以对犹太教的忠实信仰而著称。在菲利普·罗斯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1997)中就对这信仰的坚守和动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二、犹太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娄·利沃夫
犹太人最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欧文·豪(Irving Howe)曾记述道,“商店墙围和地板极其糟糕,分隔的洗手间是个例外。用餐的地方抑或不复存在,抑或在肮脏阴暗的角落里,抑或在另一层门警的住所里。”②菲利普·罗斯将二战后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映照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流露出几分无奈、几分同情。在《美国牧歌》中,娄·利沃夫(Lou Levov)曾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挣扎着。作者描述道,制革厂充满了油脂臭气,地上杂乱不堪,工人在其中“被迫像牲口一样忙个不停”③。当时生活如此艰难,可是娄·利沃夫却未曾放弃希望。他依照犹太法典对于勤奋的劝诫,努力地工作着。生活上有了奋斗的目标,精神上有了动力支持,使他敢于面对任何困难,最终取得成功。可是,面对美国文化的冲击,娄·利沃夫有些力不从心。
摩西十诫记述道,犹太人应该“尊敬你的父亲和母亲”。在传统犹太人家庭中,父母亲拥有绝对权力,子女应该对父母的意愿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美国牧歌》中,这种稳定的家庭关系被解构。娄·利沃夫的权威受到儿子杰里(J e r r y)极大的挑战。在小说中,杰里这个有些近似于漫画似的人物,显得活泼而富有幽默性。一沉不变的家庭和事业对他来说是一种束缚。皮革产业是娄·利沃夫发家致富的法宝。他深知皮革业的重要性,把它视为一种近乎于生命的事业。可是娄·利沃的二儿子杰里对此却不屑一顾。为了赢取一位女孩的欢心,杰里将神圣的皮革制品加工的一塌糊涂。当娄·利沃夫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简直怒不可遏。当他开始教杰里如何制作皮革制品的时候,恐怕很难想象儿子竟怀有此种想法,“这似乎比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怒骂更使杰里难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杰里发誓决不去碰他父亲干的那一行。”④几年以后,杰里果然背离父亲的意愿,选择成为了一名医生。美国文化强调解放自我,发挥独立个性。在这种文化的冲击下,犹太传统文化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三、理想幻灭的追梦人——塞莫尔·利沃夫
《美国牧歌》中,娄·利沃夫的大儿子瑞典佬(Swede),即塞莫尔·利沃夫(Seymour Levov)迫不及待地想冲出种族、身份和地位的束缚,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然而,作为一名犹太人,如何在这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的目标是什么?瑞典佬将“美国梦”当做自己动力的源泉。约翰尼·阿普瑟斯(Johnny Appleseed)是他的偶像。他曾梦想到,“约翰尼·阿普瑟斯,那才是我(瑞典佬)要的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新教徒,约翰尼·阿普瑟斯只是个快乐的美国人。”⑤但是,当遇到真正的美国人比尔·沃库特(Bill Orcutt)的时候,他的梦想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比尔·沃库特的家族有着辉煌的历史,瑞典佬在这个新新世界像无根的野草不知去往何处。
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瑞典佬却有些盲从,最终迷失了自我。为了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瑞典佬选择和一名非犹太人结婚。开放的美国,崭新的世界,让犹太人有更多的机会同非犹太人接触。魏啸飞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犹太青年中约有一半以上与非犹太人结婚,而且这些非犹太婚姻伴侣皈依犹太教者已寥寥无几”⑥。在《美国牧歌》中,瑞典佬迎娶非犹太人做妻子并非偶然。在他看来,这是成为美国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他的偶像约翰尼·阿普瑟斯一样,瑞典佬也希望可以播撒自由和快乐的种子,不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而是作为一名真正的美国人。然而,他的美国梦却随着妻子的背叛化作一曲悲歌。
四、精神荒芜的恐怖分子——梅里·利沃夫
1959年,越南战争爆发。投入战争以来,美国国民和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霍华德·布里克(Howard Brick)发现,“直到1965年底,美国为南越提供18万军队支持,一年以后,数量增加到35万人次,1967年底几乎50万人力投入到越南战争当中。1968年底,战争经费已经增加到每年消耗300亿美元,美国已经伤亡20万人次,包括3万死伤人员。”⑦。面对这样巨大的损失,美国民众开始思考这场战争的意义。1960年,反战运动拉开序幕。其中一些反战组织采用极端的方式,制造恐怖袭击。《美国牧歌》中,梅里·利沃夫(Merry Levov)是瑞典佬·利沃夫的独生女,在社会运动频繁发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她空虚的心灵不能得到安慰,便选择成为了一名恐怖分子。
事实上,梅里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她怜惜越战中受难的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可是她的恐怖行动非但没有拯救这些人们,反而使更多无辜者受到了牵连。父亲瑞典佬无奈地发现了梅里杀害了四个无辜的人。梅里的极端行为类似于“个人暴力”。王伟光分析道,“个人暴力,首先是一般刑事犯罪中的暴力行为……(其中一类)非源于个人利益或情感上的动因,也非出于政治目的,而只能说出于对社会的怨恨,极端的宗教信仰或其他一些疯狂念头,这也就是一些人所称的后现代恐怖主义”⑧。梅里将自己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扩散到对整个美国社会的憎恨。她不断地制造炸弹,杀害无辜。最终,梅里被这种疯狂的行径腐蚀成为一个残忍的恶魔。拯救遇难的人们——这最初单纯的梦想转变成了无辜市民的噩梦。
五、结 论
虞建华在《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代表价值》中评述道:“美国犹太作家一方面植根于半封闭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旧世界的经验;另一方面又被卷入新世界的漩涡,连根拔起,面对大萧条,战争,事业,阶级与种族冲突和反文化运动。”⑨这段话表现了美国犹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两难的身份危机。菲利普·罗斯具体体现出来的是他对“传统文化”犹太教的认识。另外,对这种宗教的认识一部分来自于他所生长的纽瓦克犹太社区。而在他所生长的年代,犹太教色彩已经慢慢被淡化,这种“旧世界的经验”表现在小说中,是对娄·利沃夫保守派宗教捍卫者的一种无奈的叹息。犹太教在美国这“新世界的漩涡”中,到底能成为多少美国犹太人的精神依靠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小说中瑞典佬希望能把控事业和家庭方向,使其驶向美国文化大潮,而逐渐远离犹太教。这种背离是一种“连根拔起”,是对美国犹太作家思考方式的一种极大的挑战。这种背离带来的后果,小说作者采取的方式是用悲剧来阐释的。
小说当中个人情感意识和精神生活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美国犹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走出这种困境,似乎是连作者都无法回答的问题。娄·利沃夫极力维护犹太传统,瑞典佬·利沃夫拼命融入美国社会,梅里·利沃夫面对美国文化极端叛逆。在美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对垒中,他们抑或无奈,抑或追寻,抑或反抗。菲利普·罗斯笔下二战后的美国社会有着光芒四射的诱惑力,可是更多的是空虚与迷茫,表现了作者对于浮华美国社会的批判和对美国犹太人命运的叹息。只是在文化冲击下,这种理想该如何行进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小说最后,三代犹太人不是已经故去,就是被俘。父亲和儿子的故去似乎预兆一种文化对抗的消逝,可是女儿的被俘似乎印证这种文化冲突将永无止境。美国犹太人将何去何从?
① Sheskin,IraM.“AmreicanJews.”Ed.McKee,JesseO.EthnicityinContemporaryAmerica:AGeographical Appraisal,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0,p10.
② Howe, Irving.World of Our Fathers.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b, 1976, p156.
③④⑤ 罗斯,菲利普:《美国牧歌》,罗小云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第31页,第307页。
⑥ 魏啸飞:《美国犹太文学与犹太特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209页。
⑦ Brick, Howard.Age of Contradiction: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60s.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1998,p 555.
⑧ 王伟光:《暴力分析与恐怖主义的界定》,《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1页。
⑨ 虞建华:《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其代表价值》,《外国语》1990年第3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