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回家的路
01
2012年5月,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第十部长篇小说《家园》(Home)由美国兰登书屋旗下的克诺夫出版社在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发行。
就在同一个月,莫里森在美国白宫获得了总统奥巴马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此奖是美国最高的公民荣誉奖,旨在表彰那些终身为美国国家利益、世界和平、文化事业做出特别贡献的杰出人士。在白宫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奥巴马总统说:“托尼·莫里森的文字所带有的道德和情感厚重感,是很少有作家能够企及的。从《所罗门之歌》到《宠儿》,托尼用她优美、恰当、明晰和精炼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感动。”莫里森的这枚奖章可谓实至名归。
奥巴马的颁奖词是对莫里森最诚挚的褒奖,也从一个方面对其整个创作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莫里森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其小说涵盖了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她凭着犀利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运用黑人女性的视角、富有诗意的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技巧创作了大量真挚感人的文学作品。《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孩匹克拉无法摆脱的悲惨命运,《宠儿》中那份撼人心魄的母爱悲歌,《慈悲》中弗洛伦斯承受双重奴役下的艰难成长,这些都倾注了作者对美国历史和族裔问题,特别是黑人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和强烈关注。她对种族、性别、道德、政治问题独到的诠释表现了她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社会责任感。
《家园》和莫里森的其他文学创作一样,都在追踪历史进步的轨迹,记载人类发展历史,同时也在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
而在最新的作品《家园》中,莫里森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20世纪的50年代。
《家园》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围绕着1950年代初从朝鲜战场回来的黑人退伍军人、24岁的弗兰克·莫尼(Frank Money)跨越半个美国,救妹妹于危难之中的故事展开,讲述了弗兰克在饱受多重创伤之后历练成长、回归精神家园的故事。

弗兰克出生在美国南方得克萨斯州一个黑人家庭。种族歧视下发出的搬迁令使他们逃难般地迁往佐治亚州的莲花镇,投靠没有任何怜悯之情的祖父母。父母的早逝和祖母的尖刻冷酷使他和妹妹的生活陷入更大的窘境之中。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入伍,参加了朝鲜战争。在朝鲜战场上,他目睹了同乡战友的死亡,使他认识到战争的残酷,也形成了他心中难以磨灭的创伤。留在家乡的妹妹遭受骗婚的打击之后,迫于生存压力,做了一个白人医生的家庭助理,成为白人医生的医学试验品,落得重病在身,生命垂危。接到妹妹重病消息的弗兰克,即刻踏上了拯救妹妹同时也是拯救自己灵魂的回归之旅。
02
《家园》与莫里森过去的小说不同,不见了莫里森以往感人至深的凄婉与悲悯,也没有了扣人心弦的神秘与魔幻。《家园》里有的是简单的故事情节,舒缓的故事进程。
1950年代的美国虽然远离朝鲜战场,但绝非一片净土乐园。种族隔离制度的毒瘤蔓延在生活的各个角落,迷惘的一代青年人的躁动为社会平添了诸多纷乱。从美国西北的喧闹都市,到南方平淡无奇的家乡小镇,弗兰克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不仅让他见证了人世百态,尝尽了人间冷暖,也为我们展示了种族歧视带给黑人的种种苦难。
在火车上,他看到一个黑人男青年毫无缘由地遭到殴打和欺凌;在给他提供住处的友人家中,他看到一个八岁的小男孩被警察无端枪击致伤,只是因为“警察想打谁就打谁”;在同居女友那里,当女友循着出租房屋信息要求看房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此房不能租给希伯来人、黑人、马来人,或者亚洲人”。而他自己,从朝鲜返回祖国,尽管怀揣着退伍军章却身无分文,穿梭于繁华闹市却无处安身。面对这样的生活现状,弗兰克无所适从。
弗兰克是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可作者并没有对这一故事背景加以浓墨重彩,小说中没有出现枪林弹雨或厮杀拼战的场面,但这并不是说战争已经远离了弗兰克。恰恰相反,战争已经在弗兰克的内心深处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在小说中,所有关于战争的记忆通过一些片段式的简单画面而展露无遗:受伤战友残缺的身体,两个同乡战友惨死在弗兰克面前的痛苦表情,还有那只在垃圾堆里摸索淘食孩子的小手。
正是这几个定格在弗兰克记忆深处的画面,如影随形地控制着他的大脑,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痛苦的根源,既让他愤恨,又让他颓废。恰恰是这些痛彻心扉的记忆,造就了他外表冷漠、内心激愤的性格。他也试图通过做短工维持生活,但更多的时间,他都是消沉而懒散地呆坐着,茫然地望着地板,无视屋内的凌乱和女友的抱怨,百无聊赖,茫然无助。
由此可见,正是从波澜不惊的故事里,我们走进了一个黑人男青年的内心世界,也通过他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也感受到了他自己的迷失与困惑。
03
《家园》塑造了一位觉醒了的、刚毅的黑人男性形象——弗兰克。
正当弗兰克在社会、家庭和战争创伤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的时候,来自妹妹那里的求救信让他从混沌状态之中走了出来。

在莫里森的许多小说中,黑人女性总是境遇悲惨,命运多舛。《家园》里弗兰克妹妹希(Cee)的经历同样让人唏嘘。妹妹在种族主义的重压下艰难度日,最终成为白人雇主的医学试验品,奄奄一息。妹妹的求救信刺痛了弗兰克近乎麻木的灵魂,触动了他对亲人的真挚情感,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大威猛的男性形象也开始变得清晰。
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弗兰克不顾一切踏上了归程,返回那个他希望从回忆中抹去的地方,那个他曾发誓永远都不要回去的家乡——佐治亚州的莲花镇。在他眼里,那里曾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比战场都糟糕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未来……没有目标……没有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在弗兰克的内心深处,一直珍藏着一个男性的勇敢形象,这个强壮男性的形象来自儿时同妹妹一起看到的一幅画面,那是一群骏马在碧草蓝天下构成的壮美的图画。当他和妹妹透过树桩铁丝围栏看到那群马匹“如同男人一样站立着”,一个威猛、壮美,充满野性、刚毅的完美男性形象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尽管残酷的生活和战争一度消磨了弗兰克身上的英勇豪气,但此时复苏的男性气概唤起了他身心的坚强和刚毅。
在返回佐治亚的旅途中,一个男人与他人发生争斗,弗兰克在一旁围观,该男子迁怒于他,对他进行谩骂和殴打。愤怒的弗兰克挥起拳头,给了那个男人一顿暴打,彻底摧毁了他的嚣张气焰。这次成功的出手刺激着弗兰克,给他带去了极大的兴奋,让他品味到了胜利者的快感。最终,凭着这种充满野性的勇猛,弗兰克不顾一切地冲进妹妹的白人雇主家中,愤然抱起妹妹,带她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乡之路既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也是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弗兰克重塑了黑人男性的形象,找回了遗失的男性气概。与此同时,在黑人社区的关爱和帮助下,妹妹也摆脱了奴役的束缚,找回了自我,获得了身心的自由。如果说弗兰克救助妹妹的过程是一场挑战自我的战斗,那么在这场战斗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胜利者:他不但拯救了妹妹,使其重获自由,还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04
《家园》无疑是一部带有浓烈的莫里森风格的作品。从背景到主题,从人物刻画到写作技巧,作者秉承了其作品中一贯的严肃与深沉,同时也超越了往昔的悲情与沉重。小说篇幅短小(英文小开本143页),但内涵丰富,语气虽然温婉平淡,但却带有不失厚重的气势。
《家园》的叙事方式依然是“莫里森式”的,在现实主义的写实和白描中巧妙地交织着一些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全知视角的叙事模式和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交替出现,两者相得益彰、交相呼应,增加了故事的空间感和完整性;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时采用斜体字排版,营造了一种书信体的格式,拉近了读者与弗兰克的距离;黑人口语的不规则表达,在流畅简洁中增加了几分语言的灵动性;不留痕迹的意识流般的时间跳跃,让读者更好地去捕捉人物的思想变化。
相对于莫里森之前的小说,该小说的语言更加简练,结构更加明晰,语气更加沉稳,这一切都使小说平添了一种返璞归真的韵味,增加了几分纯朴的大气,让读者感受到莫里森这位文坛巨匠经过岁月沉淀之后获得的深厚和纯美。
在接受CBS访谈时,莫里森谈到了这部作品。她说:家是一个真正安全、舒适的地方,是你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是你能够获得帮助的地方,是充满爱的地方。这或许可以看做莫里森写作《家园》的内在原因。
在后“9·11”时代回归文学的浪潮中,美国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以“家”为题目或主题的文学作品。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关于浪子回头故事的《家园》(Home,2008),试图为人们在纷乱繁杂的政治世界中理出一条用宗教信仰获得救赎的回归之路。相对而言,莫里森的《家园》的政治意义更加明了。她把朝鲜战争作为创作背景,其寓意不言自明: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战争带给世界的都只能是伤痛,无论何时,和平都是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家都是人类最安全的所在。莫里森说:我们关注过去就是关注现在,过去的并未完全过去,我们要从中学会怎样面对现在。
《家园》和莫里森的其他文学创作一样,都在追踪历史进步的轨迹,记载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在指明人类进步的方向。莫里森作品中弘扬的自由和谐、成长的观念,将永远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永恒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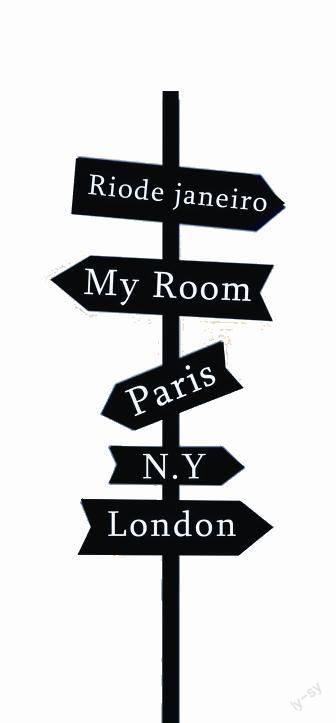
(该文系作者所主持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项目“英美新现实主义文学重要作家研究”[编号:2011GWX033]的研究成果。)
(郝素玲: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邮编:4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