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出你的手
[美国]纳森·普尔
我看见了,那一缕缕的光,奶白色的光,从她的发端飘了出来,飘向上空。每根发丝都射出了丝般的光芒,随即在飘过灯影之后,光芒渐退,直至消逝不见。这一缕缕的光从露丝的头上映射出来,在房顶上聚拢,整个屋子一片光明,闪闪发亮。
“烧退啦。”我父亲说道。父亲把妹妹从床上抱了起来。妹妹双腿耷拉着,脚指头朝下。她的双臂松松地垂在父亲的后颈,十指蜷着,呈轻轻握拳状。父亲把脸贴在妹妹额头上,再次试了试她的体温。
这样过了许久,父亲对我母亲几乎是大叫着说:“露丝妈,烧退啦!”
“啊,上帝呀,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母亲说道,同时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脖颈。每当母亲心存感激时,就会这么有节奏地拍着。母亲在露丝床边坐下,抚摸着床垫上露丝之前躺过而留下的空荡荡的凹痕。她用手掌轻轻拍着那凹痕,然后将床单抚平。母亲的手掌在床单上摩挲,有一种特别的律动,似乎在说:“上帝啊,为了这儿久违的清凉,床上的这片清凉,我感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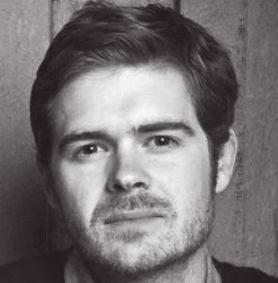
我妹妹高烧已经持续三个多星期,快整整一个月了。体温时高时低,烧却从未退过。到了月底,高烧同妹妹的声音或她不拘小节的个性一样,似乎成为了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烧就这么退了?烧明明没退,我看见的,烧根本就没退,它还在我们头上盘旋,让我们头昏眼花。我们要不要关掉灯,把窗户打开?高烧就像一只小鸟吗,还是像飞蛾?
这间屋子已然变了样,仿佛曾被倾覆或摇晃过似的,所有家具的摆放位置都不一样了。这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房间。过去一周我母亲一直睡在那里。在那把小小的黄色阅读椅上,母亲曾没精打采地蜷着,双腿十分痛苦地曲向一边,双手压在两膝之间。如今这屋子已不似原来那般黑暗了,反而变得温暖了起来。灯光不再晦暗,只是映衬在杨木之上的一抹淡淡的红。就连露丝身上那熟悉的汗珠子,如今看来也不过是像撒在她发际上的一层细细的盐霜罢了,无伤大雅。
父亲在露丝的床和开着的房门之间徘徊,轻轻拍着怀中的露丝。“露丝?露丝?露丝?”父亲呼唤着,“听见了吗?”妹妹似乎醒了一下,马上又陷入沉睡之中。在此之前,我不确定父亲是否真的了解他自己对妹妹的那份感情。
妹妹四肢骤然一紧,父亲连忙将她贴近自己,没有一丝犹豫,也没有一丝威严。我从中看到了那份感情,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他们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彼此拥有着。妹妹又睡着了,父亲依然抱着她。我不记得有人像父亲抱妹妹那样抱过我。
“她需要休息。”母亲说道。“露丝?”父亲又叫了一声。
“她没事儿啦,”母亲说道。她把妹妹抱过来,放回床上。“我们早上试着喂她点东西吧,吐司还有菜汤之类的。”
“本杰明,”父亲说道,“去给你妹妹再打点水来。要凉水。”
疾病能让你明白一些事情,一些就算你经历了许多时日,却不知为何,总也弄不明白的事情。是妹妹高烧中那闪闪发光的景象不可思议,还是父亲抱妹妹的那种样子更难以置信,我说不上来。我在心中为这些事情留出了一块位置,我把我的嫉妒也放了进去。在那儿,嫉妒以我难以想象的方式酝酿着,恐惧也是如此。我感觉得到,这些东西在那儿汇集,就如百川归海一般。可是我听不见,也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打开后门,踏上了通往水井的那条小道。秋天慢条斯理地来了。这个夏天本来挺好,可是现在看来,整个夏天都黯然失色。在那两亩地大的院子对面,布莱森家灯火阑珊。灯光透过树木间的缝隙溢了出来,在地上投射出大大的、脉状的黑影。
1924年的8月,酷热直直地逼向我们。它钻进了我们的躯体,就像那些看不见的鱼儿,在河水中活蹦乱跳,钻进了游泳者的身体,再也不出去了。季节会更替,冬天最终会来临,地窖里罐中的腌菜,那些糖渍秋葵、泡白菜泡萝卜之类的,终究要拿出来吃掉,但是今年夏天以及随之而来的这场高烧却永远留了下来。对我们是如此,对布莱森一家更是如此。
我的双眼在黑暗中努力搜寻井边那台水泵暗淡的轮廓,虽然那水泵其实还离我很远,根本看不见。在一片漆黑之中,我让双眼平视前方。我沿着小道的中间往前走,脚下的道路已被夯实,感觉凉飕飕的。要是我觉得脚底一边或另一边踩着有些软,我就回到路中央来。
几周以来,一切似乎都悬而未决。我记忆中的每个动作一定都是以露丝的床为中心的。既然我现在又出来了,站在这清凉的夜色之中,我就想一直走下去,直到走不动为止。我很想离开那个房间,离一切远远的,就站在这儿,站在树影中一个隐匿之处,回望我们家那栋房子。这样会让我觉得很自由,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想被人发现,就没人找得着我。水泵的铁把手依稀可辨了,月光照在上面,为它镶上了一圈蓝蓝的光边。其下的井水中,一道小小的光环闪闪发光。
水泵喷嘴下的土里,有只大桶半埋在其中,里面有潭死水。我将打水的吊桶放进去,把它往下压,桶的一半便没入了那潭死水之中。我感受到水的浮力将它直往上顶。我将吊桶移到水泵下,轻轻敲了敲泵嘴上的把手,觉得挺稳当的,我便抓住水泵的泵杆,开始往上抽水。
我姐姐在盐湖城上大学。从戴尔斯堡去那儿要坐两天的火车。姐姐与露丝从来都玩不到一块儿。对露丝来说,汉娜姐姐不过是母亲的翻版。汉娜比我大八岁,比露丝大十四岁,监管着家务琐事。她性子很像父亲,因此总是令人费解,难以亲近。就算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汉娜也总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只有母亲要她做事,比如摆饭桌之类的,她才会暂时放下自己的事情。
有几次我几乎相信汉娜和父亲试图通过他们的沉默寡言向我和露丝诉说什么,好像我们应该自己从他们的坦然淡定之中发现他们某些隐秘的感情倾向。我觉得这好比是一个人长时间地盯着一尊塑像看,心中就会升起一丝怪异的感觉,交织着忧虑与期盼,想要看看那塑像会不会眨眨眼睛,或是笑一笑。我知道露丝跟我一样也有这种想法。我们一直期盼着,相信我们的父亲不是个冷冰冰的人,他只不过是很聪明罢了。他特意设计了一场周密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他总是表现得与自己的感受相反。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好,这种方式我们还理解不了,因为我们还太小。
露丝唯一真正的玩伴是我们邻居家的小女孩。她叫萨姆,有六个哥哥。萨姆跟露丝一样,瘦瘦高高的,对什么都好奇。露丝上学那年,萨姆家里还不让她上学。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父亲去拜访了一次布莱森先生。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假装摆弄柴火堆,母亲则把土豆埋进后院门廊的地里。父亲穿过树丛,在布莱森家前廊与布莱森先生会面。我们则偷偷看着。
他俩只聊了二十分钟,我不知道父亲到底说了什么,不过第二天萨姆和露丝就手拉着手去戴尔斯堡市里上学去了。萨姆家里还为她准备了午饭,包好了裹在一条淡紫色的背带当中,萨姆把它背在肩上。她俩走在我的前面。这两个七岁大的小丫头,说起话来倒是挺一本正经、轻言细语的。
从那天下午起,这两个孩子就已经如榫卯相接似的,紧紧连在了一起。萨姆和露丝平心静气地对待学业和课本,学得还不赖。不过,要说令她俩茁壮成长起来的,还是田纳西州漫长的夏天。她们的皮肤都晒黑了,回到家中时还带着干草和溪水的味道。有时她俩被逼着陪萨姆的小哥哥玩,两人会一块儿消失在屋旁山下的树林中,再出现时,裙边都湿透了,还沾上了污泥。她们把裙子兜起来,形成口袋状,里面装了几只小龙虾。那几只粉色的,脾气暴躁的小玩意儿正在彼此的头上扭动着,滚来滚去。
在她俩一起度过的第四个夏末时节,两人都发烧病倒了。
布莱森先生经营着一间小型的奶牛场,总共养了三十头牛。萨姆的几个哥哥时不时地给两个女孩牛奶喝,喝了已经有几周了。
“几周了!”布莱森先生在我父母面前说道。在他的地盘上发生了这种事情,布莱森先生似乎对此大为吃惊。
他吓坏了,我们都吓坏了。
布莱森家的几个大儿子们知道,他们是不允许喝生牛奶的。那几个小儿子也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越是不让做的事,就越是诱人。两个丫头将又大又重的奶桶举起来,大口大口地喝着,互相帮着不让奶洒出来。牛奶暖暖的,富含脂肪。奶水顺着她们的脸颊和脖子流淌下来,流到了她们的衣领上。她们感觉像是在一同亲吻或者跨越某种界限,又像是把夏天满满地装到了自己身体里面。两人所做的这一切,每一次肆意挥霍,都是携手完成的。
铝制奶桶桶颈的内侧,一层层朦胧的白色奶痕铺开来,每一层都留有牛奶沉渣,昭示着两个女孩的逾矩行为。哥哥们在一旁使劲挤奶,她们则一边将舌头抵住上腭,去感受那滑动的残渣,一边拍着奶牛充满汗味的身子,盯着奶牛们湿湿的大眼珠子看,这些眼珠子可比她们自己的大多了。奶牛们原本顺从的目光,现在却几近恐慌。一股股奶水滋在半满的奶桶壁上,发出嘶嘶的声响。奶桶越来越满,这声音也越来越尖。
萨姆先病倒了。布莱森先生过来告诉我母亲说,萨姆发高烧了。我记得他都没走上我家门廊,只是站在第二级台阶上,一手搭在栏杆上,一手把帽子往腿上重重摔打,低头看着栏杆与地基的连接处,似乎在仔细检查那儿。他说,他认为儿子们在给两个女孩喝生牛奶。他的手在他红通通的、汗湿的秃头上挠来挠去。我母亲对他表示感谢,然后马上去找露丝。露丝这时候正在后院把床单从晾衣绳上收下来。她没把床单收进筐里,而是堆在草地上,把床单叠得乱七八糟。母亲飞快地冲向露丝。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她也顾不上了。她一脸凝重的神情把露丝吓得扔下床单,任其在脚下团成一堆,自己直往后退,好像是要逃离一个闯入者似的。母亲抓住露丝的胳膊,把她往后一拉,拉向自己这边,用双腿把露丝夹住,把手放到露丝额头上,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单腿跪地,双手拇指把露丝双眼的下眼皮翻出来,仔仔细细地看着。
“妈妈,怎么了?”露丝问道。
吃晚饭时,母亲三次把手伸过餐桌,捧着露丝的脸颊,用掌心试温。她让露丝多喝水。最后,父亲问露丝她有没有在布莱森家喝过牛奶。露丝说:“没有,爸爸。”过了一会儿,又说:“有,爸爸。”父亲告诉露丝说,萨姆病了,没有他们允许,露丝不能去看她。
那顿饭剩下的时间,露丝非常安静地坐着,使劲嚼着盘中的蔬菜。嘴里还含着许多东西时,她就喝水,结果弄得两个腮帮子难看地鼓了出来,好像她只知道机械地咀嚼而忘了吞咽。我们尽量不盯着她看。母亲很快地吃完饭,我还没吃完,她就把我的盘子收走了。然后我们就看着露丝吃菜喝水。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仿佛她会突然燃烧殆尽似的。她故意大口地嚼着,在椅子上微微地前后晃悠,双腿在桌子底下踢来踢去。
那天傍晚,露丝问她能不能听唱片。母亲再一次捧着她的脸,过了很长时间才说道:“就听几分钟吧。”那晚,露丝躺在地毯上,听着一张唱片睡着了。那张唱片我们在那一年听过无数次了,是音乐家乔治·格什温在纽约风神音乐厅演奏的《蓝色狂想曲》。
第二天一早,露丝在餐桌旁挨着我坐下,我感觉到她肌肤上散发出来的热气。那热度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
“露丝?”我说道。我伸出手去摸摸她的胳膊。触手所及,感觉她的肌肤都发胀了。她双眼黯淡无光,眼睛四周的皮肤异常地发灰。母亲头也没回,把双手在围裙上一擦,拿出一口煎锅,架在炉子上,往里倒上水,从头顶上的小橱子里抓了一把柳皮扔进锅里,稍微搅了搅,然后又从灶台上边的架子上取下一只玻璃罐子,往里倒了半罐水,用勺子加了些糖进去,接着开始搅拌起来。母亲小心翼翼,从容不迫。我和露丝望着她,都看呆了。
现在,母亲开始了一连串的动作。她安排这些事情的先后顺序,其中有什么突发状况或变数也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母亲的本事。锅中的水一开,母亲就从冰柜上面的架子上取下锯子,去仓库把冰块上的锯末一拂,从一角切下一大块正三角形的冰块。要是我这么干,就会被父亲骂。因为取冰块时得切三下,切下正方的冰块,然后再把锯末铲回冰面上去。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规矩。而规矩这么轻易就被弃之不顾,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
身后的纱门还没来得及关上,母亲已经把这块金字塔形状的冰块放到了桌上的一只大桶里。她在肩上搭了一块毛巾,往桶里加满水,说道:“露丝,去你房间,把衣服脱了,放在你脚边……放整齐点。”母亲把烧开的水灌到装着糖水的玻璃罐子中,搅了搅。罐中的液体变成了迷蒙的浅棕色,像是被搅浑的池水。母亲把这浑浑的柳皮水倒进冰柜中,然后就提着装冰块的桶,手拿一块抹布,消失在走廊那头。
母亲由此开始主导我们全家的所有行动。我和父亲成了她的左膀右臂,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执着,势必要让露丝康复。我们取冰块,我们熬汤,我们给露丝洗床单。父亲还在磨坊上班,不过中午会回来。我负责做饭。
两天后,高烧没离开我们家,也没离开布莱森家。那天一大早,树林那边才开始闪现一丝幽蓝的晨光之时,我就被人叫醒了。黑暗中我看不见是谁,只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要我走路去鲍比兹家借电话用一下。如果他们家有人,我就打电话找琼斯伯勒镇上的医生来。如果他们家没人,我得接着走,去高恩家。那个昏暗的清晨,我出发了,感觉像是在一场战争之中,从一位将军那儿接过一封至关重要的信,要送到另一位将军那儿去。天色渐亮,当晨光的投影穿越犁沟,我穿过了弗莱希曼家的庄稼地,从他家的铁丝栅栏下钻过去,踏上了大马路。路脊上长着些高高的青草,青草上的露珠沾湿了我的鞋和裤腿。
鲍比兹太太已经听说两个女孩发高烧的事儿了。她在门口迎上我,大大的身躯把门堵得死死的,对我说道:“你要打电话?上这边来,亲爱的。”
医生那天晚上就来了。我母亲坚持要他先诊治萨姆,再过来看露丝。我看着医生将露丝的一只胳膊伸展开来,把他的两根指头轻轻放在露丝的手腕上,然后盯着他的表看了好长时间。他还用指尖在露丝肚子上按来按去,直到露丝动了动,呻吟了一声方才作罢。
母亲同医生去了厨房,我则坐在露丝床边,用硬币给她玩戏法。我把双手伸出去,摊开来,把一枚硬币放在我的右手。我听见母亲给医生冲咖啡。
“肝脏肿大,”医生说。
我迅速将双手翻过来,小心翼翼地把硬币转移到另一只手中去。
“是马耳他热,一种波状热,喝生牛奶引起的。”医生说道。
“阿司匹林管用吗?”母亲问医生。
“不管用。”
我双手握拳放到露丝面前,“在哪只手里?”我问她。
离医生第一次来有一周了。一天早上,布莱森家的六个儿子全部背靠墙壁,坐在他家房子外面的背阴处。他们穿着背心和短裤,但是没穿工作服。有几个盯着我这边看,另外两个交叉双臂,脑袋耷拉着,最小的那个正把一片树叶撕成两半,往两腿中间扔。
他们蓬头垢面,困倦不堪,都一言不发。我记得以前从没见过这几兄弟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更别说还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地坐着了。就是在教堂里,他们也没这么安静过。见他们这样,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得逼着自己再迈开腿,努力想着我本来要去哪儿或者要做什么。突然,我懂了。我转过身去看他们,他们也看着我。忽然间我听见了,明白了。
一个可怕的声音从他们家中传了出来,而后这声音仿佛不仅仅从他们家中传出来,四面八方都是,就像吊在树枝上的秃鹰一样。布莱森太太哭天抢地,那喊叫声时断时续,像快要生孩子了似的。布莱森家的儿子们全都满脸痛苦。布莱森太太每哭一声,他们的脸就被那哭声挤压得扭曲一点,拧作一团。
我把冰桶和毛巾撂在院中,朝后门跑去。我的手抓了两次都没抓住门把手,然后我又一抓,门开了,我找到母亲。她正在给露丝洗澡。露丝躺在床上,瘦瘦的躯体一丝不挂,像一具尸体。我双眼直盯着看。这时我才意识到,露丝的房门本来是关着的,我刚才没敲门。露丝大腿根处有一小撮薄薄的阴毛,泛着灰铜色的光。我径直盯着那儿看。她的髋骨比我想象的要宽,更加女性化,从她骨盆的小弧线及那儿微微突起的地方陡然凸了出来。我从没见过露丝裸体,打从她生出来就没见过。这是她的身体吗?她一直都瘦骨嶙峋的,但从没有像这样看起来轻飘飘的。她那两只小瘦胳膊被毛巾擦过之后还湿湿的,看起来无与伦比的细小。她的肋骨比我想象的要粗,从她那对小小的乳房边突了出来。她的皮肤由于发烧依然红通通的。
母亲把被单拉过来给露丝盖上,一直盖到她脖子那儿。我这才猛然惊醒。我已经忘我了。还活着,我想,那哭天抢地的是谁?我觉得双膝发软,整个房间都在颤抖。我又想起了那六个男孩穿着白背心的那一幕,还有那可怕的哭叫声。
“本杰明?”母亲问道。
我使劲抓着门框,却觉得虚弱无力,快撑不住了。我头昏眼花,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条黑洞洞的隧道,隧道那头,我母亲坐在我妹妹的床边。那儿突然离我好远。我跪了下来,死死抓着门框,可还是觉得我好像要掉进洞里去了似的。死了?不,还活着。那我要说什么?我的所见所闻又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想法如一道气流般冲口而出。
“萨姆……我想萨姆她……”我说。
我话没说完,母亲就抓住我,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她轻轻地把我转过来。她小小的身体里所蕴含的沉着与力量超出我的想象。我现在侧躺在过道里,母亲冰冷的、散发着冰块味道的手捂在我的嘴上。
“嘘,嘘,嘘。”母亲说道。
那天晚上,我父母亲去布莱森家待了一小会儿。母亲穿了一条棕色的裙子,袖口和领口处镶着深红色的蕾丝。父亲穿的是他那套黑色套装。去之前的那天下午,我母亲给他们家炖了一锅肉,足够他家六个儿子吃的。母亲把胡萝卜和土豆都切得很大块,因为她的手颤巍巍的。她清理鸡仔时手在发抖。而现在,这锅炖菜装在我们家唯一一个体面的餐具里,那是只白色的大陶盆,配有一个又大又宽的盖子,侧面画着蓝色的花朵。母亲端着这盆菜时,我发现她几乎站不住了。恐惧全力而至,我们都被它震慑住了。我们全家慢慢认识到,这种恐惧能够强迫我们的心智进入一种痛苦万分、反复无常的状态。父亲从母亲手上接过那盆炖鸡肉,领着她穿过花园,小心翼翼地踏上布莱森家屋前的台阶。
萨姆比露丝矮几英寸,但有着一头跟露丝一样的深棕色头发。她现在躺在餐桌上,穿着她那条白色的礼拜裙。验尸官还没来。该如何对待这个小女孩呢?对她来说,她不该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把她放在自己房间?或许他们受不了那个房间了。布莱森太太从我父亲手上接过那锅炖肉。她的头发有的呈银灰色,有的呈浅金色,一缕缕纠结着,包住了她那张哭肿的脸。她把陶盆放在自己脚边的地板上,然后觉得放错了,又把它挪近餐桌,之后又突然转过身去,把盆子放到了客厅的架子上,好像这盆子是个装饰品。
我父母简直都不敢看萨姆。他们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布莱森太太开了口:“我们非常抱歉。那几个小子昏了头,什么也不懂。”我母亲使劲地来回摆着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说:“别说了,别说了。”因为她得拒绝这份道歉,拒绝布莱森太太话中未道明的那层意思,也就是接着该轮到露丝了。
那天晚上,我待在露丝身边,等着盖在她脖子上的毛巾变热,等着把它拧干,再换上另一条在我脚边的冰水里泡凉了的毛巾。镀锌金属桶的桶壁上,渗出了一些水珠子。这些水珠子又同挂在它们之下的一些小水珠子汇集到一块儿,形成一条条长长的水流,沿着桶壁往地上流。当我把水桶移向床边时,水桶在还没完工的松木地板上留下了一圈圈湿润的水印子,每一圈水印都是不同圆心的弧线,好像是有人在徒手画一个圆圈,把每一道弧线收紧,想要尽量画得圆一些。
在葬礼仪式上,牧师引用了《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来布道。牧师是个年轻人,又瘦又高,有一头黑黑的鬈发,表情有点凶。他属于那种因为太紧张,才表现得一本正经的牧师。我和母亲参加了葬礼,父亲陪着露丝。我现在知道了,妈妈当时一定非常渴望,甚至是非常需要离开那个葬礼。她听牧师布道时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这个年轻牧师说道:“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做多疑的多马,怀疑主的复活。正如我们的主曾对他说,‘伸出汝之手,放于吾之侧;勿多疑心,宁信为上。”牧师抬起眼来,看向布莱森一家,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又过了好一会儿,才找着刚才读到的地方。他的沉默突然让人明白,此时无声胜有声。对我来说似乎过了许久,牧师终于才又接着念道:“正如我主对多马所言,‘未亲眼所见,然笃信之诸人,主必佑之。让我们祈祷吧。”
笃信之人,主必佑之!露丝比萨姆晚一天发烧,她也会比萨姆晚一天离世。露丝会追随萨姆去哪儿呢?随便哪儿吗?去某个看不见的无极世界?我们等待着。我知道,如果母亲在祈祷的话,一定不是希望露丝去那个看不见的世界,而是坚定地希望她不要去。我母亲是个眼见为实的女人,她会骄傲地伸出她的手,不会有一丝忏悔。
对布莱森一家来说,死亡平淡无奇,只是肉体上的折磨。他们还没懂得害怕,死亡就已降临。对我们来说,死亡更加恐怖,它挥之不去。它那酸臭的味道在我们家中跳动。死亡通过一个词将自己呈现出来,那个词就是:牛奶。我们努力不去想这个词,但是恐惧已经控制了我们脑子中的词语,把我们又慢慢拉回到那个词。在前门,微风吹向我们家,树叶嘶嘶作响,我能清楚地听到那个词,同屋门一块儿摆动着,一遍又一遍地:牛奶,牛奶,牛奶。我们为悲痛所环绕,等着卸下惴惴不安的心绪。
萨姆死后,我母亲就不在自己房中睡觉了。她双唇总是难以察觉地嚅动着,念着祷词,甚至在椅子上小睡一会儿时也是这样。每次她醒过来就要抽搐一下,好像整个房子在路上颠了一下。然后她就会往床上看看,仿佛觉得床上是空的,好像露丝已经被颠下了床,从地缝里掉了下去,再也找不着了。
母亲前去露丝床边量她的体温时,走得非常慢,好像是在警告高烧,她要过去了。然后她每次都会站那儿好几个小时,一只手贴在露丝一边的脸颊上,重心无意识地在双腿间转换,眼睛通常都闭着,不过有几次是目光空洞地盯着窗外。
这样过了一周。高烧不再起伏不定,而是持续高热。
在八月末的一天晚上,母亲醒来,觉得房间里吹拂着一股新的并且异样的微风。这是高烧轻轻地在运动,在往屋顶上飘着,母亲是看不见的。
我不知道露丝是不是要随萨姆去那个地方。在那儿,高烧不会从你的头发里流淌出来,而是将你升起来,带你进入另一个光明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更加模糊不清。我们还没有机会告诉布莱森一家。而且,我们要跟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该等露丝好一些,能去花园或者跑来跑去,像个幽灵似的打水了的时候再说呢?
吊桶现在半满了。我从泵嘴上提起把手,将它放到我脚边的地上。我把头深深扎进大桶中,水立马就涨到了桶口那儿。我继续往下扎,把双肩也埋入水中,桶中的水于是溢了出来,流到草地上。我感觉到水从我的脚趾缝间流过,冰凉了我脚下湿湿的泥土。我再一次一头扎进桶里,这次我让水淹过我的胸口,直淹到我肚子。我伸出双臂,抵着桶底,用双手感受着光滑的桶壁。
我把湿衣服脱下来,把脸埋在上面,这样过了好久,我才把衣服揉成一团,又把它贴在我的脸颊之上。
“烧退啦,”我说,“妈妈,烧退啦。”
我绕着井边转圈,手里还抱着我的衣服。
“烧退啦,”我又说,“妈妈,烧退啦。感谢你,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上帝。”我说道。
我把那桶水从地上拎起来,把它想象成是一整桶的热牛奶,大大地喝了几口。屋子上空,我妹妹高烧散发出的那一团炽热的光飘入了夜色之中,四散开来,变成无数个光点,最后如燃尽的繁星般被黝黑的苍穹吞噬掉了。
我把新打的水提进家中,放到餐桌上。我父母亲在客厅中轻声交谈着。我在门厅那儿站了一会儿,等着看他们会不会抬头看看我。他们并没有。我去找露丝,靠在她的床边。我头发上滴下来几滴水,滴到了露丝的枕头上,枕套上浮现出几处水渍。我在露丝的嘴角上亲了亲,想看看她会不会醒。露丝没醒,我又把嘴凑上去,亲了亲她的下嘴唇,用我的双唇含着她的。露丝的双唇凉丝丝的,有些苦涩,像是煮熟的柳皮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