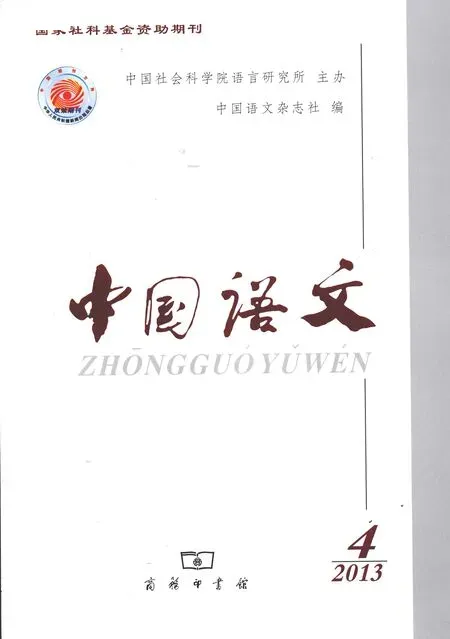社会性别平等、自然附着成本与再分配政策
朱柏铭
社会性别平等、自然附着成本与再分配政策
朱柏铭
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无论是税收制度还是转移支出机制,均存在性别盲视的缺陷,看似中性的政策措施,背后存在着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再分配政策,应考虑不同政策手段可能产生的不同性别影响,关键是让自然附着成本由女性为主承担转变为由男女两性共同分担。家庭—社区—政府联动是这一目标的实现模式,税收与转移支出政策均应支持家庭和社区共同提供照顾服务。
社会性别;自然附着成本;再分配政策
一、引言
主流经济学认为,由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和供求均衡所决定的收入初次分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能够保证效率,但不能保证平等。税收和转移支出制度的实施,不会损害市场机制有效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从而增进社会的福利。
然而,传统的再分配机制存在社会性别盲视(Gender Blindness)的缺陷。税收制度的设计往往忽视男女两性在取得收入时支付的成本大小,也不考虑两性对某些商品(如化妆品)的偏好差异;在安排转移支付时,无视两性对财政支出项目(如社会救助、卫生健康)的不同需求,从而在客观上限制了性别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以通常的眼光来审视,税收和转移支出不去刻意强调性别倾斜,那是公平公正的。其实,忽视再分配政策对不同社会性别群体的影响,并非是“性别中立”,恰恰是社会性别盲视。
主张再分配政策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就是要从社会性别视角(Gender Perspective)去考察,不仅关注再分配政策中的显性内容,更审视其中的隐性内容,即那些看似中性其实隐藏着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内容。
二、概念释义与文献回顾
(一)概念释义
1.社会性别平等
在英文中,Sex和Gender两个词都表示性别。但是,Sex指生理性别,而Gender指社会性别。《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简言之,Sex指的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男女特征,而Gender则是以文化为基础作出的关于男性或女性的判断,以及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不同角色的期待和规划。
社会性别理论是要从探寻两性关系的奥秘入手,寻找建构良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的新途径。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必须变得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说所有的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不受生理性别观念的限制,自由发展个人能力,自由作出选择,其不同行为、期望和需求均能得到同等的对待。
2.自然附着成本
通常认为,自然附着成本(Naturally Attached Costs)是指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从事生育孩子、操持家务等劳动。主要包括生育成本、补偿性工资、预期的低劳动生产率、转岗培训成本和额外福利成本等几个方面。自然附着成本是企业不愿意吸纳女性为其雇员的主要原因。
生育成本是指企业为女性雇员在生育和哺乳期间付出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补偿性工资是指较差工作条件下,为吸引雇员所必须支付的额外工资;预期的低劳动生产率是指女性雇员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男性雇员;转岗培训成本是指女性雇员倾向于选择语言类或服务性的工作,如果让她们转向高科技含量的岗位,企业需付出较多的培训费;额外福利成本是指女性雇员要比男性雇员提前退休,而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雇佣女性员工即意味着承担额外的福利支出。
(二)文献回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经济学,注重从社会性别视角评判公共政策。相关的文献很多,其中“照顾劳动”的研究与本文的关系甚为密切。董晓媛认为,照顾劳动(Care Work)是指对人的直接照料活动,比如给被照顾者洗澡、喂饭、带他们去看医生、与他们交谈和带儿童玩耍等。[1]
照顾劳动的性别分工是怎样决定的?G.Becker等学者认为,在家庭成员目标一致的假定下,家庭内部丈夫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的专业分工是由男女之间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男性的工资比女性高,而在家务劳动上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比男性高。家庭内部的专业分工优化了家庭资源配置,不过,家务劳动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有负面影响。[2]
N.Folbre认为,Becker的理论有缺陷:夸大了家庭成员利益的一致性,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没有考虑家庭分工是否公平;家务劳动使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人,在丧偶或离婚时会失去生活来源,女性在照顾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容易贬值。[3]P.England和N.Folbre认为,男女的性别角色是社会构造的,传统的性别规范通过与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男女性别分工。社会对女性无私照顾家庭的赞美,使女性自愿接受了这种角色。[4]N.R.Hooyman和J.G.Gonyea认为,要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使社会充分承认照顾劳动的价值和贡献,降低照顾责任给女性带来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使女性和男性、照顾者和被照顾者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5]
社会政策的制定应以什么样的性别模式为目标?J.Lewis和S.Giullar主张,公共政策通过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促进男女就业工资的等同来实现社会性别平等,还主张把照顾由家庭转移到社会。[6]173-192C.Ungerson主张通过公共政策支持女性照顾家庭,但在经济上补偿她们的贡献,社会保障政策要给家庭照顾劳动者与工资劳动者提供同等待遇。[7]S.Razavi倡导男女共同分担家庭照顾劳动,实现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全面性别平等。[8]
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1995年中国承办世界妇女大会之后,社会性别的概念备受国人关注。国内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是关于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研究,李兰英、马蔡琛等学者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涉及再分配政策中转移支出的安排。[9][10]另外,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也与再分配政策相关。如梁洨洁、张再生认为,有必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人口生育、教育、就业、土地承包等现行公共政策进行反思,加深对与社会性别角色相交织的深层文化观念的理解,实现性别平等。[11]鲍静认为,我国现阶段在就业、医疗保健、受教育机会等许多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12]
总体来说,目前我国似乎没有人专门从社会性别视角去研究再分配政策。这正好说明,揭示再分配政策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并为政策完善提供建议,是很有意义的。
三、再分配政策中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缺失
(一)被“生理性别平等”所掩盖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传统的“性别平等”是一种生理性别的平等。如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种政策本意是要给予男女两性同样的待遇,但在事实上很容易抹杀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变成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从而加重女性的社会负担。
现行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是,职工缴纳保险费满15年后,在退休时享受的保险金是所在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20%。在满15年的情况下,如果多缴费1年,便可提高一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女性的退休年龄要少于男性5—10年,所以,女性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要少于男性。也就是说,女性在退休后领取超过20%比例基础养老金的机会少于男性,从而导致女性在退休后的养老金平均水平低于男性。
失业保险的领取条件也是将男性、女性当成完全相同的个体来对待。其实,单身母亲的生活异常艰难,她们失业之后的负担远比其他群体大。但是,社会保险政策对于她们缺乏应有的倾斜。
医疗保险是为在职人员设立的,就业是加入医疗保险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由于职业的性别隔离,女性就业的机会比男性少,尤其是女性从事正规化就业的机会相对少,这无疑成为女性进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一道门槛。
目前工伤保险的规定,将男性、女性作为完全相同的个体,而忽视了女性的特异性。如今由于辐射等因素,导致婴儿在胎儿期就出现生理或心智不正常,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多,这也是一种“工伤”。但是在现有工伤保险的受保范围中,却找不到适用的条款。
城镇职工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办法规定,企业须按月全额缴纳生育保险费,不需职工个人负担,女职工在职期间生育或终止妊娠,由领取工资变更为享受生育津贴。可事实上,这种社会统筹只限于城镇职工,农村地区企业并不缴纳生育保险费,那些女性雇员就享受不到生育保险待遇;即便在城镇,也不是所有女性雇员都能享受,有些是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以她们的户口不在企业所在地城市为借口,拒绝为她们缴纳生育保险费,于是,这些女性雇员也无法享受当地财政提供的生育保险待遇。
(二)“性别中性”政策中暗含着的社会性别不平等
性别中性政策是指政策制定者尚未自觉地意识到整体社会利益格局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把男女假定为无差别的群体,政策可以无差别地对待。比如,1995年农业部制定的土地政策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没有考虑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体力差别。
税收政策存在“性别中性”的烙印。在流转税层面,现行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税目税率的确定,似乎与性别无关。其实,商品消费是有性别偏好的,如果说,护肤护发品是性别中性的,那么化妆品肯定是有性别倾斜的,女性对化妆品的需求远远超过男性,但是消费税、关税制度却视化妆品为奢侈品而课征,适用的消费税税率为30%,进口关税税率为30%,明显高于一般商品。在所得税层面,企业之间所得税税负与企业雇员的性别比是无关的,企业吸纳的女性雇员多,并不能享受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性别歧视与此相关。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定也没有考虑性别差异。个人所得税税制中设定免征额,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了获取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和费用,二是养活自身、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所必需的开支。两性为获取工资薪金而支付的成本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化妆品支出,对于女性尤其是服务性行业中的女性而言,化妆是工作需要,体现自身的尊严,也体现对顾客的尊重,男性就相对节省了这笔开支。至于老人、子女的养护,如果是双亲家庭,费用开支共同负担,但是在单亲家庭,负担就比较重,现行税制并没有提高单亲家庭的免征额,尤其是女性单亲家庭。
转移支出同样存在社会性别的不平等。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教育投资是按学生人头划拨的,不区分性别差异。其实,有女生住宿的学校,需根据女生生理的特殊需要,优先建设热水饮用和洗漱工程;男女生如厕时间差异较大,女生多的学校,女厕所数量也应增多。这说明,财政投资应该考虑性别比。医疗卫生支出的划拨也较少考虑性别差异。两性对健康卫生支出的需求也是不同的,男性遭受灾害损失的风险较大,而女性保健服务的需要多于男性。可见,如果按性别中性原则拨款,难免失却平等。
四、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目标
(一)自然附着成本的分担:再分配政策的操作目标
再分配政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使两性真正享有平等的地位和人格、平等的责任和义务、平等的职业发展机会、均等的资源占有权利。
再分配政策的操作目标应该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出的作用,使自然附着成本由女性承担为主转变为男女两性共同分担。
如前所述,自然附着成本包括生育成本、补偿性工资、预期的低劳动生产率、转岗培训成本和额外福利成本等几个方面。实际上,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女性怀孕、生产、哺乳等行为的成本,处于孕期、哺乳期的女性既减少工作时间,又分散工作精力,无法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市场收益;另一部分是女性为照看孩子、服侍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居室、购买生活用品等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家务劳动同样不可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收益,是一种家庭无酬劳动。
本文不像女性主义经济学者那样只关注照顾劳动或者无酬劳动(Unpaid Work)。因为在笔者看来,自然附着成本中操持家务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育行为的附带成本,不能只关注照顾劳动而忽视生育成本本身。另外,在社会上免费照顾老弱病残的义务劳动也是一种照顾劳动,但那是互惠利他乃至纯粹利他的表现,有别于体现亲缘利他的家庭照顾劳动。至于无酬劳动,其范围很广,以家庭经营形式表现的小规模企业中的劳动和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也都是无酬劳动。本文考察自然附着成本时涉及的劳动,是指家庭内部的无酬照顾劳动。
作为经纪人的企业,或许无意歧视女性,只不过在规避“性别亏损”而已。但恰恰是企业在乎自然附着成本,才导致女性在就业、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与男性出现差距,进而影响着社会性别的平等。
作为政府,有责任通过政策引导,使自然附着成本让男女两性共同分担。问题是,既然它是“自然”附在女性身上的成本,男性怎么去分担?两性该如何分担,与政府又有什么相干?
第一,自然附着成本让女性为主承担,这是社会经济制度被扭曲的结果。
怀孕、生产、哺乳等直接的生育成本由女性承担,那是“上帝”安排的结果,男性无法替代,说它是一种“自然附着”的成本无可争议。然而,照看孩子、老人及买菜、做饭等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那是有失公平的。究竟有多少成分可以归结为自然的属性,着实令人怀疑。
大量繁重的家务劳动跟女性的生理、心理没有太多的必然联系,属于非“自然附着”的成本,本来可以由男性分担一部分,如今却主要压在女性的肩膀上,这可能是家庭成员出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协商的结果,也可能是男性强权施压的结果。但是,无论怎样,背后一定与社会经济制度有关,是某种制度设计驱使男主外、女主内。扭曲的制度使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实现了,女性自由、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却被葬送了。
第二,要肯定女性的生育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外部性。
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生育的外部性主要是负向的,庞大的人口已经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社会生育成本实际上就是个人生育行为的负外部性。
在人口总量过多的前提下,生育行为对于社会有负外部性。然而,正、负外部性往往是同时存在的。生育行为有没有正外部性呢?孩子的出生,为家庭养老奠定了基础,给父母带来情感的满足,给社会提供了潜在的兵源、劳动力、社会管理者,也有了潜在的市场需求者。一个社会要保持人口的稳定,每个妇女至少需要生育2.1个孩子。没有生育行为,国家就后继乏人,人类社会不复存在。
家庭照顾劳动对于社会发展也有正外部性。研究表明,对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投入所产生的社会回报率很高(World Bank)。[13]对儿童照顾的社会回报率往往高于家庭私人回报率,因为父母没有对子女财富和收入的产权,他们不能完全收回对子女投入的回报。育儿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越高,社会回报率与家庭私人回报率之间的差异也就越大。
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女性却为生育行为付出巨大的成本。她们特有的生理周期天然地与生育相关;不稳定的情绪是内分泌周期的外在表现;富于同情心、敏感、体贴人等心理特质,也与对子代的投入直接关联;生育行为还可能导致女性出现疾病甚至死亡。
女性作为劳动力较之男性可能处于劣势,但是她们为人类的繁衍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政府应当给她们提供必要的补偿,如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受教育机会等方面享有优先权,这种补偿的经济含义是正外部性的矫正,实质是让自然附着成本由男女两性共同分担。
(二)自然附着成本的分担:“H-C-G模式”
关于自然附着成本的分担,至少可以有两种思路:一是由政府提供有利于女性就业的社会服务,如建公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等,便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二是承认家务劳动有价值,工资劳动者对家务劳动者支付工资,至于谁承担家务劳动、谁外出从事工资劳动,自由选择。
这两种思路都能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但是都有一些缺陷。第一种思路忽略了家庭在提供照顾服务上独特的优势,社会化的照顾服务未必能完全替代家庭照顾,尤其对于孩子和老人。第二种思路将家庭无酬劳动变为有酬劳动,这会遇到操作的困难,每个人从事家庭照顾劳动的质量不同,面临的机会成本不同,支付工资很困难。
笔者主张采用“家庭—社区—政府联合提供模式”(可称之为“H-C-G模式”),即在家庭继续提供一部分照顾服务的同时,社区也提供部分照顾服务,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支持社区建设,并鼓励家庭分离部分照顾服务让社区提供。

图1 “H-C-G模式”示意
让家庭继续提供照顾服务,是为了发挥家庭特有的功能。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了家人的相互关怀与支持,才能消融生活中的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的慰藉和寄托。另外,这也符合中国几千年孝道文化的传统。提倡减轻女性的自然附着成本,并不等于摒弃家庭的照顾功能。
从家庭中分离出来的部分照顾劳动,由社区来承担。社区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实体,是聚落区居民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场所。社区服务体系,包括托儿所、养老院、保健医院、快餐店、净菜店、洗衣房等,便于女性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
在该模式中,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离开政府这个重要的角色,由社区提供服务简直就是空谈。社区照顾要以政府为主,政府资助服务设施和非营利性机构的建设,部分工作人员是政府雇员,社区、家庭和个人的支出负担不多。当然,社区可以吸纳一些私营的商业性服务机构,但要有政策支持。
五、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手段
政府怎样通过政策的实施和引导,使自然附着成本由女性承担为主变为男女两性共同分担?总体思路是,完善现行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出政策,作用于家庭和社区两个领域。在家庭领域,对女性生育行为提供较多的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障待遇;在社区领域,增加财政对城乡社区事务的支出,给社区服务组织提供税收优惠,建构合理的财政转移支出结构等。
(一)税收政策
1.减轻就业者的税收负担
鉴于化妆品是很多女性的工作必需品,妇女用品又与特殊的生理周期有关,建议在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时,采用较低的税率。现在男性使用化妆品之风逐渐兴起,为了体现性别平等,较低的税率也可适用于男士化妆品。
企业不太愿意吸纳女性就业,原因之一是担心出现“性别亏损”。为消除企业的这种顾虑,建议当企业吸纳的女性雇员超过一定比例时,实行企业所得税部分税款先征后退政策。
个人所得税政策要鼓励照顾服务非家庭化。近年来,学界有人主张将纳税单位由个人改为家庭,甚至有政协委员提交了提案。按照美国的税法,已婚者享受的免征额比未婚者少,适用的边际税率反而高。“惩罚婚姻”的后果之一是许多低收入的已婚妇女更愿意在家从事照顾劳动,因为自己外出就业,再聘请佣人承担家务,税负会更重。如果仍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应该研究家庭共同收入如何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在传统观念支配下,家庭财产的孳息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家庭企业收入,通常会归于家庭中较为强势的一方。为体现社会性别平等,税法应鼓励夫妻分割共同收入。夫妻双方都可从家庭中分得一部分共有收入,并以自己的名义申报纳税。但是,在纳税扣除上要给就业者提供更多的优惠。现行每月3500元免征额是不考虑性别因素的,所有就业者都能享受。中国同样存在女性的劳动弹性大于男性的事实,因而要让女性在此基础上再享受一定金额的纳税扣除,扣除额的确定以税负减轻程度能超过家庭照顾劳动社区化或者雇佣保姆的支付成本为原则,以此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在劳动市场上寻找工作。
2.减轻在社区服务的商贸企业税收负担
有人在美国做过调查,就业妻子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约是不就业妻子所花时间的一半,但是丈夫却没有因为妻子就业而多分担家务——就业妻子少做的家务劳动是由她们增加的财力购买劳务解决的。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政府有必要适当减轻在社区服务的商贸企业的税收负担。
商贸企业常常采用连锁经营等方式到社区设立便利店、“菜篮子”专营店、净菜店、洗衣房及各种社区配送服务、代理服务、保健服务等,如果税收不堪重负,他们就难以提供优质的服务。建议适当减免这些商贸企业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
3.生育保险社会统筹改为征收社会保险税
生育保险制度是给孕育后代的女性提供特殊福利的制度,目前国家实行社会统筹办法,要求所有企业不论是否雇佣女性员工,都要缴纳生育保险费。这是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的重要政策手段。然而,从实施情况看,一些企业以女性雇员没有本地户口为借口,拒绝为她们缴纳生育保险费。这说明,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办法存在实施范围上的局限性,筹款方式也缺乏严肃性。
建议选择合适的时机,将生育保险社会统筹改为征税方式,如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合并,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雇主、雇员各自缴纳一部分。以税收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征收,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同时也大大提高强制性程度。
(二)转移支出政策
1.增加财政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社区提供的服务主要有三类,一是社区公共服务,如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二是社区非营利性服务,如居家养老服务、老年活动、社区食堂、日间托养照料、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三是企业在社区提供的营利性商贸服务。这三类服务中,第一、二类服务都要由财政拨款为主供给经费,否则难以保障。
财政增加城乡社区事务支出,除了靠公共财政预算之外,还应从政府性基金中划拨。将来条件具备时,开征房产持有税,就可以从该税种收入中划出一部分用于城乡社区事务。将地产受益用于社区服务,改善居住条件,进一步提升社区的房地产价值,这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做法。
2.优化财政转移性支出结构
某些财政经费的划拨要考虑员工的性别比例,如保健支出。男女员工患病的种类有差别,因而,男性员工多的单位,野外劳动伤害、自然灾害伤害的补助费要多一些;女性员工多的单位,慢性病、妇科病补助要多一些。职业病的患病概率可能相差不多,经费可以按人头划拨。
某些财政经费的使用要给男女两性同等的机会,如医疗保险支出。目前医疗保险仅仅为在职人员设立,就业是加入医疗保险的前置条件,这就造成家务劳动者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待遇差别。今后要让家务劳动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有机会加入医疗保险,且享受同等的待遇。
还有一些支出应该向女性倾斜。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中没有向女性倾斜的理念,财政预算的安排都是“性别中性”的。从理论上说,建构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应该是为男女两性提供平等的机会,不能认为凡有利于女性利益的规定就是合理的,凡不利于女性利益的规定就是不合理的。但是,从自然附着成本的特点和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看,的确需要给女性提供利益倾斜。这是因为女性就业比例低、失业率高、老年丧偶比例高,她们对社会救助的需求高于男性。建议采用有助于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手段,如凡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产妇,在休产假期间可领取政府发放的产假补贴,逐月递减;职业女性送孩子上公立幼儿园,免除费用,孩子还可享受一顿免费午餐;丧偶、离婚及长期患病的老年妇女,在规定的次数范围内,可以找社区护理工上门服务,费用由政府负担。
六、结束语
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应当是开明的、宽容的。然而,无论是税收政策还是转移支出政策的设计,对自然附着成本的界定都是一件棘手的事。每个女性、每个家庭,都有自然附着成本,可是在总量与比例结构上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给成本补偿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尽管如此,笔者仍然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把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再分配政策,是公共经济研究中不可逆转的方向。
[1]董晓媛.照顾提供、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09,(6).
[2]Becker,Gary.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Economic Journal,1965,(75).
[3]Folbre N..A Theory of the Misallocation of Time[A].Folbre N.,Bittman M..Family Time: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e[C].New York:Routledge,2004.
[4]England,Paula and Nancy Folbre.Contracting for Care[A].Marianne A.Ferber and Julie A.Nelson.Feminist Economics Today: Beyond Economic Man[C].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
[5]Hooyman,Nancy R.and Judith G.Gonyea.A Feminist Model of Family Care:Practice and Policy Directions[J].Journal of Women and Aging,1999,(11).
[6]Lewis,Jane and Susanna Giullari.The Adult-worker-model Family and Gender Equality:Principles to Enable the Valuing and Sharing of Care[A].S.Razavi and S.Hassin.Gender and Social Policy in a Global Context:Uncovering the Gendered Structure of the“Social”[C].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6.
[7]Ungerson,Clare.Social Politic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are[J].State and Society,1997,(3).
[8]Razavi,Shahra.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conomy of Care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A].Gender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Paper No.3[C].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
[9]李兰英,郭彦卿.社会性别预算:一个独特视角的思考[J].当代财经,2008,(5).
[10]马蔡琛,季仲赟,王丽.社会性别反应预算的演进与启示: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考察[J].广东社会科学,2008,(5).
[11]梁洨洁,张再生.透视我国公共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首届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论坛”综述[J].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5).
[12]鲍静.应把社会性别理论纳入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06,(8).
[13]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 and Development[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责任编辑:张艳玲
Gender Equality,Naturally Attached Costs and Redistribution Policy
ZHU Baiming
The traditional 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y,no matter the tax system or the transfer expenditure mechanism,had defects in terms of gender.While the policy measures seemed to be neutral,there were hidden defects of gender inequality behind them.Therefore,the New Redistribution Policy should concentrate on reducing the different gender effects caused by different policies.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 naturally attached costs need to be shared between men and women,instead of only being shouldered by women.This goal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united efforts of the family,community and government.Additionally,the tax system and transfer expenditure mechanism need to provide enough services and support for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y.
gender;naturally attached costs;income redistribution policy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2.010
:2013-02-20
F062.6
:A
:1007-3698(2013)02-0060-07
朱柏铭,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31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