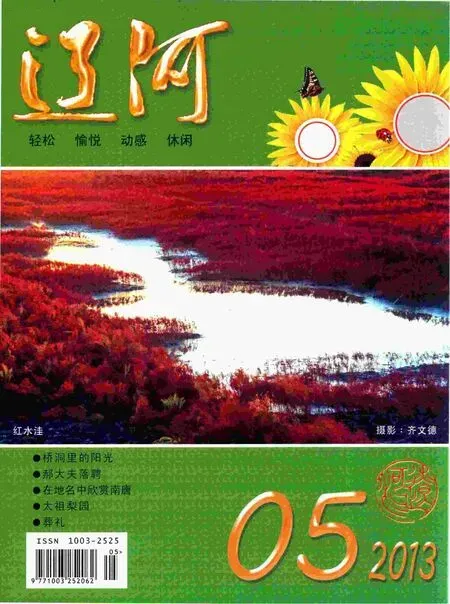在地名中欣赏南唐(外一篇)
石红许
我们外出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从地名开始的。经过千百年留存下来的地名,都是经得起反复推敲而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们认识每一个地方,首先接受的是地名的照耀。地名,就像一盏高高悬挂的明灯使我们不迷失方向。
生活在鄱阳、上饶,工作之余,喜欢四处走走看看,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一头钻进破旧的弄堂、蜘蛛网缠绕的老宅,也会翻地方志、史志等书籍,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怎么辉煌的南唐却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少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即地名符号,他们就像血脉一样贯穿在这里的山山水水间,不事张扬,一千多年来,默默地任人叫着名字,比如德兴、铅山、石塘、(沙溪)龙门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南唐如此眷顾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如此依赖南唐?
回顾南唐,我们只能从“五代十国”去筛寻,我想,这是它不怎么起眼的原因之一吧。一个跨越时间短暂的王朝,定都金陵,才39年(937年—975年)残破江山,却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生活富裕,“比年丰稔,兵食有余”,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南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权之一。然而,它最为读书人记住的倒不是这些政治的、经济的东西,恰恰是后主李煜的一首《虞美人》,全词仅仅56个字,却被千古传诵,个中况味,不一样的人生读出不一样的意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一个断送了王朝被俘的皇帝,我原先并不怎么喜欢他,而今,我越来越觉得有几分亲切,李煜是父母官啊,尤其是文化人的明君。南宋鄱阳洪迈欣赏过一幅王维的名画《辋川图》临摹本,并以文记录之,载画上钤有南唐李氏所用印: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遗憾这幅画在鄱阳已经找不到踪迹了。由此可推测,南唐是个诗词书画繁荣的社会,文人不必担心怀才不遇,尽可大展身手。假如,我们生活在那个朝代,我想,他一定会读懂我们的,“爱卿免礼平身”就会常常在耳畔荡漾。那是读书人修来的福分,文化人在南唐是扬眉吐气的。正是因为有了南唐重视文化人尊重文化人的良好开端,所以为宋朝文化人地位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人当感谢南唐,其功不可没,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观点在南唐受到了正面挑战,文化人不必当官同样享有崇高的地位。
“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多么诗意的语境,多么宜居的环境,多么安宁的国土,南唐是人类追求的美好幸福生活的一个光辉典范。然而,在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群雄纷争,谁不厉兵秣马,谁就会被淘汰出局。歌舞升平的鱼米之乡——南唐,没有扩张野心,缺乏开疆辟土雄略,很快被由周世宗柴荣掌权且日益强大的后周撕开一道血口,经过三年征战,至958年李煜即位时,南唐辖区的长江以北地方尽归后周据有,连饶州(鄱阳)实际上也已被周世宗攻取,为日后宋军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南唐的结局是美好河山拱手送人,连同后主也一起被宋掳走到开封。我们失去了一位皇帝,但是,却升起了一位多才多艺、多愁善感的词人,李煜是中国词坛的第一座高峰,我们说他是宋词走向辉煌的开路先锋,一点也不为过。我们可以去痛斥李煜政治上的不思建树,甚至我还可以去讥笑李煜的卿卿我我、缠绵悲切,面对亡国,李煜不是反抗(纵然反抗,不啻于飞蛾扑火),而是淡定环顾金銮殿,在丝弦竹管莺歌燕舞下,吟唱词曲《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当时李煜的心情谁能读懂?江山社稷丢弃了,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李煜准备好了柴火选择自焚,最终胆怯战胜了慷慨而未果。但是,我们何不想想,人啊,为什么总要以战争这种极端的形式征服对手,使得和平成为奢侈的追求。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无情的战争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池,一个又一个文明也早已沦为陈迹。看来,人类走向大同的路确实很遥远。
说实话,我本不会去刻意关注小小王朝南唐的,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统治时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它的背影实在太渺小了。函授期间学的虽然是历史专业,写毕业论文时没有考虑在南唐里作文章,原因是由于史料很少。工作之后,职业的关系,我有条件深入周边县乡,那南唐的风,不经意就以地名的符号进入我的视线,在我的耳畔萦绕,以至于我不得不去关注起南唐来。江西是南唐唯一一个完全统治的省份。像靖安、清江、德兴、上高、上犹、铅山、瑞金、龙南、瑞昌、湖口、吉水、石城、东流、龙泉、宜黄、万安、奉新等县就是在南唐时所置。江西与南唐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那是无比的密切,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洗礼,这些县名依然飘扬在江南大地上,南唐为奠定江西县域政区的格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上饶就有两个县市德兴、铅山是南唐的产物,这些地方的城镇无不弥散着南唐的韵味,所谓“德兴”,取“惟德乃兴”之义,于南唐昇元二年(938)置县;铅山是保大十一年(953)置县,县治永平镇,因附近有铅山,故有县名。两地均是因为采矿业的兴旺而由场升格为县治。还有,像铅山重镇江南纸都石塘,又是中国“茶叶之路”上武夷山红茶的重要集散中心,就是南唐保大十一年所置。饶州在南唐时还一度改叫永平军。那时,江西远离战火,百姓只顾埋头发展经济,增置的各县大都是在开发得比较好的场、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千余年前就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江西是个好地方”。
沧桑岁月,季节轮回,随着世事的变迁,经济的推进,如今,许多老的地名正在慢慢的冷清,慢慢的消失,有的甚至将一去不再复返。这就出现了一个课题,抢救保护老地名。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级人大、政协、文化界人士已经自觉觉醒,抢救保护老地名呼声日渐高涨,有关建议、提案、报告等占了相当的比率。老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承载着许多历史信息、传说掌故和文化内涵,不能说丢就丢,必须抢救保护老地名,甚至可以考虑在新开发的小区、现代建筑、新建的道路等融入老地名,从而唤起更多的人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些有着历史年轮的地名符号,非但不会消失,而且还会越来越光大,它们以自己的方式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依然静静地屹立在老地方守望着家园。
如今,有些地方,为了恢复原有的已经融入灵魂深处的地名,甚至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向上一级一级申报,因为好的地名就是一张无形的文化名片。鄱阳在解放初期即1957年改为“波阳”后叫了近半个世纪,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即2003年才还其本名。湖北襄阳是一座古城,阴差阳错改为襄樊后似乎割裂了历史,让多少人魂牵梦绕总觉得不习惯,恢复襄阳的呼声日益高涨,终如愿以偿。我以为,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老地名叫了两千多年。一个地名,不要单纯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口头飘扬的历史记忆。
学历史、聊历史,我们往往不经意为汉、唐的强盛而骄傲。作为江南人,我们绝不可以忽视那个偏安温柔乡里的南唐,它虽然弱小得不堪一击,但它的强大体现在文化上。什么是江南?我以为,从地理概念上来说,南唐的辖区就是江南,长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就在南唐。从品格上来说,江南是水性的,江南是诗意的,江南是兼容并蓄的。
平日里,或许我们不小心呼唤一下地名,很可能就呼唤到了南唐的温情与风物。这就是我脚下厚实的土地,顺着老地名这条线去寻觅,我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经坎坷走过来的。
记忆里散落的家园
没有机器响的日子,宁静的村子显得无比的空旷和低碳,童年的夏天,仰望头顶永远是瓷蓝瓷蓝的天空,因为有抽水机的弥散而充满了响亮的意趣。
“Z”字形的摇把由慢到快,循序渐进旋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轰、轰、轰……”随着一股黑烟腾空而起,很快飘散在田野上,抽水机开始欢快地把歌声送往田间地头为小麦、水稻或棉花伴舞。村背埠头是我常常光顾的地方,我并不反感站在抽水机旁彼此说话听不清楚,傻傻的在那里看师傅怎么加固螺丝、添柴油、上皮带,怎么把机器弄响,听抽水机声是我小时候借助耳朵贴近机械化生活的唯一途径,单调、不知疲倦的抽水机给了我比家乡的小河还长的想象和日出日落一样简单的开心。
摇摇把也是一门学问,弄不好会反弹到自己,机器歇下来,趁师傅不注意,我也会使出吃奶气力学着师傅的样子用力去摇,才明白自己表演了一幕蚍蜉撼树。至于为什么要把水从小河里引入高处修筑的渠道,是我当年一直不关心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跳进渠道的水里嬉戏,去体验冲浪的感觉,更好奇的是水怎么从管子里出来,我的快乐却往往由于抽水机师傅莫名其妙的呵斥“想死啊——”而化为泡影。抱起湿淋淋的衣服,走了一些路,转过头,我会不知好歹对着远处的师傅扔下一两句粗话,甚至捡块小石头朝抽水机的方向以抛物线的方式示威,然后撒腿就跑。
过了几天,我没心没肺忘记了对抽水机师傅的无礼,又无忧无虑过来看他熟练地抡起摇把发动机器,可恶的师傅总会扬起那钢铁摇把凶狠狠地瞪我一眼,心情不好时还会拧我耳朵报复我,质问我上次为什么骂他,我就学语文课本上刘文学的样子宁死不屈,把师傅想象成偷摘生产队地里辣椒的地主。更多的时候,他也就做做样子而已。在村里,师傅比较受人尊敬,况且我们村只有一台抽水机,它离村庄有一里多路,搭建了简易的棚子遮风避雨。抽水机一般还难得响,我总盼望一身油渍的它响起来,寂静的村庄会因为它的响声的填充而明媚、生动、饱满起来,现在终于明白儿时的无知,抽水机一响就意味着干旱或内涝,队长的眉头就会皱起来,担心收成。看来,抽水机连同师傅的地位比它的响声高。到了冬天,抽水机派不上用场近乎冬眠,怕有梁上君子的惦记,生产队里会派强壮劳力将抽水机抬进队屋保养,来年春天再弄回埠头草棚里,日夜守护着全村的丰收。
抽水机师傅和我同村的,同姓,他是生产队长的儿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乡村,开拖拉机的、碾米机的、抽水机的,还有进合作社(就是商店)当营业员的,大都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子女。我那时也就十岁左右,成天就知道混玩,书包、书本是放学路上很不错的武器。但是,对类似于那抽水机师傅的职业我是又敬又畏,甚至把想当一名拖拉机手的理想呈现给了作文,那个摇响机器的勇猛连贯动作我用成语“一气呵成”描述还得到老师的夸赞呢。
那个时候,农村最接近科学、最先进生产力的东西就是三机四机的,比如拖拉机、碾米机。假如在村子里来了辆绿色吉普车,总给人一种不太现实或者不真实的感觉。我姑夫在景德镇市直机关做事,逢年过节,就会调部车过来看我奶奶,村里人都觉得很新奇,纷纷过来看车子、凑热闹,当时我也觉得特别神气,以治安巡防队员般的警惕性忠实地守卫吉普车,不许邻家孩子接近去摸去碰,那几天,我很山大王,同伴们都比平时听话,但这种良好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就被乡村的无聊乏味冲淡。一年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过年,儿时最向往,有时,妈妈手里的活忙不过来,会叫孩子们到合作社打瓶酱油,或称几斤盐,我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干,其后就用几个剩钱买糖果或几卷纸炮回去,妈妈是不会吝啬的。怀揣纸炮,会有一大帮伙伴围绕,此时我很有号召力。找来尖石头一锤,“叭”,脆亮的响声连同自己的喜悦一起在伙伴们周围炸开,享受到的是乡村孩子那最淳朴的几分刺激带来的快乐。其时,印象中最深的还是碰上谁家宰杀“年猪”,可兴奋坏了以我为首的一帮凑热闹、瞎忙乱的小家伙,从捉猪时起,便围着看大人如何绑、杀、烧开水褪毛、取猪头、倒悬在木梯上、剖肚翻洗大小肠……整个过程我全看个彻底,大人们也不责骂,要在平时,早把我们轰散开。捡起猪脚趾壳,装些案板上的碎肉,放在烘桶里煨,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肉让人垂涎三尺,我半生不熟地吃起来,便觉得是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了。其实我家在村子里地位并不高,一是论辈分偏低,二关键还是家里成分偏高,据说是上中农(在农村有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划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到历史书里去了解详细意思了),不过好在没有影响升学,也没有给我平时的生活带来阴影,现在想来才清楚毕竟上中农也是要求团结、争取的对象。
还有一个和别人家不一样的是,我家居然没有放养生产队里的耕牛。我像一个没有恋爱的孤独孩子,站在栎子树下发呆,很羡慕不少伙伴放学回家骑牛出去到村前的草洲放养,炊烟飘散时分,在夕阳里他们带着饱满的神情、拖着老长老长的影子缓缓而归。这个“牧归图”已深深地烙进我的脑海,多么的诗情画意啊,而听得最多的是大人的软硬兼施:“不好好读书,放牛种田去!”我常常纳闷,放牛——那么美好的事,怎么被当作吓唬人的代名词了。那时,我显然没有听过贺绿汀创作的驰名世界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但我特陶醉那样的情景意境,这是与我的儿时生活息息相关的啊,遗憾的是我只是当了一名临渊羡鱼者,以至至今我也没有掌握骑牛的本领,虽然在读师范时学会了吹一手漂亮的竹笛,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当一名优秀的牧童了,只能选择到舞台上演奏陆春龄的《小放牛》,而那种原生态的味道怕是永远也无法通过笛孔表达出来。
对啦,说到草洲,那是鄱阳湖的温床,那是我从小摸爬滚打的家园。那里生长着两样植物,遍地都是,挖出来,洗干净取根剥皮,可以生吃,味道甜,有点粉,学名我说不上来,土话分别叫做“叽葛哩”、“老虎姜姜”,“叽葛哩”像微缩版的葛,开紫色的花,皮是褐色的;“老虎姜姜”则像葱蒜,开白花。更多的时候,我的眼睛比鄱阳湖畔无边的草洲空旷,面对没什么零食吃没什么玩的偏僻乡村,我们只能选择泥巴水草为伴。因为有“叽葛哩”“老虎姜姜”的点缀,草洲给饥饿的岁月带来了许多的欢笑,它们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成为那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当年,我羡慕死了城市的公园,每天面对的是毫不起眼的草洲。而今,草洲拥有一个时髦诱人的名词:湿地。有的地方开始建湿地公园,叫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带之不走的草洲资源吸引游客。草洲还是那个草洲,居然换个叫法身价倍增也能卖钱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叫旅游了。
我一直没去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资格养耕牛,难道是照顾我家没有剩余劳力吗?还是妈妈为了考虑我们学习而拒绝了生产队的安排?现在妈妈年岁大了,我想当时应该是有很多原因生产队才不给牛让我家养吧,时过境迁,何必再去勾起老人家对那段酸楚往事的回忆。恰恰相反的是,除了缺穿少吃,我并没有感觉受到什么偏见和歧视,我还是很喜欢、留恋在老家的日子。
记得我家菜园离村庄有一里多路,妈妈弄农家有机肥去园里时,总要我在前面搭把肩。这是我唯一乐意参与的家务活,到了菜园扁担一放就可以在山水田垄间去放牧一颗稚嫩的心灵。那个时候,渴了,蹲下去掬一捧田沟里流淌的溪水喝,绝对不用担心是否有农药、除草剂的残留。这是乡村留给我最沁人心脾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