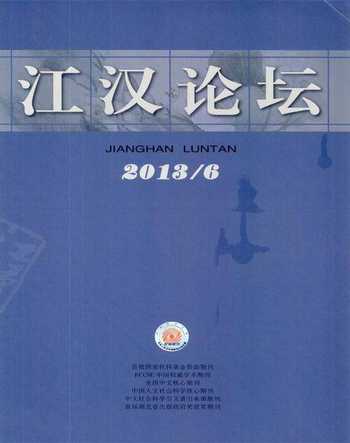规训与政治:儒家性别体系探论
杨剑利
摘要:“五四”妇女史观认为传统中国妇女在儒家性别体系中受压迫,海外学者高彦颐教授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五四”史观解释不了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用“受压迫”来形容儒家女子的处境是不恰当的。本文通过疏解作为儒家性别体系支柱的性别规训,如“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和“以顺为正”,揭示了这些规训与儒家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指出儒家性别体系是儒家政教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探讨其稳定性和延续性需要超越性别视域。在辨析高彦颐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她对儒家性别体系的阐释不过是对“五四”史观作的一个另类注解。
关键词:性别规训;儒家性别体系;儒家政教体系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94-08
传统中国妇女在男尊女卑的儒家性别体系中一直受压迫,这个由追求男女平等的解放话语建构的史学信念主导了“五四”以来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几乎没有受过怀疑。然而,近年来海外学者高彦颐教授提出的反“五四”妇女史观动摇了这一信念。她的挑战是:既然妇女普遍受压迫,为何她们不反抗儒家性别体系,而让其顺畅运转了那么久?“五四”开创的现代正统史学应该要对此做个解答。但在她看来,正统史学的解答不会令人满意,因为传统妇女实际上并没有经历“五四”公式描绘的那种压迫,祥林嫂的受害者形象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是“非历史的”发明;“五四”史观最大的失误就在于错把“应然的”准则当做了“实然的”事实。为了解释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她提出了“好处”说,认为该体系具有弹性,女性可以利用它获得“好处”,并能在其中享有“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毋庸置疑,高彦颐提出的问题和看法都带有颠覆性,她的开创性工作在给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带来启发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高彦颐的反“五四”史观创造了众多可供争辩的话题,其中最核心的当属“儒家性别体系”,本文亦拟就这一话题做个探讨。按高彦颐的观点,儒家性别体系是一个伦理体系,其中有两根支柱,分别是“男女有别”和“三从”。本文也将以此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所不同的是,本文还将关注另外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性别规训:“男尊女卑”与“以顺为正”。这些规训相互关联,纵贯了儒家传统社会,不仅是儒家男女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而且也是构建儒家性别体系不可或缺的要素。通过疏解,本文试图揭示这些规训与儒家政教体系之间的关联,而这对于我们明辨高彦颐的挑战也许会有所裨益。
一、“男女有别”:从“父子亲”到“国之大节”
如高彦颐所见。“男女有别”是儒家建构人伦秩序的一条基本准则。《礼记·郊特性》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男女有别”被看做是万物相安的源头,也是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之所在。《礼记-昏义》云:“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男女有别”亦被看做是君臣之道的本源。
作为人伦准则,“男女有别”可以追溯到周代。在周代,“男女有别”有三重涵义:性别隔离、性别分工、性别塑造。
性别隔离是指昭隔内外的“男女大防”,如:“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榈,内言不出于榈。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外内不共井,不共滔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等。性别隔离制造了对后世影响极深的“男外女内”的空间分割观念,历代“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民宅的功能布局即是此种观念的一种反映。
性别分工原则也是“男外女内”,如《周易·家人·彖传》所言,“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在周代,内事主指蚕织、中馈、生育,外事主指耕事、政事。⑨这种“男耕女织”式的内外分工与“男外女内”的性别隔离相一致,一般也被看做是“男女有别”的题中之义,但需要指出的是,
“男耕女织”式的分工在周之前就已基本定型,殷商甲骨文中的“男”“女”二字仿“男耕女织”的构形就是明证,这说明性别分工要早于“男女有别”这一规训的提出,性别隔离的“男外女内”原则也应该是根据性别分工而来的。这其中的因缘关联不应颠倒。
性别分工界定了男女的社会角色,而为了让男女在成年时能担当既定的角色。他们就要被不同的方式培养和塑造。《诗经·小雅·斯干》有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说明了男女一出生就被区别对待,并被赋予不同的社会角色期盼。《礼记-内则》载有为实现这份期盼而采行的塑造方式: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红组钏,学女事以共衣服。……十有五年而笄”。这里说的对冠笄之前男女的培养和塑造,显然是为了婚后“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这种性别塑造印证了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周代的性别隔离、性别分工、性别塑造相互关联,共同营造了“男女有别”,儒家“男外女内”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来源于此。这里有个疑问:周代的“男女有别”缘何要性别隔离、男女严防?这个问题涉及了父权制的原始秘密。
如《礼记》所言,“男女有别”的初衷是为了明父子亲,即确立父子间的血缘关系,所谓“父权”,最原始的含义就在于此。我们通常对父权采用一种字典式的理解,而对它的原初意义缺乏反思。父权不像母权那样是天然的,在部落群婚或“多妻多夫”时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知父”有赖于“一夫制”,而从“聚生群处”转向“一夫制”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代应该还处在这一转折之中。《礼记》说“(男女)无别”是“禽兽之道”,孔子说“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唐”,都包含了对“聚生群处”的贬责。金景芳曾说,“‘男女有别的真实意义说穿了就是严防异性之间发生性行为”,此言虽简,但一语破的。“男女有别”、性别隔离的真实意图就是为了扫荡“聚生群处”,解决“聚虐”问题。解决“聚扈”就要变革婚制,推行“一夫制”,其中之理有如《礼记·经解》所言:“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另据王国维的研究,“男女有别”源于周代“同姓不婚”之制的“辨姓”需要,所谓“辨姓”,说到底,就是要明确子女的父姓,而做到这一点亦需要“一夫制”。
因此,周代的“男女有别”可以看做是变革婚制的一个手段。窃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做是男子在争取父权的过程中以一种社会化的“男女有别”来反对生理上的“男女有别”;相对于现代女权运动,它是上古时代一种另类“男权运动”。生理上的“男女有别”,即女子特有而男子不具备的孕育能力,使得“母权”是先天的,而“父权”只能是后天的。我认为,这种生理上的“不公”隐含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在“知母不知父”的年代,这种“不公”是不是男女的一种不平等?如果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男女有别”看做是上古男子争取男女平等的一种宣言?进而,如果可以,这种男女平等的诉求和现今女性主义的男女平等诉求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关涉平等的政治学和女性主义理论,可能从未被提及,但值得深思。
另类“男权运动”表明了“男女有别”之于父权的意义。而在“朕即国家”的王朝体制中,“父子有亲”,才“君臣有正”,所以,“男女有别”之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义也非同凡响。《国语·鲁语上》说,“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又说,“节,政之所成也”。“男女有别”被看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大节,是用以“安国家,定社稷”的。
从根本上看,儒家的政治生活、君臣之道要靠制度来保障和支撑,“男女有别”之所以能安国家、定社稷,关键在于它与国家政治制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兹以周制为例。
王国维在研究周制时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些纲纪天下之制皆与“男女有别”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立子制是父权制的根本,其内蕴的血统关系要求“男女有别”。庙数制是周人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与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的嫡庶制交互为文。而嫡庶制衍生于立子制。至于“同姓不婚”,前文已有提及,这里还需要再加说明。“同姓不婚”是族外婚的次生形式。它的流行可能与早先社会的乱伦禁忌有关,也可能与古人说的“惧不殖”、“畏乱灾”、“重人伦,防淫佚”等有关。而在王国维看来,它是为了周的“大一统”。他说:“有同姓不婚之制度,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制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家,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王氏观点符合《礼记·郊特性》的“附远厚别”说,很有说服力,也能说明传统中国为什么会有那种“家族伦理即政治伦理”、“家族称谓即政治称谓”的奇异景观。范文澜持与王国维类似的观点,认为“周人同姓不婚制,主要还在联异姓为甥舅,政治意义大于生育意义”。从王氏和范氏的观点来看,“同姓不婚”带有大一统的政治意图,与此相联系,“男女有别”也就可以看做是内置在大一统的王道观念中的一条性别规训。
儒家政治理念来源于周,周代的政治制度和王道观念是儒家政教体系之原型,基于是,“男女有别”自然也是儒家政教体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男女有别”是后世儒家男女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高彦颐把它当做建构儒家性别体系的一根支柱,这一点没有问题。这里想说的是:当高彦颐提出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时,如果考虑到“男女有别”与儒家政教体系之间的共生关系,她是不是更应该考虑儒家政教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而不是只局限在性别问题上呢?
二、“男尊女卑":从玄学定性到身份准则
与“男女有别”相联系,“男尊女卑”是儒家性别伦理的另一根本准则,也是儒家社会男本位的象征。作为儒家的性别观念,“男尊女卑”在春秋时期就已颇为流行。《列子·天瑞》载:“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邸之野,鹿裘带索,鼓瑟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在这一对话中,“知足常乐”的荣启期把“男尊女卑”作为自己的乐之“因”,“因”表明“男尊女卑”已是其时的通识。
从观念上看,“男尊女卑”源自儒家学说的天人观对男女本性的界定。《周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用乾坤来界定男女的本性,这样,男女就有了高下之分,尊卑亦随之而定。《周易》对男女的二元定性奠定了儒家性别伦理的基调。汉儒董仲舒循此基调,用“天道”界定“人道”,用阴阳定性男女,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故“男尊女卑”。宋明理学也因循旧学,主张“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理”,其突出之处在于把性别伦理“天理”化,强调“天理”不可违。从天地乾坤到天道天理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来看,不管是用宇宙秩序界定人间秩序,还是用人间秩序来说明宇宙秩序,儒家学说对男女的本性和尊卑之序的界定始终如一。如果说“男女有别”通过区隔社会生活制造了男女的社会差异,“男尊女卑”则通过玄学定性进一步制造了男女的本性差异,并给这一差异赋予了永恒的阶序涵义。
在儒家玄学话语中,“尊卑”是一二元关系,有如“上下”、“左右”、“内外”,构造整体,包含秩序,无尊即无卑,无卑亦无尊。“尊卑”的这种特性实际上把可分的男女统合成了一个观念上不可分的整体,有如天地、乾坤、阴阳,在这个整体中,对立的双方虽有尊卑之分,但又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儒家性别体系中,如果说“男女有别”强调的是一种“分”,“男尊女卑”则隐含了一种“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合”在儒家学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万物生化靠的就是“合”,即《荀子·论礼》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但“合”不是随意的,同类才能相“合”,是阴合于阳,下合于上,卑合于尊。“尊卑”将男女“合”为一体,尊者为上,上者为主,男主女从。
儒家玄学在观念层面预设了一个男上女下的两分世界,这个观念的世界显然不是儒家社会生活世界的真实反映,因为生活世界并不存在所有男子比所有女子都尊贵的现实。应该指出,观念世界中的“尊卑”和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尊卑”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前者指涉人的本性,后者指涉人的身份和地位;身份和地位属于现实社会,不属于观念。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把这两者理清,在制造错谬的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不必要的误解,譬如,笼统地谈论女子的地位问题、受压迫问题,给人的直观印象就如高彦颐所指出的那样:儒家女子普遍受男子压迫。如果不分情况,不辨就里,这样的看法就存在问题。高彦颐指出了这样的问题,但她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用“受压迫”和“受害”去形容儒家女子的处境是不恰当的。关于“压迫”问题,我认为本质上是一个“等级”问题,但“等级”分为多种,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有社会层面的。也有家庭层面的,不同层面的划分标准并不一样,因此,相应地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压迫”概念。如果我们把“压迫”理解为一种单一的形式,譬如阶级压迫,那么用这种形式的“压迫”去谈论家庭层面的“压迫”、男女之间的“压迫”就明显不适当。由于“男尊女卑”经常与男女之间的“压迫”问题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应该要区分它的层次。我认为要区分两个层面:观念层面和社会层面。社会层面的“男尊女卑”不同于观念层面的“男尊女卑”,它指涉男女的身份和地位,而身份和地位不存在两分。
联系到社会生活。“男尊女卑”中的“合”就有了特定的所指,针对的其实是夫妻之合,说的是女子合于一个特定的男子。我认为,儒家制造“男尊女卑”之说的真实意图就在这里,即确立家庭中夫妻的主从关系。当然,由于家国同构,夫妇之道是“君臣父子之本”,它也是为了君臣之道。
夫妻是家庭之本,夫妻的尊卑阶序一旦确定,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阶序关系按长幼、亲疏、嫡庶等也随之而定,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男尊女卑”是儒家社会的家庭身份准则,它与尊尊、亲亲、长长一道构造了家庭的阶序。儒家社会的家庭形式有多种,但一般而言,家庭成员之间的阶序关系不会偏离尊卑、长幼之序,不外乎夫尊妻卑、父尊母卑、父尊子卑等等。儒家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都是相对的,如父与子、母与子、夫与妻、妻与妾、婆与媳、兄与弟、弟与妹等等,这种相对性使得每个家庭成员都具有多种称谓,譬如,就一个女子而言,相对于夫,她是妻,相对于婆,她是媳,相对于子,她是母。这种相对性也把家庭成员连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其中,每个成员都是网络中的节点。“男尊女卑”、长幼嫡庶等原则赋予这张网络以秩序和等级,称谓于是就成为名分,名分就是身份和地位。在这张网络中,父居上,是一家之主,家无二主。当然,家庭成员的阶序网络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婚嫁、生养等因素。节点会经常变化,个人的名分也会因此而具有流动性。以女子为例,如《礼记-大传》所言未嫁是女,既嫁是妻;嫁后,“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生子之后是母。这里需要对母子关系做一说明。儒家重母,讲究子孝,母在家庭中有较高的地位,一方面,母与父构成一个阶序,相对于子,母与父都是尊者,母的地位高于子;另一方面,在多妻家庭,母子的贵贱相辅相成:由于嫡庶制的“立子以贵不以长”。母的嫡庶决定子的贵贱,即“子以母贵”,而由于母子关系,同样也会“母以子贵”。从“贱女”到“贵母”。儒家女子一般就在这个弹性时空中经营人生。
应该说,儒家社会中家庭的“尊卑”并非是一个空洞的观念,而是有权利内涵的,有法律制度的支撑,譬如,婚律有“七出”,刑律有夫妻同罪不同罚,继承有诸子析产,丧服有斩衰与齐衰,等等,这些都说明“男尊女卑”具有实质内容,同时也表明它是父权社会的一种官方意志。
“男尊女卑”界定了儒家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在社会中的地位又当如何?如高彦颐所言,儒家的“三从”之说对此做了完整规定,《礼记·效特性》说,“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儒家女子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她的社会身份随同男性家长,即所谓“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关于“三从”之“从”有多种解释,通常的一种解释是“服从”,高彦颐指责这是20世纪学者的一种“曲解”。但她对“三从”的解释同样令人费解,一方面,她认为“三从”使女子的社会身份从属于男性家长,另一方面,她又说“三从”剥夺了女子“正式的社会身份”。女子“正式的社会身份”是“三从”剥夺的吗?我认为不是,《白虎通》讲得很明白:“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女子“正式的社会身份”是“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剥夺的,不是“三从”。恰恰相反,因为女子没有“正式的社会身份”,才需要“三从”,是“三从”赋予了女子“非正式”的社会身份。家庭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儒家女子家外的社会地位依“三从”随附一家之主。与一家之主所处的社会阶层相关。所以,不存在所有女子比所有男子地位低的问题,譬如,皇后和公主的地位就远远高于一般士人,士人之妻(如“郡君”、“县君”、“乡君”)的地位也要高于佃农。
“男尊女卑”与“三从”是儒家女子的身份准则,前者用于家内,后者用于家外,两者相互关联。但就两者在儒家性别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我认为,“男尊女卑”更为根本,“三从”只能算一个“补充”规定,是对“男尊女卑”中隐含的“合”的一种展开说明,譬如夫妻,在家内,两者有尊卑之分,而在家外,由于“合”的原因,两者是共尊卑。“三从”是“男尊女卑”的题中之义,我不认同高彦颐把两者断然分开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因为激烈反对“五四”史观的缘故(“男尊女卑”是“五四”史观谈论传统社会最常用的话语),她在谈论儒家性别体系时把“三从”当支柱,没用“男尊女卑”。
“男尊女卑”训诫女子,塑造家庭。而在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格局中,“男女之别尊卑”与“王庶之判贵贱”具有内在一致性。从君王、士大夫到乡绅、庶民,以男性家长为主体构成的社会阶层也是一个差等序列,正如《左传·昭公七年》所说“天有十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个由阶层构成的序列与家庭成员组成的序列异曲同工。尽管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同一个阶层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要远比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复杂。费孝通曾说,“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就是上下、远近、亲疏、贵贱、尊卑,赋予人名分和德性规定。将人固定于社会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充当特定角色,同时也将社会网络差序化。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家庭的阶序格局相互映照,“男尊女卑”也就在这种映照之中达成了一个从家庭身份准则到社会普适伦理的转化。
三、“以顺为正”:从男性主张到女性认同
“男尊女卑”界定了夫妻的主从,表明妻要“合”于夫,而对于如何“合”,儒家另有一套相应的准则。按儒家的理想,“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夫是“大丈夫”,如孟子所言,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而妻是事人者,要事于一家之主,所谓“夫天也,妻地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事”的原则是“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顺”,即为“如何合”的原则。如果说“男尊女卑”是一种本性规定,那么,这一本性规定转化为生活领域的行事准则就是“以顺为正”。
儒家士大夫主张为妻的正道是“顺”,但“顺”需要“教”,所谓“民有质朴,不教不成”,“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笔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礼记》用“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框定了儒家女教的内容,也点明了女教的目的。在儒家士大夫眼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四德”即为此而立。
男性士大夫提出“以顺为正”,并不仅仅是为了正家室,也是为了王道政治。在儒家理念中,“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要求卑妻顺于尊夫,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也是要求位卑者顺于位尊者,因为尊卑往往与德性相联系,“顺”可以弥补德性的欠缺。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孔子以此表达了王道理念,而该理念的核心无疑是“尊”“德”“顺”的关系:先王是“至德”标杆,王者至尊,至尊者要至德,以“顺”天下。韩非子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把“妻事夫”与“臣事君”、“子事父”并陈。实际上是道出了“以顺为正”之于王道的意义。女教典籍《列女传》的作者刘向也认为,“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他作《列女传》,一方面是为女子“佐夫”、“匡夫”树学习典范,用历史先例“言传身教”的具象化方式来倡导“以顺为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倡兴王教,通过列陈历史上的贤妃贞妇及孽璧乱亡者来说明“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之理,“以戒天子”,进而维护和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
“以顺为正”既然是王道政治的内在要求,自然也就成为女教责无旁贷要担纲的教化使命。“古人立教男女并重”,但是,男女职责不同,女教也就异于“男教”。“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女子并不需要像男子那样习“小艺”、学“大艺”、通“四书五经”,她的习得围绕“事夫”,女教的主要使命就是教女子如何“事夫”,灌输“顺”的理念。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是女教第一个“专业课本”,其后的女教书有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氏姐妹的《女论语》、明代仁孝皇后的《内训》和明末山东琅琊王相之母的《女范捷录》,后四者均出自女性之手,史称“女四书”。“女四书”用之闺阁,虽然内容自然大异于“四书”。但“四书”之名无疑表明了其在女教中的地位。
“女四书”均以“四德”为本,内容大同小异,主旨都是宣扬“以顺为正”之道,教妻子如何当好“贤内助”以及母亲。譬如,《女诫》强调女有“四行”(即“四德”),“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乏无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主张女子要将“顺”内化为自身的行事理念。又如《内训》,教导女子要“修身立德,以佐内治”,“夫上下之分,尊卑之等也,夫妇之道,阴阳之义也。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妻,能推是道,以事其君子,则家道鲜有不盛矣。”再如《女论语》,传承《女诫》,告诫妻子:一要勤俭,所谓“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俭则家富,奢则家贫”;二要侍奉孝顺夫家父母、舅姑,“如有使令,听其嘱咐”;三要以丈夫为中心,“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四要做好家内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对女儿的教育,要让女儿“学礼”,“女不知礼……有沾父母,如此之人,养猪养鼠”;五要善于处理与四邻的关系,做好贤内助,“大抵人家,皆有宾主。滚涤壶瓶,抹光橐子。准备人来,点汤递水。退立堂后,听夫言语”,“酒饭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客称晓事”。可以看出,“女四书”涉及了为妻为母从大到小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套以“顺”为宗旨的儒家女子的行事手册。相较于《列女传》,“女四书”是女性自身的一种讲述,女性作者对“顺妇”的认同是文本之外的“言传身教”的模板,这使得“女四书”具有一种双重的教化意义。
女性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态度是中国妇女史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一般的历史想象中,女子对于不平等性别秩序的接受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她们不会参与此种性别秩序的建设,更谈不上主动去维护和支持。但是,“女四书”的作者们却恰恰相反。高彦颐通过对17世纪知识女性的解读更进一步指出,儒家性别体系得到了“享受着教育程度最高的妇女们的支持”。对于这类想象中的例外,20世纪的女权论者大多会认为这是儒家文化教化的结果,她们受的“毒害”过深。高彦颐则认为,“教化”是一项效果难以明确界定的事业。女性是能动的主体,她们之所以支持儒家性别秩序是因为她们能从中得到“回报”:“毒害”说包含了一种后世标准,并且也没有把女子当做能动的主体来对待。在她看来,妇女史研究不应该沉迷于“五四”史观想象的政治“蓝图”,而应该换一种思路,去发现女子能从儒家性别体系中得到什么“好处”,“好处”才是理解儒家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顺畅运转的关键。
应该说,高彦颐的“好处”说不无道理。“好处”可以平衡性别秩序带来的不利,在女子不能自主选择性别体系的情境下,它可以解释女子参与建设的主动性。但是,“好处”可能并没有高彦颐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可由女子自主掌控。在儒家社会,社会身份的依附性决定女子不是自由的个体,她的“好处”要以家庭这个利益共同体为中介才能获得,取决于由男性家长(或丈夫,或儿子)的政治权力、财富、职业等界定的社会地位或社会阶层。知识女性都处在社会上层,譬如“女四书”的作者都身处仕宦家庭,她们不仅比下层社会的女子有更好的生活和既得利益,也比下层社会的男子有更好的生活和地位,我认为,这才是知识女性真正的“好处”和支持儒家性别体系的动力之源,离开这一点,其他所谓“好处”,如作为家庭卫道士的“自豪”和“满足”。都将是无本之木。儒家女子并不是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其中,有能得到“好处”的女子,还有不能得到“好处”的女子,而且后者终归是多数。高彦颐试图用“好处”说取代“压迫”说,并以此来解释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此看来,她的这种做法同她批判的对象一样,也难免以偏概全。
应该指出,儒家女子对“以顺为正”或者说性别秩序的认同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解释。上层女性对性别秩序的认同也许是出于“好处”,她们有主动性;而下层女性的认同则完全可能是被动的,男性话语霸权的主宰、王道政治和等级文化的教化、家庭利益共同体的现实要求、上层女性的主张和示范等等,都可能对她们产生影响,使她们成为“顺妇”。“顺”,才是理解儒家性别体系得以长期顺畅运转的关键。
四、余论
通过疏解“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以顺为正”,上文揭示了儒家的性别观念与王道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主要想要说明的是:儒家性别体系是儒家政教体系的一个子系统。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在考虑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时,就不应仅仅局限于性别视野,把这一问题归结为“男是否压迫女”的问题。高彦颐提出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并以此来挑战“五四”史观,其潜在的逻辑是:如果女子在儒家性别体系中是受压迫的,那么该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就会成问题;既然该体系能长期顺畅运转,那么女子在其中就没有受压迫。这种想法无疑是过于简单了。儒家性别体系与儒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纠结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联提醒我们,儒家性别体系并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单独谈论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不考虑其他更宏大的背景因素,并不是一种恰当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我认为,谈论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需要超越性别视域,要放在儒家政教体系的框架中,所谓儒家性别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实质上就是儒家政教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问题。儒家性别体系与政教体系共生共荣,只有从这个视角审视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譬如,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儒家礼教时为何要把妇女解放当做一个重要议题。
高彦颐反复申辩“五四”史观用“受压迫”和“受害”去形容儒家女子的处境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她看来,儒家女子是儒家社会的一份子,也是儒家传统的产物,而“受压迫”和“受害”这种被动式只能用于身处儒家传统之外的异类。高彦颐的申辩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说通(譬如对仕宦家庭中的女子),但她的理由却显得牵强而奇怪,因为按照她的理由,我们可以这样来类推:譬如,奴隶是奴隶制社会的一份子和产物,说他们是“受压迫”和“受害”的就不恰当。这显然不能成立。在“五四”历史中。“压迫”也许是一个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语词,但这并不能表明其所指的不是事实。“压迫”表示等级间的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像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压迫”有多种,有什么样的等级就有什么样的“压迫”,“压迫”去意识形态化后指的实际上就是等级。儒家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儒家性别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如果说有等级就有压迫,那么“五四”史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能够说通的,譬如,我们可以说儒家女子在意识形态上受男性士大夫话语霸权的压迫,在家庭中受夫权的压迫,等等。高彦颐试图用儒家社会的“两面性”来论证儒家女子不受压迫,她说,“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实践”之间、伦理准则和生活实际之间存在差别,并说这是理解儒家传统社会“两面性”的关键,这种说法有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两面性”并不为儒家传统社会所专有,哪个社会没有这种“两面性”呢?因此,儒家社会的“两面性”并不能成为女子在其中不受压迫的理由。
儒家性别体系是一个男女不平等的体系,高彦颐深知这一点,也知道儒家女子对此无法自主选择,但她认为儒家性别体系具有弹性,女子有自己的生存策略,使自己免受压迫。她说:“尽管女子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在我看来,高彦颐说的这些恰恰说明了女子在儒家性别体系中是受压迫的,因为如果没有压迫。儒家女子也就不存在开辟生存空间的问题,并以此来获得“意义、安慰和尊严”。如此看来,高彦颐对儒家性别体系的阐释与其说是反“五四”史观,还不如说是对“五四”史观作的一个另类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