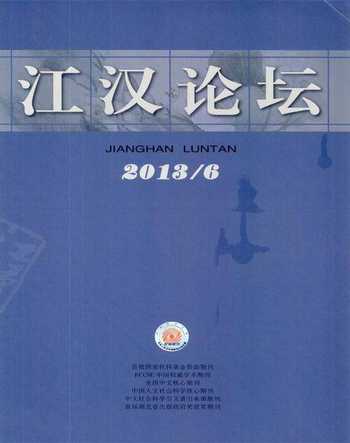卢梭与庄子
杨亦雨
摘要:尽管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卢梭与庄子在思想倾向和价值观上却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当然,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同时又赋予二者以不同的思想特点,从而使之在相通之中又呈现出内在的相异。进一步分析卢梭与庄子思想的同异,可以看到前者在理论上的某种张力。作为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试图化解这种张力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抽象的思想趋向。
关键词:卢梭;庄子;自然状态;社会状态
中图分类号:B56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44-04
卢梭与庄子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中,但二者在价值观上却存在某些相通之处。不过,进一步的考察又表明,相通之中又蕴含着相异。在卢梭与庄子思想的同异背后,可以看到更深层面的理论张力。卢梭在试图化解这种张力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抽象的思想趋向。
预设人的自然状态,是卢梭整个政治、伦理思想的前提。按照卢梭的理解,在形成文明社会以前,人首先处于自然的状态之中,卢梭从不同的方面对这种自然状态作了描述,并对其作了种种肯定。
在卢梭看来,作为自然状态中的存在,人在生活方式方面与动物并没有根本的区分,这种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然的环境。使人“体格健壮”。由于身体健壮,因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疾病很少,不用吃药,更用不着看医生②。这种看法从人的肉体存在的层面,肯定了自然状态的完美性。
按卢梭的看法,在自然状态之下,不仅人的身体,而且人的精神,都处于更合乎人性的状态。文明生活中人们遭受的各种痛苦,都是在脱离了自然状态之后人自己所造成的,只要我们保持大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生活,这些痛苦都可以避免③。自然状态中不存在教育,人没有受到文明社会中各种观念的影响,心灵简单而淳朴,从而也没有文明社会中精神的冲突和痛苦。相反,人一旦变成社会的人,便既在肉体的层面失去体力,也在精神层面失去勇气,无法应对各种纷扰的社会现象。
精神的淳朴,更具体地体现于欲望。自然状态下的人没有文明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强烈欲望。从而,“他们之间发生争夺的情况既稀少,又没有那么残酷”。在这里,精神的简单淳朴不仅在个体的层面使人避免了内在的痛苦,而且在社会领域构成了社会秩序形成的前提:抑制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从另一个方面看,也就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有序化。对卢梭而言,在自然状态下,社会同时具有自然之序,它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为特点,社会秩序同时呈现平等的形态。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比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小得多”。这里的差别既指身体的层面,也涉及社会的地位,等等。对卢梭而言,自然状态之下的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异,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表现出原始的平等关系。“什么一叫‘奴役。什么叫‘统治,这两个概念野蛮人就从来没有过”。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等不平等的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为前提的,而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没有出现:“奴役的链条是由于人们的互相依赖和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互相需要形成的。不先使一个人处于不能不依赖另一个人的状态,就不可能奴役他:这种情况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的身上都没有枷锁,最强者的法律是没有用的。”秩序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卢梭的以上看法则进一步将自然状态中的秩序与平等联系起来。
从肯定自然状态的立场出发,卢梭对工具的运用提出了批评:“我们的工艺使我们失去了为满足生活的需要而非具有不可的体力和灵巧的本能。如果野蛮人当初有一把斧子,他的手腕能折断那么粗的树枝吗?如果他当初有一架投石器,他能用手那么有力地投掷石头吗?”质言之,工具的使用,不仅无助于人的发展,而且导致人的退化。同样,技术的进步也主要呈现负面的意义:“冶金和农耕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带来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黄金和白银,但在哲人看来是铁和小麦。”冶金和农耕分别与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相联系,而按照卢梭的看法,这一类技术所导致的是人类的堕落。这一观点同时体现了一般意义上卢梭对技术的理解:技术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具有消极的性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卢梭认为:“第一个给自己制作衣服或建造住所的人,实在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些没有多大必要的东西。”制作衣服和建造住所涉及的,是服装和建筑方面的技术,而在卢梭看来,它们对人的发展。并没有实际的积极意义。
与赞美自然状态相联系,卢梭对个体的价值给予了多方面的肯定。如前所述,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彼此之间没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作为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价值。基于以上看法。卢梭将维护个体自身的生存视为人性的首要法则:“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对个体自身的这种关切,无疑将个体的原则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卢梭的以上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将人的自然状态加以理想化。事实上,卢梭一再地强调自然的实在性、真实性,所谓“凡是来自自然的东西。都是真的”,便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点。卢梭对自然的这种推崇,与中国先秦哲学家庄子的看法具有相通之处。从哲学上看,庄子以天人关系为其关注的重点之一。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论题,天人之辨同时涉及天道观与人道观。在人道观的论域中,“天”主要与广义上的自然相关,“人”则与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历史活动及其结果、礼义等社会规范等相联系。在庄子那里,表现为自然的“天”,首先区别于社会的文明形态。在天(自然)这种存在形态中,人并不以自身的力量作用于外部世界,万物则相应于地表现为原初状态:“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是指自然状态之下人的存在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非有意而为之;“山无蹊隧,泽无舟梁”等等,则是当时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其特点在于没有经过人的作用和改造。在庄子所描述的这种天人之境中,人以及外部的世界都具有自然、原初的形态。
按庄子的理解,就人而言,其自然形态与人的自然之性相联系,这种自然之性,庄子称之为“常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作为人一开始就具有的天性或自然之性,它具体体现为超越各种欲求、安于自然状态。在庄子看来,随着各种世间欲望的产生,人就会渐渐远离这种本来的状态。对此他作了具体的分析:“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这里所说的“道德”不同于现代语境中伦理道德意义上的道德,而是分别指“道”与“德”,其根本涵义则是事物原初所具有的内在属性。所谓“残朴以为器”,也就是破坏事物的原初形态。制作文明所需要的器物:“毁道德以为仁义”,则是破坏人的天性。以形成仁义等文明规范。尽管二者有不同的侧重。但又呈现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违背人的自然之性。
庄子进一步认为。礼乐等社会文明的发展演进,不仅不能使人保持纯朴之性,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考察历史演进过程,庄子对此作了具体的描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天,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庄子·缮性》)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在这里区分了“性”与“心”:“性”表述人的原初存在形态.“心”则体现了礼乐文明的发展。在庄子看来,历史的演进以礼乐等文明规范的形成、发展为线索。与之相联系的却是人越来越远离自身的原初形态。这里既包含着对理想存在形态的追求,也彰显了礼乐文明的发展与走向理想形态之间的悖离。
可以注意到,与卢梭相近,庄子对天人关系的以上理解,也是以自然状态(天)的理想化为其理论前提:在肯定自然状态的完美性这一点上,庄子与卢梭确实具有相通之处。就现实的形态而言,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不断超越自然,实现文明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它也往往包含某些负面的趋向。如何使文明的演进更合乎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是反思文明发展过程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卢梭与庄子笼统地将历史的演进理解为远离人性的过程。无疑失之抽象和片面。但他们对礼乐文明演进中各种消极现象的批评,则多少表现了对以上问题的某种自觉意识。
将自然状态理想化。是否意味着以回归自然为历史发展的唯一进路?在这一问题上,卢梭与庄子表现出不同的视域。庄子在推崇与赞美自然状态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回归自然的趋向。按庄子之见,礼乐等文明形态,虽以“人”超越了“天”,但往往同时表现为以“人”灭“天”,他的主张则是“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庄子特别强调外在之“礼”与内在之“真”的区别:“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礼”只是社会世俗所认同的形式,“真”则是合乎自然的内在之性。所谓“法天贵真”,也就是回归自然、实现人的真实之性。这一过程在人自身的发展中,具体表现为“反(返)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在庄子那里“复其初”与回归真实之性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庄子不同,卢梭在将自然理想化的同时,并没有由此引出回到自然的结论。在卢梭看来,人本身有其历史性,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自然状态也往往难以继续:“人类曾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不能继续维持。”作为人类存在的早期形态,自然状态尽管合乎理想、十分完美,但却无法永远维持,换言之,人的自然状态并非人的永恒状态。在这里,理想性与历史性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而对自然状态历史性的肯定,则使卢梭难以像庄子那样,形成“法天贵真”的结论。
自然状态的历史性。决定了它将超越自身。转化为社会形态。按卢梭的理解,社会形态固然不同于自然状态,但对人而言,它并非仅仅具有否定的意义。首先,在社会的形态中,人不再受本能的限制而开始获得道德的品格:“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本能是人的自然属性,在自然状态中,人的行动往往首先出于本能,而进入社会形态后,人则开始形成了正义的意识,其行动也相应地获得了道德的性质。从本能到正义,这种变化对人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看,在社会状态中,虽然人失去了“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面重新获得了如此之巨大的收获;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灵魂整个的得到了提高,
“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能力表现为人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力量,思想与情感则从不同方面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从其实质的内容看,能力、思想、情感已不限于道德的领域,它们从更广的层面表征着人的存在形态,作为人的能力发展、精神提升的前提,社会状态同样呈现了积极的意义。
在自然状态中,人首先呈现个体的形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则开始形成各种共同体,卢梭将这种共同体称之为“公共的大我”、“公共的人格”,它具体表现为“城邦”、“共和国”或“政治体”,等等。这种共同体所体现的是所谓“公意”,而“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⑩。对“公意”的这种肯定,同时体现了对共同体的注重。而无论是观念层面的“公意”,抑或实体形态的共同体,在这里都呈现正面的价值。
与注重社会状态相近,卢梭对公意及共同体的如上看法,也表现了不同于庄子的立场。从注重自然的价值原则出发,庄子将个体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庄子看来,与自然相对的是礼义文明,这种文明的形态往往体现了整体性的力量,与之相对,本然的天性则更多地体现于个体的存在。当以礼义等普遍规范来塑造人时,作为个体的人,常常便失去了个体性的规定。成为社会整体的附属物。庄子反对将“己”(个体、自我)仅仅归结为礼义文明的化身,而一再强调个体之“独”:“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庄子·在宥》)“独”与整体相对,突显的是独特性、个体性,正是这种独立性,使个体在社会中能够特立独行、无所依傍。这种独往独来于六合、九州之中的“独有之人”,被视为具有至上价值的个体:所谓“至贵”,便体现了这一点。作为身体力行其人生理想的哲学家,庄子本人所追求的,同样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个体的特立独行,使之往往与众人形成了某种距离,个体本身则或多或少超然于社会共同体之外。相对与庄子之强调个体超然于社会共同体,卢梭对公意与共同体的肯定,显然表现了不同的视域。
不难注意到,尽管在把自然状态理想化这一点上,卢梭与庄子有相近之处,但二者在如何看待社会形态、如何定位社会共同体等问题上。却存在重要的差异。当然,这里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卢梭与庄子思想的异同,从深层的视域看,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是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卢梭与庄子的差异背后,是卢梭思想中内含的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他将自然状态视为完美的形态,另一方面,又赋予社会状态以积极的意义;一方面,他将个体的权利、自由提到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二者呈现某种内在的紧张。如何克服这种张力?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解决以上问题的一种尝试。
自然状态的理想性.首先体现于凡人都享有自身的权利。而在卢梭看来,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即构成了人的权利的一种担保:“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社会的契约(约定)固然是一种“非自然”的社会程序,但却为自然状态下人已获得的权利提供了担保,在这里,自然状态下人所享有的权利与社会状态下的秩序呈现为相互统一的关系.而这种统一,便是通过社会契约(约定)而达到的。
卢梭以家庭为例对此作了阐释。在他看来,“一切社会中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但在社会状态中,家庭并非仅仅基于自然。家庭的存在,也需要约定:“家庭本身就只靠约定来维系。”家庭本身具有二重性:它既是“社会”的最原初的形态,又源于“自然”(建立于自然的血缘关系之上)。在自然状态之下,家庭已经存在。家庭中的成员也享有自身的权利。而在社会状态下,通过伦理、法律的规范,这种权利进一步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而伦理、法律的规范无疑具有约定性。在这里,通过约定,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存在形态与社会状态下的存在形态.再一次得到了沟通。
同样,就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而言,通过社会契约。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形成了相互规约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方面,个体让渡自身的一部分权利给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社会共同体又接纳个体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并同时为个体的权利提供担保,由此,个体不再独立于共同体之外,而社会也非超然于个体,二者形成相互协调的关系。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无疑表现了沟通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并化解二者张力的内在意向。然而,从理论上看,社会契约论本身具有抽象的性质。首先,它以“自然状态”的预设为前提,这种预设本身缺乏历史的根据。再者,所谓订立契约,也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想象,人类全体或一定社会共同体如何订立契约,一定历史时期所订立的契约如何对以后的历史时代形成实际约束等等,都是这种想象未能解决的问题。试图在这种抽象的观念之上化解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在理论上显然难以成功。